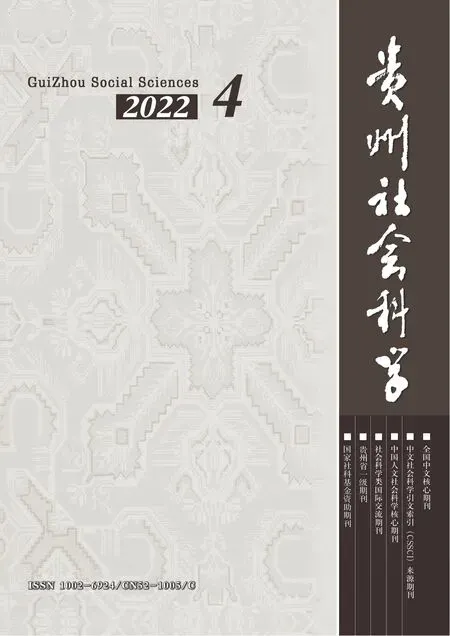疾病展演:一种医学化下的医患互动
2022-07-05李海燕
李海燕 程 瑜
(中山大学 ,广东 广州 510275)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急剧增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18766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35280人,占13.50%。[1]《中国健康管理与健康产业发展报告No.2(2019)》指出,我国80%以上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2018年全国住院总人数中,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达29.2%[2]。其中部分老年患者长期住院,由医疗机构提供养老照护。对于这些老人来说,医院既是医学空间,又是养老的日常生活场所。在这种医学化的日常生活空间中,医生、患者如何看待和表达疾病,成为本文的研究起点。
从生物医学的角度而言,疾病是在一定病因作用下,机体自稳调节紊乱而导致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并引发一系列代谢、功能、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症状、体征和行为的异常。简言之,疾病是一种异常状态或行为。从人类学的角度讲,疾病是患病者不想要的自身状况[3]。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将“疾痛”从“疾病”概念中剥离,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学科对于疾病的认识。他认为“疾痛指的是种种鲜活的经验,是病人对疾病引起的身体异常和不适反应的切身感受”,疾病则是“医生根据病理理论解释和重组疾痛时提出或发明的”。[4]也就是说,对于病人而言,疾病是一种疾痛感知,而医生则从病人的疾痛经验中得出患有某种疾病的判断。疾病在医患之间呈现不同面向,这在医患互动中有具体体现。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医患双方对疾病展演认识不一致:患者认为是表达自己身体不舒服的症状表达,而医护人员则认为有的疾病展演是患者故意“装病”。本文试从医患互动的角度,探究医患双方如何看待、参与疾病展演,进而探寻背后的文化动因。
二、田野点介绍与研究方法
某慢性病医院(以下简称“N医院”)(1)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匿名原则以及伦理要求,文中医院和人名作匿名处理。是一家以老年病、慢性病治疗为主,集治疗、康复、照护等为一体的市级公立专科医院,现有床位1200张,共十二个病区。2019年3月~2020年8月笔者在其中的S区、Q区进行深入调查。S区有医生6人、护士21人、护工22人;Q区有医生5人、护士12人、护工19人。S区现有108位老人(93床和108床(2)108床南某某于2020年7月27日离世,统计时未入住新病人,故空缺。统计时空缺),最高年龄98岁,最低年龄67岁(3)统计时间为2020年7月,年龄以此来计算,下同。,平均年龄82岁;Q区住院老人总数82人(23、35、75床统计时空缺),最高年龄97岁,最低年龄73岁,平均年龄85.7岁。两区老人每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疾病,以高血压、心脏病、阿尔茨海默病、慢性阻塞性肺病、糖尿病等为主。
在观察中,笔者发现医患双方对于疾病展演有不同的解读和处理方式。为了理解这种现象,笔者围绕医学空间里疾病如何展演、各主体之间如何互动、疾病展演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等问题,以具体事件为线索向住院老人、医生、护士、护工作深度访谈,搜集疾病展演的情境、角色、方式、原因等相关资料。共访谈医生7人、护士3人、护工6人、住院老人14人,获得11个疾病展演案例,笔者参与了其中6个展演疾病现场,另外5个案例为事后访谈所得。
三、医疗场域中的疾病展演
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论强调人的表演性,把人的日常生活看作是戏剧表演。每个人都是表演者,或作为个体表演,或作为剧班一员。人们注重自我印象管理,在前台、后台等区域扮演和诠释角色,试图通过表演引导和控制他人的行为,尤其是他人应对自己的方式[5]。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患者、医护人员等既是表演者又是观众,他们在疾病展演的互动过程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患者将病房当成前台,以患病经历或者药品说明书为剧本,扮演病人角色,展演疾病症状,引起医护人员关注。医护人员以相应的诊疗活动配合、参与疾病展演。
案例1:“叮铃铃”,护士站的铃又响了,这是每天晚上都会响起的声音。飞飞护士看到按铃的是房某某(女,88岁,以高血压3级极高危收治入院),赶紧去病房。房某某捂住头说自己头晕、头痛得厉害。飞飞护士立即量体温,用水银血压计测血压,然后告诉她一切正常。随后,房某某就会安静休息了。医院针对高血压患者每日例行用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并做好记录。张医生说:“房某某其实没有发病,她只是不想用电子血压计测血压,觉得测得不准,想用水银血压计测血压。她会按铃告诉医生护士她头晕、头痛,然后让护士拿水银血压计来测。如果她每天直接喊护士拿水银血压计来测血压,怕医生护士觉得增加工作量,烦她,所以就装病。生病时要求用水银血压计测血压就是正常需求了。”(4)资料来源:护士站与病房的参与观察。地点:S区护士站+5病房;时间:20190812。
案例2:34床程某某(女,88岁,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入院)那真是装病的高手,如果谁得罪了她,她就装病。她装病不是简单地说痛,而是会研究她所吃药的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描述的症状来表演。比如,有一次俞医生白天查房的时候,程某某说她心绞痛。俞医生看了下说继续观察,并没有给她进一步处理。晚上俞医生去查房的时候问她:“婆婆,你还好么?”程某某说:“还好!”又接着说:“今天你值班?”俞医生说:“是呀!我值班,”程某某立马捂住胸口说:“好痛,心绞痛”。俞医生就赶紧处理。程某某说:“我白天跟你说,你都不理的嘛!”后来俞医生对我说:“程某某肯定是装的嘛,刚开始问她都是好的,听到我值班就喊痛了。”(5)资料来源:深度访谈。访谈对象:韦医生;地点:Q区医生办公室;时间:20190813。
案例3:一日科室主任带队查房,高某某(女,92岁,离休,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慢性支气管炎入院)向科室主任反映护工七姐的床坏了,一直都没人来修。主任说:“七姐是您私人请的护工,不归医院管,床的事情她自己解决”。护工七姐使劲向主任眨眼睛,说:“嗯,没事儿,我自己去买床”。查完房,主管俞医生刚回到办公室就接到护士站电话,说高某某发病了。俞医生连忙跑到病房,刚好听见高某某说:“我原来在X医院当领导的时候,一直为人民服务,现在我护工床坏了,都没法解决。我的心好慌呀!心口疼呀!没用了,死了算了!”俞医生连忙查体,处理完后联系护士负责人,告知家属这一情况,高某某的女儿说她知道这个事情,床都买了,让医生去告诉她床的事情医院已经解决了。事后,俞医生跟我说:“高某某经常装病,她的心理需求高。有时候没有那么严重,也要做成那个样子。”(6)资料来源:病房里参与观察。地点:Q区四楼18病房;时间:20190919。
这三个案例说明,患者经由疾病展演展示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疾病,而且也是心理情感、人际关系、社会地位等带来的疾痛体验;医护人员通过疾病诊疗回应病人的“非疾病”诉求,参与了疾病展演。可见,医护人员和患者在一定的互动情境中,共同完成疾病展演。不过,医患双方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和行为表现。
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人类社会由思想事件和行为事件构成,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同等关注思想领域与行为领域[6],对思想、行为的解读存在主位和客位的差异。在疾病展演中,医护人员和病人构成多元主位。因此,我们应分别站在不同主位的立场上,理解疾病展演过程中医患双方的思想和行为。通过对上述疾病展演案例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医患双方有关疾病展演的认识和行为的矩阵图(见表1)。

表1 医患双方关于疾病展演的思想、行为
对于患者来说,他们思想上认为疾病展演是身体疾病的一种表达,而行为上可能特别突出某个疾病症状的展演。医护人员在思想上认为患者有时是“装病”,但在行为上仍旧予以诊疗,配合疾病展演。医患双方思想和行为上对疾病展演的不同认识体现在医患互动之中。
四、医学化:疾病展演的“框架”
戈夫曼认为展演总是在一定“框架”下进行的[5]203-204。“框架”指人们内化的现存社会规范和社会准则,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惯例和共识,正是它们构成了人们在社会生活舞台上进行表演的依据[7]。这个“框架”是一种正式的、抽象的、动态的框架,体现在人们大量的社会互动中[5]204。医院场域中,由专业医护人员提供正式照护,老人日常生活被医学化。医学化成为医患双方认识和形构疾病展演的“框架”。
衰老本是一个自然过程,却被视为疾病,将衰老与老年病混同起来,成为医疗干预的对象。衰老被“病理化”的同时,养老走进“医学化”的领域。上世纪70年代左拉(Zola)、康拉德(Conrad)等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探讨医学与社会的关系,提出医学化(medicalization)概念。医学化指将非医学问题定义为医学意义上的疾病并加以治疗的过程[8][9]。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医学化逐渐进入自然生命过程及日常生活问题领域。左拉认为医学化是一个“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在医学统治、影响和监督下的过程”[10]。日常生活医学化过程扩大了疾病范围,医学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刘仲翔认为:“生活医学化是指对生活中原来不是医学问题的某些方面,加以医学的定义,纳入到医学范围之内,对这些问题进行医学的解释,并且提出医学的解决方案,从而使得医学作为一门职业和知识体系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11]迈克里·菲茨帕特里克(Michael Fitzpatrick)认为政府和机构以健康的名义将医学渗透到了患者的日常生活之中[12]。伊里奇对日常生活医学化提出批判,认为医学化把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变成病理性的,有损人们自我管理疾病和健康事务的能力[13],进而影响人们日常生活能力。老人因衰老导致的生活能力下降也被当成疾病予以治疗,极端体现就是老人晚年需要在医院度过。
医疗机构养老使得老年日常生活被彻底医学化。老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被当成医学问题对待,并反过来影响日常生活。老年日常生活医学化不仅将生命中的自然变化和日常生活扭曲成病态加以治疗,而且使得老人的生活需求被病理化表达,通过单一的疾病诊疗来满足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在从五七干校、干部疗养院到慢性病医院的发展过程中,N医院的医学化程度逐渐加深。早在五七干校时期,这里作为知识分子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配备了医务人员。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同年干部疗养院在此基础上建立。在此建疗养院的原因,一是地理优势,比邻植物园,空气环境好,利于疗养;二是成立干部疗养院可以解决原来五七干校医务人员的工作问题。疗养院提供疗养服务,配有医务人员,建有钓鱼池、游泳池、娱乐室、康复中心等配套设施。当时来疗养的人不多,疗养院采取了伙食、住宿补贴等方式动员离休干部来疗养。
疗养院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时代的卫生体系与日渐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的矛盾日渐扩大。2000年前后,全国都在探索疗养院发展战略。随着机构养老需求的增加,面对改革后自身经营发展压力,这个疗养院整合自身的养老资源和医疗能力,逐步向医养结合的医疗机构转型,开始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其结果是业务范围从单纯的疗养医学拓宽至慢性病管理、预防保健、康复治疗等,收治对象也从离休干部人群扩展到慢性病群体。
N医院从干部疗养院转变为医院,生活场域也就相应地从疗养空间变成了医学空间,老人从“疗养”变成“住院”,从“疗养的主体”成为“被医治的对象”,老人成为“病人”。与此同时,医务人员的工作职责从提供疗养服务转变为慢性病管理。医院利用住院管理制度,建立以病房为中心的三级医生诊疗体系管理病人。其中查房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医疗活动。重复性的查房活动使得老人逐渐认可病人身份。同时,居住的空间布局也由便于生活到便于诊疗,以标准化病房设置来完成空间管理。
医院的日常生活主要围绕疾病与治疗展开。老人日常生活中的情感需求、社会关系、社会地位通过疾病展演得以展示或满足;医护人员以疾病诊疗方式参与疾病展演,以此回应部分老人的“非疾病”诉求。在医学化“框架”下,疾病展演成为医患双方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方式之一。
五、疾病展演中的医患互动
在医院,医患间通过疾病表达、诊疗实践着人与人、人与生活的关系。医学化下,患病的老人通过疾病展演表达自身的疾病感知、生活诉求、情感渴望等;看病的医生对患者身体的不适和生活遭遇作出病理性解读,并通过参与疾病展演的方式回应患者身体、生活问题。
(一)“有病”的感知与“装病”的判断
“疾病”取决于“主体”本身是如何表述和建构的[14]。“生病”和“看病”的主体通常对疾病有着不同的看法。于患者而言,疾病是患者身体上的一种不协调、不平衡、失去能力和不舒适的状态[15],这种状态不仅是患者的身体感知,更体现在社会文化意义上。患者所经历的社会苦难,也经由身体的某种不适症状体现。疾病在身体上的症状构成了患者“有病”的感知。
然而,对于医生而言,症状≠疾病。长期的医学训练使医生形成了系统辨识疾病的方式。患者主诉的疾病感知通常只是医生诊疗疾病的起点,医生在诊疗中会使用其他检查手段确诊疾病。以“头晕”症状的疾病诊断为例:头晕常表现为身体发飘、不稳、虚弱无力或头轻感等一组症状,在头晕的诊疗中可以依赖详细的病史收集与体格检查、有针对性的辅助检查予以确诊,继而进行预防和治疗[16]。医生结合病人的疾病史以及各项辅助监测手段将病人“头晕”感知诊断为某种具体的疾病,如高血压、脑血管病、颈椎病等。当缺乏相互印证的证据时,病人主诉的疾病感知常常会显得有些乏力,导致医生做出“装病”判断。
从案例1可以看到房某某几乎每天都会展演疾病,表演疾病的生理症状。她每天选择在晚饭后,洗漱好并躺在床上,然后就开始表演她的“头晕、头痛”。在她按铃后,护士回应她的行为,用她想要的水银血压计测血压,配合着她的表演,直到告诉她一切正常。这似乎是完成房某某一种睡前“仪式”,医生也不会因此改变对她的医嘱,不会针对她这个头晕做特殊治疗。
当身体疾病感知经由诊疗活动确定为某种疾病时,这种疾病在医学上的临床表现会影响病人的疾病感知。例如,病人身体上感受的头晕,一旦被医学确诊为是由高血压等疾病引起,病人以后就会常常感受到“高血压”头晕。高血压患者房某某常常被高血压头晕所困扰,以至于她心理上期待精确的数字证明她是否处于高血压状态。当“科学”的水银血压计显示血压正常时,房某某高血压的头晕症状消失了,一切回归正常。每晚“发病”头晕,又无其他症状表现时,房某某就被认为是在“装病”。
(二)作为筹码的“生病”与日常生活病理化解读
医疗机构的养老照护围绕疾病诊疗活动来开展。医疗活动之外的人际关系、社会地位、心理情感等常常得不到重视,而这些才是影响老人生活质量的关键。因此,在医院,老人试图用疾病展演来表达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非疾病”问题。
案例4:邓某某(男,77岁,以神经根型颈椎病、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入院)和松某某(男,87岁,以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入院)住同一个病房,两人一起住了三年多,平时相处比较融洽,但每年夏天都会因为开空调的问题闹得很不愉快。松某某想打开空调,邓某某不许。如果松某某执意打开空调,邓某某就会生病,一会儿说自己脑壳晕,一会儿说自己肚子痛。邓某某会让护工周叔帮他喊医生过来,医生过来发现没什么疾病问题,便让继续观察。韦医生说:“邓某某是肿瘤患者,怕冷。而松某某患有糖尿病,怕热。确实很难调和,以至于每年夏天都吵架!我们也只有给双方解释下他们疾病的特点,调换床位,怕冷的不要对着空调吹。”(7)资料来源: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地点:Q区四楼4病房;时间:20190627。访谈对象:韦医生;地点:Q区医生办公室;时间:20190722。
在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病房里,患者通过疾病展演实践着人与人的关系。案例4中邓某某喜温而松某某喜凉,双方都想把控房间温度。未能调和时,邓某某便通过疾病展演的方式将医护人员卷入到病人间的“内战”中。邓某某表现出疾病症状,并将其归因为松某某打开空调的行为导致。常理来说,两人发生争端时,若一方突发病痛,争端的结果一般会有利于生病者。原本两人势均力敌的“战争”,邓某某以为通过疾病展演能更胜一筹。然而在医院里,双方都是病人,医生在邓某某的疾病展演中也没有发现他所展演的疾病,只能让他继续观察。
韦医生对于两位患者之间的矛盾也是从疾病的角度来解读。她认为正是由于身患不同疾病导致两人的温度感知不一样,对空调的需求也就不一样。鉴于两人平时相处融洽,医院采取两人换床、不对着空调吹等措施缓解他们暂时的矛盾。医生从“病理”的角度理解患者日常生活中的冲突,试图从医学上寻求解决冲突的方式。慢性病老人疾病无法治愈,那么矛盾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三)夸大症状与“诊疗式”回应
在医院,由医生、护士、护工共同提供养老照护,医生、护士负责疾病诊疗,护工负责生活照护,家属自由安排探望时间。家属的陪伴比医护人员少很多,有的老人甚至因缺乏陪护而自称“孤人”。所谓“孤人”,就是无子女的人。住院老人会以“孤人”来表达自身的住院体验。
朱某某(女,77岁,以颈椎病入院)说:“为啥我们是‘孤人’呢?因为在这里,虽然有医生护士护工的陪伴,但是没有子女的陪伴,子女来了一会儿就走,那不是陪伴。”(8)资料来源: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朱某某;地点:Q区四楼;时间:20190722。
“孤人”一词将老人们的孤独、空虚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表明他们内心期待多一点关心、多一点陪护。为此,老人们常常刻意突出某个疾病症状表现。例如王某某(9)王某某,男,83岁,以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加重期入院。资料来源:参与观察。地点:S区医生办公室+7病房;时间:20190509、20190510。告诉医生,他生病了,拉肚子,拉了很多次,拉得都没有力气了。实际上他当天只拉了两次稀便,不算严重。王某某通过模糊表述突出疾病症状、夸大病情,以期引起重视。
老人利用病人权利,通过展演病人角色,突出某个疾病感知来表达内心需求。医院住院管理制度规定了医生查房次数和时间,保障了病人得到治疗的权利,这使得患者诸如心理情感等医疗之外的需求,被“转换”成疾病症状表达。老人通过展演疾病引起关注,进而获得情感慰藉。
案例5:昌医生开玩笑地说道:“我们这里有一个‘慈禧太后’,为什么叫她‘慈禧太后’呢?因为我们早晚必须去她那里‘请安’。我们早上晚上都得去她房间看看。如果去的时候,她不在房间,我们就得等她在的时候,再去看她一下。一定要让她看见我们,仅仅说我们去过了是不行的。因为,她如果没看到我们去她房间,半夜定会按铃呼叫医生,说身体不舒服。医生半夜去房间看她后,她才心安。如果我们白天没有看她,她就让我们睡不好觉。”(10)资料来源: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昌医生;地点:Q区医生办公室;时间:20190809。
所谓“慈禧太后”就是孝某某(女,81岁,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入院),她所说的身体不舒服,并非真正身体上的不适。孝某某利用查房制度获得医护人员的关心,一旦没有满足时,便行使病人权利,扮演病人角色,展演疾病。医护人员履行职责过程中,配合“演出”以达到老人心理预期。长此以往,医护人员和老人熟知彼此行动逻辑。老人利用查房制度展演疾病,获得关爱。医生通过疾病诊疗的方式,处理患者疾病展演中的身体症状和回应情感需求。
六、结语
衰老本是人生自然的生命状态,在现代医疗体系下“养老”日渐纳入医学范围,养老过程被医学化;医疗机构养老,老人生存环境变成医学空间,生活场域亦被医学化。医学空间里,疾病治疗占据主旋律。老人们试图通过疾病展演来展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当生活中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老人展示“病人角色”以得到医生的更多关注。在医生看病、治疗过程中“疾病”获得了社会意义。日常生活中,因缺乏陪护造成的老人心理、情感需求被医学化表达。医学化将老人的日常生活简化为单一的疾病诊疗活动,使得住院老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心理情感及人际关系表达等需借助疾病展演得到关注和满足。老人将疾病展演视为身体疾病症状的表达,通过突出某个疾病症状来表达诉求、展现日常需要。医学化下,即使意识到患者某些疾病展演不是真正的疾病表现而是“装病”后,医生们仍通过疾病治疗的方式来回应患者的生活诉求。
因此,疾病展演的意义不在于所展演出的疾病是否是医学意义上的疾病,是否符合病理学的“科学性”,而在于通过疾病展演与回应的过程,老人得到了医护人员更多的照护。也即是,即使是对“装”出来的疾病诊疗,也回应了老人的非疾病诉求。疾病展演成为医学化下医患互动的方式之一。然而,疾病展演不仅会导致大量医疗资源的浪费,也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和满足老年人对于日常照护多样性需求。有鉴于此,本文提出:正视养老问题医学化弊端,提供基于日常生活的长期养老照护,让养老活动走出医疗机构,走进社区和家庭,构筑社会化和人文化的照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