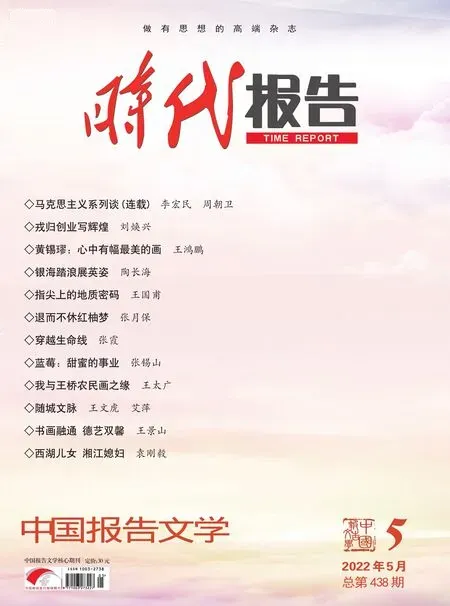随城文脉
2022-06-23王文虎艾萍
王文虎 艾萍


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随城也许是最不张扬的。不像其他城市那样,将历史与文化空间化为建筑。古诗中随城的建筑也有“西风肠断白云楼”(〔元〕刘秉恕《白云楼》),但是那些从古到今的建筑虽曾是立体的诗,今天却诗意全无。如今的随城以厚重的传说、精美的彝器以及简约的文献,将其历史与文化激荡为时间、文脉以及精神谱系。它用远古的原声唤醒人们对历史记忆的温情与敬意。沿着文脉,穿越幽长的历史隧道,我们这些精神游子能触摸到中华文明的最初,也能读到——
创造盛世的“精致之制”
穿越历史隧道,离我们最近的一道历史风景,是一个伟大的“风云之际”——隋唐盛世。盛世隋唐,令每个中华儿女备感荣光。当此盛世,柳宗元看到“裂都会而为之郡邑”是“势也”;韩愈看到了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的道统;刘禹锡更是表达了李唐之人的文化自信:天人相交胜,还相用;李白、杜甫各纵歌喉,唱出了这盛世的喜怒哀乐。
谈隋唐盛世之美,世人多美李唐,而斥隋炀之荒淫。然隋之于隋唐盛世,有开启之功;谈隋者亦有之,然往往有隋而无“随”,而真实的历史却是“隨”之于隋,有滥觞之功。
普六茹对“随”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随”是令他魂牵梦绕的“龙居之地”,其帝业滥觞于“随”,实验于“随”。他在朝为官,虽先后任定州、扬州总管,但“随国公”未变。普六茹坚,字那罗延(金刚不坏),汉名叫杨坚。考之《北史·隋本纪》《周书·杨忠传》和《隋书·高祖本纪》所言,本祖居武川镇,姓杨,讳坚,是弘农郡华阴人氏。他与随州结缘乃因杨忠。忠本系北魏、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是西魏大将军之一。因“从周太祖起义”被魏恭帝拓跋廓(汉名元廓)赐姓为普六茹,一作普陆茹(后改为茹姓)。但考据《周书·杨忠传》《隋书·外戚传·高祖外家吕氏传》以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典籍,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当如陈寅恪先生所推断:“从文帝母系来看,疑杨家本系山东杨氏。”亦即杨忠、杨坚的真正出身极有可能是寒门庶族,而非攀龙附凤、自抬门第的所谓弘农杨氏。
西魏大统十五年(549年),亦即南朝梁武帝太清三年,萧詧据有襄阳,但强敌环伺恐难自保,乃请为西魏附庸。忠奉命出师樊、邓,饮马汉滨,而取随州、安陆。自此,汉东之地被忠尽收西魏囊中。因表其功,西魏王朝赐姓忠为普六茹氏。北周取代西魏后,忠仍然受重用,历任小宗伯、柱国大将军,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进封随国公,其后任御正中大夫、大司空、都督泾豳灵云盐显六州诸军事、泾州总管等要职。
北周武帝天和三年(568年)杨忠病逝,坚袭爵随国公。故杨坚仕途乃子承父职,是典型的官二代,甚至是“官N代”。北周武帝即位不久,杨坚又任随州刺史。建德六年(577年),杨坚随周武帝灭北齐,进为柱国。此后两年之内,周武帝、宣帝相继去世,周室留下年仅7岁的静帝掌权,出现了权力真空。此时的杨坚凭着军事贵族的家世和皇太后之父的姥爷辈身份,入朝填补了权力真空。执掌周室权柄自然遭人反对,但从公元580年5月起,杨坚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先后平定了郧州(治今湖北安陆)司马消难等三州总管的军事反抗,相继剪除北周宗室赵王、越王等政敌。
此后,杨坚便胁迫静帝诏赠其曾祖杨烈为隋康公、祖杨祯为隋献公,他本人亦进爵为王,以崇业、安陆、城阳、平靖、上明、淮南、永川、广昌、安昌、义阳、淮安、新蔡、建安、汝南、临颍、广宁、初安、蔡阳、郢州之汉东二十郡建立隋国。这隋国,实际上是周室被逼无奈下封建的“政治特区”,它允许“置丞相已下,一依旧式”,朝廷之威俨然。因此这是一个即将诞生的新王朝的“试验田”。次年周帝被迫“一依唐虞、汉魏故事”“禅位于隋”,而杨坚在半推半就中受禅,自此隋国由一个“样板田”变成了全国性政权,即大隋王朝。完成了政权实验的隋国改为郡,被称为“汉东郡”或“隋州”,辖安贵、顺义、光化、平林、上明、唐城等8县,户47193人。
但是在另一方面,传说他忌恶“隨”带“走之旁”(辶),遂改“隨”为“隋”。不管是牵强附会也好,还是确有其事也罢,这其实是在思考如何使国祚长久的问题。此忌恶虽然是传说,然方志与乡邦文献皆如此记载。
从1988年版《随州志》到明人颜木所编《随州志》,从元人胡三省到宋人罗泌《路史》,再到南唐徐楚金,都传“随文帝恶随字为走,乃去之,成隋字”。目前我所能找到的最早出处见于唐末李涪《刊误·洛随》:“汉以火德有天下。后汉都洛阳,字旁有水,以水克火,故就佳。隨以魏、周、齐不遑宁处,文帝恶之,遂去走,单书隋字。故今洛字,有水有佳,隨有走无走。夫文字者,致理之本,岂以汉隨两朝不迳之忌而可法哉?今宜依故文去佳书走。”李涪的“隨以魏、周、齐不遑宁处,文帝恶之,遂去走,单书隋字”之说,出于何处他没说,可谓无根之谈。但是这个传说真实反映了结束了中华数百年乱世的普六茹氏,确实在思考国祚长久的“兴化之道”这一大问题。
隋废前朝严苛“深刻”的“法令滋彰”,以“三省六部制”代替了为门阀士族所操纵利用的“九品中正制”,进一步抑制了士族对国家政权的把控;创立科举制度,为寒门子弟参与国家治理开辟了通道,寒门之士从书本中看到了“黄金屋”与“颜如玉”(宋真宗赵恒《劝学诗》)。虽然希望还是很虚渺,但畢竟是有希望。隋的贡献当然不止于此。但是省部制与考试制度的设计,至今还在使用。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东亚(如日本),乃至于近代兴起于英国的公务员制度也能看到其印记。应该说,它们是隋唐之后中国社会治理的精致的制度设计之渊薮。
隋之于唐,恰如秦之于汉。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对何以让国祚长久的“兴化之道”作了精致制度设计的隋王朝,国祚不及40年。省部制、科举制等在封建时代不可谓不精致。如此精致的制度设计很快让隋朝富裕了起来,但是制度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还包括理顺国富与民富、国与国关系处理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幸福关系等制度设计。隋王朝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其国之富,富在杨家,而民仍穷;其国虽强,但征战多年,民不得休息,统治阶级上层也矛盾重重;运河工程堪称浩大,遗泽千年,但是役民过急,民力不支。透支民力,最终的结果是丢失江山,国破家亡。李唐王朝则在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三朝较好地吸取了杨家教训,推行前隋良制,又藏富于民,广施恩泽,这个让人自信地唱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朝代,国祚近300年之久。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隋“恶隨有走”,那么杨氏父子为何又受封于此呢?这是因为当时随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州西通宛洛,南达吴越,地当荆豫要冲,扼阻襄汉咽喉。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如是描绘:“随北接黾厄,东蔽汉沔,介襄、郢、申、安之间,实为要地;义阳南阳之锁钥,随实司之;其山溪四周,关隘旁列,几于鸟道羊肠之险,洵用武者所必资也。”
当是时,其东与北齐对峙,南与陈相望,西南则比邻附庸小国西梁。由北周宇文氏派出靠得住的大将出镇随州,犹如在三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是一统江山非常重要的战略安排。拥有军事贵族世家背景又深受信任重用的杨氏父子,自然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随不仅战备地位重要,而且有深厚历史文化的积淀,它有——
精美之器背后的礼乐华章
随是汉王室特别敬重的先秦诸侯。《汉书·郊祀志下》记载,汉宣帝“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随”于先秦又称“曾”,既不是春秋五霸,又不属战国七雄,汉宣帝何以要在未央宫为随侯立祠?
这个问题,我们在文献上找不到答案。文献上找不到的答案,我们可以借助于考古学。在考古学上,我们能找到确切的答案。
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到1978年。这一年,中国即将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迎接盛世的第一道乐声用什么、由谁来敲响?历史选中了随城!
这一年,一座以乙为墓主的曾国大墓在随州擂鼓墩出土,出土文物达15000余件,包括礼器、乐器、漆木用具、金玉器、兵器、车马器和竹简。青铜器共计6239件,主要有镬鼎、升鼎、饲鼎、簋、簠、大尊缶、联座壶、冰鉴、尊盘及盥缶等,其中一套65件编钟的三层组合创迄今所发现的编钟完整之最。上为钮钟,形体较小,有方形钮,有篆体铭文,但文呈圆柱形,枚为柱状,字较少,只标注音名。分3组共19件。中下两层为5组共45件,为甬钟,有长柄,钟体遍饰浮雕式蟠虺纹,细密精致。这个组合中有楚惠王送镈钟一枚,共65枚。
当专家们对这套编钟进行音乐鉴定时,它竟然从2400多年的沉睡中苏醒来,用2400多年前的中华原声唱起了现代中国人所唱的“东方红太阳升”。不知不觉之中,随城用编钟为盛世的来临敲响第一道乐声。
曾侯乙墓出土青铜礼器是历年来我国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较全的一次,因发掘前未经扰动,所以它真实地记录了墓主人享用器物的礼制规定。
这是一部记录春秋与战国之际礼乐之制的“礼乐全书”,我们或可称之为“曾书”。其青铜礼器的组合,构成“礼乐全书”的“礼论篇”。墓以鼎为核心,形成了鼎成序、簋成套、鬲成组、豆成对、盘匜成配的礼仪组合。先秦时代,礼器的使用有严格规定,天子鼎九,诸侯鼎七,大夫、士人又逐层递减。但曾侯乙墓中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已近于天子之制。有人说,这明显僭越了诸侯能享有的鼎数,在曾侯乙生活的时代自商周以来的礼乐制度已经遭到破坏。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曾随国是超越诸侯的“南公”,其用鼎近于天子之制是否“僭越”,有待于继续研究。其乐器达125件,为世界考古史上所仅见。包括编钟、编磬、建鼓、琴、瑟、笙、箎、排箫8种,编钟、编磬各1组,琴、筝、五弦各件,瑟5件,笙1件,悬鼓1件。用于击奏乐器的工具12件,各种乐器的构件、附件1714件。出土时各种乐器基本位于原位,排列有序。64件青铜双音编钟十二律俱全,其上错金铭文除“曾侯乙作持”外,皆与音乐有关,包括不同音高的宫、羽、宫曾等22个名称;律名、调式和高音名称以及曾国与楚、周、齐、晋的律名和音阶名称的对应关系。音乐铭文有2800多字,构成了迄今所能见到的数量最大、体例最完备、内容最丰富、文化蕴涵最深的音乐理论文献,是“礼乐全书”的“乐论篇”。其衣箱完整地书写二十八宿名称,二十字漆书的首句为“民祀佳坊(房)”,说明曾国民重房星之祭,祈求的是政治修明,和气致祥,经天常和。这构成了“礼乐全书”的“天文篇”。其青铜器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纹饰华美,采用的冶铸技术有浑铸、分铸,其中尊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工艺包括平雕、浮雕、圆雕、透雕、错金、镶嵌、铸镶、铜焊、镴焊、铆接等,被认为是集先秦青铜制造技术之大成,集中反映了我国在春秋与战国之际的先进冶铸水平,可以说它是“礼乐全书”的 “考工篇”。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总计6696字,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竹简实物,亦可视为“礼乐全书”的“杂记篇”。一座曾侯乙墓就是曾人在精美之器上用人类听得懂的音乐语言书出的“曾书”,它是由礼论篇、乐论篇、天文篇、考工篇、杂记篇所构成的“礼乐全书”。
这部“礼乐全书”具有世界性价值。1985年8月,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E·G·麦克伦在美国《社会生物工程》杂志(Journal of Social and Biological Strutures)上发表了《曾侯乙青铜编钟》一文。该文结论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西方学术界注重文字学方法而忽视乐器上证明的极端偏向,一直是使汉学研究不健全的因素,这一点以前也有人提出过反对(库特纳,1965)。如果编钟为其同代希腊人希罗多德所知,我们可能早已听说到它们并视其为古代世界第八大奇迹。今天通过中国的报告所表现出的民族自豪与喜悦完全是應该的。现今中国人知道了他们的祖先在公元前5世纪时在音乐才能方面达到了如何惊人的高度,而且我们的世界教导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无法与这一成就相比的。
2016年,第十届国际音乐考古大会在武汉举行。来自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考古学家、音乐学家,以“人类学视野下的音乐考古”为主题,紧紧围绕“音乐文物研究”“声学与声景”“音乐人类学”等话题对曾侯乙编钟从历史、文化、音乐、美术等角度展开研讨。与会学者形成共识:曾侯乙编钟在人文以及声学铸造等科学技术方面,均能反映出公元前5世纪人类文化的丰富内涵。大会期间,在韩国汉阳大学权五圣教授的倡议下,来自世界各地的70多位代表共同签署了《东湖宣言》。《宣言》指出:曾侯乙编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重大发现,在人类文化史、音乐史、科技史等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展现了人类智慧在轴心时代所创造的高度,它音乐性能卓越、音律纯正、音色丰富,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其长篇铭文系统记载了中国当时的音乐学理论;以声音和文字互相印证的方式,保存了2400年前人类的音乐记忆。
很多人感叹曾国创造了人类奇迹。但是我从《曾书》中读到的曾侯乙,只是“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的庸君。他整天醉生梦死,什么“圣王之事”“万民之利”,他早就丢进他那大酒缸里了吧?其实,曾侯乙的先辈可不是这样,其中不乏思考“圣王之事”“万民之利”的大贤,他们的思考展现了人类智慧在轴心时代所创造的高度,从而形成了——
以民为本的经世之道
两周之际,中华文明进入了老孔称之为“天下无道”的礼崩乐坏时代,这是一个呼唤用新范式化混乱为有序的时代。当此之时,曾随文化没有缺位,而是在文化高位向中华文明贡献了一个化混乱为有序的新范式——道。对道的阐述,让我们重新请回了历史失忆已久的大贤季梁。
季梁,又作季良,生活在春秋早期。根据随州发掘的季怡墓资料分析,他可能是随国君后裔。《左传》记载季梁有两条。一是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的记载,重于记言,涉及祭祀、修政、论道。有人称之为“季梁论祀神”,也有人称之为“季梁劝修政”,都有道理。但我们认为这两個概括都没有抓住灵魂。季梁立言,其魂在道。所以,我们将其概括为“季梁论道”。二是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的记载,重于记事,是季梁对随君提出的军事建议,可以称为“季梁论兵”。
两条资料是一个整体,包括了如下要点:
福为天授神降;
小之能敌大;
所谓道;
道即忠信;
上忠于民;
利民,忠也;
祝史正辞,信也;
以故生辞;
夫民,神主;
民和年丰;
民和而动则有成;
民力普存;
先和不许而后战,怒我而怠寇;
避实击虚。
这些题涉政治、军事、哲学诸多领域的论点构成了季梁的思想精粹。既是季梁的行事之基,又是季梁的立言之据,其中“普存”这个范畴达到了对“普遍性”追求的思想高度。在此追求中,统率一切的是道。道在季梁之前已经开始使用了,但是第一次超出经验站在普遍性高度对道进行反复思考,也就是从道自身,又将道当作对象进行反思的是季梁。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季梁说:“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在这句话中,道是被反复思考的东西。第一个道,是指实际治理层面的道自身;第二个道则超出了实际治理,将道变成所谓的对象。从“道”而进于“所谓道”,形成了逻辑的递进关系,它就是反思,这就跨进了哲学门槛思考。
“所谓道”三个字看似简单,但它却为中国思想史即道的追求历程划了一个界:此前人们对“道”是“用”,由此形成的历史就是思想史;“所谓道”事实上是道的追求由自在进入自觉的标志。在“所谓道”支配下形成的思想史,就是哲学史。
季梁将生活世界分为“道”和“淫”两层次。“淫”指的是统治阶级放纵、贪婪等不守正义的行为,是治理的现实状况;“道”是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是理想世界。只有当现实最终符合于理想时,国才可免于难,才会有福可言,这就有了“道统治世界”的意味。
因有“道统治世界”的思想,两周之际流行的“天授神降”思想受到季梁的限制。季梁更看重的是民的决定作用。他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民和而动则有成”等命题,强调国家之福系于民和,民和系于“民力普存”。这里有“民为神主”“神为君主”两个类如形式逻辑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其蕴含结论是:民乃君之根。不过,如按逻辑形式,我们从民为神本、神为君本两个前提中引不出“民为君本”的结论。但在形式逻辑之外,季梁思想确实含有民为君本的意思。他通过君福天授论让“君”取信于神,通过民为神主论让神为民代言。“民为君之本”是这种思路的必然结果。从季梁的论述来看,“君”对“民”之“忠”要在“利民”;“利民”之要在于民和年丰、“民力普存”。故季梁虽然还有信“神”的一面,但他此“神”是季梁过渡到君“忠于民”的中介环节。这个由“神”到“人”飞跃的思想历程,构成了春秋早期在南公国发生的精神现象学,其本质上就是经世以道的民本学。
季梁的思想对后世儒家产生了影响,但是季梁却很少见称于诸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后,忠君思想日益成为治世之需,而季梁念念不忘的是万民之利,强调君忠于民。所以历史选择了孔子儒家,而对季梁却是选择性的失忆。直到中国社会进入到以民主为追求的时代,季梁思想才又重现其光芒。
为什么在曾随这样一个国家,竟然能出现像季梁这样旷古烁今的思想家呢?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早在殷周之际,曾随就已经成为周文化——
南方的经典之都
殷周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革命时期,大师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在这个政治与文化变革之际,曾随文化也没有缺位。不仅如此,它以巨大的历史与文化的张力,为周文化对南国(南方)的经营提供了 “经典范式”。
殷周之际的随国是周人在南方建立起来的领袖之国,称“南公”。“随”之先祖与周武王早已经出了“五服”,既不是“文之昭”,也不是“武之穆”,还不是“周公之胤”。但如王符《潜夫论·五德志》所云,它只是与周室同为姬姓,皆为“弃”裔,即“皆姬姓也”而已。随州文峰塔M1所出钟铭直书曾为“稷之玄孙”。“玄孙”虽然是虚指,但是它表明了曾是后稷的远孙,是知王符此说不虚。
“稷之玄孙”甚多,但是曾人却能封于南,且为南方之长,这是有原因的。2009年,随州义地岗墓地出土了曾侯舆的一套编钟,其中有一件铸于公元前497年的甬钟有铭文160余字:
唯王五月,吉日甲午,曾侯与曰:伯适上谔,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周室之既卑,吾用燮就楚。吴恃有众庶,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荆邦既残,而天命将虞。有严曾侯,业业厥声。亲敷武功,楚命是请。复定楚王,曾侯之灵。於穆曾侯,壮武畏忌,恭寅斋盟,伐武之表,怀燮四方。余申固楚成,改复曾疆。择予吉金,自作宗彝。龢钟鸣皇,用孝以享于予皇祖,以祈眉寿,大命之长,其纯德降余,万世是尚。
从铭文可知,曾人以“适”为“皇祖”。“适”最早见于《尚书·君奭》,称“南宫括”。依照《史记·周本纪》记载,在周革殷命的过程中,南宫括深得武王信任,完成了武王交给他的两个任务:“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灭殷后,南宫括很少见于典籍记载。幸而曾侯舆钟铭对此事有了交代:“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原来灭殷之后,武王又遣命南宫括到了“江夏”,任务是在汭土这地儿“营宅”即筑城,目的是统率淮夷。礼乐是曾侯统率淮夷的重要方式,至“周室之既卑”时,曾侯仍然讲“吾用燮就楚”。此“燮”可作“和”解,这就是说,曾侯仍然以和(乐)与楚相处。
有人说,南宫括本人或并没有到“江夏”汭土,然而钟铭清楚记载至“江夏”汭土“营宅”是“王遣”结果。“君此淮夷”意味着曾国的地位很高,是“淮夷”之君,周人称之为“南公”。“南公”之位要世袭,所以“括”之后多有称“公”的,如随地出土文物铭文:“犺乍刺南公宝尊彝”“曾公求”。文献中,我们亦见《左传》称随君为“公”的记载,云“汉东之国随为大”。是知曾随国是以 “汭土”为都的南公国。随地在新石器時代就出现中心聚落,不过中心聚落毕竟不是城市。南公国是周人在江夏之地所筑的最早、规模亦最大的国都,“汭土”之名至于春秋而未变。《左传·庄公四年》记载: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
楚原本是小国,地狭民少。楚武王时,它发明了一种很厉害的“荆尸”阵法。楚武王准备凭这种阵法征随。可是当时的随人哪里知道,征随的楚武已死于樠树之下。假若随人此时主动出击,楚人必不能胜。但为楚人“营军临随”假象所惑,且被“荆尸”阵法吓怕了的随人却向楚人求和。楚人开出的谈判条件是:莫敖屈重以楚王的名义到“汉汭”与随侯结盟。从南公“营宅汭土”可知,“汉汭”乃曾人宗庙所在地。春秋早期曾国的行政中心似乎不在“汉汭”,应该在安居一带,但是莫敖要求与随侯会见的地点一定要在“汉汭”。这说明,“汉汭”比随侯行政中心重要,说明它是曾人的宗庙所在地。楚人的这种会盟地点要求,是在向随侯传达这样一个信号:楚人随时可以占领随国的宗庙,即随时可以让随灭国。可见汉汭是随州古城的根。一个楚臣竟然邀请随侯在其宗庙所在地见面谈和,这对于随来说是耻辱,所以随人得知真相后不服楚。到了僖公二十年,乃以“汉东诸侯”为由背叛与楚的盟约。楚伐之,结果是楚人“取成而还”,当时的评论者称“随之被伐,不量力也”。从此随附庸于楚了,这就有了昭公十七年“吴伐楚”那场战争楚对随言“使”的记载。
“汉汭”于今天或许仅剩考古学上的遗迹,然于殷周之际,它却有经典范式的意义: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城市之一,它虽然不像洛阳那样是“中国”,却是周人筑于江夏的南公国,是周文化在南方的“标征”。而这个“标征”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到上古烈山氏,因此经典之都实乃——
华夏精神之源
虞夏之际是中华文明十分重要的原创期,此时的曾随文化是滋生中华文明之社稷精神的母体,是探源中国国家精神形成的最早社稷标本。
“随”初为姜姓,是对中华文明有重大贡献的氏族之一。《世本》云:“随作笙”“随作竿”。此时“随”氏族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东汉学者宋衷注:随乃“女娲氏之臣”。按:此“女娲氏”非抟土造人之“女娲氏”。据民国学者丁山所考,“女娲,《北山经》则又作女娃”,是知“女娲氏”即炎帝之女。此时,她已经臣服于黄帝,故东汉学者宋均注:“女娲氏”系“黄帝臣也”。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条历史谱系:女娃氏是臣服于黄帝氏(中央国)的方国,而“随”则是女娃国的一个诸侯。这也说明了历史上为何有随“为神农之后,姜姓”之说的原因。
随是起于黄帝时期的炎裔部落,其先民能歌善舞,发明了笙竿。不过随氏族更大的成就在于发明了谷蔬混种,即种植百谷百蔬。农学史证明,随氏族“在平原沼泽地种稻,居住生活在附近的山坡上”,因而随地有“原始稻作赖以发生发展的生境”之称。从考古上看,随州境内发现大量古文化遗存,据统计目前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56处。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江汉考古》2010年第1期所公布的数字,已经被确认为是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有38处。它们反映了距今约4500年~6000年内的曾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状况,其文化内涵是“农的生活”。除此之外,随地淮河源头存有大量的4200年以前的岩画,其中神像见证了当时“农的生活”。1958年,胡耀邦在随考察时也曾指出,相传原始农业始于随县,几千年随县人民一直是以农业为生计,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
随氏族的农业经济至虞夏时期已经很强大了,他们耕于厉山而有天下,就连虞舜也曾于此耕作。随州至今还有秦立舜井碑。此时随被“记曰厉山氏。左氏曰烈山氏。”《国语·鲁语》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烈山氏因能植百谷百蔬,故被尊为社稷之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
但是后来烈山氏的神农地位发生了变化,即“柱”的社稷神地位被周人先祖弃所取代。这就是《礼记·祭法篇》所说的“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我们今天知道了,周人南公括在“营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的过程中,将其先祖弃列为社稷神。神农祭祀由烈山祭转变为后稷祭,意味着随地文化实现了从姜姓到姬姓的革新与转换。不过,无论怎么转换,由烈山氏开创的社稷精神在曾随文化中却得以保存与发展。它最终作为农耕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宗教具象而与黄帝所开创的礼教制度的宗教具象——“宗庙”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宗庙社稷”,由此有了“中华文明的细胞”。
穿越随城历史,我们虽然看不到历史建筑,但从隋唐的精致之制出发,我们可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源;从精美之器的和声,我们可聆人类轴心期原音、悟人类轴心期经世原道。一言以蔽之,随城是文脉激荡的经典之都……
(谨以此文表达对武汉工商学院2021年校级智库建设项目——“武汉支点建设的文化支撑与对策建议”之积极响应)
责任编辑/赵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