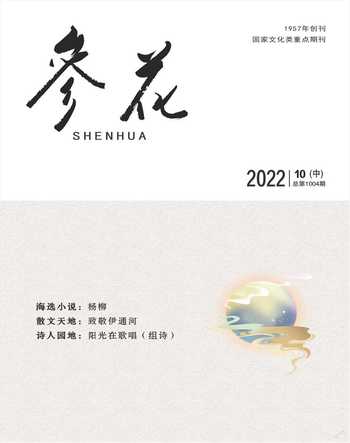论小说《红高粱》的跨媒介改编
2022-05-30豆盼盼
“媒”,《说文解字》认为,“媒,谋也。谋合二姓”,后引申为事物发展的诱因。“介”在甲骨文中指铠甲,后演变为介于两者之间。“媒介”一词,魏晋经学家杜预为《春秋左传正义·桓公三年》中“会于嬴,成昏于齐也”作注时,提出了“公不由媒介,自与齐侯会而成昏,非礼也”,指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后在《旧唐书·张行成传》中再次出现,含义与之前一致。可见,“媒介”即是讯息送达受播者途中的工具或方法。“跨媒介”又称跨平台,跨平台是实现跨媒介叙事的基础,它能为叙事提供不同的呈现方式,也能为受众提供更多的讨论空间。跨媒介叙事由亨利·詹金斯在《融合文化》一书中提出,经多年的补充完善,逐步发展成一套成熟的叙事理论体系。跨媒介叙事是一个故事横跨多种平台的展现,每一个媒介都对整个故事进行创新,使故事具有更加立体、多元的讨论空间。
《红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品,这篇小说蕴含多种红色意象,而“红高粱”作为小说中的典型意象,是地域文化符号的表现。小说采用意识流叙事手法,跳跃式地呈现一个一个的魔幻现实主义场景,强烈刺激了读者的感官,为诉诸视听的多种媒介改编提供了创作空间。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电影、电视剧、戏剧等版本的《红高粱》逐渐出现,使文本解读更加多样。《红高粱》作为文学文本,经过不同媒介的改编使其成为莫言作品中跨媒介制作和传播的经典文本,就传播广度、发掘深度和艺术高度而言,此作品的跨媒介改编值得深入探究。
一、电影版《红高粱》
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糅合了《高粱酒》中的部分情节,由张艺谋执导,姜文和巩俐担任男女主角,荣获了金熊奖。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呈现出了“纯、简、极致”的影像风格。“纯”:将男女主角复杂的爱情提纯为美丽童话。“简”:简化时代背景,删减次要人物。“极致”:将情感发挥到极致。影片以“中国红”为特色,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象征民间的喜庆热闹和中华民族蓬勃的生命力。影片中的红嫁衣、红花轿等物化符号建构出一个被红色晕染的空间场景,身处这一空间下的人物心理状态也被凸显出来,红色高粱和红色火焰将人物的欢快、躁动和悲愤情绪外化,表现了人物与命运抗争的残酷性,给观众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具有民俗审美趣味。在这一片由红色高粱浸染的场景之中,老百姓旺盛的生命力得以迸发,张艺谋由此谱写了一首张力十足的生命赞歌。影片《红高粱》作为首次对小说进行再创作的作品,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戏剧和影视改编。
二、电视剧版《红高粱》
2014年10月,《红高粱》电视剧登上了影视舞台,宏大的故事情节、复杂的人物关系等使导演以《红高粱家族》为参照进行改编,重点选取《高粱殡》来扩充情节,将小说的写意叙事转换为抗日叙事,将男主戏转化为以九儿为主的女主戏,“红高粱精神”由男性的雄浑遒劲转变为女性的柔韧刚强,九儿与余占鳌的爱情被调整为两个个体间的相互征服。此改编作品塑造了“女主角”九儿,情节紧凑,满足了观众对影视剧充满戏剧性的审美需求。此外,电视剧将故事场景由影片中的黄土地置换为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搭建了古色古香的单家大院、单家酒窖等场景,增加了代表传统的单家大奶奶这一角色,其与九儿展开了一系列明争暗斗的故事。两院之间的空间对峙,使九儿与大少奶奶的性格凸显出来,并形成强烈对比,更具商业性。
可见,电视剧《红高粱》的改编策略是符合跨媒介改编特质的成功演绎的,但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俗化改编,譬如九儿与大少奶奶的宅斗内容过多,占全剧的五分之三,削弱了文本的艺术性。
三、纪录片《高粱红了》
纪录片《高粱红了》记录了电视剧从拍摄到杀青的所有事情的经过,如购买版权、拍摄过程等,记录了电视剧详细的制作过程。它与寻常纪录片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對真实发生事件的戏剧化安排,既满足了观众的需求,又达到了解构电视剧的效果;它又不同于拍摄花絮,《高粱红了》具有完整的叙事单元,超出了花絮的叙事容量;它还不同于宣传片,宣传片是在影视剧播出前,制作方用来造势、吸引观众的短片,包括重点情节、故事悬念等,不涉及过多的幕后制作的细节。这种崭新的影视类型,更适合依托于中长篇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或是拥有庞大粉丝群的大IP改编作品。这样,纪录片节目就有了众多可解密的内容,能够引起观众强烈的兴趣。《高粱红了》作为国内电视剧史上第一个真人实际纪录片,具有特殊的审美娱乐价值,它既发掘了电视剧叙事文本的娱乐功能,又满足了观众二次观看的喜好,丰富了观众在观看电视剧外的娱乐体验。但其作为一种新兴的影视样式,还有待成熟,可以视为纪录片与真人节目的粗糙结合,因此,其价值有待考量。
四、戏剧版《红高粱》
(一)舞剧
由小说《红高粱》改编而来的舞剧共两部:1988年王举的《高粱魂》和2013年王舸、许锐的《红高粱》。
王举的舞剧分为颠轿、野合、祭酒神、序和尾声五块,每一块均为独立的“意象单元”,呈现出大跨度跳跃的“组舞式”结构,从人的生命欲望出发,交织着“人”“神”“魂”三个生命主题,“既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又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北方地域文化的特色”。王舸、许锐的舞剧比王举的舞剧多了三个场景,正是这多出的场景,融入了历史背景,使剧作主题由个人“小义”升华为民族“大义”,历史感更为厚重。全剧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当属群像之舞,融合了山东鼓子秧歌、胶州秧歌和生活基本体态,是舞剧最突出的“表意”机制。但舞剧作为戏剧的一种,还要完成写意之外的故事叙述,王舸和许锐在“大表意”的群像中穿插了一些生活化的“细写实”,如性格化的造型、“跑驴”等民俗细节,这种“大表意”与“细写实”的交融,使舞剧《红高粱》成为一部优秀作品。但舞台表演也有其弊端,如对复杂情绪的牵强呈现、浮夸的肢体动作等,反而限制了舞剧的表现力。
(二)晋剧
晋剧《红高粱》不再将小说文本中的伦理感情作为叙事核心,剧作将余占鳌、罗汉、九儿定为青梅竹马的三角关系。晋剧《红高粱》吸收了民间舞蹈的表现体态、蒲剧和梆子戏等表演程式,如九儿的“站椅子”、用“踩轿”表现“跑驴”,双人舞展现男女主的野合等,既推动了情节发展,又突出了人物形象。剧院采用三维技术,用LED屏打造出漫山遍野的红高粱和奔腾直下的黄河水的场景,舞台极具现代特色,满足了观众的视觉审美期待。以上融合了多种艺术门类的全新表现手法,使现代戏剧取得了创造性的突破,为传统戏曲的现代化转换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晋剧对《红高粱》的二次创作,可谓大醇小疵,虽有创新,但削弱了九儿和余占鳌之间充满野性的叛逆精神和生命张力。
(三)豫剧
豫剧《红高粱》开场以抗日为大背景,以男女主角的爱恨情仇为故事发展的主线,叙述了农民英雄反抗侵略者的事迹。为适应豫剧的艺术表现形式,导演将故事发生地改为豫西地区,将余占鳌更名为“十八刀”,身份设置为草莽英雄。九儿的身份变为草台戏班的女演员,并融入扈三娘的扮相。在剧中,九儿被卖给麻风病人单扁郎,经十八刀解救后互生爱慕之情,结为连理。抗日战争爆发后,二人义无反顾地带领全体乡亲抗日,最终牺牲。其中,二人互诉衷肠和壮烈牺牲的场面感人至深,呈现出了震撼的艺术效果,尤其是九儿着扈三娘戏服演唱“靠山吼”的场面,象征着人物对悲剧命运的强烈反抗。剧中血海似的高粱地、酣畅淋漓地喝酒的场面等呈现了一场丰富的视觉盛宴,再加上豫腔特有的唱法,使剧作更具感染力。
(四)评剧
评剧《红高粱》采用倒叙手法,开场就将抗日英雄们慷慨赴死的悲壮画面呈现了出来,奠定了戏剧的格调。整部剧以鲜艳的红色大色块铺呈开来,动态的红高粱、红嫁衣等红色道具构建出具有生命力的色彩世界,红色意象被运用到了极致,“接通了文本、地域、民族与戏曲审美的通道,在当代戏曲舞台上成为无可替代的唯一”。化用旧程式,创造新程式,塑造了刚烈妩媚、充满野性的新女性形象。评剧还糅合了《檀香刑》中的行刑场面,将刘罗汉被行刑这一场景进行立体呈现,成为戏剧化特色舞台的一个重要呈现途径。导演熟练运用“小仔儿”这一串场人,为整部评剧无序的“意识流”结构建立情感逻辑秩序,使文本与舞台的“碎片”和“定格”在情感纬度上得到统一。这使观众获得了强烈的审美体验,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文本的戏剧化特色。此评剧是文本、舞台和表演效果的有效统一,是《红高粱》小说戏剧改编的绚烂乐章。美中不足的是,评剧中男性旁白语调怪异,红高粱地和法场的舞台场景布置奇巧不足,笨重有余,这与舞台的固定、有限性有关,显得拖泥带水。
(五)茂腔戏
茂腔戏《红高粱》以茂腔为主,既采用高密方言,曲调质朴自然,又融合京剧、话剧等多种剧种,具有多样化性。全戏共八场,如抗婚守身、心心相印、罗汉救友、复仇烈火等,集中展现九儿、余占鳌和刘罗汉之间的三角恋关系及众人的抗战故事。剧作采用茂腔特有的表演技巧和传统的唱腔风格,运用原板、摇板等多种板式,加入山东快板、顺口溜、现代音乐等,极具舞台效果,戏剧演员优美的身段和融入现代音乐的唱腔,带给观众极强的视听冲击力,建构出更为立体的戏剧空间。不足之处在于导演为迎合观众的审美期待,将厚重的《红高粱》变成了通俗的爱情戏,淡化了戏剧原有的表现力。简而言之,以上五种戏剧对《红高粱》的再创作,各有特色,丰富了小说文本,但白玉微瑕,也颇需注意,在当下,更要警惕戏剧向市场过度靠拢的趋势。
五、戏剧电影版《红高粱》
剧作改编自《红高粱家族》,全剧自始至终贯穿着茂腔戏,包括九儿被颠轿前后的哀怨无助、洞房前后的无可奈何、回门路上的为爱呐喊和为罗汉报仇之际的声嘶力竭,演员们以婉转幽怨、质朴自然的高密茂腔进行演唱,极具感染力。同时,还融合了多种现代流行音乐、童谣的唱法,为传统茂腔唱腔增添了不少色彩。并介入电影技术,呈现了单家大院、十八里坡民俗村等场景,打破了戏剧原有的舞台限制,扩充了戏剧的叙事时空,增强了演员的语言表达能力,将“戏”与“影”的美学风格相贯通,使影片的趣味性和观赏性有所增强。与珠玉版的电影《红高粱》相比,茂腔版的《红高粱》将高密市两大瑰宝“茂腔”和“红高粱”糅合在一起,洋溢着浓郁的本土气息。茂腔戏作为一种小众的艺术形式,对观众本身的品位、艺术感知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观众需要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此电影打破了这种限制,促进了传统戏剧的传播。可见,这是创作者在茂腔戏和电影《红高粱》基础之上的再创新,吸收了二者为观众所乐道的长处,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改编作品。此外,戏剧电影版《红高粱》虽是一部创新之作,但影片将余占鳌和九儿曲折的爱情故事作为核心,占据全剧情的四分之三,对部分细节处理得不够细致,尤其是颠轿这一情节,淡化了抗日大背景,不免落入了俗套之中。
六、结语
小说《红高粱》作为一部经典作品,自发表至今,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戏剧、戏剧电影等多种作品,这些改编作品将小说文本引向了多种媒介领域,每一次阐释,既是对原著的再解读,又是艺术的再创造,呈现出了不同的叙事特征,使《红高粱》这一作品愈加趋向立体化。通过梳理和比较不同媒介对《红高粱》的改编,发现在当前的市场和技术水平下,其改编质量参差不齐,也做出了一些突破性尝试,既有对小说文本的呈现、创新,也有对其的遮蔽。这样的跨媒介叙事理论实践,彰显了优势,也暴露了不足。随着这一理论的发展,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经典作品的跨媒介改编,《红高粱》不失为一个可借鉴的先例。此外,跨媒介叙事理论的发展领先于实践,文学作品的跨媒介改编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注释:
①周诗蓉:“魂”惊四座,舞蹈,1988年,第11期。
②彭维:“浓墨重彩”推动场面变形与结构流动——以评剧《红高粱》为例,戏曲研究,2019年(02),第79页。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2][挪威]雅各布·卢特.申丹,校.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M].徐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张智华.电视剧叙事艺术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4]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5]刘晶.叙事学视野下《红高粱》的改编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6.
[6]周诗蓉.“魂”惊四座[J].舞蹈,1988(11):45-
47.
[7]彭维.“浓墨重彩”推动场面变形与结构流动——以评剧《红高粱》为例[J].戏曲研究,2019(02):73-87.
[8]周安華.论当代中国戏剧的电影化倾向[J].文艺研究,2002(05):92-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水师范学院2021年
研究生创新引导项目(项目编号:TYCX2143)
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豆盼盼,女,硕士研究生在读,天水师范学院,研究方向:文艺学)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