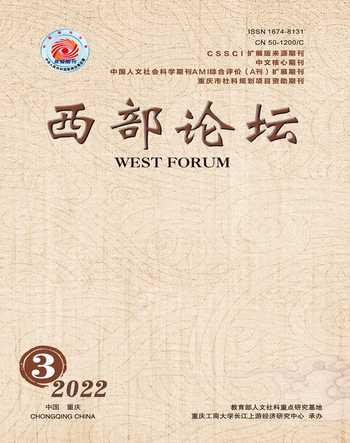我国家庭农场研究进展与展望
2022-05-30郭熙保吴方查科
郭熙保 吴方 查科
主持人语
郭熙保: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是我国家庭农场迎来快速发展的标志性文献,可以说,2013年是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元年。首先,自2013年开始,国家和各地密集出台了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其次,近10年来,我国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兴起,至今已发展到300多万家;最后,学术界关于家庭农场的研究爆发性增长,每年以千篇论文以上速度递增。十年是一个值得总结的时间节点。为此,本专题从理论与政策两个层面对我国家庭农场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我国家庭农场研究进展与展望》一文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和归纳了我国学术界关于家庭农场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家庭农场研究:知识图谱、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一文基于文献统计从知识图谱、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等方面刻画了10年来我国家庭农场研究的演进和趋势;《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评析》一文对21个省份和31个城市出台的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进行归类和比较,并提出改进建议。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22.03.001
摘要: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促进了我国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也掀起了家庭农场研究的热潮并一直延续至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家庭农场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给家庭农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因而有必要对已有的家庭农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家庭农场研究提供启示和方向。
本文通过回顾和梳理CSSCI收录的题目包含“家庭农场”的382篇论文,从家庭农场的概念特征与地位作用、形成原因与发展条件、发展模式与经营模式、适度经营规模与经营效率(绩效)、制约因素与应对策略等5个方面总结其主要研究成果:(1)家庭农场是介于企业和普通农户之间的农业经营主体,既有“家庭”的特征,也有“农场”的属性;当前,家庭农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力军,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之一。(2)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不均衡催生了家庭农场;我国家庭农场的产生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密切相关,而制度改革是家庭农场形成机制中的关键因素;家庭农场的持续发展需要有相应的土地流转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市场机制和政府支持、投资保障和社会保障等。(3)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基本方向和主要模式;各地资源状况和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家庭农场实践也形成了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和经营模式。(4)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要“适度”,而“适度”的标准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具有显著差异;我国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明显高于普通农户,但经营效率普遍不高,尤其是技术效率水平整体偏低;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和绩效受到农场主及其家庭特征、农场经营方式和技术水平、经营环境和配套设施、农业扶持政策和政府补贴等因素的影响。(5)我国家庭农场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制约因素,比如:农场主素质不高、经营管理能力欠缺,农场经营规模或方式不当、投资不足、技术水平不高,土地产权和流转制度有待完善,融资较为困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等,应从土地流转、农地改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场主培育、金融支持、财政补贴等方面加以完善。
我国学者对家庭农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如:截面分析较多,长期跟踪分析不足;经济学角度分析较多,多学科分析不足;国内分析较多,国际比较分析不足。
关键词:家庭农场;适度规模;农地制度;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2)03—0001—16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使“家庭农场”迅速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家庭农场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2013年无疑是家庭农场研究的分水岭。在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显示,家庭农场研究的论文数量从2012年的127篇激增至2013年的1316篇,此后每年发文数量稳定在1000篇以上。截至2022年4月25日,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家庭农场”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1.58万余篇;在CSSCI数据库中以“家庭农场”为主题的论文有706篇,其中篇名直接包含“家庭农场”的论文有382篇。
面对家庭农场研究的爆发式增长,一些学者对家庭农场研究进行了文献回顾和综述(韩朝华,2017;陈德仙等;2019)[1-2]。然而,现有关于家庭农场研究的文献综述仍需改进。首先,在研究主题上,有些文献综述主题不够全面,涉及内容不够广泛,仅回顾了家庭农场研究的某一个主题,如家庭农场的最优适度规模或经营效率评价、制度环境对家庭农场的影响等。其次,很多文献综述涉及的话题和内容存在重复和雷同,主要集中在介绍家庭农场的内涵和特征、阐述其发展问题和对策、梳理其影响因素和规模效应等方面。最后,在研究时间上,没有及时总结和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大多是2017年以前的文献。本文综述的内容不仅涵盖了当前国内家庭农场研究的多个主题,而且及时吸收了相关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一、家庭农场的概念特征与作用地位
1.家庭农场的概念与特征研究
家庭农场顾名思义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主体,但不是所有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主体都可以叫家庭农场。家庭农场是与现代农业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占支配地位,农户一般不称作家庭农场(family farm),而称作小农(small peasant household)。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来 定义家庭农场。在早期的研究中,有学者把家庭农场定义为具有企业性質的经营组织(房慧玲,1999;黎东升等,202000)[3-4]。2013年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家庭农场不是企业,而是介于小农户与企业之间的一种微观经济组织。例如,高强等(2013)基于农业生产要素的角度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融合科技、信息、农业机械、金融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现代经营理念,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5]。黄新建等(2013)基于经济收益的角度认为,家庭农场应当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适度规模经营为目标、以高效的劳动生产率从事农产品的商品化生产活动,并获取与农户从事非农产业收入相当甚至略高的经济利润的经济单位[61。高帆和张文景(2013)基于组织方式的角度认为,家庭农场是介于小农户和农业企业之间的中间型经营组织方式,而之所以介于二者之间,一方面是由于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与小农户相似),另一方面是因为家庭农场具有法人性质和规模化生产机制(与农业企业相似)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在定义家庭农场时不强调经营规模,但绝大多数家庭农场规模都比较大,因此,家庭农场大多数是规模经营单位。我国的家庭农场从一开始提出就是与经营规模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87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中发[1987]5号)就提出要在发达地区兴办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二十多年后,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家庭农场作为规模经营主体提出来。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不过,我国的家庭农场与西方的家庭农场在土地所有制上具有显著差别。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农村集体享有农用地所有权,而农户仅享有农用地的承包经营权,导致“租地农场”成为我国家庭农场区别于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一个显著特征(王贻术等,2013)[8]。
规模经营是家庭农场的主要特征,但不是唯一特征。郭熙保(2013)认为,家庭农场主要有以下四个特性:一是以家庭作为经营单位,二是劳动力主要是家庭成员,三是农地经营长期稳定并达到一定规模,四是农业经营收入是家庭的全部或主要收入来源[1。关付新(2018)将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规模化经营,以此区别于小规模经营的小农户和兼业农户;二是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以此区别于雇工经营的农业公司和专业大户;三是家庭主要收入来自农业(种植和养殖),以此区别于非农化的从事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农村工商户以及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兼业户[10]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尽管不同学者对家庭农场的概念界定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内涵大同小异,只是所强调的维度有所不同。与传统普通农户相比,家庭农场的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家庭为经营单位,这是最基本特征,否则就不能冠名“家庭”二字;二是适度规模经营,要比小农户经营规模大得多,否则就不称其为“农场”,但也是在家庭劳动力能够经营的范围内;三是从事专业化、市场化生产,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是其与小农户的本质区别,后者主要是为满足自己消费而进行农业生产,追求产量最大化。
2.家庭农场在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家庭农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且在农业生产乃至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所不同。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提出要重点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可见,中央非常重视家庭农场的发展,强调家庭农场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重要作用。相关研究也基于家庭农场的性质和特点认为,家庭农场必将成为主导我国现代农业的新型市场主体,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军。
郭熙保(2013)较早提出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途径,而家庭农场是实施农业规模经营的最重要主体[]。郭庆海(2013)分析了家庭农场在家庭经营、规模经营方面的优势,指出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基本主体,具有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推广农业科技等重要作用。杜志雄和王新志(2013)通过对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征辨析认为,家庭农场体现着改造传统农业的历史规律性,引领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代表着中国农业的先进生产力,其理应成为未来我国农业经营体系当中最主要的形式[121。姜涛(2017)指出,家庭农场的一系列特征决定了其具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枢纽”地位,并在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推广农业科技、保护耕地、传承农耕文明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王新志和杜志雄(2020)认为,家庭农场具有内在的制度优势,是现阶段中国“最适宜”“最合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4]。陈德仙等(2021)指出,家庭农场保留了家庭在农业生产中的“监督成本优势”,既具有土地规模适度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还具有产业叠加和融合带来的“多层利益优势”,是一种有效的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方式,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成效,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15]。此外,家庭农场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主体。肖望喜等(2018)提出,家庭农场可以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多种积极的作用,包括以市场为导向改善农产品供给结构、促进农业产业体系整合与“三产”融合、推动农业生产技术与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等[16]。
二、家庭农场形成原因与发展条件
1.家庭农场的形成原因研究
学术界对家庭农场形成原因的探究大都是从制度层面展开的。有学者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家庭农场形成的原因。例如,屈学书(2016)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农业生产二重性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分析认为,家庭农场是与当前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一种生产关系,是符合农业生产二重性特点要求的农业生产方式。王春来(2014)也认为,家庭农场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结果[18]。也有不少学者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阐述家庭农场形成的原因。例如,高强等(2013)、何劲和熊学萍(2014)认为,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均衡是家庭农场形成的主要动因,制度安排与环境相容是家庭农场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渐进式發展是家庭农场的必然选择[5][19]。伍开群(2014)则认为,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民诱导性制度变迁共同促进和实现了家庭农场的制度变迁[20]。程军国等(2020)也认为,我国家庭农场的形成是需求诱导和政府引导两种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需求诱致来源于农业产业的宏观发展需求和微观农户为节约自身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政府引导则是通过制度改革创造有利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环境而发挥作用[2]。兰勇(2015)认为,从传统农民到家庭农场的演变是一个多因素相互作用和演变的过程,包括环境、制度和农民行为等,它们的相互作用和演化是家庭农场产生的基本动力机制[22]。杨成林(2014)指出,家庭农场形成的根本驱动力来自农民对经济激励的自发反应,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如何为这一生成扫清障碍,降低农民在其生成过程中付出的“交易成本”,同时降低农业经营风险,使农业生产更具可预测性
还一些学者从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角度探讨家庭农场形成和规模扩大的原因。郭熙保和冯玲玲(2015)运用动态均衡理论分析发现,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农场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从而使农场规模不断扩大[24]。其他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如陈楠和王晓笛(2017)认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环境因素,工业化和城镇化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并解决土地集中问题,进而为新型职业农民和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可能,因此,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家庭农场发展的经济基础与前提,家庭农场的发展需要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推进[25]。何劲和熊学萍(2014)指出,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创新不仅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而且也为家庭农场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生产专业化、农民职业化的前提条件。王振等(2017)基于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较好的地区大多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客观事实认为,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发展家庭农场必须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开拓力量[26]。
2.家庭农场的发展条件研究
作为一种全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家庭农场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基础和条件。高强等(2013)认为,家庭农场形成和发展所需的制度条件至少应包括: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稳定和明晰的土地产权制度,以农机作业服务、金融服务、市场信息服务、农技服务为主的社会化服务制度等[5]。朱 启臻等(2014)指出,家庭农场的发育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特定的社会条件,包括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高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和政府的配套支持等[27]。王振和李凡(2014)基于对上海松江地区的考察认为,家庭农场的发展应满足几个基本条件:一是农业人口减少且土地流转顺畅,二是政府有效的财政支持和政策引导,三是良好的社会化服务和外部环境[28]。屈学书和矫丽会(2014)指出,工业化发展、社会保障体制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完善是家庭农场发展的条件[291。郭熙保和冷成英(2018)认为,市场化环境是家庭农场产生和兴起的关键,工业化和城市化催生了家庭农场的繁荣,土地流转市场的形成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基础,大规模投资是家庭农场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扶持对家庭农场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301。陈军民和翟印礼(2015)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认为家庭农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契约性质,契约各方的行为对家庭农场的产生具有很大的影响,因而降低家庭农场运行的交易成本是该制度顺利实施的关键,同时,政府和中介组织在降低农民适应制度成本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3。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知,学术界对家庭农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探讨,其中的主要观点是制度变迁是家庭农场产生的主要动因,但从经济发展角度考察家庭农场产生的原因更为恰当。家庭农场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留守在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少,使得每个农业劳动者经营的农地不断增加,于是促进了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家庭农场应运而生并持续发展。如果说制度变迁导致家庭农场产生和发展,其也是通过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来发挥作用的。例如,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实施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转移到非农部门,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从而导致土地流转和集中,使得家庭农场发展成为可能。
三、家庭农场发展模式与经营模式1.家庭农场的发展模式研究
家庭农場发展模式是指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方式与发展路径(冷成英,2020。家庭农场发展模式的形成是基本经济条件、制度环境、经营主体、社会资源等相互作用的结果(高强等,20014)[33]。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选择主要取决于其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禀赋和工业化水平。从经营规模角度看,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发展大致有三种主要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型家庭农场发展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中型家庭农场发展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小型家庭农场发展模式(张红宇等,
2017)[34]。人少地多的国家,农业发展首先从生产工具上进行革新,通过机械化等路径节约劳动力;人多地少的国家,则需要更多地投入劳动力和运用生化技术,通过提高单产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型家庭农场发展模式是规模化、机械化和高技术的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中型家庭农场发展模式是生产集约加机械技术的复合型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小型家庭农场发展模式则是资源节约和资本技术密集型模式(高照军等,2008)。
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基本方向和主要模式,这是由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的。郭熙保(2013)认为,我国地域辽阔,各地人口密度、地形差异大,因此应该走多元化的农业发展道路,比如:像东北和西北的平原地区,人均耕地面积与欧洲国家相当,应该借鉴欧洲农业发展模式,选择机械化与生化技术混合的技术进步路径;而像东部与中部人口稠密的地区,人均耕地面积与日本和韩国差不多,应借鉴日韩的农业发展模式,选择以生化技术为主的技术进步道路;受制于人均耕地面积,我国无论如何也不适合采取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以机械化为主的农业发展模式[9]。
事实上,在我国的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各地因地制宜的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王新志和杜志雄(2014)总结了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五种典型模式,即“上海松江模式”“浙江宁波模式”“湖北武汉模式”“吉林延边模式”“安徽郎溪模式”:(1)上海松江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是上海市高度城市化和后工业化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建立规范统一的土地流转方式,促进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2)吉林延边地区通过发展劳务经济实现农业人口转移从而推动家庭农场发展,其主要特征是加快土地流转,创新融资模式;(3)浙江宁波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是由宁波地区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农业劳动人口转移所催生的,其主要特征是成立基金引导家庭农场发展;(4)湖北武汉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推动城郊家庭农场发展,其主要特征是细化扶持政策,着重引导家庭农场的发展与促进产业化和环境保护相结合;(5)安徽郎溪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则是传统农业地区通过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发展家庭农场的代表,其主要特征是“三驾马车”(指农民主体、政府扶持、协会帮助)拉动家庭农场发展(王怡术,2015)。高强等(2014)将我国家庭农场归纳为“上海松江自耕农模式”“吉林延边城镇化联动模式”“安徽郎溪协会带动模式”“山东诸城分类管理模式”等四种典型模式[33]。郭家栋(2017)则辨析了“上海松江”“浙江宁波”“安徽郎溪”“河南民权”四种家庭农场发展模式的具体实践、实际效果和优缺点[38]。在诸多家庭农场发展模式中,一些学者重点研究了家庭农场的一种或几种发展模式。例如,吕惠明和朱宇轩(2015)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宁波家庭农场发展模式的现状、问题及对策[31;郭熙保和冷成英(2018)对比分析了湖北武汉和安徽郎溪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并总结了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十大特征[30][40]。
2.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研究
与家庭农场发展模式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描述家庭农场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不同,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侧重于从微观层面描述家庭农场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是指单个家庭农场为了规避风险、实现利益最大化而选择与其他经营主体(包括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等)联合和合作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学术界根据家庭农场与其他经营主体的联合和合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例如:赵维清和边志瑾(2012)通过对浙江省家庭农场的实地调查,提出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的创新路径,包括“家庭农场+合作社+合作社参与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加工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超市”等模式[41];刘倩(2014)则提出我国家庭农场主要有“单打独斗”“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经营模式[;蔡颖萍和杜志雄(2017)指出,我国家庭农场已经呈现出多元化、多类型的发展趋势,包括“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发挥集体功能培育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联合经营”“家庭农场联合合作”等多种经营模式[43]。还有一些学者比较分析了不同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的优缺点。例如:张乐柱等(2012)分析了温氏集团“公司+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模式,认为该模式与“公司+农户”模式相比,化解了后者利益分配难题,实现了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更紧密的联结机制;曹林奎(2013)通过分析“公司+农户”经营模式认为,“合作社+家庭农场”是一种新型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应该给予重点关注[45];张滢(2015)则认为,“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不仅避免了“公司+农户”模式下交易成本高、违约风险频繁的问题,还利用合作社的聚合效应和农场主的高度利益同质性,解决了“合作社+农户”模式下“小农需要合作,但不擅长合作”造成的合作困境[46]。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和经营模式的研究主要基于三个不同的层次展开:一是从国际比较角度提出我国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主要是以经营规模为划分准则,例如北美大型农场模式、欧洲中型农场模式和日韩小型农场模式,认为我国的家庭农场发展应该借鉴欧洲和日韩模式,而不能走北美发展道路。二是从地区角度划分不同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例如“上海松江模式”“浙江宁波模式”“湖北武汉模式”“安徽郎溪模式”和“吉林延边模式”,这些模式是基于各地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和政府支持等情况总结出来的发展经验,各有特点,对于类似地区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三是从经营主体之间的联合和合作角度划分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如家庭农场独立经营模式、与合作社合作模式、与龙头企业合作模式以及几种经营主体联合经营模式等,这些模式对于各地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学习价值和借鉴意义。
四、家庭农场适度经营规模与经营效率和绩效
1.家庭农场的适度经营规模研究
从我国农业人口多、耕地面积少、户均经营规模较小的特殊国情出发,官方和学术界都认为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应该适度。2013年9月,原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指出,中国也需要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发展家庭农场,但中国的家庭农场要强调适度规模,不可能搞到像美国、阿根廷和巴西那么大的规模。黄宗智(2014)认为,适度规模的、“小而精”的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正确的发展道路[47。影响农场经营规模的因素非常复杂,除了技术水平之外,交易成本、市场的完善程度、税收政策和农户的风險规避能力等都会对农场经营规模产生影响(林万龙,2017)[48]。朱启臻等(2014)提出,家庭农场的具体规模是由自然和社会条件、技术水平、经营内容、经营方式与地理环境等因素综合决定的,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家庭农场规模最重要的限制因素是家庭劳动力的数量[27]。王春来(2014)也认为,自然禀赋、生产传统、科技水平和社会化服务等共同决定了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18]。丁建军和吴学兵(2016)基于对湖北荆门市家庭农场的调查认为,影响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因素有资源禀赋、土地流转、雇工状况、农场主的经营能力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等[49]。
关于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适度标准,相关文献的观点可以概括为“收入标准论”和“效率标准论”(也称为“劳动标准论”)。郭熙保(2013)认为,农业经营规模化是指农业生产者经营足够面积的农地,产生规模效应,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到接近非农业部门的水平,其所获得的收益也不低于从事其他行业的收益。朱启臻等(2014)认为,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有两个标准:一是生计标准,即家庭农场的规模收益能满足家庭人口的基本需要;二是生产力标准,即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家庭劳动力所能经营的最大面积27。郭庆海(2014)则认为,农户的最优经营规模应确保以下两点:从效率的视角看能够实现农户收益最大化,从收入的视角看农户能够获得与城市居民(或外出务工农户)大体相当的收入水平[50]。从上述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确定家庭农场的适度经营规模时,“收入标准”和“效率标准”是同样重要的。然而,一些学者提出“收入标准”是确定农场适度规模的首要因素,适度规模的核心是使务农者能够获得与打工收入相当的收入(何秀荣,2016)[51]。对此,关付新(2018)认为,“收入标准”判定的是最小适度经营规模,而“效率标准”确定的是最大适度经营规模,因而适度的土地经营规模处于由“收入标准”和“效率标准”确定的下限和上限之间0。此外,也有学者基于公平的角度来看待家庭农场的适度经营规模,如陆文荣等(2014)指出,村庄强大的集体制传统、基于村落成员权的土地福利分配、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兼顾的村庄大公平观等与政府和市场共同建构了家庭农场的适度经营规模[52]。
然而,在具体规模测算上,相关文献对家庭农场适度经营规模的估算值差异很大。例如:农业部经管司及经管总站研究组(2013)认为,从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双重标准来衡量,北方单季地区的适度经营规模在6.67公顷,南方两季地区则为3.33公顷[53;朱启臻等(2014)认为,家庭农场适度经营规模的下限为家庭成员的生计需要,上限则为家庭成员经营能力最大化所对应的规模,据此推算,山东一对种植苹果的夫妇所适合的经营规模为0.33公顷,而黑龙江一个种粮户最多可耕种20公顷左右的土地[27];黄新建等(2013)根据江西水稻种植的经验,基于规模效率边际报酬计算出的家庭农场最佳经营规模为4.73~10公顷[61;孔令成和郑少锋(2016)运用DEA模型的测度结果显示,上海松江区家庭农场的最佳土地投入规模为8.13~8.40公顷;韩苏和陈永富(2015)运用DEA模型的分析则发现,浙江省果蔬类家庭农场的最优经营面积为1.33~2.0公顷[55]。蔡瑞林和陈万明(2015)基于江苏省13市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测算出的最优经营规模约为5.17公顷[56];根据苏昕等(2014)的推算,到2030年,我国劳均耕作面积将达到0.67公顷,而家庭农场的平均规模将达到26.7公顷(57)。
[47]黄宗智.“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J].开放时代,2014(2):176-194+9.
[48]林万龙.农地经营规模:国际经验与中国的现实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17(7):33-42.
[49]丁建军,吴学兵.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及其效益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荆门市66家种植类示范家庭农场的调查[J].农业经济,2016(10):9—11.
[50]郭庆海.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尺度:效率抑或收入[J].农业经济问题,2014(7):4-10.
[51]何秀荣.关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6(9):4-15.
[52]陆文荣,段瑶,卢汉龙.家庭农场:基于村庄内部的适度规模经营实践[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95-104.
[53]农业部经管司、经管总站研究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稳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中国农村经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问题”之一[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6):38-45+91.
[54]孔令成,郑少锋.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及适度规模—基于松江模式的DEA模型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107—118.
[55]韩苏,陈永富.浙江省家庭农场经营的适度规模研究—以果蔬类家庭农场为例.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5):89-97.
[56]蔡瑞林,陈万明.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的规模经营:江苏例证[J].改革,2015(6):81-90.
[57]苏昕,王可山,张淑敏.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及其规模探讨—基于资源禀赋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14(5):8-14.
[58]高鸣,习银生,吴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与差异分析—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10-16+161.
[59]蔡键.我国家庭农场形成机制与运行效率考察[J].商业研究,2014(5):88-93
[60]钱忠好,李友艺.家庭农场的效率及其决定—基于上海松江943户家庭农场2017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20(4):168-181+219.
[61]李绍亭,周霞,周玉玺.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其差异分析—基于山东234个示范家庭农场的调查[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6):191-1
[62]张德元,宫天辰.“家庭农场”与“合作社”耦合中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64-74.
[63]吴方.基于SFA的家庭农场技术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48—56+163.
[64]蔡荣,汪紫钰,杜志雄,示范家庭农场技术效率更高吗?—基于全国家庭农场监测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9(3):65-81.
[65]高雪萍,檀竹平.基于DEA—Tobit模型粮食主产区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5(6):577-587-584.
[66]孔令成,余家凤.家庭农场适度规模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8(16):301—305.
[67]高思涵,吴海涛.典型家庭农场组织化程度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1(3):88—99.
[68]何劲,祁春节.中外家庭农场经营绩效评价比较与借鉴—基于湖北省武汉市家庭农场经营绩效评价体系构建[J].世界农业,2017(11):34-39+178
[69]任重,薛兴利.家庭农场发展效率综合评价实证分析—基于山东省541个家庭农场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8(3):56-65.
[70]张琛,黄博,孔祥智.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与分析—以全国种植类家庭农场为例[J].江淮论坛,2017(3):54-60.
[71]关迪,陈楠.基于AHP—FCE的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综合评价研究[J/OL].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1—12(2021—09—01).http://kns.cnknet/kems/detail//11.3513.S.20210901.1052.010.html
[72]郭厦,王丹.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质量评价与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22—35
[73]张德元,李静,苏帅.家庭农场经营者个人特征和管理经验对农场绩效的影响[J].经济纵横,2016(4):77-81
[74]兰勇,谢先雄,易朝辉,等.农场主经历对农场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92-97.
[75]刘同山,孔祥智.加入合作社能够提升家庭农场绩效吗?—基于全国1505个种植业家庭农场的计量分析[J].学习与探索,2019(12):98—106.
[76]来晓东,杜志雄,郜亮亮,加入合作社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全国644家粮食类家庭农场面板数据[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143-154
[77]袁斌,譚涛,陈超.多元化经营与家庭农场生产绩效—基于南京市的实证研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6(1):13-20.
[78]朱红根,宋成校.家庭农场采纳电商行为及其绩效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56—69.
[79]耿献辉,薛洲,潘超,等.品牌资产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江苏省的实证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0(3):435-442. [80]
[80]郭熙保,龚广祥,新技术采用能够提高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吗?—基于新技术需求实现度视角[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33-42+175.
[81]陈德仙,胡浩.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以长江三角洲3市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1(4):1003-1015.
[82]曾福生,李星星,扶持政策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SEM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6(12):15—22+110.
[83]刘同山,徐雪高.政府补贴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J].改革,2019(9):128—137.
[84]鲍文,张恒,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的障碍及其路径选择[J].甘肃社会科学,2015(5):204—207.
[85]顾群.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困境及破解对策[J].人民论坛,2016(11):83—85.
[86]陈明鹤.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家庭农场[J].农村经济,2013(12):42—45.
[87]陈永富,曾铮,王玲娜.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13个县、区家庭农场发展现状的调查[J].农业经济,2014(1):3—6.
[88]王建华,杨晨晨,徐玲玲.家庭农场发展的外部驱动、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苏南363个家庭农场的现实考察[J].农村经济,2016(3):21—26.
[89]汤文华,段艳丰,梁志民,促进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对策研究[J].求实,2013([90]林雪梅.家庭农场经营的组织困境与制度消解[J].管理世界,2014(2):176-1
[91]杨建利,周茂同.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障碍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4(2):49
[92]陈金兰,王士海,胡继连,家庭农场的传承障碍及支持政策研究—基于山东省的微观数据和案例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1(4):121—131.
[93]刘文勇,张悦.家庭农场的学术论争[J].改革,2014(1):103-108.
[94]周忠丽,夏英.国外“家庭农场”发展探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4(5):22-25.
[95]肖卫东,杜志雄,家庭农场发展的荷兰样本:经营特征与制度实践[J].中国农村经济,2015(2):83—96.
[96]朱学新.法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农村经济,2013(11):122—126.
[97]徐会苹.德国家庭农场发展对中国发展家庭农场的启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70—73.
[98]郎秀云.家庭农场:国际经验与启示—以法国、日本发展家庭农场为例[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10):36-41+91
[99]何劲,YIRIDOEEK,祁春节.加拿大家庭农场制度环境建设经验及启示[J].经济纵横,2017(5):118—122.
Progress and the Prospect of Family Farm in China
GUO Xi-bao, WU Fang, ZHA K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The release of the No. 1 Central Document in 2013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in China, and also set off a boom in family farm research, which has continued to this da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How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in the new era has raised new topics for family farm research. There fore,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family farm research to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direction for further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family farm research.
By reviewing and sorting out 382 papers with the title of “family farm" included in CSSCI,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research results of family farms from five aspects: the concep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status function, the reasons for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ditions, development mode and management mode, moderate management scale and management efficiency (performance),the constraints and coping strategies. Specifically,(1) family farm is the main body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ordinary farmers, which has bo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and the attributes of “farm”; at present, family farms are the new force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nd one of the main forces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2) The imbalance between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institutional demand gave birth to family farms; the emergence of family farms in Chin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is a key factor i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family farm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requires corresponding land transfer and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cultivation system,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 system, market mechanism and government support, investment security and social security. (3)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more people and less land determine that moderate scale management is the basic direction and main mode of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in China; there are huge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level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practice of family farms has also formed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model and business model. (4) The seale of family farm operation should be “moderate”, and the standard of “moderation”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family farms; although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family farms in China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ordinary farmers,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is generally not high, especially the overall low level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performance of family farms are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and their families, farm management methods and technical levels,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supporting social facilities, agricultural support policies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5)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in China still faces many constraints, such as, the quality of farmers is not high, the management ability is lacking, the scale or mode of the farm operation is improper, the investment is insufficient, the technical level is not high, the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circulation system needs to be improved, financing is more difficult, the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 system is not perfect, and the govermment support is not enough. Thus, reform and improvement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erms of land transfer, farmland reform,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 system, farmer cultivation, financial support, and financial subsidies.
Chinese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on family farms, and p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deepened and expanded. For example, there are too many cross-sectional analyses, and long-term tracking analysis is insufficient; there are too many analy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but the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 is insufficient; there are too many domestic analyses, but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insufficient. Key words: family farm; moderate scale; farmland system; a new type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system; a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y
CLC number:F325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1674-8131(2022)03-0001-16
(編辑:黄依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