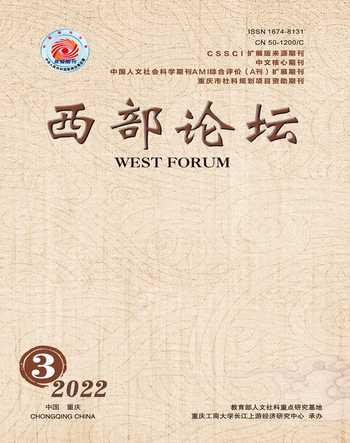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试验考察与推进建议
2022-05-30岳永兵刘向敏
岳永兵 刘向敏

摘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有利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然而,对于集体土地能否开发商品住宅还存在较大争议,且在已进行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改革中较少涉及商品住宅开发项目,相关研究也缺乏对其收益分配和具体操作的深入探讨。
本文对河南长垣、山西泽州、广西北流3个试点地区进行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试验的分析发现:政府、集体和企业均可在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中实现利益增进,三者利益的契合是改革的创新动力;进行商品住宅开发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大都位于城市规划区外的乡(镇)驻地所在村或中心村,而规划建设区虽然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潜力最大的区域,但也是改革成本最大、收益平衡难度最大的区域,因而未成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试验的首选区位;试点地区通过制定差异化的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标准、捆绑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收取增值收益平衡再分配金等方式,基本实现了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可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既符合改革的方向,也有现实的需求,并可通过适当的规制妥善解决利益平衡问题。
《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扫除了制度障碍,但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受到政策导向不明、配套制度缺位、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基础条件不具备等的影响,实践进程停滞。建议尽快部署新一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工作,并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作为试点的重点内容,鼓励试点地区将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的试验从城中村和城市规划区外逐步扩大到规划建设区、从存量集体建设用地逐步扩大到新增集体建设用地,积极探索建立合理的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并不断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相较于以往文献,本文在以下两方面做了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实践考察,从利益平衡角度分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的改革动力机制、试验区位选择和收益分配调节,进而论证了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的现实可行性。二是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宅面临的现实困难,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本文对试点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实践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消除认识分歧、推进改革实践,并为稳妥推进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关键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商品住宅开发;增值收益分配;建设用地市场
中图分类号:F301.2;F293.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2)03—0098—11
一、引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能否开发商品住宅?
201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但法律没有明确经营性用途中是否包括开发商品住宅,国家层面也尚未出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配套政策,对于集体土地能否用于开发商品住宅,政策并不明确。
目前,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相关文献分别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主体、范围、途径、用途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对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能否开发商品住宅存在较大争议。支持的一方认为: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才真正赋予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相同的权能,才能打破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符合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要求;在集体 土地上开发商品住宅,可以拓宽住宅用地供应渠道,增加商品住房用地供给,有利于降低房价[6]。反对 的一方則认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会打破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出让、以地生财”的获利模式,导致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下降,进而影响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虽然可以使集体土地价值充分释放,但只有城郊等区位较好地区的少数农民能够获得高额收益[71,最终将损坏全社会的福利。
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要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笔者认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是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题中之义,集体土地用于产生高增值的用途—商品住宅开发,已然成为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权”的一个重要标志。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2017年原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在北京、上海等13个城市开展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表明国家已将集体土地建设住房作为建立多主体供地、多渠道保障住房制度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不论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宏观改革方向来看,还是从“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客观要求来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都有其必要性。
从相关研究可以看出,争辩双方均肯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于健全集体土地权能、完善资源配置方式的积极意义,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能否用于开发商品住宅的主要争议是土地财政的传统发展模式如何接替以及“少数人获益”可能对社会整体福利增进的损害,其核心是收益分配问题。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其中,商品住宅用地出让是土地出让收入的主要来源。2015—2017年,住宅用地(包括普通商品住宅和高档住宅)出让面积占土地出让总面积的27.5%,而其出让收入占总出让收入的67.6%①。可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用于商品住宅开发确实会打破房地产用地单一由国有土地供给的格局,势必削减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因此,如果大规模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如何不对原有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模式造成颠覆性冲击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学者们针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收益分配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普遍赞同集体土地应跟国有土地承担同样的义务[8-9],并提出国家通过征收集体土地入市所得税、增值收益调节金、增值税等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10-11],但对于国家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形式和比例尚未达成统一意见。
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辨析,有利于多①数据来源于2016—2018年的《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视角审视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宅问题,但相关研究大多侧重于探讨是否应该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而对于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缺少深入研究,尤其缺乏基于地方试点实践的案例分析。有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广西北流、河南长垣、山西泽州3个试点地区进行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试验,从利益平衡角度探究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的驱动因素、区位选择和关键问题,并基于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的现实可行性,提出进一步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试点改革的若干政策建议。
二、案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的试点实践1.试点概况
2015年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授权在试点地区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法律规定,授权期限截至2017年12月31日。2015年3月,原国土资源部召开试点工作部署暨培训会议,正式启动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其中15个试点县(市、区)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2016年9月扩大为33个)。整个试点工作历经两次延期,于2019年12月底结束。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期间,试点地区按照“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目标要求,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从试点政策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用途要求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确定为工矿仓储、商服等经营性用途”,能否用于商品住宅开发在试点政策中没有明确。与集体土地能否开发商品住宅的理论争议一样,试点地区实践也出现了分化:部分试点地区,如辽宁海城、陕西高陵等明确规定集体土地入市不得用于商品住宅开发;大部分试点地区采取了回避态度,在政策中没有明确禁止用于商品住宅开发,但也没有开展相关实践;仅广西北流、山西泽州、河南长垣三个地方进行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用于商品住宅开发的试验。其中,长垣入市1宗商品住宅用地,面积为1.65公顷;泽州入市6宗商品住宅用地,共计6.45公顷;北流入市69宗商品住宅用地,共计263.3公顷。
试点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的主要做法如下:一是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实施主体,代表所有权人依法行使所有权。二是合理确定入市范围和途径。开发商品住宅的集体建设用地以存量为主、增量为辅,入市途径以就地入市为主、调整入市为辅,即区位好的地块可直接入市开发商品住宅,区域较差的地块通过复垦后,将建设用地指标调整到其他区位较好的地块入市。三是入市方式以出让为主,出让年限参照国有住宅用地出让年限确定为70年,土地使用权到期后参照国有住宅用地使用期满续期办法执行。四是建立多元化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规范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集体和个人间的分配关系。五是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交易规则、地价体系和服务监管制度,明确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参照国有土地办理规划、施工、商品住宅预售等手续。上述政策体系中,收益分配政策是核心,下文也主要围绕收益分配展开分析。
2.试点改革的创新动力:集体、企业与政府的利益增进与契合
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中,地方政府肩负着两项职责:一是自上而下地贯彻中央政府的改革政策,并及时反馈政策实施情况;二是与相关经济主体联合自下而上地开展制度创新实践,构建局部收益最大化的制度体系。上述三个试点地区在最初制定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中,都没有涉及开发商品住宅的内容,即没有强制性的制度安排。试点实施过程中,村集体、农民和房地产企业等作为第一行动集团,看到了打破“禁止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这种不均衡制度的潜在外部利益,进而试图借助试点机会谋求通过制度创新获取更多收益;而地方政府作为第二行动集团,也看到了制度创新中的获益机会,进而推行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的实践。具体分析如下:
(1)集体及其成员的收益:改善居住条件、盘活住房财产
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过程中,集体及成员除了获得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直接经济收益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收益:一是在建设用地指标短缺的情况下,很多地方减少了宅基地供应(三个试点地区入市地块所在村庄不同程度地存在宅基地供应不足问题),村民住房需求受到抑制,在审批宅基地无望的预期下农户能够接受通过建设商品住宅满足居住需求。二是村莊原有的基础设施配套普遍较差(即使是城中村,其公共设施配套与城区也存在较大差别),通过统规统建新式住宅小区可以有效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三是城市规划区外的入市地块普遍位于中心村,拥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可以吸引周边村庄的人口聚集。实践中,已有不少村民通过租房、私下买卖宅基地等方式在中心村居住生活,外来人口也有在这些村获得住房的意愿。四是少数村民已进城定居,其在农村的空房带有较强的资产属性,但因法律对宅基地流转的限制而无法流转变现,村民愿意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的路径盘活住房财产。
(2)房地产企业的收益:技术上可操作、财务上能平衡
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给予了市场主体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热情。从入市地块看,不论是城中村地块还是远离城区的地块,入市土地上原有农民住房多以自住为主,资产属性不明显,补偿相对较低,除去拆迁补偿成本,企业开发商品住宅仍有获利空间。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对金融市场有较强的依赖性,虽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押融资尚存在困难,但前期土地取得成本往往是以建好后的房屋或物业进行抵付,减轻了开发商前期资金压力,而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相较国有土地出让省去了繁杂的审批程序,节省了时间成本。国有土地出让需要经历5个阶段(组卷报批、组织实施、研究出让事项、出让前期准备、成交),至少要9个月;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只需要经历后两个阶段,用地者一般1~2个月就可以获得土地使用权,供地效率大幅提升。
(3)地方政府的收益:履行改革职责、破解实践难题
试点地区进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的试验,是充分履行国家赋予的改革职责。选择难度较大的改革事项,有利于在各试点地区之间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取得好的改革成绩。同时,三个试点地区还有一个共性—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较低(北流、长垣在20%左右,泽州约10%),这也是其推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的有利因素。此外,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和降低管理成本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获益:一是现行城中村(或棚户区)改造一般按照集体土地征收安置政策实施,拆迁后腾退的土地出让收入往往不足以支付安置成本,需要政府另行投入资金,实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后,政府不但不需要投入资金,还有一定的调节金收益;二是农村集体自主与开发商商定拆迁事宜,政府负责做好规划引导和相关服务工作,可以避免政府与群众因拆迁等问题引发的一些矛盾;三是拆迁户补偿协商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农民集体自己组织拆迁实现了拆迁成本内部化,可以降低政府的组织实施成本。
总之,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过程中,集体、农民和房地产企业主要追求增量的经济收益,地方政府则追求节约行政成本和落实改革任务的政绩收益。试点地区通过有效的利益平衡,使集体、农民、房地产企业与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追求各自收益的动机同时得到满足,达成一致性方案,进而有效推动了改革进程。
3.试点改革的区位选择:利益平衡成本最小化
商品住宅用地来源包括原国有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而在不同区位的商品住宅用地来源不尽相同,由此带来的收益分配问题也有差别。具体来讲,可以划分为三个区位:城市规划区内建成区、规划建设区和城市规划区外,其中,城市规划区内建成区、规划建设区统称为城市规划区。城市建成区的商品住宅用地主要来源于对存量建设用地的合理调整和再开发(如旧城改造和棚户区改造),虽然整治后的出让土地单价较高,但涉及基础设施配套、拆迁户安置补偿等支出,实施成本较高,因而政府的纯收益并不高;城市规划区外的商品住宅用地需求不大,地价也比较低,政府通过征收土地进行出让的获益水平一般;而在规划建设区内,主要通过征收集体所有的农用地进行商品住宅开发建设,土地出让单价虽不及城市建成区,但征地补偿成本较低,政府的收益比较可观,因而该区位也是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主要来源。
以长垣为例,2015—2019年,共出让商品住宅用地244.13公顷。从区位看,主要集中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共计238.55公顷,占房地产用地总量的97.7%。其中,城市规划区内的商品住宅用地82.63%来源于农用地(见表1),这些农用地都位于规划建设区内,在征收农用地时,其周边道路、零星经营性建设用地、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和未利用地也一同被征收。
那么,在规划建设区内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来开发商品住宅,与通过征收农用地出让来开发商品住宅相比,收益分配有怎样的差别?这里仍以长垣为例来进行说明。2015—2017年,长垣房地产用地出让平均价格为903.3万元/公顷;该区域农用地征收补偿标准约为90万元/公顷,加上社保补贴以及增值收益分享,每公顷土地可获得补偿在135万元左右。如果政府征收农用地后出让开发商品住宅,减去征地补偿支出和五通一平费用(70.5万元/公顷),政府可以获得697.8万元/公顷的收益。如果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就地入市来开发商品住宅,以成交价款的20%来计算,政府征收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为180.6万元/公顷①,而集体和农民可获得的收益为652.2万元/公顷(722.7万元/公顷减去五通一平费用70.5万元/公顷),集体和农民获得的入市收益是征地收益的4.8倍。可见,与征收农用地出让相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就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几乎相当于政府和集体(农民)的收益发生了对调②,集体和农民增加的收益恰恰是原属于地方政府的收益。这对于全国大多数城市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无法保障改革的平稳过渡。
综上所述,在城市建成区内开发商品住宅的潜力有限(主要是旧城改造和棚户区改造),而规划区外由于需求有限,也不是商品住宅开发的主要区域,规划建设区则成为商品住宅开发的主要需求区域。但是,规划建设区并未成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试验的首选区位,从三个试点地区的实践来看,进行商品住宅开发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大都位于城市规划区外的乡(镇)驻地所在村或中心村,其中泽州的入市地块均在城市规划区外,北流88.3%的集体商住用地分布在鄉镇地区。其原因就在于:规划建设区是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此进行试点改革对地方财政收入冲击很大,且改革会导致巨大的利益调整,利益关系较难平衡;而城市规划区外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区位优势不明显,入市后产生的增值收益有限,利益协调较容易,而且土地开发强度较低,安置补偿较容易,入市后建成的住宅也以附近村民购买为主,不会对城市房地产市场产生较大冲击。因此,规划建设区虽然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潜力最大的区域,但也是改革成本最大、收益平衡难度最大的区域,这也是试点地区尽量规避在此区域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试验的主要原因。
4.试点改革的关键: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土地制度改革是土地“权”与“利”在相关主体间的再调整,广西北流、山西泽州、河南长垣围绕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这个关键问题,通过平衡国家和集体的收益,兼顾集体、企业和政府利益,有效推动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的实践进程。2016年,财政部与原国土资源部印发《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税[2016]41号),规定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再转让环节,试点地区按照土地增值收益的20%~50%征收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由于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比例浮动空间较大,且不同区位的土地入市后增值幅度差距较大,试点地区主要通过控制入市土地区位和采用差别化的调节方式来实现收益分配在国家和集体间的平衡。
一是以差别化赋“权”实现“利”的平衡。区位和原用途是决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增值收益水平的重要因素。相同用途的土地,城市规划区内的价格要明显高于城市规划区外的价格;入市土地为宅基地,则涉及原使用权人的安置,入市成本相对较高,如果是耕地、闲置土地则成本相对较低。试点地区普遍选择城市规划区外的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来开发商品住宅,以避免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产生过大冲击;同时,入市地块以原居民点用地为主,将土地整治后规划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再进行就地或异地调整入市。对原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补偿,普遍采取房屋建筑面积按一定比例置换新房的方式。比如,泽州按房屋建筑面积1.1:1的比例置换新房,院落、厕所等附着物给予适当经济补偿;长垣按房屋建筑面积1:1的比例置换新房,宅基地按675元/平方米的标准对使用权人进行补偿。长垣的入市地块位于城乡接合部,原土地开发利用强度较高,对于原住户的补偿成本也较高。
二是以多元化土地增值收益调节实现“利”的平衡。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是国家分享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的保障,也是调节入市过程中国家和集体利益的有效措施。因区位、市场需求等的不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增值程度也不同,因而试点地区根据各自实际,在国家规定的征收范围内制定了差异化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标准:对于增值程度有限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的收取比例较低。泽州按成交价款的16%(2018年10月调整为50%)征收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土地受让方按成交价款的4%缴纳与契税相当的调节金;长垣按成交价款的20%征收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泽州的入市地块远离城区,入市后产生的增值有限;长垣的入市地块在拆迁安置成本较高的城中村,这些地块即使按照征收出让方式供地,政府也很难从中获得收益。而对于增值程度较高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的收取比例也较高。北流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总价款为基数,征收40%~50%的调节金、18%的增值收益平衡再分配金;同时,将商品住宅开发用地捆绑周边道路、公园等基建项目作为入市的附加条件,由用地人出资建设。北流的入市地块较多,有些地块拆迁成本较低,有些不需要拆迁安置,产生的土地增值较大,因而制定了比其他两地更高的增值收益调节金标准,并通过捆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来平衡政府收益。据不完全统计,已入市地块中,政府获得收益占净地价款的31%左右,加上轉嫁企业承担的基础设施配建费用,政府总收益比改革前降低约5%。
根据入市土地增值程度的不同制定差异化的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标准或捆绑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是平衡国家和集体间利益关系的有益探索。广西北流通过收取增值收益平衡再分配金、捆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来统筹平衡商品住宅开发与其他类型用地的收益,为更好地平衡国家与集体间以及各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有益尝试。
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面临的现实困境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的核心问题是收益分配,尤其是在规划建设区的收益平衡成为难点。试点地区在试点期间拥有制度改革的法律授权,可以进行大胆探索,包括:通过提高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标准、收取增值收益平衡再分配金、捆绑基建项目等方法调节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将相关规划没有覆盖到的入市地块视同符合规划,参照国有土地办理商品住宅建设规划、预售手续,等等。但随着试点工作的结束,一些试点期间的政策不再有效,面对未解难题,试点地区无法再自行出台政策进行探索,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不再具有制度优势。在国家没有出台接续政策的情况下,之前试点地区通过自行探索(未得到国家正式制度认可)解决的问题和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都成为下一步推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商品住宅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具体来讲,目前的主要问题有以下3个方面:
1.制度层面:政策导向不明、配套制度缺位及相关政策掣肘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属于新生事物,试点前后国家层面的政策都未明确集体土地能否开发商品住宅,阻碍了实践进程及配套制度的建立。
第一,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明确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但关于入市土地用途则沿用了试点期间的表述,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也没有对此进行细化。究其原因还是意见无法统一,故而采取了不主动碰触社会舆论敏感神经的策略,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也为下一步改革预留了空间。政策导向不明,直接影响了后续配套制度的制定出台。
第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随着试点工作结束而失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包含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的内容,并且针对入市成本难以核算的问题提出“可按照转移房地产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土地增值税”,但该法尚未出台,土地增值收益的调节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状态。
第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用于商品住宅开发办理后续相关手续存在障碍。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只为在国有土地上的房地产开发办理商品房预售和销售手续,而商品住宅预售和销售手续属行政许可,必须依法律条款规定来执行,这为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商品住宅办理预售和销售手续带来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也直接影响到后续抵押、登记等工作。
第四,建设用地的续期政策不明。长垣、泽州、北流三地在出让合同中注明续期政策参照国有土地,但由于国有住宅建设用地的续期政策尚不明确,土地使用权人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期望偏差可能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产生负面影响,亦可能留下纠纷隐患。
2.收益分配:国家与集体间需优化、集体与集体间需建立、集体与个人间需规范
合理分配土地入市后的增值收益是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的关键,但对于收益分配主体、比例和方式尚未形成普适性经验,在平衡国家、集体和个人收益关系方面,尤其如何平衡高增值区域的土地增值收益还有较大改进空间。
第一,国家和集体之间的收益分配比例有待调整。对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用于商品住宅开发等增值收益较高的用途,即使按照成交价款50%的标准来征收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对于很多地区来说,也很難与征收出让的收益实现大体平衡,这也是广西北流捆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原因。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因土地规划用途、区位不同,增值幅度差别很大,试点地区根据土地区位和用途制定不同比例的增值收益调节金缴纳标准,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如果试点工作要全国推广的话,是每个地方分别制定标准,还是国家统一标准需要提前思考。
第二,集体与集体之间的收益分享需要探索。调节金主要调节国家和集体之间的收益,并未涉及集体之间收益分配的调节。在土地发展权无偿配置的模式下,规划用途的限制意味着经营性建设用地能入市、公益性建设用地要征收、农用地只能维持现状,处理不好因用途限制导致的集体之间土地收益失衡,极易引发集体之间利益纠纷,直接影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的实施。
第三,集体和个人之间的收益分配需要规范。集体所获入市收益如何在集体和成员之间分配、使用,缺少统一的规范,容易诱发侵害农民利益的事件。
3.内部条件:规划等条件不具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高
《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实施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但从过去两年的实施情况看,除了上一轮改革试点地区外,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践的地区很少,入市用于商品住宅开发的更是没有。究其原因:一是部分地区尚不具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础条件。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符合规划并进行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才能入市。目前来看,国土空间规划处于编制阶段,缺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前提条件。二是现行的土地分类无法支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行商品住宅开发。《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中一级类“住宅用地”下仅有“城市住宅用地”和“农村宅基地”两个二级类。“农村宅基地”显然不属于经营性建设用地。2020年11月,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也仅涉及农村宅基地和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无集体土地上的商品住宅分类,致使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在规划审批、确权登记时存在技术障碍。三是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致使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流程设计[12],地方政府担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影响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和楼市去库存,也担心城镇人口到农村买房引发“逆城镇化”,缺少主动改变的勇气和智慧。以长垣为例,虽然对土地财政依赖度不高,但为防止冲击房地产市场、保障地方财政收入,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宅仅限于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区等。
四、推进集体土地用于商品住宅开发的路径选择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符合改革方向,对于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提高集体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积极作用,农民集体、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也有较强的需求。通过前文分析可知,争议的焦点和改革的难点在于收益分配问题,而试点地区的试验证明可以通过适当的规制来解决收益分配难题,因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也具有现实可行性。同时,试验在收益分配等关键问题的解决方面也积累了经验,为消除认识分歧、推进改革实践打下了良好基础。当然,由于试点地区的试验时间短、范围窄、案例少,尚未形成成熟的经验,认识上的分歧也未消除。实践是统一认识、解决分歧、推进改革的有效途径,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背景下,继续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试验尤为必要。由于政策导向不明,现实中存在多重障碍,地方政府较难自主推进此项工作,需要国家层面的适当干预与推动。
1.深化改革试点,为国家完善制度体系提供政策储备
按照试点先行的原则,部署新一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工作,将更多具备条件的地区(如土地财政依赖度低、楼市去库存压力小的地区)纳入试点范围,并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作为重点内容进行部署。授权试点地区为集体土地上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办理商品住宅预售和销售手续。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健全相关政策,逐步解决土地财政接替、入市收益分配、商品住宅建设管理等问题。试点期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应从城中村和城市规划区外逐步扩大到规划建设区,从存量集体建设用地逐步扩大到新增集体建设用地。鼓励试点地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在全域开展入市土地用于商品住宅开发的探索,丰富试点样本,完善试点政策,进而检验相关政策的适用条件、范围及普适程度,为国家相应法律法规的完善提供政策储备和实践参考。
2.建立科学的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增加改革试验的内生动力
在城市建成区和规划区外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增值收益比较容易调节,根据现行的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比例基本就可以实现土地征收转用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取得的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和集体之间分享比例大体平衡。在新一轮改革试点期间,对于规划建设区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建议:一是提高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比例(比如提高到70%甚至更高),或者通过入市土地捆绑配建基础设施等方式,提高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国家不再统一规定。二是通过镇域统筹或村级联合的方式促进集体之间合作入市,成本共担、收益共享,实现区域内入市土地开发商品住宅与建设基础设施所得收益大体相当,保障各类用地的供给。三是根据地方实际,采取收取集体间收益平衡金、土地发展权有偿配置、新增用地指标有偿配置等方式,实现同一区域内不同集体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的平衡。长期来看,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会通过税费形式收取,应同步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税法体系建设[14],按照国有土地房地产开发的税费构成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用于商品住宅开发的相关税费设置[1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中提出,按照转移房地产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增值税,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决定。这种方式充分考虑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方式、途径、用途等方面的差异,是比较可行[1]。在集体土地出让环节可以按照一定比例收税,在转让环节则采取超率累进税率,发挥土地增值税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作用,以此保障地方政府在放弃部分土地出让收入后实现财政收入的平稳过渡。
3.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保障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取得实效
一是加快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按照应编尽编的原则加快推进编制实施“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暂时没有条件编制村庄规划的,在县、乡镇国土空間规划中明确村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和建设管控要求,作为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依据。二是建立城乡协调统一的住房用地供应机制,依据定居人口数量供应住房用地,通过规划管控、计划引导实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有序入市,避免无序入市影响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17]。三是规范集体收益分配和使用,集体所获收益具体分配方式由村民自主协商决定,政府部门加强引导、强化监管。四是完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将住宅用地二级类分为城市住宅用地和农村住宅用地,农村住宅用地包括宅基地和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商品住宅,消除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在行政管理上的技术障碍。五是明确国有住宅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续期办法,并保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后处置方式一致。
本文对于社会比较关注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的收益分配以及实践中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探究,在实践与理论分析基础上论证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的现实可行性,并提出了改革的推进路径,但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由于前期试点政策不明确,试点地区的探索比较谨慎,案例相对较少,有些问题可能未充分暴露。二是对于收益分配主要针对初次入市,对于转让环节产生的增值收益如何分配以及集体是否应享受增值收益分配,由于没有案例,未进行研究。三是增值收益核算比较麻烦,试点地区普遍按成交价款的一定比例征收增值收益,未充分体现“增值”的分配关系。下一步,随着试点案例的不断丰富,应重点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转让环节的收益分配、增值收益核算以及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陆剑,陈振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的困境与出路[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12-122+159.
[2]刘亚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的进展、突出问题与对策[J].农村经济,2018(12):18—23.
[3]刘晓萍.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0:137-144.
[4]欧阳君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的政策逻辑与法制因应[J].法商研究,2021(4):46-58
[5]周广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用于商品房开发的法律问题研究[J].广州:东财经大学,2014:25.
[6]郑振源.重塑房地产市场保障人的城镇化[J].中国房地产业,2013(7):98-101
[7]贺雪峰.论土地资源与土地价值—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3):31—38.
[8]王小映.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收益的分配[J].农村经济,2014(10):3-7.
[9]吕丹,薛凯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的分配演化博弈:地方政府角色与路径[J].农业技术经济,2021(9):115-128.
[10]吴昭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试点总结与制度设计[J].法学杂志,2019(4):45-56
[11]岳永兵,刘向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探讨—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为例[J].当代经济管 理,2018(3):41—45.
[12]王玥,卢新海,贺飞菲.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政策选择研究—基于14个试点地区的政策文本分析[J].学习与实践,2021(5):79—87.
[13]魏来,黄祥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实践进程与前景展望—以土地发展权为肯綮[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34-42
[14]胡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的路径与法制保障[J].中州学刊,2014(5):68—72.
[15]岳永兵,姚国兴,黄洁.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进展、主要问题与建议[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4(11):27-30+65
[16]何芳,龙国举,范华,等.国家集体农民利益均衡分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调节金设定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9(6):67—76.
[17]余述琼,周小平,王军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用于商品住宅的改革探索与风险分析西壮族自治 区北流市的改革创新为例[J].改革与战略,2020(6):104—115.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Housing on Commercial Collective-owned Construction Land: Taking the Pilot Reforms of Beiliu in Guangxi Province, Changyuan in Henan Province and Zezhou in Shanxi Province as examples
YUE Yong-bing, LIU Xiang-min
(Chinese Academy of Natural Resources Economics, Beijing 101149, China)
Abstract: The commercial collective-owned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to develop commercial housing is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and a housing system with multi-subject supply, multi-channel guarantee, and encouragement of both renting and purchasing.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big controversy over whether collective land can be used to develop commercial housing, and in the pilot reforms of commercial collective-owned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fewer commercial housing development projects are involved, and related research also lacks in-depth discussion of its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pecific ope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periments of developing commercial housing on commercial collectively-owned construction land in three pilot areas, including Changyuan in Henan province, Zezhou in Shanxi province, and Beiliu in Guangxi province, and finds that the govemment, collectives, and enterprises can all profi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housing on collective land. The alignment of the interests of these three parties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innovation; most of commercial collective-owned construction l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housing is located in the village or central village where the township(town) station is located outside the urban planning area, and although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rea in the commercial collective- owned construction land is the area with the greatest pot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housing, it is also the area with the greatest reform cost and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in balancing the income, so it has not become the preferred location for the experimental test of developing commercial housing on commercial collective-owned construction land; by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collection standards for value-added income adjustment fees, bundling public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collecting value-added income balance redistribution fees, the pilot areas have basically achieved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among different entitie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ommercial collective-owned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to develop commercial housing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the direction of reform, but also has realistic needs, and can properly solve the problem of balance of interests through appropriate regulations.
The revision of the Land Administration Law has removed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for commercial collectively-owned construction land to enter the market, but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housing on collectively-owned land is affected by unclear policy orientation, a lack of supporting systems, imperfect incom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lack of basic conditions. Therefore,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commercial housing on commercial collective-owned construction land is stalled in practice. It is recommended to deploy a new round of pilot reform of commercial collectively-owned construction land into the marke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housing on commercial collectively-owned construction land as the key content of the pilot, encourage the pilot areas to gradually expand the experiment of developing commercial housing on commercial collectively-owned construction land from urban villages and urban planning areas to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reas, from existing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to new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actively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asonable value-added incom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relevant supporting policie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paper has expanded and deepened this study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 one hand, based on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est bal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form dynamic mechanism, pilot location selec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djustment of commercial collectively-owned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to develop commercial housing, and then demonstrates the practical feasibility of collectively-owned land to develop commercial hous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ercial housing on collective land ar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an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 of commerci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to develop commercial housing in pilot areas, this paper helps to eliminate differences in understanding, promote reform practice, and provide a policy reference for steadily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developing commercial housing on collective land.
Key words: commercial collectively-owned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commercial housing development; distribution of value-added income;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CLC number:F301.2;F293.31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1674-8131(2022)03-0098-11
(編辑:黄依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