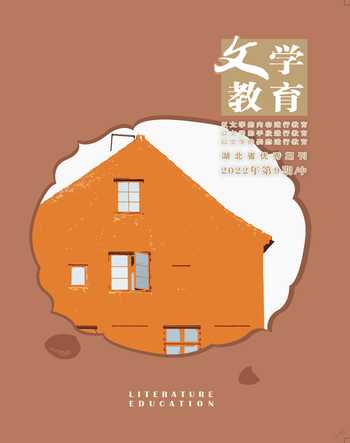《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的女性群像
2022-05-30赵淑琴
赵淑琴
内容摘要: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描绘了卫国战争中女兵们的群体形象,真实地再现了战争时期的女性生活。战争让女性遭受着精神撕裂、女性特征泯灭、母性分裂的苦难,这些痛苦直逼她们的精神极限。然而苦难并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消止,胜利的狂欢与痛苦的挣扎演示着生命的两极。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的女兵形象充分展现了女性的生存困境,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文化反思。
关键词: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战争 女性 苦难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第一部小说,也是其代表作之一。作者通过复调书写对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女兵遭受的苦难进行重新建构,500多位女性的口述实录,真实反映出百万苏联女性在卫国战争那些不为人知的经历,并从女性独特的视角去质问战争给女性所带来的苦难。总体上虽看似杂乱,但仔细阅读后会发现阿列克谢耶维奇其巧妙的构思,她将女兵们的回忆打碎、肢解、分裂到各个标题下,在用这些碎片化的记忆拼凑出一个完整的苦难历史。正如诺奖授奖词所说:“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与勇气的书写。”
一.卫国战争期间的女性
大部分的人们都认为战争是男性的,似乎那永远是男人的事情,男性是战争行动的主导,是享有主动话语权的一方,与女人们没有关系。但战争又绝对不允许女性走开,女权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指责:“我们的国家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内都视女人为奴隶,剥夺她的选举权、教育权、继承权和财产分配权,且一直将女性排除在缔造战争的决定过程之外,但当战事爆发时,国家又以民族大义之名征召女性主体参与战争履行义务”[1]而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女性也是如此,无一例外。
苏德战争早期,德军的闪电式袭击给苏联造成巨大损失,在社会资源以及兵力锐减的情况下,苏联国家政府颁布法令,征召16-45岁的苏联妇女加入战争的队伍。面对民族危难,国家号召,作为妻子、女儿、母亲的苏联妇女纷纷加入保家卫国的抗战中,这一刻她们是英勇的战士,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为战争的胜利奉献自己的一切。女性在战争期间是主要的参与人员,也是战争取胜的主要因素。战争结束后,关于卫国战争中女性形象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作家们竭力歌颂这些在战争中无畏的女战士,但是却有意的忽略掉或者说仅是简短的描述战争期间女性所遭受的苦难。而阿列克谢耶维奇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以自己新闻记者独特的视角,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竭力呈现出战争对女性的残酷蹂躏。在她的创作笔记中曾这样谈及写作目的:“我想写的是这样一本战争的书:让人一想到战争就会恶心的书,一想到战争就会产生反感、感到疯狂的书,要让将军们都会觉得不舒服的书……”[2]显然,她的目的达到了,苏联审查官这样评价此书“您却故意去表现战争肮脏的一面,见不得人的一面。在您的书中,我们的胜利是很恐怖的……”[3]因此,《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战争中那些被湮灭的女性苦难。
二.战时的女性苦难
1.精神的撕裂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战争是和男性具有紧密的联系,女人不应该出现在战争中。然而女兵们不仅和男兵一样要遭受身体上的磨难,在精神上也更加容易产生焦虑,难以走出其困境。“因为她们怀孕、分娩、哺乳,是最懂得一个生命的来之不易”。[4]她们参与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毁灭,残忍、血腥的战争让孕育生命的女性永远处于极端对立的状态。而这过程便是与女性特有的天性产生了冲突,与传统道德的观念发生碰撞,最终战争导致了精神上的撕裂。
在卫国战争期间,共有百万苏联女性踏上战场,与男兵们一起浴血奋战。但初上战场的她们便陷入了道德伦理的困境中,就像狙击手克拉芙季娅所描绘的:“我的双手不知怎么发起抖来,而且浑身都打开了寒战,产生了一种恐惧感。我怎么把一个活人打死了?我,杀死了某个与我素昧平生的人。”[5]这些在战争中往往很普遍的生死却成为女兵们难以抉择的困境,对于她们来说这是非常残酷的。关于女人杀人,阿列克谢耶维奇谈到:“女人是带来生命的,是奉献人生的。她们长久地在自己身上孕育着生命,又把这些生命抚养成人。所以我很明白,杀人,对于女人来说,是更加艰难的。”[6]孕育生命的女人不得已去残害其他的生命,而战争就是如此残酷,她把女人变得已经不是女人了。但是在国家大义面前,她们的枪不再颤抖,“一定是我们的伤员或者俘虏在这儿被烧死了,从那以后不管杀死多少敌人,我都无动于衷了,仿佛看到那些烧焦的五星帽徽……”[7]“许多年轻的女性一再申请到战场的最前线,因为她们要“亲自看到敌人死亡”[8]“颇具书卷气的老妇人忙着训练用小勺子向马路泼开水,因为“如果法西斯进了列宁格勒,走在我们的大街上,我就用开水烧死他们”[9]独自承受着生存困境带来的苦难,使得这些女兵与最开始的自我逐渐背道而驰,精神上的折磨与痛苦也让人们在战争的背后进行深刻的反思。
2.女性特征的泯灭
战争的世界是无法让人想象的,大部分男性可能都接受不了的艰辛,更何况是女性。女人爱美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是一种本能的心理需求,特别是在青春时期的女孩,那些枪林弹雨也不能阻止她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就像列兵诺娜抱怨的那样:“我是准备在军队建功立业的,但没有料到三十五码的小脚却要穿上四十二码的鞋,那么沉重又那么丑陋。”[10]
“请给我武器,我想要上战场……”这俨然已成为上战场前那些女性必定会说出的话,我们也知道,她们并不害怕战争,她们也并不柔弱,她们也不是楚楚可怜的女子,她们只是想用自己的双手来捍卫祖国的土地。当那些男人一个一个上了战场,她们也忍不住走上前线去,虽然不是每个女人都手拿武器上战杀敌,但她们都在为祖国的统一共同抵御外敌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她们有的当了护士,有的当了通讯兵……她们几乎掌握了那些“男人”的岗位:狙击手,机枪手,高炮手,她们用自己的实力诠释了什么是“巾帼不让须眉”,有力的回应了那些曾经质疑她们什么也不能干的男兵们。在国家危难时刻,面对祖国的号召,这些女人毅然决然的放弃裙子放弃鞋子放弃那些美好的原本属于她们的东西,和男人一样勇上战场保家衛国。
女兵们在战场上勇敢的追求属于自己的美丽,追求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并没有吓退她们,她们不害怕死亡,她们怕的是丧失这些美好的那样死去,追求着美但却因为美丧命。她们偷偷的将裹脚布、男性的军大衣改制成围巾、内衣、裙子,在战争的空隙里会给军大衣绣上花;白天穿军筒靴,晚上偷摸着穿高跟鞋、化妆、戴着耳环睡觉;射手工兵排长斯坦尼斯拉娃用好不容易得到的两个鸡蛋洗干净了她的大靴子,因为“当然我也想吃,但是女人爱美的天性占了上风”[11]但是,这一切却被扼杀了,当指挥官发现时,不仅不理解,反而严厉地批评了她们:“你们是来打仗还是跳舞来了?我需要的是战士,而不是淑女名媛。美女是在战争中活不下去的。”[12]让德国高级军官都震惊惧怕的狙击手萨莎牺牲的原因是在雪地单独执行任务时戴着她最喜欢的红围巾暴露了自己。在后勤工作中,女兵们不仅要做繁重的清洗工作,甚至被要求像男人一样运输超重的物资。在长期的艰苦生活中,紅润的脸颊被冻黑;秀丽的长发被剪掉;穿着冗大的鞋子穿梭于战前与战后;像男人一样战斗,她们一切按照男性的标准生活,女性特征、身份早已被男性身份所取代,狙击手拉芙季娅在采访中说到,“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女性气味,所有女人都男性化了。战争就是男子汉的味道。”[13]
3.母性的分裂
西蒙娜德波伏娃指出:“只有通过身为母亲的经验,女性才能实现身体的命运;这是她的‘自然召唤,因为她整个的有机结构是为繁衍种族而设计的”。[14]母性是女性的天然属性,其真善美的象征,代表着仁爱、牺牲、温柔等人类崇高的品性。母亲保护孩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这股强大的力量任何人都无法预估。然而当这股真挚、理性的情感面对民族大义时,却发生了彻底的分裂。
在卫国战场上,少尉柳鲍芙因为“爆发了战争,老公上了前线……就去做了流产,周围都是哭声和眼泪,叫我怎么生孩子!可恶的战争!在死亡中间怎么生育”[15],她不想在哭声、眼泪和死亡中生育;游击队联络员玛利亚为了掩护自己她“为了宝宝热得哭出来,就用盐揉搓他。他全身都被搓红了,像生了皮疹一样”[16]刚刚才生下孩子不久的游击队员为了帮助队友躲避德军的围剿,“用布把孩子包起来,侵入水中,一动不动地坚持了很久……孩子不再哭了,没有一丝动静了,可我们谁都不敢抬起眼睛,既不敢看那位母亲,也不敢互相看一眼。”[17]这些女兵们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母亲对子女应有的保护和爱惜,母性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失去了其本性,甚至被无情的践踏。她们在血缘亲情和政治伦理的困境中难以抉择,陷入了无尽的苦难之中。
4.非此即彼的生存困境
“在战争中,不管是对个人爱欲的寻求,还是对民族大义的追索,它们都有着合理、正义和神圣的一面,都体现为一种伦理理想,但它们又都是片面的,对其中任何一种伦理理想的选择都会损害另外一方。”[18]面对国家危难,在伦理道德困境的斗争中,所有参与战争的女性无一不选择了民族正义,牺牲个人利益来成全国家大义。然而,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进行的选择对她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伤害,这种伤害来源于她们面对困境具有伦理的合理性,但任何选择都不能弥补她们失去的另一面。在她们枪口瞄准敌人的时候,把双手伸向自己孩子的时候,忘记自己是女人的时候,这一幕幕都成为了她们日后难以抹去的梦魇。虽然这种痛苦在男性身上也会发生,但由于“女性独有的母性以及具有女性伦理的情感维度,需要在极端情况下作出选择的也更多,造成的痛苦也自然更加深远。”[19]一方面,她们当然爱自己,自己的孩子或其他的生命,但另一方面她们又不愿意背弃民族大义,祖国使命,而最终就只能牺牲个人爱欲的一切行为,给自己造成永远不能补偿的痛苦。
三.战后的苦难延续
在战乱环境下,女性经历苦难并能够超越苦难,因为被承诺了一个未来——女性自由和解放的未来。面对敌军的强烈进攻,苏维埃政府向苏联女性发出了征召法令,希望她们能在国家危难时刻奉献自己的力量,而这也是政府对女性的一种承诺——女人也享有和男人同样的权利和自由。正是这样的“国家承诺”,她们纷纷踏上战场,在“男女平等”的口号“敌后苏维埃儿女挺身而出吧”的温柔陷阱中,一步一步的走向深渊的苦难。她们像男人一样去建功立勋,把个人融于国家民族大义之中,她们为自己像个男人一样为国家战斗和牺牲而自豪,她们甚至不喜欢战场上男兵对自己的怜香惜玉,“所有人都对我们怜香惜玉,这使我们感到很委屈:我们不喜欢别人怜悯。难道我们不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战士吗?”[20]战争结束了,男人也回家了,那姑娘们又该去向何方?苦难过后就一定是曙光吗?
从战争上活着回来的女兵们的生活似乎比战前还要艰难,“这个社会依然只是男人的,所以与战争有关的叙述与书都主要是有关男人的”[21];男性还是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战争和胜利也只属于男人,甚至她们都不能让别人知道她们曾经上过战场,所以妈妈才会反复的劝诫:“别说话别出声!不要承认自己当过兵啊”[22]。最终,她们还是自己孤苦伶仃的扛下了这一切,“那时的姑娘们现在几乎都是孤独一人,单身未婚,居住在公共宿舍里”[23],没有人会可怜她们,当然也不会有人记住她们。国家对女兵们的承诺终究敌不过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统治,就像李小江所说:“不管她在战争中曾经怎样勇敢或怎样有所作为,婚姻还是最终决定了女人的身份、境遇和历史评价……即使在非正常秩序下的战争时代和革命队伍中,女人的社会身份和人生道路,仍然更多地取决于传统社会男性中心的意志,而不尽是她的自然命运。”[24]本该是光辉的英雄经历成为了她们的罪孽和耻辱,“从前线回来的姑娘被在战火中相恋四年的男友抛弃了”,因为“他看到的她总是穿着一双破靴子和男人的棉衣”,因为“经过与死神擦肩,谁都想追求美丽和优雅”[25],没上过战场的女性对参战回来的女性大声破骂,“我们知道你们在前方干的那些事!……前线的婊子!穿军装的母狗……”[26]丈夫会责备上过战场的妻子,“难道正常的女人会去打仗吗?会去学习开枪嘛?所以你都没有能力生下一个正常的孩子”[27]。
苦难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历史和宿命,世界上那些动人的给人以留下深刻印象都是悲剧,都是对于苦难的诉说;那些最优秀的作家都是十分关注人类苦难的作家。俄罗斯天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苦难折磨到精神失常,但他却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28]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苦难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了一种令人骄傲的资本与经历。但反观这些从战场上回來的女人们,她们经历了苦难之后得到的是什么?没有苦难之后的彩虹,更多的是苦难之后的沉重。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后记中说到:“在绝对男性的世界中,女性站稳并捍卫了自己的地位后,却为什么不能捍卫自己的历史,不能捍卫自己的话语和情感?女性的战争仍旧没有为人所知。而我就是想写这个战争的故事。女性的故事。”[29]她用自己手中的武器重新探讨了卫国战争中女性的遭遇,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一直被伤害的不仅仅是男人,还有同样在战争中英勇无畏的女战士们,在作者的真实记录里读者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些女性群体形象的无尽苦难。作者希望借此来重新审视这个时代的女性地位,控诉这种不平等的现象,让更多的人们关注这个时代中女性的生存和命运,也让读者们深刻的意识到战争带来的巨大危害。
注 释
[1]毕媛媛,林丹娅:《无处安放的女性身体:解读抗战叙事掩盖下的性别表述》.职大学报,2014,(2):1-7.
[2][3][5-13][15-17][20-23][25-27][29]S.A.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吕宁思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414,413,8,416,8,156, 119,60,223,221,296,42,48,429,6,405,409,128,86,295,297,406.
[4]刘俐莉:《战争语境下的女性苦难与成长》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22.
[14]雷霖:《现代战争叙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18]雷霖:《中国现代文学抗战叙事中的冲突女性》.求索,2016,(6):145-147.
[19]李玉:《从<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论战争语境下的女性苦难》.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7):41-42.
[24]李小江:《亲历战争:让女人自己说话》.读书,2002,11.
[28]孙雪森:《从俄罗斯宗教哲学看俄罗斯人的苦难情结》.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2):3-11.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