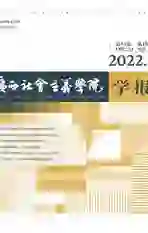器以载道:中国古代铜鼓上隐含的族群文化
2022-05-27李富强方少聪
李富强 方少聪
关键词:铜鼓;南方族群;文化变迁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2.01.012
[中圖分类号]K8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2)01-0077-10
铜鼓是历史悠久的重要文物。现有资料表明,铜鼓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滇西至滇中一带[1],而后逐渐广布于中国南方,至今依然为一些少数民族所传承和崇尚。《易经》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2]其实,从器物学的角度而言,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器”是形式,“道”是内涵。所谓器以载道,即以器物的器型和纹饰等表达造物者的所见、所闻、所思和所想。因而,铜鼓之上也承载着铜鼓铸造者的“道”,即文化意涵。通过研究南方所发现的铜鼓,可以解读其所呈现的族群文化。
一、中国古代铜鼓所表达的宇宙观
造鼓的初衷是要模仿雷声。《周礼·夏官》:“辨鼓铎镯铙之用。”《疏》称:“鼓,雷之类。”[3]之所以要模仿雷声,是因为要以铜鼓祈雨。为了实现此功能,需要铜鼓的形制和纹饰予以配合。从形制来看,铜鼓由鼓面、鼓胸、鼓腰、鼓耳和鼓足组成。不论是何种类型的铜鼓,鼓面大都饰有太阳纹,哪怕是最原始的万家坝型铜鼓,鼓面窄小,大部分光素,但一般都在鼓面中心处饰有太阳纹,而在万家坝类型鼓之后产生的各个类型铜鼓鼓面上,除太阳纹外,还有翔鹭、青蛙等纹饰,这是对当时人们心目中天上景象的描绘。鼓胸、鼓腰和鼓耳部位,其纹饰有船纹、羽人纹等,多是对人间自然环境、生产生活状态的描绘;鼓足部位大多光素或有水波纹,则是对地下世界的描绘。可见,整个铜鼓的形制就是主人心中的宇宙:鼓面象征天上的世界,鼓胸、鼓腰象征人间世界,鼓足象征地下的世界。
铜鼓形制所隐含的宇宙观,与作为中国南方古越人后裔壮侗语民族的神话传说相互印证。壮族麽经《布洛陀》有云,古老古老的时候,天地没有分家。先是宇宙间旋转着一团大气,那大气渐渐越转越急,转着转着,转成了一个大圆蛋。大圆蛋有三个蛋黄。后来大圆蛋爆炸开来,三个蛋黄分为三片,飞上上边的一片成了天空,降下下面的一片成了海洋,落在中间的一片成了大地。天地分成三界,上界由雷公管理,中界由布洛陀管理,下界由龙王管理[4]。铜鼓是这种原始“三界观”影响下的产物。
尽管铜鼓形制和纹饰表现了宇宙的“三界观”,但由于铜鼓是当时人们祈雨的神器,因而其表现的重点是天界和人间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型的铜鼓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和丰富的过程。万家坝型铜鼓比较原始古朴,纹饰简单,鼓面仅有太阳纹,有的有光体无光芒,有的有光芒,但芒数不定;其鼓胸、鼓足多通体光素无纹,鼓腰常是几条纵线划分成几个空格,这表明当时人们对天界和人间的认识是比较简单的。战国至东汉时期的石寨山型铜鼓,鼓面、鼓胸、鼓腰和鼓足的纹饰则丰富了起来。象征天界的鼓面除太阳纹之外,还有云雷纹、翔鹭纹等。象征人间的鼓胸、鼓腰除了几何纹之外,还有船纹、羽人纹等。这表明人们对天界的认识丰富了、生动了,人们在自然界中自我主体性较之前鲜明了。自东汉时期起,冷水冲型铜鼓、遵义型铜鼓、北流型铜鼓等鼓面出现了青蛙塑像或青蛙纹。青蛙之所以出现在“天界”,是因为古人发现 “青蛙闹,雨水到”的规律,青蛙具有“预报雨水”的能力,人们认为青蛙与管理雨水的“雷王”有密切的关系,是从“天界”被派下人间,沟通人间与“雷王”的使者。壮族是自古至今都铸造、使用和崇尚铜鼓的民族,不少人认为青蛙(即红水河流域壮族所称的“蚂拐”)是掌握雨水的雷王的女儿, 广西东兰一带每年仍过蚂拐节,敲击铜鼓,祭祀蛙婆,以求风调雨顺[5]。至于宋代至清末的麻江型铜鼓,除了太阳纹仍出现在鼓面之外,鼓面、鼓胸、鼓腰的纹饰界限模糊了,常见的云纹、雷纹、同心圆纹等纹饰,以及龙、鱼、花、鸟、人物、房屋、十二生肖、鹤纹、符箓纹、八骏图、兽形云纹、游旗纹等,既可以出现在鼓面,也可以出现在鼓胸和鼓腰。这说明由于受汉文化影响日深,龙作为外来的、具有布雨神力的神奇动物,被吸纳进来,替代青蛙发挥布雨的功能,而十二生肖、鹤、骏马、鱼等汉族视为祥瑞的动物也被整合到了铜鼓主人想象的世界里,成为铜鼓主人宇宙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人们越来越清晰地以人间想象“天界”,象征天上的鼓面与象征人间的鼓胸和鼓腰纹饰所描绘的景象趋于相似。
二、中国铜鼓所叙写的社会生活
(一)生境与生计模式
铜鼓纹饰多有对中国南方自然环境与生物的刻画,展现了一个多物种和谐共存的生境。这些刻画当中最典型的生物当属青蛙,青蛙塑像大量存在于除早期的万家坝型铜鼓、石寨山型铜鼓与晚期麻江型铜鼓以外的所有类型铜鼓上,是求雨信仰的产物。其中,以冷水冲型铜鼓的青蛙塑像最为精致写实,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西南所常见的华西雨蛙(Hyla annectans)[6]。北流型铜鼓、灵山型铜鼓等鼓面的青蛙塑像虽流于装饰化、刻板化,而 “累蹲蛙”大量涌现,二至四只青蛙相叠负,颇有奇趣。在一些例子中,与青蛙塑像相伴出现的还有田螺塑像。如属于冷水冲型的广西博白22号铜鼓鼓面上,就有三只青蛙背负小蛙,另外三只背负田螺。除此之外,铜鼓上的动物塑像还有牛、马、虎、豹、穿山甲、鸭、鸠鸟、龟、鱼、蟹等。其中,牛塑像与马塑像较为常见,多见于冷水冲型铜鼓,点缀于青蛙塑像之间。冷水冲型铜鼓的牛塑像身躯浑圆,牛角粗横,是典型的南方水牛(Bubalus bubalis)。可与之对比的是云南石寨山型铜鼓常见的牛纹,牛角向上弯曲而颈后有瘤峰,是典型的南亚瘤牛(Bos taurus indicus),常见于古滇国铜器。冷水冲型铜鼓的马塑像较牛塑像粗糙,头大身小,比例不太协调,往往伴有骑者塑像。马塑像之所以看似不协调,原因有二:其一是马的形象出现于铜鼓,直到汉代才常见,百越先民较少接触马匹,因此在刻画上未能惟妙惟肖;其二是《汉书注》提到“汉厩有果下马,高三尺”[7],《岭外代答》称西南地区出果下马,或“健而善行”,或“短项如猪”[8],铜鼓上的马塑像身量矮小,头颅硕大,或与果下马有相当的联系。牛马以外,铜鼓的鸭塑像也值得留意。岭南、西南地区养鸭历史悠久,广西贵港汉墓曾出土铜鸭模型,可知在广西地区,汉代已开始养鸭。时至今日,广西壮族人民不但擅于养鸭,更形成了喜食鸭、中元节以鸭为牺牲的文化。在属于冷水冲型的广西桂平新燕村铜鼓上,青蛙塑像之间有孩童戏鸭的塑像,一个椎髻孩童怀抱惊慌的小鸭,母鸭在后追赶,栩栩如生[9]。学者认为该鼓年代在晋代至南北朝之间,当为壮族先民乌浒人或俚人使用[10],对了解其时南方族群的生境与生产有重大价值。
如果说铜鼓塑像中最常见的生物是青蛙,那么铜鼓纹饰中最常见的生物便是鹭鸟。翔鹭纹普遍存在于石寨山型铜鼓上,在之后的冷水冲型铜鼓上变形为抽象的几何纹。石寨山型铜鼓鼓面多饰有一圈翔鹭纹,相当写实。鹭鸟喙部长而尖,有时叼着一尾小鱼,脑后有细长羽毛形成羽冠,其颈部细长,双翅呈窄小三角形,展翅翱翔,初级飞羽飘扬,尾羽呈扇形。铜鼓上的翔鹭数量多为偶数,从四只到四十只不等,逆时针围绕铜鼓中心的太阳纹飞翔。根据翔鹭纹的种种特点,可以猜测所刻画的是苍鹭(Ardea cinerea),今天在南方诸省的水泽地带还能够看到苍鹭。除了翔鹭纹,鹿纹也出现于石寨山型铜鼓,多处于鼓腰而环绕铜鼓。以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出土的280号铜鼓为例,鹿纹与舞人纹相对,共十二组,每组二至三只鹿,昂首张口而立,鹿角硕大,身体遍布圆斑,四足修长,每组都有一只雄鹿,生殖器突出。雌雄鹿皆生大角,在鹿科动物中唯有驯鹿,然而驯鹿并不生存于亚热带地区,制鼓者或是出于美观而为雌鹿加上了鹿角。根据鹿纹周身圆斑的特点,可以推测这是斑鹿(Axis axis)或梅花鹿(Cervus nippon),两个物种的野生种群现在已从中国南方消失,但不能就此认为它们从不曾生活于南方,在桂林甑皮岩遗址就曾发现过大批梅花鹿的骨骼。
相比于动物,铜鼓的植物塑像或纹饰出现较晚,种类也较少。属于冷水冲型的桂平12号鼓鼓面上,有三株花树塑像,是冷水冲型铜鼓植物塑像的唯一一例,树干粗壮,树顶端开放四瓣的硕大花朵,难以判断是何种植物。流行于宋代以后的麻江型铜鼓鼓面背后,一部分刻有风俗图案,常见蔓草缠枝,多为阔叶植物,如桑、莲、兰等,是受汉文化影响的产物。
铜鼓叙写了一派生机勃勃的亚热带景象,河流纵横,百兽出没,花树盛放,同时也叙写了稻作文化下活跃的农业生产活动。越人等南方族群种植水稻的历史极为悠久,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邻近广西的湖南玉蟾岩遗址发现距今1.2万年的碳化水稻壳,说明古代越人或为最早种植水稻的人群之一[11]。稻作农耕对南方族群影响深远,从衣食住行到族群深层心理均有表现,铜鼓也不例外。铜鼓纹饰中的太阳纹、云雷纹、翔鹭纹、蛙纹、牛纹等都与稻作文化相关,种植水稻需要充分日照、充足降雨以及用牛来耕作,也需要向青蛙、鹭鸟等灵性生物祈愿风调雨顺,铜鼓纹饰就是稻作文化心态的直观表达。
从铜鼓纹饰与塑像,能看到清晰具象的诸种农业用具、农业建筑与农业设施。根据考古材料,岭南、西南部分地区在汉代开始出现牛耕,其技术由中原传入。于南方各族而言,牛是耕作的需要,也是财富的象征。许多石寨山型铜鼓的腰部,能看到昂然威武的牛纹。在属于冷水冲型的广西平南白坟坪铜鼓鼓面上,有三组水牛塑像,其中一头水牛背上有一人骑坐,当是牧牛者,可知这些牛已被驯化。在前文提到的桂平新燕村铜鼓上,除有一组儿童戏鸭塑像外,还有一组人牛播耕塑像,水牛牛鼻穿有鼻环,环系粗绳,驾牛人左手腕缠绕牛绳一端,颈部挂有半球形篓,右手控制篓孔,这是对驾牛耕播的写实,反映了其时南方族群熟练的耕作技术[9]。粮仓也在铜鼓上有所展现,如属于冷水冲型的广西平南1304号鼓,鼓面除青蛙塑像外,有一组牛塑像与一组干栏式粮囷建筑模型,两座粮囷顶部圆而尖,由一座四足地台支撑,其结构具有浓厚南方特色,通风防潮,颇富智慧。南方各族常与水泽打交道,不但精于种植业,也长于渔业。属于冷水冲型的象州大普化村铜鼓鼓面上有两条大鱼的塑像,二鱼尾部相连,被粗绳系在一根立柱上。同属冷水冲型的瑞士丽特贝格博物馆藏RCH22号鼓鼓面上[12],刻画了两条比人还长的大鱼,鱼尾后有一人双手合于胸前拉一物,物已残坏,或为渔网[13],此人身后是一个釜状器,另有一人持物伸向釜状器。这组塑像对捕鱼、烹鱼的刻画生动表现出古代南方族群的渔业技巧与喜鱼食俗。
宋代以来的麻江型铜鼓所叙写的农业风貌更为具体,在与汉族农耕文化越来越接近的同时仍能保持自身特色。麻江型铜鼓,尤其是清代广西西部、北部的铜鼓,鼓面人物纹多为农夫形象,有荷锄者,有荷耙者,短衣束带,长裤赤脚[14]212,已不再是早期铜鼓上发椎髻、衣披风的形象,与汉人农夫无异。与这些劳动者形象相伴的还有符箓纹与家畜纹,寓意吉祥。前文提到一部分麻江型铜鼓鼓面背后刻有风俗图案,它们被学界称为铜鼓“风俗画”,内容大多复杂,包括建筑、田园、人物、家畜等各类乡村事象。以闻宥《古铜鼓图录》第二十一号鼓为例[15],刻画了凉亭、鱼塘、禾晾、谷仓等建筑,建筑物之间有谷堆,有犁耙,有牧牛者也有骑马者,有荷担农具者以及家畜,两组缠枝纹围绕着建筑與人群,可谓生机盎然。其余的铜鼓风俗画大体与之相似,人物穿梭于凉亭、禾晾、谷仓之间。这些建筑物带有壮侗语民族特色,与早期铜鼓上表现的晒台、粮囷等建筑,形制一脉相承,是村庄农业的重要象征。这些铜鼓图像为我们提供了明清以来广西等地农业与村社风貌的重要记录,其特殊性不亚于古滇国贮贝器器盖上的塑像,很值得学者留意。
(二)交通与交流
《淮南子》云“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16],《越绝书》称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17]43。古代南方的越人善于使舟、制舟,舟船是极其重要的交通工具,江苏武进淹城遗址出土的周代独木舟,足可证明越人舟船文化历史之悠久。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南方青铜器上,屡见舟船纹饰,其中展现得最为丰富而集中的,莫过于铜鼓。带有船纹的铜鼓基本属于石寨山型。广西贵港罗泊湾一号西汉墓出土的M1:10铜鼓,鼓胸有对舟船的细致刻画,共六条船,船型狭长而首尾翘起,首尾呈鸟头鸟尾状,船身有多组竖纹,有学者据此认为是双身船之间的横梁[18],也有学者认为是水密舱壁[19]。每条船坐有六人,皆裸身,戴羽冠或脑后挽髻,靠近船头者手执羽杖,似为指挥者,后四人划桨,最后一人操梢。船纹以外,还有鹭鸟、乌龟、游鱼等图案。前文提过的西林280号铜鼓,鼓胸部有六组船纹,船型首尾高翘,翘起幅度较M1:10鼓船纹更大,首尾同样呈鸟头鸟尾状,船身遍布圆点,船中后部有一插羽栅台,台下有鼎状器。每条船人数在八到十一人之间,头戴羽冠或脑后挽髻,其中一人坐于栅台之上,似为指挥者,其余有跨坐船头者,有执羽杖起舞者,有划桨者。除上述两面铜鼓以外,云南的广南鼓、开化鼓、部分晋宁鼓的鼓胸都能看到类似的船纹,这些船有共同的特征,船身窄长,首尾翘起而装饰成鸟形,船大者能载十数人,能放置双层栅台,与中原舟船有很大差异。
关于铜鼓船纹的属性,学界长期存在争议。法国学者戈露波引印尼婆罗洲达雅克人的“黄金船”神话,认为船纹是丧仪上的送魂船[20];越南学者陶维英认为船纹是铜鼓使用者对祖先航海记忆的保存[21];龙村倪、陈凤梅等学者则认为这些船纹表现的是越人的航海船只[19] [22];李昆声、黄德荣总结铜鼓船纹,将之分为渔船、交通船、战船、祭祀船、竞渡船、游戏船、海船七类[23]。这些观点或证据不足,或过于宽泛,我们认同蒋廷瑜、汪宁生等人的观点,铜鼓上的船纹是竞渡习俗的写照[14] 212、[24]。可对比现代西双版纳傣族的竞渡龙舟,窄长而首尾高翘,与舟船图案如出一辙。仔细观察船纹,船身单薄且无帆无舵,载重量小,不适合航海,有学者将船身竖纹解释为利于航海的水密舱壁其实是对图像的误读。另外,船上的人头戴羽冠,更有手持羽竿者,正是竞渡之时的穿着。晋代《风土记》记载吴越地区于端午有竞渡活动,宋代《溪蛮丛笑》称五溪蛮对端午“爬船”竞渡最为重视,古代南方族群有龙舟竞渡习俗,娱神娱人,视为大事,因此将之刻画在铜鼓之上,这是不难理解的。竞渡之舟的制作远比普通的独木舟复杂,从这些细致写实的船纹我们足可想见越人、濮人高超的造船技艺。
《史记·夏本纪》载,“水行乘船,泥行乘橇”[25] 6。在冷水冲型铜鼓之上,我们发现了一些牛橇的塑像。所谓牛橇,是一种以牛牵引的交通工具,形制有些像北方的爬犁,似车而无轮,能载物,便于泥泞地带的交通,今天海南岛的黎族仍在使用类似的交通工具[26]。20世纪50年代征集于桂平的103号鼓,鼓面上的水牛身体两侧各有一条辕木,前端有轭联结套于牛肩,后端拉有一橇架,架上放置一篓筐,架下装有木脚,当用以停靠牛橇。桂平12号铜鼓鼓面上亦有牛橇,架构相似,橇架上也放置一篓筐,牛背上骑人,可知在行进时人并不坐在橇架上。南方多雨,地多泥泞,人行、畜行固然不便,车行也容易轮陷泥中,牛橇则因地制宜,制造简易,是古代南方族群对交通工具发明的一大贡献。
除了独特的舟船与牛橇,人们也乘马出行,冷水冲型铜鼓鼓面上多有骑乘塑像,形象质朴。汉代的岭南、西南地区,随着与中原交往日渐频繁,马匹也变得常见。桂平福山村鹤岭铜鼓有婢女喂马塑像,贵港万新村铜鼓上的骑乘者身后背着小孩。从这些生活化的场景,可知在当时的南方,马匹已用于日常交通。在宋代以后的麻江型铜鼓中,一些出自桂西的铜鼓鼓面上有奔马纹,这与南宋时邕州横山寨的马市贸易或有一定关系,马匹在宋代以后的南方社会已是常见的畜力运输。
(三)信仰与祭祀
《史记·孝武本纪》云“越人俗信鬼”[25] 88,越人、濮人等南方各族俗信巫鬼,而铜鼓是他们的仪礼重器,只有在祭祀、仪式时才使用,其形制与纹饰本身便是古代南方族群世界观、宗教观的具象化呈现。许多学者讨论过铜鼓与南方族群信仰之联系,更有学者提出铜鼓实际是萨满教的法器[27]。尽管今天的铜鼓使用者往往难以道出各种纹饰的具体含义,但在早期的铜鼓设计与制作中,纹饰具有很强的宗教象征意义,反映了古代南方民族万物有灵的信仰世界。
铜鼓最核心的纹饰是居于鼓面中心的太阳纹,在绝大多数的铜鼓上都可发现,已知最早的铜鼓——万家坝型M23:159号鼓,鼓面上有八芒的太阳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铜鼓,太阳纹并不相同,光体大小不一,芒数从六道到十六道不等,但基本结构大致相似。太阳纹反映早期南方族群的太阳崇拜,而这种崇拜与稻作文化息息相关,对于农业发展迅速的早期社会来说,没有先进的农业技术,阳光与雨水尤为重要,容易发展出太阳崇拜。
与太阳纹相伴出现的是翔鹭纹,常见于石寨山型与冷水冲型铜鼓,鹭鸟围绕鼓面中心的太阳纹作飞翔状。对于翔鹭纹可有三种理解,即作为太阳神鸟的翔鹭,作为“鼓精”的翔鹭,以及作为“魂鸟”的翔鹭。首先,古人将鸟视为阳性的动物,与太阳相联系,如《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28]。为何太阳崇拜会与鸟崇拜相结合?因为两者皆对稻作生产产生重要影响,传说越人先民曾依靠鸟群耕作,即所谓的“鸟田”。《越绝书》云:“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17] 42人们祈求稻米丰收,故将对太阳与鸟的崇拜结合为“太阳神鸟”。无独有偶,同属稻作文化区的古蜀国,也出现了表现“太阳神鸟”的文物,如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箔。其次,鹭鸟与鼓有悠久的联系,早在春秋鲁僖公时期的《诗经·鲁颂·有駜》载有“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29]。《隋书·音乐志》更提到“鹭,鼓精也”“饰鼓以鹭,存其风流”[30]。战国楚墓有一类独特乐器“虎座鸟架鼓”,学者认为所谓“鸟架”其实是“鹭架”[31]。无论是中原还是荆楚,都有着饰鼓以鹭的传统,这或与“鹭为鼓精”的神话存在联系,当这种传统传播至岭南、西南,便诞生了铜鼓上的翔鹭纹。最后,在原始宗教中,鸟因其飞翔的能力而被视为沟通天地的神奇动物,是超越人间力量的强者[32]。有学者认为铜鼓上的翔鹭实为“魂鸟”,具有引渡灵魂的作用[33],是巫师的助理精灵[34]。综合这几种理解,翔鹭纹的信仰内涵极其独特而丰富。
铜鼓鼓面上常见的青蛙塑像,也表达了古代南方的独特信仰。前文讲过,青蛙与稻作文化有很深联系,因为蛙鸣是降雨的前兆,青蛙被神化为蛙婆。青蛙除了特殊的召雨能力外,也因其繁殖力强而被视为神奇动物。铜鼓上的累蹲蛙,小蛙叠于大蛙之上,正如体型小的雄蛙在交配时跨骑于体型大的雌蛙之上,累蹲蛙形象能夠使子孙繁昌,作物丰收,还能诱发降雨[35]。不过,如果将累蹲蛙解释为交配蛙,则难以解释铜鼓常见的三蛙、四蛙累蹲。但无论如何,青蛙崇拜是南方族群最重要的信仰之一。青蛙在越人的观念中还是勇气的象征,《韩非子·内储说上》云:“越王勾践见怒蛙而式之。御者曰:‘何为式?’王曰:‘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乎?’士人闻之曰:‘蛙有气,王犹为式,况士人有勇者乎!’”[36]越王勾践致敬怒蛙的勇气,士气大振。在属冷水冲型的广西武宣1号铜鼓上原有两座观蛙台塑像,现存一座,方台之上四角各有一只头朝桌子中心的青蛙,四蛙相对,似乎跃跃欲斗,诚是“蛙有气如此”。方台一侧站立二人,其中一人背着小孩,都注目着台上斗蛙,生动地叙写了古代南方人民对青蛙的喜爱与尊敬。
铜鼓不但表达了丰富的泛神信仰,还细致刻画了各种祭祀场景,是我们了解古代南方族群宗教生活的一扇宝贵窗口。最典型的祭祀场景是羽人舞蹈纹所反映的集体祈年。羽人舞蹈纹常见于石寨山型铜鼓,在冷水冲型铜鼓上则简化为几何纹饰,舞者多头戴羽冠,上身赤裸,下身着长裳,双手做各种动作,或持羽杖,或执武器、乐器,模仿鹭鸟的姿态而群舞祈年。在罗泊湾MI:10铜鼓上,除了鼓胸的羽人划船纹,鼓腰的羽人舞蹈纹也十分精彩。舞人八组共二十人,每组二至三人,脸部朝向同一方,手臂向左右伸扬,上半身向后倾斜,双腿迈开,姿势优美,舞人头顶有衔鱼鹭鸟飞过。舞人中有一人戴蕉叶状羽冠,与他人不同,当是领舞者。同样类似的羽人舞蹈,也可以在西林280号鼓鼓腰上发现,人们以手臂模仿鹭鸟的展翅与敛翅,场面宏大。前文描述过这两面铜鼓鼓胸處的划船竞渡纹,人们同样也头戴羽冠,或有持羽杖起舞者,这其实都与对鹭鸟、太阳的崇拜有关。人们集体模仿鹭鸟而舞,为的是祈愿风调雨顺,作物丰收。
出土于云南文山开化的开化鼓鼓面叙写了更为复杂的祭祀场景。开化鼓鼓面主晕有两组相似的图案,各以一座干栏式的船型屋为中心,屋内对坐二人,屋旁是一座晒台,高坐二人持棒击鼓。屋外是舞蹈的队伍,共有八人,戴羽冠或头插羽毛,下身着长裳,人群执弓摆手而舞,其中一人持匏笙吹奏。队伍中间是一座木架,上列圆形物十余个,或为锣架。这是一场盛大的农业祈年祭典与狂欢,船型屋顶饰以神鸟塑像,晒台上的人奋力捶打“公母”铜鼓[37],舞蹈的人群模仿着鹭鸟,敲击架上编锣,吹奏着浓郁南方色彩的匏笙,娱神娱人,场面热闹非凡。还有许多石寨山型铜鼓刻画了古代南方族群的祭祀,如广南鼓鼓腰上的剽牛舞蹈纹,如石寨山M13:3号铜鼓上的巫师祈雨纹,不一而足,种类丰富,都寄托了人们对农事年景的美好愿望。
从麻江型铜鼓鼓背“风俗画”中,我们也能一窥明清以来南方族群祭祀情况。这些风俗画常出现舞者形象,如《古铜鼓图录》第21号鼓[15],鼓背图像展现了村庄的凉亭中放置大鼓,两个人在鼓边舞蹈。又如中国历史博物馆1959年从北京文物商店购入的铜鼓,鼓背图像也有凉亭内鼓边作舞的舞者形象,同时还有一组剪影式人物,共六人,身体赤裸,垂手半蹲而舞。这些图像中的舞人,是南方族群舞蹈祈年之遗风,反映了当时乡村农业庆典情况。东兰旧州1号鼓画面则颇为奇特,一队婚礼迎亲的队伍,有仪仗队,两名骑马者,两名抬着轿子的轿夫,队伍经过一处凉亭,亭子立柱插着民间道公的法器,亭内一人扭腰扬臂而舞,当是仪式性舞蹈。传统的祭祀舞蹈与婚礼相结合,是在此前铜鼓中未曾出现过的新变化。
三、中国古代铜鼓呈现的文化变迁
(一)外来宗教对南方族群文化的影响
万物有灵的泛灵宗教是古代南方族群的原有信仰,但在汉晋之后,随着与中原的联系增加,道教、佛教逐步渗入到南方社会中。在东晋,鲍靓、葛洪等道教家在岭南地区研究道术与丹道,其后,广东罗浮山成为道教圣地,广西北流勾漏洞名列道家三十六小洞天之一。同样也是在两晋时期,佛寺开始常见于岭南、西南地区。宋代以后,南方社会的道、佛信仰与原有信仰相结合,呈现杂糅面向,这在铜鼓中亦有所体现。
道教对南方族群影响巨大,壮族的麽教、瑶族的瑶传道教,都是万物有灵信仰与道教结合的产物。宋代以后南方各族常以铜鼓供奉寺观,求神庇护[38],如麻江型铜鼓上就有大量游旗纹、符箓纹、八卦纹等受道教影响的纹饰。游旗纹并非一开始就是道教化纹饰,而是由冷水冲型铜鼓抽象化的羽人舞蹈纹进一步变形而成,舞者头部成了圆圈,头顶的羽冠成了飞扬的飘带,是道教仪式常见的旗幡。游旗纹的成型与普遍,正是说明南方族群信仰衍变的例子。符箓本是道教中用以招徕神鬼、趋吉避凶的神秘字符,也屡见于铜鼓之上,如篆如籀,富有神秘色彩而别具曲折的美感。八卦原是《易经》的概念符号,以代表自然中的各种变化,先秦方士将八卦吸收入方术当中,后又被道教所吸纳。八卦纹常见于道教法器,而融合于民间器物,如广西钦州唐代宁氏家族墓出土的十二生肖八卦纹铜镜。在铜鼓上有八卦纹,如铸造于明代的广西河池065号鼓鼓面沿有四个八卦纹,全为坎卦,坎为水,可以推断出此鼓是利用八卦纹来求雨。尽管道教符号充斥于许多近世铜鼓之上,但这些铜鼓并非道教法器,纹饰也没有深刻的道教内涵,而是融合于南方之巫教传统,且尤为注重世俗性的审美意义。
佛教在铜鼓上的呈现也是如此,而审美意义更强。除了傣族、佤族等一部分西南地区民族,佛教于南方族群社会的影响力不及道教,不过佛教纹饰在麻江型铜鼓上并不罕见。莲花纹是典型的佛教纹饰,象征清净无染,在南朝以后甚为常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旧藏257号鼓鼓胸有莲花纹与奔马纹,莲花七重,奔马稚拙,是佛教纹饰与本地纹饰的巧妙结合。卍字纹是佛教的神圣符号,唐宋以后日渐常见于艺术品,铜鼓也不例外,如1972年征集于南宁废品仓库的052号铜鼓鼓耳就有卍字纹。佛像纹偶然可见,同样在1972年征集于南宁废品仓库的039号铜鼓鼓面,第五晕就饰有佛像纹与四鱼纹。除了麻江型铜鼓外,西盟型铜鼓的佛教纹也饰颇为常见。
(二)汉族世俗观念对南方族群文化的影响
汉族与南方族群长期密切交往,在汉族世俗观念的影响下,铜鼓的神秘色彩越来越淡薄,其形体越来越轻便,纹饰越来越浅显,总体朝着世俗化、平民化的趋势发展。到了铜鼓发展晚期的麻江型铜鼓,除铜鼓本身的形制与铜鼓鼓面的太阳纹之外,几乎铜鼓的每一部分都可见到汉族世俗观念的痕迹。
汉族世俗观念对铜鼓的早期影响主要体现在钱纹上。除了万家坝型铜鼓与石寨山型铜鼓,各类型铜鼓都出现过钱纹,是一类十分常见的铜鼓纹饰。钱纹之钱,即汉地铜钱,有五铢钱纹、四出钱纹、连钱纹等。以五铢钱纹为例,五铢钱出现于汉代,沿用七百余年,影响极大,无论在中原还是在南方,许多文物上可以看到五铢钱纹,寓意富贵吉祥。钱纹在灵山型铜鼓上最为常见,或装饰于鼓面,或于鼓胸、鼓足。灵山型铜鼓多见于广西东部、南部与东南部,这里正是处于俚人与汉人的交界地带,俚人等族群能接触到王朝货币,亦易受汉族世俗观念影响,他们以钱纹与铜鼓的夸富性质相结合,同时也满足了审美的需求。铜鼓钱纹发展至隋唐,愈加少见[39],直到宋代麻江型铜鼓的出现,钱纹再次繁荣。在宋代,货币经济于岭南、西南地区发展迅速,民间大量钱币流通,这时的铜鼓钱纹较汉魏两晋时世俗性更强,不再是夸富的象征,而带有招财进宝的意味。麻江型铜鼓常饰有四出钱纹,四出钱纹与常见的纸钱样式一致,都象征着流通的货币。同时,宋以后的铜鼓会被用来贮藏钱币[14] 215,这也是世俗化的结果。
龙是最典型的汉文化神兽,与古代南方族群崇拜的蛙、鹭迥然有别。龙纹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期文物上,或诞生于图腾崇拜,长期是神圣象征,专用于皇室,唐宋以降走向民间,逐步世俗化。在早期铜鼓上找不到龙的痕迹,直到麻江型铜鼓,龙纹从十二生肖纹的其中一个,逐渐生动形象,有单独或成双的龙纹,至明清时期已与汉地龙纹无二。1977年广西东兰县钢精厂送南宁金属制品厂的310号鼓鼓面主晕饰有龙纹、鲤鱼纹、波浪纹、四出钱纹,寓意着鲤鱼化龙,富贵荣华。对河池063号鼓,据铭文可知该鼓铸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鼓面主纹有四条龙,二龙一组,龙之间有寿字,是为双龙献寿,刻画得颇为细致。双龙献印、双龙献珠、双龙献游旗等各式龙纹在铜鼓上并不鲜见,一方面是富贵吉祥的象征,另一方面是龙作为能带来降雨的神奇动物,从信仰功能上也取代了青蛙等南方族群原有的神奇动物。龙纹以外,还有鲤鱼纹、家畜纹、缠枝花纹等各种受汉族世俗观念影响的纹饰,大都表达求富求吉的愿望。
汉族的民间传说、小说也对南方族群文化产生一定影响,最突出的是诸葛亮传说。唐宋以后,民间流行三国故事,诸葛亮被视为半神化的人物。人们结合诸葛亮南征的史实,延伸出了许多传说,集大成者莫过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情节。故事里的诸葛亮软硬兼施,宽宏大量,使西南蛮族酋首孟获为之顺服。诸葛亮传说传播至西南、岭南地区,渐成为箭垛式的文化英雄、神化英雄,较汉文化中的诸葛亮形象更为传奇。明代开始,西南各族常将铜鼓称为“诸葛鼓”“孔明鼓”,认为是诸葛亮南征时的发明,如《遵义府志·金石志》载有:“世传铜鼓,诸葛所遗,此或然也”[40]。诸葛亮的神化形象在铜鼓上亦有所呈现。收集于河池的广西民族博物馆078号鼓,鼓面背部有风俗图画,人们弯弓射箭,纵马执刀,还有屋社、花草、怪兽等图案,最引人注目者,是铜鼓的两处“孔明将君”铭文(其中一处为反文)与一处“孔明鼓”铭文,似乎表明画面上的武士、异兽与诸葛亮南征有关。另外,画面有集体舞蹈的人群,有凉亭内作舞的人像,与农村祈年风俗相关,诸葛亮被纳入到农业祭祀体系当中,可见其影响力之深。前文提过用于求雨的河池065号鼓鼓面上,有“天元孔明”的铭文,可知诸葛亮崇拜也与求雨风习不无关系。
汉族世俗观念在铜鼓上最明显的体现是汉字铭文,已知最早的一面铸有铭文的铜鼓便是河池065号“天元孔明”鼓。铜鼓上铸作的汉字多半为年款与吉祥语,小部分是物主或工匠的题名、印记。铜鼓吉祥语与汉族吉祥语无二,诸如“万代进宝”“永世家财”“寿比南山”“大吉大利”或篆文“寿”字等,表明铜鼓已经彻底走入了民间,甚至也成为了汉族人家的用具。
(三)各族文化交融
在秦汉时期,汉族与南方族群已有大规模的接触,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岭南地区被统一,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滇国被汉王朝征服,从此南方与中原的联系无断绝。汉族移民自宋代大批进入广西,自明代大批进入云南,成为当地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化上有深层次的融合。同时,南方各族群之间亦互相影响、涵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尽管过去千百年了,许多文字材料消逝了,然而铜鼓作为不会说话的“器”,其揭示出的文化交融之“道”,却依然能给今天的我们在理解、处理民族关系时以极大的启发。
铜鼓中汉文化对古代南方族群文化的影响,从铸造技艺到纹饰,从物质文化到观念文化,处处有深刻的体现,如铜鼓上质朴的乘马、牛耕塑像,折射出汉族农耕与畜牧的影响;翔鹭纹、鹿纹等动物纹饰,既包含着本土的万物有灵信仰,也折射出中原、荆楚宗教的影响;更不用说宋代以后的麻江型铜鼓,是汉族世俗观念与本土器具的深度融合。文化影响并非单向,我们也能从铜鼓看到南方族群对汉族文化产生的影响。如浙江安吉上马山西汉墓曾出土过一面小铜鼓,与越南北部东山遗址出土的小铜鼓相像[41],可知早在西汉,铜鼓就已经流入了汉族地区。汉族的一些文化形象来自南方,譬如常与刘海图像同时出现,寓意招财进宝的三足蟾。流行于汉代至唐代的灵山型铜鼓鼓面上的青蛙塑像,蛙的一双后足合为一足,成三足蛙,而同时的汉族地区蛙蟾形象为四足,象征阴、月,多与象征阳、日的三足鸟相配对,蛙蟾后来演化为三足当受到南方文化影响。铜鼓亦对汉族文学产生影响,自唐代起文人以铜鼓入诗。到了清代,文人被铜鼓繁复的纹饰与奇特的形制深深吸引,以金石学的角度把铜鼓各细节引入诗歌,巨细无遗,诞生了《铜鼓联吟集》这样的文学奇葩,铜鼓在文人眼中成为多民族国家大一统的表征。
南方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铜鼓而充分展露。据学者发现,早在战国时期,从云南到广西就存在着一条“銅鼓之路”,汉代之前铜鼓主要从云南流向广西,如万家坝型铜鼓、石寨山型铜鼓,东汉之后铜鼓主要从广西流向云南,如冷水冲型铜鼓[42]。这条铜鼓之路至唐宋时期仍然流通不息,绵延千年,起源地各异的不同种类铜鼓得以传入岭南、西南地区的各个角落,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辉煌的铜鼓文化圈。宋元之后,铜鼓不仅为越人、濮人的后代壮侗语民族、孟高棉语民族所用,也为苗瑶语族的苗族、瑶族及藏缅语族的彝族等诸多民族所用,皆对铜鼓有创新性的理解与使用。各族文化融合于铜鼓,求同存异,交相辉映。通过对铜鼓纹饰、塑像的细致考察,探索“器”中深意,我们不仅能够发现南方族群独特文化之“道”,也能够理解族际和谐交往之“道”。
[参考文献]
[1]李昆声,黄德荣.谈云南早期铜鼓[J].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4).
[2]金景芳,吕绍刚.周易全解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69.
[3][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815.
[4]民族院校公共哲学课教材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资料选编[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395.
[5]覃剑萍.壮族蛙婆节初探[J].广西民族研究,1988(1).
[6]李伟卿.铜鼓立体饰物研究[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
[7][东汉]班固.汉书[M]. 颜师古,张晏,等,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2003.
[8][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M]. 杨武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351.
[9]陈江波.孩童戏鸭和人牛播耕立体饰铜鼓[Z]//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十三期).南宁: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93:1.
[10]农俊海.近四十年新发现铜鼓选鉴[D].南京:南京大学,2016.
[11]梁庭望.栽培稻起源研究新证[J].广西民族研究,1998(2).
[12]黄德荣.瑞士丽特贝格博物馆收藏的一面冷水冲型铜鼓[Z]//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六期).南宁: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89:15.
[13]罗坤馨.冷水冲型铜鼓立饰浅议(一)[Z]//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十六期).南宁: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2000:20.
[14]蒋廷瑜.铜鼓艺术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15]闻宥.古铜鼓图录[M].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4:34.
[16][汉]刘安.淮南鸿烈解[M].[明]刘绩,补注.陈广忠,校理.合肥:黄山书社,2012:301.
[17]袁康.越绝书[M].济南:齐鲁书社,2000.
[18]梁钊韬.西瓯族源初探[J].学术研究,1978(1).
[19]陈凤梅,樊道智,万辅彬.西汉时期岭南越人的航海证据——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铜鼓(M1∶10)船纹解析[J].中国科技史杂志,2019(4).
[20][法]鲍克兰.读《东南亚铜鼓考》[M]//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考古、民族学研究室.民族考古译丛(第一辑).汪宁生,译.昆明: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考古、民族学研究室,1979:58.
[21][越南]陶维英.越南古代史[M].刘统文,子钺,译.北京:商務印书馆,1976:225.
[22]龙村倪.从铜鼓船纹看越人航海(提要) [C]//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铜鼓和青铜文化研究——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第四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66—67.
[23]李昆声,黄德荣.铜鼓船纹考[C]//中国铜鼓研究会.中国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49—261.
[24]汪宁生.试论中国古代铜鼓[J].考古学报,1978(2).
[25][西汉]司马迁.史记 [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6]李露露.春牛辟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05.
[27]肖波,徐昕.试论铜鼓的萨满教属性[J].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8(4).
[28]袁珂,校注.山海经 [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149.
[29]屈万里.诗经诠释[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444.
[30][唐]魏征,等.隋书 [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236.
[31]黄懿陆.楚文化在石寨山型铜鼓上的影响[N].云南政协报,2005-03-19(A03).
[32]潜明兹.从萨满教神话窥其生命观[J].民间文化论坛, 2004(5).
[33]董晓京.石寨山型铜鼓花纹新解[J].思想阵线,2007(6).
[34]梁英旭.铸“器”象物——滇文化叠鼓形贮贝器上动物形象刍议[J].黄河.黄土.黄种人,2019(22).
[35]萧兵.铜鼓图纹与沧源崖画[Z]//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资料集.南宁: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85:29—47.
[36]张觉.韩非子译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39.
[37]罗坤馨.椎髻文身舞翩跹——铜鼓羽人舞蹈纹探析(二)[M]//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十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299—315.
[38]蒋廷瑜,彭书琳.铜鼓供奉寺庙习俗的检讨 [Z]//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二十一期).南宁: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2021:20.
[39]陈左眉.谈铜鼓上装饰的钱纹图案 [Z]//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铜鼓和青铜文化的再探索——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第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增刊).南宁:民族艺术杂志社,1997:104—108.
[40][清]郑珍,等.遵义府志·金石志[M].[清]平翰,等,修.遵义: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333.
[41]杨勇.论浙江安吉上马山西汉墓出土的小铜鼓[J].东南文化,2017(1).
[42]蒋廷瑜.“百越古道”中的铜鼓路[M]//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十二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5:108—117.
责任编辑:祝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