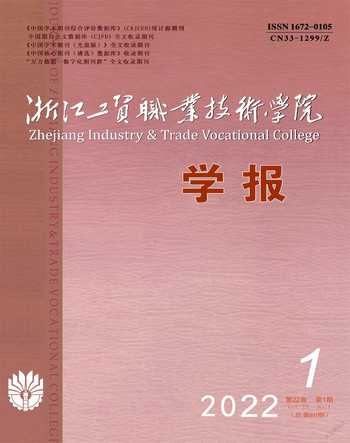论庄子“吾丧我”的反知意蕴
2022-05-27陈中权周蓉
陈中权 周蓉
摘 要:《齐物论》是《庄子》诸篇中最难理解的一篇,理解的关键在于何为“吾丧我”,学术界对此多有争议。庄子是反知主义者,认为“知”(知识、知觉)越多,越不是真我。从“坐忘”和“心斋”的视角看“吾丧我”,“吾丧我”是一个彻底的“反知”的过程,最终限度是无“无我”,即对宇宙无意识的洞见和冥合。“丧”即“忘”,有“坐忘”、“相忘”、“两忘”等形式。通过“吾丧我”,最终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逍遥游”之境。
关键词:庄子;吾丧我;心斋;坐忘;反知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105(2022)01-0077-04
On the Anti-knowledge Implication of Zhuangzi's “I lose myself”
CHEN Zhongquan, ZHOU Rong
Abstract: Qi Wu Lun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texts to understand in Zhuangzi.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text lies in the sentence “I lose myself”, which is controversial in academic circles. Zhuangzi is an anti-epistemologist, believing that the more "zhi" (knowledge, perception), the less true 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uowang” and “xinzhai”, “I lose myself” is a complete process of “anti-intellecture”, and the ultimate limit is “no me”, namely, the insight into the unconsciousness of the universe. “Lose” is “forget”, there are “sitting forgetfulness”, “forget”, “two forget” and other forms. Through “I lose myself”, finally achieve “heaven and earth and I live together, and all things and I are one” of the “free and unfettered” realm.
Key Words: Zhuangzi; I lose myself; xinzhai; zuowang; anti-intellecture
《莊子》第一篇《逍遥游》展示了一个自由的人生境界,第二篇《齐物论》则讨论其实现途径。《齐物论》是《庄子》诸篇中最难解的一篇,文意曲折隐晦,理解的关键在于“吾丧我”。“吾丧我”乃“齐物”之发端,学术界对此多有争议。不少人认为“吾”是本性、本体、自性的“吾”,而“我”则是被是非、执念、名利所羁的“我”,是被本真遮蔽的现象的“我”,是血肉之躯的“我”。比如陈鼓应认为:“吾丧我:摒弃成见。‘丧我’的‘我’指偏执的我。‘吾’指真我。”[1]林希逸认为:“吾即我也,不云‘我丧我’,而云‘吾丧我’,言人身中才有一毫私心未化,则吾、我之间亦有分别矣。”[2]陈清春认为“庄子哲学中的‘我’有三个意义,即真我、现象我和逻辑我;‘成心’不仅可以统摄‘我’的三个意义,而且是现象世界或者说我的意义世界的生成论根源。”[3]陈静认为“‘我’被外物裹携且陷溺于角色的序列之中,与‘游’无缘,‘吾’才能‘游’,‘吾’的‘游’展示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4]王蒙认为“吾与我有所区分,又实际上是一回事。吾当然是我,我无疑即吾。吾丧我,当然就是我忘记了我自己,我忘记了自己的存在。”[5]本文从反知视角论述“吾丧我”。
一、反知者的庄子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注重人的天性亦即自然性。道家批判儒家的仁义礼乐,认为它们会造成人的天性的异化,造成人的压抑,是社会祸乱的根源。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6]道家确实很强调自我,强调自我天性的自由。但有意思的是,道家强调自我恰恰是想忘记自我,认为最彻底的自我恰恰是无我。这样一来,道家必须有一套解构的理论来消解这个自我,以致于抵达最终的无我。老子和庄子都是反知主义者,认为“知”(知识或知觉)越多,越不是我自己,越不是真我。所谓“反知者”,就是一层一层把附着在自我身心的东西,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都剥离干净,最后只剩下“无”。但这个“无”还要忘掉,那就是无“无”。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7]105-106“为道日损”,就是以减法对待自我的修道。减到什么程度?先把外在的东西减掉(特别是儒家的仁义礼知信),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我”。这还不算,还要把我的身体知觉减掉,剩下一个纯粹的本真的我。这还不算,还要把本我、真我这种感知也去掉,抵达“无我”。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7]27-28老子这里说的是把自己的形体去掉,就没有任何忧虑了。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是死了,形体去掉,还有灵魂。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这种“反知”思想,并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心斋”和“坐忘”。
关于“心斋”,《庄子·人间世》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反知”过程。“一志”其实是一种专注到出神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听什么不是以耳朵来听,而是以心来听;进一步,不是以心来听,而是以气来听。气,虚也。所以说“心斋”就是一种以虚待物的状态,它的终极是“无己”。
关于“坐忘”,《庄子·大宗师》中借孔子与颜回的对话说:“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坐忘”是忘什么呢?就是忘记自己,就是忘我。连我都忘记了,那么我之外的天下万事万物自然也都忘记了。这又是一个彻底的“反知”的过程,不但反礼乐,反仁义,还把“肢体”去掉,“聪明”去掉,就是“离形去知”。“坐忘”的终极是“无我”。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和知识“损之又损”,减到最低限度,才能体悟到“同于大道”。
《庄子·大宗师》又说:“吾独守而告之,叁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生不死。”这是一个完整的反知过程。这里的三个“吾”都是社会人格的我,是受儒家道德系统束缚的我。这里的六个“外”就是一步一步去除“知”的过程,“外天下”、“外物”、“外生”、“古今”;“见独”后,也就是获得了纯粹清净的“我”、本真的“我”、天性的“我”。这既是“心斋”,也是“坐忘”。
二、何为“吾丧我”?
“吾丧我”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坐忘”,“忘”掉的是什么?是忘掉“吾”?还是忘掉“我”?为了解决此问题,先要把“吾丧我”的由来找出来。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答焉若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籟;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这段用子綦的“丧其耦”来比喻后面的“吾丧我”。关于“耦”,有人说匹配、配偶,似不妥。但成玄英进一步解释得有些道理:“耦,匹也,谓身与神为匹,物与我为耦也。”[8]43所以“耦”即“我”,“身”为“形我”,“神”为“心我”,“身”与“心”的匹配为“耦”。“丧其耦”就是“吾丧我”。“形如槁木”指陈现实中的“成形”,“心如死灰”指陈现实中的“成心”,其实就是“离形去知”,这里是类比“坐忘”的境界。这段关键是“吾丧我”。“吾”和“我”都是“我”的意思,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有学者认为前面的“吾”是本体的“我”,后面的“我”是现象的“我”;“吾”通过“丧我”的功夫体验到本体的“吾”。对此笔者不苟认同。“吾”已然是个本真、澄明的“吾”,那还有必要“丧我”吗?还要“丧”去那个被尘世“成心”遮蔽的“我”吗?
有学者认为“丧我”才得“吾”。“丧我”之后仍有“吾”的存在,这就说不通了,“丧我”之后应该是一无所剩,就是“无我”。晋人郭象注曰:“吾丧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识哉?故都忘外内,然后超然俱得。”[8]45“吾丧我”固然是“我自忘”;“我自忘”,就天下万物都不识,就是“忘内外”,但是,最后的“超然俱得”的“得”就有问题。根据“反知”的逻辑,“吾丧我”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都放弃,什么都忘记,包括自己;而“得”却是得到,尽管那是得到“超然”,那也不行,那就是还没完全放下自我,还有一个“超然”的自我存在。由此说来,说“丧我”是“得”到“吾”那也是错的。
笔者以为,既然“吾”已经是自然的我,天性的我,本真的我,那么他要“丧”去的应该是作为本体的“自我意识”,后面那个“我”就是前面那个“吾”的“自我意识”,而不是那个被遮蔽的尘世的我。庄子要做的是彻底的“反知”,就算体悟到本真的“吾”,那还是有自我存在感,因为他还有灵魂。他要“反知”到底,把“吾”中的那点“自我意识”也要“丧”掉。所以“吾丧我”中的那个“我”就是“自我意识”,只有把这个“我”也“丧”掉,才能达到“无我”;更进一步地,把“无我”这种意识也“丧”掉,达到无“无我”。至此,“我”才能被稀释在茫茫太虚中,就如《庄子·在宥》中说的:“大同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由此也可知,一切所谓“坐忘”的“忘”,都建立在“反知”的基础上,把自我感知到的一层一层剥离,不但是社会人伦的,还是自我的身体和感知,都要剥离。“坐忘”到最后连一点极少的“自我意识”也要剥去,才能抵达“无”,进而抵达无“无”。
三、“吾丧我”的途径
“吾丧我”中的“吾”确实就是本真的本体,但“我”只是“吾”中的一部分,亦即当了悟到本真的本体的“吾”时,人还有一丝未化的“自我意识”(也可称“私心”),还意识到一个本真本体的“吾”存在,这就是“我”。既然“吾”要“丧我”,就说明“吾”中还有一丝一毫的“我”的知觉还未丧掉,这就涉及到心理学的问题。“我”只是“吾”的未化的“自我意识”,而“丧”所做的只是把“吾”中的“自我意识”去掉,剩下的就是“无我”。但是即使是“无我”也还有丝毫未化的“无我”意识,体道者最终要做的是了悟到“无意识”的“我”,即灵魂都虚化了似的,至此才能化入太虚,大通于道。
(一)“不与物化”和“物化”
道家反对生命异化,强调自我,并非多私多欲。相反,它强调自我正是为了忘却自我。人要自由,要先做自我。但现实情况是,人不但有“成心”,而且有“成形”。《庄子·齐物论》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无论“成形”或“成心”都是被物化的社会化生态的倾轧状态。做自我固然是为了自由,更是为了舍掉自我。这就是“丧”,也是“忘”。“丧”比“忘”的语气更强。“忘”是你意识上忘了,但你原先的存在还在,但“丧”是必须去除。“丧我”或“忘我”是一个时空扩大至无限的过程。关于“吾丧我”的办法,庄子首先主张“不与物化”,即不为是非利害、功名利禄、欲望执念等外物所“物化”,那不是“吾丧我”,而是丧己于物,心为物役。这里这个“物化”的“化”,是基于一分为二的理性分析。
接着,庄子又主张“物化”。这个提法首见于《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这是一种清醒的理智。但这里的“物化”之“化”,却不是一种理智的分析,而是一种直观、圆融、与物交感、合二为一。我化为物,物化为我,我因此浑然忘我,获得自由。这里的“化”就是“忘”。通过“化”,而将自我的存在境涯扩延。与前面的“成心”相对,“物化”就是忘掉“形我”。忘掉“成心”和“形我”就“自喻适志”了。“自喻适志”则是一种物我冥合为一的自由态。庄子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互相自化,当然也包括人与万物的互相自化。这种“化”就是通过自我心灵的直观、冥想、交感、合一,使存在自由、扩大。这就是“忘我”,也是“丧我”。所以所谓自由不自由,就是以什么样的“心”处理什么样的“我”。
(二)“忘(丧)”的不同形式和层次:坐忘、相忘、两忘
作为反知者的庄子,其工具就是“忘”或“丧”。关于其中的“丧”,成玄英云:“丧,犹忘也。子綦境智两忘,物我双绝。”[9]“忘”有多种形式,也有不同层次;相应的,“我”也有多种形式,不同层次。比如“坐忘”、“相忘”、“两忘”等,其主体都是“我”。一是“坐忘”。“坐忘”是“我”针对自己的形体和知性,就是《庄子·大宗师》里面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就是把自己从形体和知性里抽离出来,达到“同于大通”的境界,即人与道冥合无间。庄子对于人被自己的“形”所羁的苦是深有体会的。《庄子·齐物论》说:“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还有“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至于“知”主要是针对仁义。《庄子·在宥》说:“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可见仁义制约人心。二是“相忘”。“相忘”的来源,《庄子·大宗师》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以这个寓言告诉人们,当“我”被周围环境中一种同质的关系所维系所束缚,不如抽身离去,在更大的时空中自由自在。一旦置身于关联网中,就会产生是非利害等。事物的关系本来是虚清的,一旦产生群体的社会化之关系,此关系就变成实浊了。所以庄子在《大宗师》中说:“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把事物之间的关系归于本然的虚清,也就“道通为一”了,也就“通天下一气耳”。三是“两忘”。“两忘”的来源,庄子在《大宗师》中说:“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两忘”往往指矛盾对立的双方,互为主体与客体。主体忘了客体,客体也忘了主体,物我两忘,两者一同化入大道。总而言之,以上的“坐忘”、“相忘”、“两忘”都是一种个体心理上“反知”的过程,“忘(丧)”就是一层一层剥离与“我”有关的一切,包括是非、关系、自身,最后的“我”也变成“无我”,就无挂无碍,周流不拘,化入无限的时空,化入大道,达到《齐物论》中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归纳上述三点,“首先是忘知的功夫。‘知’所制造的问题,必须靠‘忘’来消解。因此《庄子》认为以道观之,唯有透过‘坐忘’等功夫,抛弃理智区分才能体‘道’。所谓的去知,去智,去成心,去机心。庄子很多的寓言故事讲的就是由技到道的过程。”[10]
(三)“吾丧我”的心理难度:“无意识的意识”和“有意识的无意识”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吾丧我”的办法是“不与物化”和“物化”。那化来化去还是人间的此岸性。现在的“吾丧我”要的是体道,体悟到“天籁”,这就要增加“丧”的难度。至于“丧”的办法,就是极致的“坐忘”和“心斋”。关于“坐忘”,就是《庄子·大宗师》里面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关于“心斋”,前面说过(《庄子·人间世》):“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两者都是典型的“反知”过程。“坐忘”是把自己从形体和知性中抽象出来,达到“无己”和“道通”。“心斋”的“一志”是一种专注到出神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听什么不是以耳朵来听,而是以心来听;进一步,不是以心来听,而是以气来听。气,虚也。所以说“心斋”就是一种以虚待物的状态。但是“虚而待物”的“虚”也是有层次有深度的,要“虚”到什么程度呢?终极达到的,就是“无”。而“无”还有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无”,要用“无”完全甩掉那个粘乎乎的“我”,心理难度颇大。
从“吾”和“我”的字义和语境来理解,“吾”更多的是一种客观称谓,而“我”更多的是一种情态的称谓。相应的,“丧”更多的是一种客观行为,而“忘”却更多的是一种意识行为,所以从“吾”到“我”,从“丧”到“忘”,应该涉及到心理学的范畴。“忘”不是一般的忘记,而是颇有心理难度的。无论你已经是个本体的我,天然的我,自性的我,只要你还有一点点“自我意识”,你就还未达到本体的我,天然的我,自性的我,即未化入天道。按照“反知”的逻辑,“忘”的彻底限度应该是对“我”层层剥离,抵达“无”,即“无我”。但只要人清醒着,要完全忘掉“我”是很困难的。所以“吾丧我”的“我”是非常有深度有层次的,就像大海上的冰山,大部分的“我”是淹没在海水之下的,即淹没在人的潜意识或无意识之中的;只有露出海面的一角才是人意识得到的。所以,所谓“丧我”不仅仅是“忘”了人能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那一小部分,更多的“忘”了潜意识或无意识中的“我”。当“丧我”的程度到达“无我”时,它还未终结。因为“无我”还是有一点“自我意识”的存在,是“无意识的意识”或是“有意识的无意识”。只要“吾”中还有一点点“自我意识”,那就还有自我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的嫌疑。只有“吾”把那一点点的“自我意识”也丧掉,人才能大通于天宇(或说无痕迹地消化于天道)。所以“丧我”的最终限度是无“无我”,即对宇宙无意识的洞见和冥合。这是一种极端精微的“反知”修为。至此,人才能跟宇宙万物一并化入大道,达到“莫然无魂”的状态(《庄子·在宥》)。并且这种状态是无法言说的。《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老子也说,道是不可说的。凡是悟道的人,都有那种妙不可言的大自由和大喜悦,因为他整个人被“化”了。“化”亦即“忘我”,无限深度的“忘我”。
收稿日期:2021-11-03
作者简介:陈中权(1964—),男,浙江瑞安人,中共温州市委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华传统文化、温州地域文化;周 蓉(1966—),女,浙江温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二级作家,主要研究方向:古典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