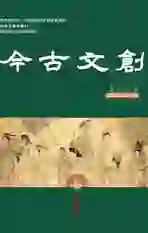西夏蒙学研究综述
2022-05-19马力张祯
马力 张祯
【摘要】西夏蒙学研究由来已久,本文对西夏蒙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梳理,第一部分从教育史和蒙学及蒙书研究两个大的方面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第二部分将西夏蒙书分为应用类蒙书、识字类蒙书和教育类蒙书三类,将西夏蒙书的专题性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
【关键词】西夏;蒙学;蒙书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8-0062-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8.019
西夏蒙学的研究,从黑水城文献的刊布开始。之后国内外学者开拓了研究道路,丰富了研究内容,纵观西夏蒙学的研究,道路曲折但研究成果颇丰。学者们从版本介绍文献校勘、校注到各类写本的专题研究,进而扩展到对西夏教育的研究。内容涉及教育体制、启蒙教材、学校等。
一、综合性研究
(一)对教育史的研究
蒙学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西夏教育史是我国历史的重要内容。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三卷中论述了西夏的文教政策、教育制度、科举制度,提及西夏蒙学。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十章2.3节集中论述了西夏蒙学。
与专著相比,论述西夏教育的论文观点相对比较集中。稚农《五代宋西夏金时期的甘肃教育》(甘肃教育,1985年04期)认为西夏在封建化过程中,西夏蒙童记忆的启蒙教材有西夏文翻译的儒家经典。稚农《五代宋西夏金时期的甘肃教育》(《甘肃教育》,1985年04期)认为西夏向封建制转化过程中,为便于蒙童记忆用西夏文翻译传统儒家经典作为教科书和启藏课本;金超《西夏教育概述》(《宁夏教育》,1986年09期)提及设有童子科;张传燧《西夏教育发展述略》 (《民族教育研究》,1994年04期)对西夏教育发展的社会背景、文教政策、教育制度及学校的教师及教学情形做了详细叙述,提及西夏蒙学的相关内容;刘兴全《论西夏的文化教育》(《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04期)一文在论证西夏文化教育的贡献时,列举了不少西夏蒙学教育的相关内容并肯定了西夏蒙学教育的作用。卜然然《民族文化交流对西夏教育的影响》中提及西夏翻译传统蒙学教材以普及西夏文,赵倩、张学强《西夏教育考述》 (《鸡西大学学报》,2013年02期)提及西夏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传统儒学启蒙教材。
赵生泉《西夏文教育钩沉》(《西夏学》,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王静如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专辑,2014年)文中提及蒙学在西夏的概况。米晨榕《西夏教育刍议》(2015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定程度上对西夏蒙学教育进行了概括。潘贝《汉传世俗文献与西夏文化》(2017年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认为西夏对蒙童读物的重视,始于元昊翻译汉籍《四言杂字》,西夏文本蒙书在内容和体例上受中原蒙书影响,汉传蒙书种类丰富、层次多样,有“面向普通大众的识字读本” 、德行类蒙书和辞书。金滢坤《宋辽金西夏元儒家经典与蒙童教育考察》(童蒙文化研究(第五卷),2020年)中提及了儒家经典翻译对童蒙教育的影响,认为西夏政权与辽金政权一样,经学启蒙教育是其汉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西夏重视《孝经》教育,将其翻译成西夏文,便于儿童学习,并认为“童子科”是科举考试对蒙童经典教育的影响。
(二)对西夏蒙学和蒙书的研究
杨彦林《西夏启蒙教育初探》(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3期)从西夏时期对启蒙教育的重视,启蒙教育的教材和内容,以及启蒙教育成果等多个方面对西夏时期的启蒙教育做出简要论证;杨树娜、杨彦彬《西夏童蒙教育刍议》(《科教文汇》,2009年08期)提出西夏蒙童教育的主要内容紧紧围绕着识字和生活常识、传统思想道德教育培养和宗教思想,认为西夏蒙童教育流行时间短,地方特色浓郁,具有一定宗教色彩。
杨树娜《黑城出土西夏蒙书研究》(2012年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对黑城出土识字类和德行类蒙书从概述、录文、学术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整理,对黑城出土蒙书整体反映的思想内容、特点和价值进行了分析;何宏米、李德芳、陈封椿《简议黑城出土的西夏蒙书》(《兰台世界》,2014年17期)认为西夏蒙书内容丰富、种类齐全,是少数民族蒙书中的个中翘楚,它存在对儒家典籍的借鉴和对佛教文化的吸收,但其编排体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另外,惠宏、段玉泉《西夏文献解题目录》(阳光出版社,2015年6月版)将《番汉合时掌中珠》 《三才杂字》 《新集碎金置掌文》 《纂要》 《经史杂钞》等书籍归于蒙书类目。
二、专题研究
(一)应用类蒙书的研究
西夏的应用类蒙书主要以字典为主,学界对《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研究源于1924年,罗福成将其整理刊布。①史金波《简论西夏文辞书》(《辞书研究》,1980年02期)肯定了“掌中珠”的文献价值,并对其进行了简明介绍。吴峰云《〈番汉合时掌中珠〉校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和首次学术讨论会议论文,1980年8月)根据苏联刊布及国内所藏的西夏文资料,以表格形式,对《掌中珠》进行了校补。聂鸿音《〈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音符号研究》(《语言研究》,1987年02期)从語言学角度,确定了西夏文的28个声母,认为《掌中珠》中注音符号的位置不同,作用不同。李范文《〈番汉合时掌中珠〉复字注音考释之一》(《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05期)、《〈番汉合时掌中珠〉复字注音考释之二》(《宁夏社会科学》, 1989年06期)两文从“音值”出发,关注西夏复字的注意问题。孙宏开《西夏语鼻冠声母构拟中的几个问题——从《掌中珠》西夏语汉字注音谈起》(《民族语文》,1996年04期)将《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汉字注音材料与藏缅语族语言进行比较,认为西夏语中存在鼻冠声母。景永时《〈番汉合时掌中珠〉俄藏编号内容复原与版本考证》(《宁夏社会科学》,2013年06期)以原序录和文献实物照片为依据,将俄藏《番汉合时掌中珠》原编号内容进行了复原,认为其为初编本和修订本两个版本,而修订本又属于两个不同版本。穆旋《〈番汉合时掌中珠〉管窥》(《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5期)对《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发现及内容、研究状况、编纂体例和版本进行了论述。贾常业《〈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异讹字》 (《西夏研究》,2015年01期)对《番汉合时掌中珠》甲种本和乙种本比对,发现了11个异体字、26个讹体字、4个存疑字。景永时《20世纪〈番汉合时掌中珠〉刊印史考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05期)考述了20世纪以来,《掌中珠》整理、刊布的历史。段玉泉《〈番汉合时掌中珠〉“急随钵子”考释》 (《敦煌学辑刊》,2018年03期)研究得出《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急随”乃传世文献材料中所载煮茶或温酒器皿“急须”,钵子并无意义。郭明明、杜建录《〈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芍葵花”考》(《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01期)及庞倩《〈番汉合时掌中珠〉“笼床”考》(《西夏研究》,2021年02期)均是结合各方材,对《掌中珠》中的词汇进行考释。综合各方研究成果,可知学界对于《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其内容和版本的考证,二是其反应的13世纪西北方音语音问题,三是对书中字、词含义的考证。
《纂要》以前被译为《要集》,是西夏人编撰的蒙书之一,书中的西夏文词皆以西夏文音译的汉语词解释。出土的纂要为残本。1963年,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对其作了介绍。1983年,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月诗”的研究》第八页中刊布了《纂要》的部分内容,并对其仅从了初步研究。聂鸿音《列宁格勒藏本西夏文词书残叶考》(《民族语文》,1990年01期)参考西田龙雄刊布材料,对《纂要》的书名和体例来源进行了讨论。韩小忙认为《纂要》体例独特。②
(二)对识字类蒙书的研究
《三才杂字》既有写本又有刻本,主要出土于黑水城、莫高窟、武威小西沟岘等西夏遗址。国内最早关注到《三才杂字》的是罗福成先生,其《杂字》(《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2年04期)一文刊布并翻译了其中的十二部分内容。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三才杂字〉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06期)利用当时俄中英三方材料对《三才杂字》内容进行了复原和初步研究。王静如、李范文《西夏文〈杂字〉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02期)对《杂字》的来历及文本做了介绍,并对夏汉两个文本做了相互比较,同时也对西夏文《杂字》的特点及反映出的问题做了深入研究,认为西夏文《杂字》体例上受《孝经》“三才”的影响,内容上受“尔雅”的影响,突出西夏党项姓氏和人名以及亲属称谓,此外,文章最后还附有西夏文《杂字》夏汉对照表。佟建荣《西夏文刊本〈三才杂字〉残页考》(《西夏学》,2016年01期)认为对俄藏、英藏、中国藏《三才杂字》残页分属于两类不同的西夏文《三才杂字》,其中一类又有不同的版本类型。段玉泉《新见英藏西夏文〈杂字〉考释》 (《西夏学》,2017年01期)对“国际敦煌项目(IOP)数据库中《英藏黑水城文献》未刊布的37个残页进行考拼,认为其为目前出土的西夏文文献《杂字》的一个新刻本,可为西夏文《杂字》的继续拼配补充材料,有较高的补缺及校刊价值;高仁、王培培《西夏文〈杂字·汉姓〉译考》 (《西夏研究》,2017年02)期)对西夏文《杂字》中的“汉姓”部也进行了译释并提供了更为准确的译文,同时结合其他文献中的汉姓译法比较差异,认为西夏文《杂字·汉姓》四字一韵,体例类同于《百家姓》,但其排序并非按照姓氏的尊贵程度,而系其普遍程度而来;吴雪梅、邵译萱《新见西夏文〈三才杂字〉残片考释》(《西夏研究》,2019年03期)对宁夏佑啓堂藏的四件西夏文《三才杂字》残片进行译释,比对俄藏、中国藏、英藏《三才杂字》,认为其属于新见版本,同时这四件残片本身也属于不同版本,对于研究西夏印刷科技史及《三才杂字》版本具有文献版本学价值。可以说,学界关于西夏文《三才杂字》的研究主要是从其版本和价值、所反映社会历史文化、刊布和释诠三个方面展开。
国际上对于《新集碎金置掌文》的研究起于1935年,苏联学者聂历山指出了《碎金》和汉文《千字文》之间的相似之处;1963年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在《西夏文写本和刻本》中介绍了《新集碎金置掌文》两种抄本的形制和内容,1969年克恰诺夫对《碎金》 进行了细致地研究并将全书除番汉姓氏以外的部分作了俄译。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02期)对俄藏741、742的抄本《新集碎金置掌文》进行翻译,认为其是西夏蒙童识字的读本。景永时、王荣飞的《未刊布的西夏文刻本〈碎金〉考论》 (《敦煌学辑刊》,2016年04期)认为,《碎金》在埋入地下之前,便是由刻本和抄本两部分合成,写本一般为书法作品和习抄文书,刻本对于校勘写本意义重大,肯定了其文献价值和版本学意义;对于其中前人认为其中汉姓部分隐含 “双关”意义提出了质询。马静《西夏字书〈新集碎金置掌文〉探析》(北方民族大學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利用拟音和意译对西夏文《碎金》的内容进行了誊写和释诠,认为其反映了西夏人的世界宇宙观、存在对西夏帝王社会治理和当时民族及部落特征、社会生活状况、动物的记述;作者认为,《碎金》的不同版本学术价值和意义不同,但其存在普遍性、地域性,具有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
《圣立义海》以“天”“地”“人”三才的体例收录了西夏人生活中的常见事务。由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合著的《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00年1月版)展示了克恰诺夫、李范文对《圣立义海》研究的成果,刊布了当时《圣立义海》的影印件,罗矛昆对清进行了对译和音译。汤晓芳《西夏史研究的两部重要史料—— 〈圣立义海〉和〈贞观玉镜将〉简介》(《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01期)对当时俄藏的《圣立义海》从版本、装帧方式、内容及编纂目的进行了介绍。朱海《西夏孝观念研究——以〈圣立义海〉为中心》 (《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5月版)对西夏的“孝观念”进行了考察。袁志伟《〈圣立义海〉与西夏“佛儒融合”的哲学思想》(《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03期)认为《圣立义海》体现了党项民族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以及他们的宇宙论的同时体现党项民族对人类起源、人本性的认识及其人性论,《圣立义海》体现出了党项人对儒佛思想的融合和创新,顺应了唐宋以来“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郭明明《〈圣立义海〉孝子故事史源补考》(《西夏研究》,2017年01期)结合传世文献、敦煌艺术和考古资料,对《圣立义海》中“子孝顺父母名义”“依孝成吉祥名”“兄弟之名分”“媳礼名义”进行考源,得出《圣立义海》中29 位孝子故事的史源。和智《西夏文〈圣立义海〉翻译中的若干语法问题》 (《西夏学》,2017年01期)就《圣立义海研究》中部分译文中的语法问题做了校勘和补充。张彤云《西夏类书〈圣立义海〉故事新考三则》(《西夏研究》,2019年01期)和《西夏类书〈圣立义海〉故事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毕业论文)对《圣立义海》则故事进行了史源考证。格根珠拉《〈圣立义海〉中反映的“九品才性”问题——古代民族语童蒙教材中的“等级”观念》(《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6期)以西夏文《圣立义海》第13章部分的记载为线索,结合儒学“九品”相关的说法以及佛教概念里的“十界”以及诸如“二十五等”“四十八等”等分类学说对该文献中的“九品才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论述了儒家思想及其社会制度渊源和与宋代中原佛教对西夏社会性读物编纂的影响。和智《西夏语两种重要语法现象拾得——以西夏文〈圣立义海〉为中心》(《西夏学》,2019年01期)和《〈圣立义海〉校译补正》(《西夏研究》,2020年02期)两文,一文从语法角度出发,挑选西夏文《圣立义海》中数则与存在动词、人称呼应相关的词句进行了重新校勘和翻译;另一文将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一书中值得商榷的问题参照《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刊布的《圣立义海》从译字、译词和译句出发,进行了校补。格根珠拉《西夏蒙书〈圣立义海〉史源补考四则》(《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04期)对《圣立义海》中未知来源的四则故事进行了来源考证。
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了俄藏《新集文词九经抄》原件图版,其编者仿敦煌文献书题定名为“经史杂抄”。聂鸿音《西夏本〈经史杂抄〉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03期)中增补了其古语出处12种,认为《经史杂钞》摘抄多种汉文典籍拼凑而成,存在问题。郭良《西夏文〈经史杂抄〉译注》(宁夏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明确了《经史杂抄》的版本、体例和性质并增补了《经史杂抄》征引古籍的出处。郭良《西夏文〈经史杂抄〉的版本和研究现状》(《南北桥》,2008年02期)结合国内外西夏学界的研究著录情况,通过对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以及原始文献的识读,对文献版本和研究状况进行论述。黄延军《西夏文〈经史杂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主要采用文献学和考据学的方法,通过文本识读、内容对译、条目考源、与敦煌汉文本《新集文辞九经抄》和《文词教林》文本比较,对“九经抄”进行系统解读。黄氏另文《西夏文〈经史杂抄〉考源》(《民族研究》,2009年02期)中认为其性质、内容、形式和语言风格与敦煌汉文文献《新集文辞九经抄》相似;条目编排和所引条目内容有明显继承关系;反映了西夏社会底层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也反映了西夏人受汉文化影响的情况。梁丽莎《英藏西夏文〈贞观政要〉〈新集文詞九经抄〉残片考释》(《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09期)认为英藏编号为Or.12380-2636(K.K.Ⅱ.0275.z)的写本残片和英藏编号为Or.12380-3494(K.K.Ⅱ.0282.fff)的刻本残片分属同题同内容但版本不同的两份文献,均属于《九经抄》。
(三)对教育类蒙书的研究
西夏常见的教育类蒙书多为中原地区常见的刻本。
黑水城所出《孝经》主要有吕惠卿注和唐玄宗注两个版本的西夏语译本。学界对吕惠卿版本的研究较多。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就曾写道西夏文译《孝经》。胡若飞《俄藏西夏文草书〈孝经传〉序及篇目译考》(《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05期)和《俄藏西夏文草书〈孝经传〉正文译考》(《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05期)两文对《孝经》的内容进行了考证。聂鸿音《吕注〈孝经〉考》(《中华文化论丛》,2007年02期)分析了吕惠卿的序言并尝试解读了《孝经传》中的五章,讨论了不见于史书记载的吕惠卿的几个职衔以及西夏中晚期教育的基本情况,指出西夏政府从来也没有以《孝经》为代表的中原典籍译本作为正式颁布的科举教材。孔维京《碰撞与融合:西夏社会变革中的“孝文化”》(《西夏研究》,2017年02期)提出《孝经》对西夏文化的发展有特殊意义。孙颖新《英国国家图书馆藏〈孝经〉西夏译本考》 (《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05期)比对了英藏本和俄藏本《孝经》,认为西夏翻译《孝经》的时间俄藏本晚于英藏本。段玉泉《〈孝经〉两种西夏文译本的比较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01期)一文认为西夏文《孝经》不同译本的存在,说明西夏时期《孝经》流传广,影响大。
北宋陈祥道撰写了《论语全解》的西夏语译本,聂鸿音1992年在西夏文史论丛中对西夏译本《论语全解》进行了考释。③
西夏语译《孟子》的译者和成书时间不详,因为内容残缺学界研究较少,主要以彭向前的研究为主,彭向前《夏译〈孟子〉初探》(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议论文集,2008年)文首次研究了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现存卷四到卷六的西夏文行书写本《孟子》,为学界提供了西夏文语料。汤君和尤丽娅肯定了彭向前对于孟子的研究,认为彭向前《西夏文〈孟子〉整理与研究》 ④一书整理规范,考证详尽,编排合理。⑤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学界对西夏蒙学的综合性研究较少,对蒙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出土蒙书的刊布和释诠、版本和价值以及蒙书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风貌出发进行探讨。也有很多学者,从音韵学角度出发,探讨蒙书所反映出的语音问题,成果颇丰,但不属于蒙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暂不讨论。
注释:
①罗福成:《番汉合时掌中珠》,1924年版。
②韩小忙:《西夏文正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4年。
③聂鸿音:《西夏译本〈论语全解〉考释》,《西夏文史论丛(一)》,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④彭向前:《夏译〈孟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⑤汤君、尤丽娅:《〈西夏文《孟子》整理研究〉评介》,《西夏研究》2014年第3期。
作者简介:
马力,女,回族,甘肃华亭人,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夏历史与文化。
张祯,男,汉族,山东肥城人,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夏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