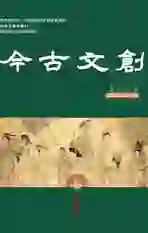现代黑人女性的成长之困
2022-05-19王竹英
【摘要】非裔美国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将自己的小说定位为黑人妇女写作,关注黑人女性在阶级、种族、性别三座大山压迫下的种种遭遇和艰难成长。本文结合成长小说叙事结构原型模式分析莫里森第四部小说《柏油孩子》中女主人公吉丁遭遇的成长困境及其原因,幫助读者理解小说创作技巧,揭示莫里森通过吉丁的成长为现代黑人女性成长指明的出路。
【关键词】《柏油孩子》、现代黑人女性、成长困境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8-001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8.006
基金项目:淮南师范学院科学研究项目“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女性成长研究”(项目编号:2019XJYB58)。
非裔美国女作家托尼·莫里(1931-2019)一生创作了11部小说,获奖无数,1993年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作家。1986年,当托尼·莫里森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你认为自己小说的读者群是哪些人”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为黑人妇女写作的。”[1]46在她看来,和她一样,黑人女作家们在其作品中再现黑人女性阶级、种族、性别歧视而被多重边缘化的悲惨境遇,但他们“以决不妥协但又充满爱心的方式面对问题”,目的是“重新命名,重新拥有” [1]46。
莫里森的小说中,面临种族、阶级、性别多重压迫与束缚,依然勇于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实现的黑人女性形象比比皆是,1981年出版的《柏油孩子》中女主人公吉丁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小说描述了女主人公吉丁从接受主流文化教育迷失黑人意识,产生身份危机;到与黑人男子儿子相恋,恢复黑人意识;与儿子生活在现代都市纽约,遭遇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矛盾,理想幻灭;到最后积极行动、主动建构新的自我的过程,是一部经典成长小说的成长小说。
成长小说源自德国,主要“描绘成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或“认识自我身份与价值,并调整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过程”[2]5。经典成长小说中主人公一般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往往经历“天真——诱惑——出走——考验——迷惘——顿悟——失去天真——认识人生和自我”[2]84这一过程,最终调整自我,融入社会。然而,《柏油孩子》中的黑人女主人公吉丁的成长经历显然与之不符。在白人世界成长、打拼的她25岁才遭遇身份危机,不是经典成长小说中十几岁的青少年;与儿子相恋后辗转于骑士岛、纽约、黑人小镇埃罗,恢复黑人意识,意识到自己的黑人女性身份与责任,但她最终还是拒绝回归传统黑人文化,与儿子分手,孤身远走巴黎。
小说模糊的、开放式结局没有告诉大家吉丁是否为自己找到了清晰的社会、文化、民族定位,下一步会如何抉择。那么是哪些因素让吉丁的成长偏离正常的轨道?在成长旅途中,她遭遇了哪些困境?导致她成长困境的原因又哪些?小说的开放式结局如何解读?这些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吉丁的成长困境
(一)缺乏单一、稳定的文化语境
埃里克森认为,身份认同是指一个人在成长中经历了某种心理危机或精神危机后,获得的一种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健全人格[2]238。在单一文化语境中,个人更容易清晰地认知所在社会语境的价值标准与行为规范,调整自我并最终与社会和谐共存,建构一个完整的、和谐的社会自我。但在双重甚至多元语境中,个人的身份被割裂,不同文化价值观在个体身上不断撕扯,让个体矛盾、痛苦,在不同的文化身份之间摇摆,要建构单一、纯粹的文化身份几乎不可能。
《柏油孩子》中,吉丁出生在巴尔的摩的一个黑人社区,如果她家庭幸福,必然会受到黑人文化的滋养,嫁给同村的黑人男子,结婚生子,过着和她母亲一样的生活,顺利建构所在社区的传统黑人女性的身份。但吉丁2岁丧父,12岁丧母。12年的童年时光里她对黑人文化有一定的认识,但黑人文化价值观没能在刚满12岁,刚迈入青春期大门的吉丁身上内化。后来,她被为白人糖果商瓦利连工作的叔叔婶婶带到费城,继而接受瓦利连的资助去白人学校上学,接受正规教育,高中毕业又去了法国巴黎读大学,业余在纽约从事模特的工作,只有寒暑假偶尔去地中海上的骑士岛与叔叔婶婶以及瓦利连一家待在一起。主流文化的熏陶让她认同西方文化,瓦利连的儿子麦克尔说她在抛弃她的历史,她的人民,但白人霸权文化让她“喜欢《圣母玛利亚》胜过福音音乐”,认为“毕加索比伊图玛面具要强”,甚至在想到在美国一年两三次得以展现的所有那些黑人艺术时,“脸上甚至闪过一丝尴尬” [3]63。直到圣诞大餐上的闹剧让她发现她认同的白人文化并不那么美好。她一直觉得很“体面”,慷慨资助她上学,如家人般的瓦利连夫妇不堪的一面。白人男子瓦利连因为黑人奴仆的抱怨就要解雇兢兢业业为他工作了50余年的他们,吉丁明白身为黑人的她,永远不可能属于那个家,永远不可能获得平等的地位与尊重;白人女性玛格丽特虽然嫁给了多金的瓦利连,衣食无忧,但丈夫对她的漠视、轻视让她心理畸形,靠虐待自己不会说话的儿子发泄内心的痛苦,吉丁瞬间发现嫁给白人男子不能让她获得她想要的性别平等。她嫁给白人男子,融入白人世界的梦破碎了,她毅然选择了与儿子离开。与儿子的埃罗之行让她再次受到黑人文化的滋养,但埃罗的贫穷、落后让她逃离。
穿梭于黑人文化(巴尔的摩)、美国白人文化(费城、纽约)、法国文化(巴黎)、后殖民文化(骑士岛)之间的吉丁感觉哪都是她的家,又哪都不属于她。小说中儿子问吉丁她的家在哪,她的回答是“巴尔的摩。费城。巴黎。[3]148”为了融入白人世界,她努力迎合白人世界的世界观和行为规范,与白人在一起时,她“装聋作哑,让他们相信她不像他们那样机灵能干……说显而易见的道理……问愚蠢的问题”,“做出感兴趣的样子,如果他们表现出有辱人格,也要相迎”[3]109。她被小说中的传统黑人男子看成白人,充满民族自信、肤如柏油的黄裙女人唾弃她。文化语境的交叠与重合让吉丁混乱、焦虑,白人眼里她是黑人,黑人眼里她是白人,但其实她都是,又都不是。文化身份的交叠让吉丁没有安全感、完整感。
自我建构过程中“对自我、他者、群体的认同绝非从一种认同到另一种认同的简单的直线运动,而是不断地来回往复、在斗争、挪用的过程中曲折向前[4]123”,单一、稳定的文化语境的缺失给吉丁主体文化身份的建构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二)阶级、种族、性别歧视下多重边缘化的社会地位
与黑人男性相比,黑人女性处境更艰难,他们遭受种族和阶级压迫的同时,还承受着来自白人和黑人内部男性的性别压制。“这种压制既体现在物质层面,如在蓄奴制下沦为繁殖财产的牲口,在黑人家庭内部作为男性权威的顺从者;也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如各种权力话语和机制对黑人女性形象、性特征的利用与操纵”[5]55。
阶级、种族、性别歧视让黑人女性不仅遭受着来自白人,还有来自黑人男子的歧视和轻视。现代男权社会中,性别歧视让黑人女性在黑人文化和白人文化中都难逃被“物化”的悲惨命运。在儿子的故乡埃罗,吉丁发现女人们被歧视、边缘化。女人们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不能参与男人的谈话,被男人们人们“看她的目光就像她是赢来的、偷来的、甚或是买来的一辆卡迪拉克高级轿车”[3]222。在白人世界,吉丁从事的模特工作看似光鲜亮丽、报酬丰厚,但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她那浅色的皮肤符合白人的审美标准、黑人面孔满足了欧洲人的猎奇心理。生活中,她不断地抻直黑人女性标志性的蓬松卷发,保持浅色皮肤,雪白人姑娘戴上流行的大耳环,刮遍全身的汗毛;杂志封面上的她“头发被平压在头上,从眉毛处梳开,露出清晰的发线……湿润的嘴唇张开着”。她甚至不清楚白人未婚夫愿意娶她是因为爱她还是她物化的特征与身份。“我猜想我要嫁的男人是他,不过我不知道他要娶的人是我或者仅仅是个黑人姑娘。而如果他要的不是我,却是长得像我、言谈举止也像我的任何女孩……他会怎样呢?”[3]41。
在黑人社区里因为性别被歧视,在白人文化里因为种族被忽视与物化,种族与性别歧视将吉丁置于“多重边缘位置和被忽视” [3]236的处境,“没有别的团体像黑人女性那样拥有脱离存在的社会化身份” [5]59。
(三)传统女性观与现代女性意识的矛盾与对立
《柏油孩子》集中体现了黑人传统文化与白人现代文化女性观的交锋。黑人群体内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让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对黑人女性角色的定位也产生了分歧。一方面,传统黑人文化要求女性承担大量的工作,还要生儿育女,赡养老人,顺从丈夫。随着民权运动的推进,黑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越来越多的黑人女性走出家门,进入学校、工厂,他们要求获得与男人同等的权利,渴望独立、自主。受过高等教育的吉丁是现代女性的代表,她不愿意按照年长一代的要求与期望,将自己束缚在埃罗简陋的小房间里,“作养育子女的贤妻良母”,顺从男人,被男人歧视与欺凌,她要“发挥创造性去建立自己的事业”,她要建构自己的家;她追求男女平等,追求对“彼此忠诚如一”的爱情。
吉丁的现代女性意识让她没法认同黑人传统价值观,回归黑人传统文化,没法承担传统黑人女性的角色。
(四)理想引路人的缺失
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总是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丰富着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的认知”[2]125。 “在当代成长小说中,理想的或者比较理想的引路人越来越难以寻觅。主人公往往只能孤独地寻找自己成长的道路”[2]129。《柏油孩子》中,吉丁25岁之前就一直没有引路人。12岁丧母成为孤儿,她失去了教她黑人传统文化与习俗,建构黑人女性身份的引路人,她的黑人身份建构停滞在12岁。虽然随后吉丁被在费城给白人资本家瓦利连工作的叔叔、婶婶(西德尼和昂丁)所收养。但养母昂丁有意识地拒绝了黑人传统文化引路人的角色。作为养母,昂丁觉得吉丁“是一个她可以赏识、迁就、保护的‘孩子’,而且由于这个‘孩子’是个外甥女,就不必强调一种母女关系”[3]82。“在养育吉丁的过程中,昂丁让吉丁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她为荣,但是她没有尽到黑人母亲传承黑人文化的责任,没有向她灌输黑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6]68,让她成了黑人文化的孤儿。昂丁和西德尼劝说瓦利连资助吉丁上学,但没有提醒吉丁注意白人的文化殖民;相反,“他们喜欢她待在巴黎,喜欢她上的学校,她在那交的朋友。他们到处吹嘘这些”[3]41。他们很乐意看到她们的牺牲让吉丁获得了好的教育,体面的工作和突破原来的社会阶层,向上进阶的机会。小说结束部分,昂丁看到吉丁丝毫不知道作为黑人女性应该生儿育女,照顾老人、丈夫时,懊悔地说:“我从来没跟你说过。我一点都没告诉过你,我对这件事要负全部责任”[3]246。
吉丁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到重重困难。作为散居的少数族裔,她没有单一、稳定的文化身份;作为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受害者,她没有相对稳定的社会身份;面对黑人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的冲突,她没有既定的角色定位;没有称职的成长引路人,没有适合的结婚对象,没有可以让她持续发展的职业。总之,她的种族、性别、阶级属性以及时代特征使她在这个特定的时代被多重边缘化,其成长因此滞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二、吉丁的顿悟与成长
重重困境让既定的成长异常艰难、曲折。经历了“黑人文化养育(巴尔的摩) ——认同西方文化(费城、纽约)——黑人文化滋养(埃罗) ——认同西方文化(纽约)”,吉丁恢复了黑人意识,但拒绝活在历史、活在过去,她把纽约这个“黑人妇女的城市”是唯一能让她嫁给儿子、融合现代白人文化和传统黑人文化、建构完整的黑人女性身份的地方。但截然不同的生活阅历和文化价值观造成了两人之间日益激烈的分歧和冲突,固守黑人传统文化的儿子认为家乡埃罗是最好,他沉浸在黑人痛苦的历史中,痛恨白人的一切,不愿意为了生存去学习任何白人主流文化;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吉丁则认为埃罗是贫穷、落后的,她追求物质,认为“贫穷是一座監狱”[3]146,物质财富是幸福生活的基础。最后一次争吵中,儿子像传统黑人男子一样殴打、强暴了吉丁。吉丁顿悟,能让她感觉完整、不再孤独的黑人女性身份不是她想要的,哪怕脱离埃罗,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也是不行的。玛格丽特虐婴也让吉丁发现,即便是白人女性身份,也没法让她获得想要的幸福。最终,吉丁与儿子分手,孤身前往巴黎。
《柏油孩子》开放式的结局是莫里森给身处现代多元语境的非裔女同胞指出的出路,未来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蚁后的象征、巴黎的选择让大家不难想象,吉丁是去巴黎这样一个能让她摆脱黑人、美国人的文化身份的第三空间寻找她认为的“第四种选择”:“只做躯体内的人——不是美国人,不是黑种人,只做我自己” [3]41,一个自我定义,只属于自己的人。面对种族、阶级、性别歧视的黑人女性要想获得性别平等,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应该勇于冲破身份的疆域,敢于定义自我、塑造自我。
总之,种族、性别、阶级问题仍然是摆在黑人女性面前的现实问题。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问题的表现不是日趋简单,相反而是呈现出愈益复杂的特征。黑人女性的身份困境仍然存在,其积极的主体性建构仍然非常迫切。每一位积极建构自我的黑人女性都不得不回答现实提出的身份问题。
参考文献:
[1]Russell,Sandi.Critical Essays on Toni Morrison[M].ed.Nellie Y.Mckay.Boston:G.K.Hall&Co.,1988.
[2]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莫里森·托妮.柏油孩子[M].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4]马艳,刘立辉.第三空间与身份再现:《柏油孩子》中后殖民主义身份建构[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3).
[5]唐红梅.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托尼·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6]Coleman,James.The Quest for Wholeness in Toni
Morrison’s Tar Baby[J].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Vol.20,No.1/2,1986:63-73.
作者简介:
王竹英,女,汉族,湖南株洲人,淮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