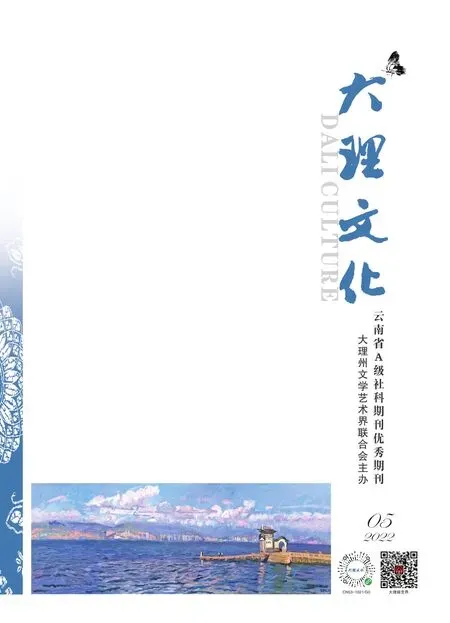心嗅梅香
2022-05-17刘绍良
●刘绍良
三万五千亩的梅树齐刷刷地开花了,花朵清一色是洁白的,因有不远处的罗坪山山脊上的积雪辉映着,让我把梅花想象成了雪花。
梅林一片连一片,由于山形地貌的作用,这梅花真的就如海洋,如波涛,如绸缎,让我们隐在其中不见人影。
2022年2月12日,是洱源县在此举办“中国洱源梅花文化节”的日子。有资料介绍说,洱源已有两千多年的栽培梅子的历史,而此地,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知道,这里的梅树早已都是大树、老树,每一株大都枝干虬结,树色苍黑,梅刺如铁,造型各异。只有树冠,因无需修剪整形,都形成了伞状的模样。今天的梅花开在伞面上,明天的梅子自然也就结在伞面上。
洱源因梅子而增辉,梅子因洱源而出名。在云南各种旅游景区的特产店铺里,都会售卖经深加工之后的各种青梅制品。它们被包装在精美的包装袋里,引得游客满口生津、馋涎欲滴。
这个地方叫大松甸,是洱源县茈碧湖镇松鹤村委会所辖的一个自然山村,全是彝族。村民金泉的媳妇对我说,他们会说三种话——汉话、彝话和白话。二十年前,在我所经营的山地上,有五十亩梅林,六年生的,但结果不好,我便打听到了大松甸的情况,进而进村认识了二十多岁的村民金泉和他们一家。我第一次进村,正值梅子采收季节,便碰到几伙来收购梅子的商贩,有昆明的、大理的,让我感觉到有产销两旺的势头。我怕酸,不能吃青梅,但我带去的雇工能吃,挑着不同地方的不同的梅树,吃了几个之后便对我说:“太好了,个大肉厚,味盐。”在我的家乡巍山,群众对梅子只有两种分类,那就是咬一口品尝味道,适口的叫盐梅,不适口的叫苦梅。我询问大松甸的梅子品种,金泉说,都是老树了,也只有酸梅和苦梅两种。这就是说,都是县内本地的老品种,没有近期引进的外地品种或外国品种。那个时候,洱源也已经把梅子作为经济支柱产业了,最有名的梅子企业就是“洱宝”公司,地址在茈碧湖镇下坡处的公路边。在我的土地上,管理梅子是很容易的,而且因季节的原因,跟大松甸一样,不需给梅子打任何农药,只需在梅子采收之后的雨水到来时,给它们施点农家肥为来年做准备。但是,这样结出的梅子却个小、颜色不好。喜食梅子的来客会随意地摘一个放进嘴里,嚼一下就吐出来,说:“真苦,不好吃!”好吃的梅树只有极少数,当然很快会被抢摘一空。需要说明的是,我上山时是从下关汽车总站下海转型的,对山地上的一切作物都不熟悉,所以,我想把大松甸的经验搬过去,那梅树就一定会结出同样的果实。同时,从经济角度看,我付出与大松甸村民一样的努力和投资,就一定会得到与他们一样的回报。
金泉是个非常朴实热情的年轻人,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吃的是砖头般的苦荞粑粑蘸蜂蜜,喝的是用山泉水稀释的雕梅水。临走,他还给我送了一小塑料桶雕梅水。夏天,那种少见的饮料,滋养了我种好梅子的信心。金泉家的梅林有好几块,相隔不太远。在梅子成熟的季节看梅林,感觉就跟喝了雕梅水一般,不仅爽口爽胃,而且爽心。
洱源早就出名了,但大松甸并不出名,它只默默地匍匐在距县城十三公里的西山上。只有我,在漫长的山地生涯中,若有同样的种植户说起林果,我就会讲到大松甸,说那个山村的村民全都靠种梅子吃饭,他们不种粮食,因为所有能耕种的土地都种梅子了。为了梅子,我多次进出大松甸,引了种芽回来嫁接。在我的山地上,本地的特色品种红雪梨是主项,我就很快掌握了梨树枝条嫁接技术,但我的梅子在嫁接后的成活率却极低,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耗费不少精力。大约五年之后,我才在嫁接成活的梅树上找到了结不出像大松甸那样品质的梅子的原因:大松甸海拔二千四百米,我这里海拔一千九百米;大松甸都是红色沙壤土,我这里都是黄褐胶质土;大松甸的土壤里有自然含水的成分,我这里的土壤干得冒烟,即便有雨,若时间短,也会因土地板结,雨水也渗不到土层深处。这个时期,县林业局还正在本地大力推广着种梅子呢。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大约在2005年吧,我把有限的梅子采摘后卖到近旁的大仓镇,收入刚好够付采摘和运输的费用。对于林果的认识,一年只能总结一次,若干年后,在这块土地上,我才认识到,梅子开花都在农历腊月,采收都在五月,都处在一年中最干旱的季节。如此,梅子这种植物,根本就不对应我这里的土壤、雨水和气候条件。如今,我放弃对梅树的管理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那些属于违反因地制宜原则错种的梅树,有的已经死亡,有的还顽强地活着,有的死了一半活着一半,只把苍黑虬劲的带刺的枝条指向天空。
大松甸早该出名了。眼前,我以山地作家的身份,应邀到洱源参加洱源的首届梅花文化节。这是故地重游,中间一晃竟相隔了二十年的光阴。那时,通讯还没有现在发达,我就与那位叫金泉的农民朋友失去了联系。梅花文化节的直播现场,也就在约五六亩相对平坦的梅林里,我参加了开幕式。在观看了丰富多彩的歌舞节目之后,我就与身旁一位四十多岁的瘦高个的毛姓村民闲谈起来。我说:“你们的梅子那么好,梅树那么多,全村人吃梅子就行了,没有人出去打工了吧?”他回答说:“梅子的收购价不稳定,去年我家的卖了一万多块钱,不够用,我和我儿子出去打工,供一个姑娘在昆明上大学。”我又问:“你认识金泉吗?”他说:“认识,这块过节用的地就是金泉家的。”我说:“怪不得似曾相识呢,二十年前我来过。”
关于我与大松甸之间的故事,一路上,我与同行的文友麦田讲了很多,他也是一位从山村走出来的编辑和诗人。如此,我愿意讲时,他便愿意听。我用我种梅子的经历向他说明我对物种与土地的认识,我说,古人传下来的“因地制宜”四个字,每字都是千金啊!大松甸的梅树多、梅子好,都是因地制宜的结果。在云南,只有洱源的梅子最出名;在洱源那么广袤的山地上,只有大松甸的梅子最好。今天,洱源县举办的首届“中国洱源梅花文化节”在此举行,这足以说明大松甸梅子也在塑造着洱源形象。
我一直以为大松甸是个白族山村。在白族为主的洱源县,大松甸的彝族群众,毫无疑问地在日常生活中首先有了被“白化”的可能,其次才是汉化。我们从村委会停车场走向直播现场的途中,碰到一个年轻漂亮的汉装女人,领着两个更年轻漂亮的身着少数民族盛装的女孩。女人长得漂亮,是应该受到赞美的,但两个小女孩的民族服装,更让我感觉漂亮和好奇。其中一个小女孩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吧。首先是她的头饰,像一顶用银器和珠宝串联起来的缨络般的网状帽子,扣在乌黑浓密的头发上;其次是她穿的羊皮褂,又似披风,长长的浓密的白色的羊毛覆盖了整个后背和两侧。只有前胸是敞开的,露出白族小女孩喜欢的红绒领褂。我要给她照相,她害羞得转过身去。其实,我正想照的就是她的背影。背影是美丽的,美得新奇,美得自然,美得与这个日子重叠在一起。及至直播现场,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如此样式的羊皮褂,都穿在这个村的成年男人身上。我由此推断,这是高寒山区才有的白色的绵羊皮,它经硝制后,原皮柔软暖和,原毛更洁白牢固,是与这个民族、这个地区、这方风景最协调的服装了。这一群穿羊皮褂的男人,都是吹唢呐的群众演员,到他们出场时,一人一把铜制唢呐,一字排开,唢呐口先抬高,吹出既洪亮又清脆的声音,响彻云霄;然后又渐渐放低,吹出的声音绵长而柔和。演出队伍都在梅林里,都被梅花覆盖着,簇拥着。但我听来,唢呐的声音既是大松甸群众对世界自豪的宣言,又是民族自信、地方自信、文化自信和经济自信的表现。不远处的路边插了一块牌子,上书“爱情表白地”的字样,我觉得也贴切也浪漫,但范围还是窄了一些,只适合做山村旅游的广告词。

眼前,在全国都还处在疫情防控期间,把洱源大松甸的梅花以文化的形式,展现给山外世界,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直播可以尽量减少来宾的人数。只有本地特色的展演队伍必不可少。唢呐演出之后,上场的是白族服饰打扮的白族女人,她们表演白族歌舞。同时,与我们一同参会的书画家们,也在相距不远的地方创作着,摄影家们则跑前跑后地去捕捉他们眼中最美的镜头。这些活动都在梅林里,视野当然受到了限制。这个时候,在第一次到大松甸的麦田面前,我就有了“指点江山”的自豪。在地势高亢开阔处,我说,你瞧下面这个小坝子,不仅历史文化悠久,当代也出过好几位很有成就的文人,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大理报》总编赵怀瑾,州文化局长、作家尹明举,州文联副主席、《大理文化》杂志主编、作家施立卓等。
大松甸处于这个坝子的北山。西山均为罗坪山山脉,这段山脉里延伸至最南端与苍山相连接的一个部分,因候鸟迁徙的缘故,古时就叫做鸟吊山。现在虽已过了春节,但白雪覆盖了整条山脊,就形成了一条银白的巨龙形状,龙头紧靠大松甸,龙尾就甩到了略显模糊的最南端。十八年前,最南端还有一个关于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大都在客观的艰苦与主观的诗意中展开。十八年前,因我拥有二十亩优质板栗接穗圃,就在州科协的介绍下,与凤羽坝子最南端的一个村庄的沈姓村民达成了合作协议。我指着坝子略东南方向的山脚对麦田说,那个地方有一股从苍山底部淌出来的水,一出来就形成了一条河,洞口上方,有一个庙,那是祭祀龙王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条河是洱海之源的一条重要支流。洞口左侧的漫坡上,那位姓沈的农民有三十多亩地,离洞口也就三十来米。我们合作的内容是他在那块地上种十一万板栗实生苗,由我出技术、出工,我负责用优质芽嫁接,成活后卖出,所得一人一半。他是个完全不懂板栗种苗的外行人,他说只因前一年到金沙江边的维西塔城买了一车原生小板栗,准备在中秋节前拉到外地去卖,但因公路塌方堵住了,误了节期,想了想,便把一车板栗都种在地里,育种苗。我为此从巍山找了十七个懂嫁接的农民,带上接穗,雇了辆中型客车,到那里搭帐篷住下,一住就是半个月。那时也是春节刚过,早晚还是很冷的,但中午已经很热,出汗太多,我便带着民工们到河里洗澡。有时,还能在水草中捉住几条小鱼。那段日子里,凤羽坝子是最美的坝子。苍山雪我们看不见,但罗坪山的雪景就在对面,而坝子里的油菜花,黄黄地开满整个坝子,在晨阳和晚霞的作用下,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在这个小坝子的村庄里,到处也都有梅树。沈姓朋友送了一罐炖梅给我,黑糊糊的却很好吃,也可做烹调用的调料。
每个人的记忆,就是属于每个人的时间隧道。一旦进入这个隧道,自然地就会串连起许多故事。我为什么总是与洱源这个地方有缘呢?1995年,我又认识了一位姓段的胖胖的从兰坪矿山回来的工头,由他组织了十余个凤羽人,为我在巍山牛街的锑矿山打矿洞。这伙凤羽人很能吃苦也很能吃肉,也就是舍得地干,舍得地吃。我们的经济关系是打进尺,但还要给他们提供生活服务。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在那些尘土飞扬、炮声不断的极为干旱的日子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我对他们亲热的方式,就是学着他们讲话。比如,工头小段站在我的工棚后面,喊对面坡的一个小伙子吃饭,就把“瑞松”喊成乐谱中的“2(Re)、5(Sol)”,而且,把“5(Sol)”拖得很长,如一句歌曲的尾音。同时,当别人问他们“你是哪里人”的时候,他们回答的都是“我是洱源呢”,音调就跟乐谱中的“1(Do)、5(Sol)、1(Do)、5(Sol)、3(Mi)”一样。所以我对他们说,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只有洱源的白族说话跟唱歌一样。如今,这一群“1(Do)、5(Sol)、1(Do)、5(Sol)、3(Mi)”们早已与我失去了联系,但我相信他们不管身处何地,根都还牢固地扎在这块土地上,“1(Do)、5(Sol)、1(Do)、5(Sol)、3(Mi)”这句话、这种发音,就是他们永远的乡愁。
我有时也开北京吉普车送他们回家,途中路过邓川,他们在那儿请我吃了一顿最好吃的酸辣鱼。我问为什么这么好吃呢?他们说:用梅子醋煮的。
在那些辛劳艰苦的日子里,他们还会带给我用水碓舂好的糯米面、用传统方法压榨的菜籽油。偶尔也会有人在梅子成熟时回家,带一袋青梅来温暖我。所以,今天我站在北山的大松甸,仿佛看见了南山脚下的那湾河水,那些欢快流淌着的沟渠、吱呀着的水磨坊、咚咚作响的水碓,还有那盘沈姓农民家里的生皮之外的生猪肝……
直播现场的文化节目丰富多彩,但我既然打听到了金泉的情况,也就迫切地想去看看他。我约上麦田,在原路返回的途中,有一条半大的黑花狗,一直不紧不慢地亲热随和地跟着我。我边走边想着另一件往事。那几年,我在开矿山、搞果园的同时,还在巍山创办了个红河源旅行社。我们不断地往西双版纳送本地的游客。版纳一位周姓的部门经理电话上对我说:“请给我带几斤洱源的话梅吧,我姑娘喜欢。”当我把金泉送我的话梅交给那位小姑娘的时候,她说:“我太想去看看梅子树的样子,嗅嗅梅花的香味。”之后,我们每次有团队到版纳,我都在下关的店铺里买上几斤,让那位小姑娘含着话梅考上了大学。那么今天,金泉家还有话梅或者雕梅吗?
金泉家已经没有话梅了,只有不多的半盆雕梅。他为我们的到来感到片刻惊讶之后,立马热情地招呼我们,我们便在院子里喝茶、吃雕梅。雕梅很脆,甜中含着固有的酸。二十年前的记忆是一笔财富,金泉有些愧疚地说:“雕梅没有了,带点雕梅水回去吧,我知道你喜欢。”又说,“这雕梅水稠得跟蜂蜜一样,洱源有名的雕梅酒,就是用这水兑出来的。”我跟巍山一个酒厂老板交好,他们也生产雕梅酒,原料也是洱源的,我便想为金泉搭成一条销路。金泉说,这二十年来,他两口子都没有外出打工,收入就靠梅子,但加工的梅制品有的交洱宝公司,有的卖给下关的生意人,都不太好卖,所以,还是青梅卖得多,一年也就一万多块钱。另外的收入,就是雨季到更高的松林里以承包的方式捡松茸,平均也能收入一万多。我说:“加起来就近三万吧,那你的小卖部收入好吗?”他说不行,只是铺面闲着。他今天的这个家,我里里外外看了个遍,都是新房子,很宽敞,早已不是我熟悉的土墙、青瓦、木屋架还有火炕床的老房子了。
对于这位老朋友,对于这个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五百多口人的彝族山村,都靠梅子吃饭的现象,我一直充满好奇。因此,当麦田很礼貌地当客人、当听众,并且,一定在构思着他的既朴实又哲思的诗句的时候,我和金泉说了许多关于大松甸的话,关于天南海北的话。这时,有在直播现场的同行友人不断发来视频,都是那些梅林中的文化活动场面,有的文字里,也引经据典地重复着关于梅花如何之香的名句。想了想,我也拍了几张金泉家的照片,附了几句临时涌上心头的文字。我说我抽烟厉害,鼻子嗅觉不灵,闻不到梅花的清浅暗香了,那么我用心嗅,也正在嗅着梅树、梅花和梅子制品固有的生命之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