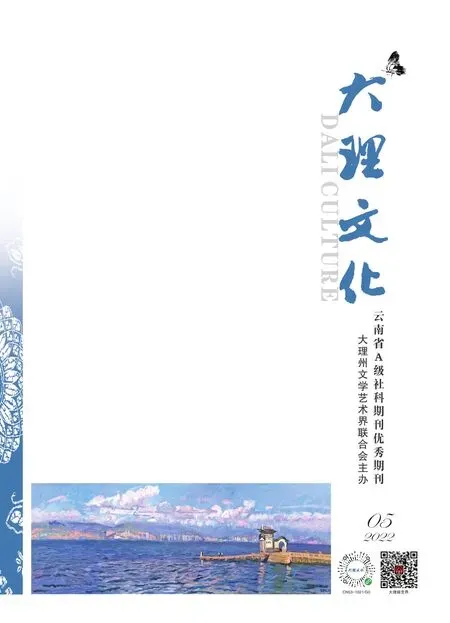情醉鸡足山巅
2022-05-17安羽文/图
●安 羽 文/图
金顶听雪
鸡足山天柱峰上的“绝顶四观”,让历览天下、任意东西的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大为惊奇。明崇祯十一年(1638)12月22日,徐霞客第一次登上云南宾川鸡足山,当他登临最高峰——天柱峰,站在金顶之上,东观日出,西望苍山洱海,南睹祥云,北眺玉龙雪山,他被眼前的景致所折服,不禁惊叹:“东日、西海、南云、北雪,四之中,海内得其一,已为奇绝,而天柱峰一顶一萃天下之四观,此不特首鸡山,实首海内矣!”
“绝顶四观”中,“西海、南云、北雪”相对易得,但要观“东日”,需凌晨便置身金顶。
去年的深冬时节,为了在天柱峰一睹“东日”——群山之上云海翻涌、红日喷薄而出的美景,我们一家夜宿金顶寺外的一家宾馆。小儿尚幼,对美景并不期待;女儿已14岁,反复提醒我,早晨一定要按时叫醒她。
入夜,一轮圆月悬在金顶之上,万籁俱寂,耳畔唯有禅音萦绕。突然想到金顶寺东门的楹联与此情此景正是契合,于是趁着月色又去读了一遍——“四围山色观无相,千里月华听有声。”极目四望,月光洒遍千山万壑。闭上眼睛,月华如水,拂过千年往事,也拂过我此刻安宁的心。山风安静下来,站在寺门前的睹光台上,惬意无比。这睹光台,主要是为看日出而建,但在这里看月亮,也别有一番情趣。回到寺院中,踏着月光又游历了一番,直到寺院的当家师催促说要关寺门,才戴月而出。
翌日凌晨五点半便醒来,约着妻子出去先查看一下。外面还一片漆黑,只觉山风凛冽。才走出宾馆,脚下便有轻轻“嚓嚓”声,打开手机电筒一看,地上已是一层积雪。妻子压着声音惊呼:“哇,下雪了!”我们生活在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想要置身于一场飘雪之中,一生遇不到几次。
本是要看一回壮丽的日出,不想却遇上了一场婉约的南方飘雪。
不到六点,金顶寺的大门已经打开。迎着寺门的灯光,便可以看见细碎的雪花窸窸窣窣飘飘而下。进入寺内,大雄宝殿里僧人们已经开始早课,有几个信众在雪中上早香。一个约莫三十多岁的妇女背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孩站在大殿廊檐下听诵经,小孩不哭不闹,眼睛里满是好奇看着院中的飘雪。
我绕着院内的楞严塔和金殿走了一圈,院里已有一层积雪。天尚黑,看不清空中的飘雪。楞严塔的身影静默而朦胧,影影绰绰直指苍穹。据说滇西抗战时期,它曾是驼峰航线上的一个航标,正是因此,在往后的劫难中才得以幸存。
山风又起,寒冷难当,于是又回到大殿外的廊檐下。
廊檐的灯光照到了飘飘的雪花。风向飘忽不定,落雪时大时小。被灯光照耀的雪花,细细碎碎,忽东忽西,有时甚至打起旋儿。灯光之外,雪花隐匿在沉沉的夜色之中。大殿里的诵经声低沉而浑圆,透过格子窗缓缓向外流溢,与轻灵的雪花交融在一起。
我忍不住又走下台阶,站在院中,仰头,闭上眼睛,任雪花落上我安宁的喘息。整个世界,仿佛都是一片无瑕的白和无边的清冷洁净,将所有的杂念冻结。没有赞美,没有诅咒。
天蒙蒙放亮,四围的群山间起雾了。心心念念的日出,终究是要错过。不期而遇的雪,却让此次鸡足山之行变得趣味盎然。
回到宾馆,一双儿女都已经醒来。女儿迫不及待地问:“可以看日出了吗?”
我拉开窗帘,让女儿过来看看。她走到窗前一看,激动地发出了几声“啊啊”,然后把窗子打开,探出头去看,“居然下雪了!你说意外不意外?”
宾馆是建在山巅之侧的,窗外都是树,一直顺坡而下。松树、栗树、杜鹃树,树冠上全都已是洁白。眼前的雪景,加之远山的云雾缥缈,这样的清晨,真如置身于仙境一般。
小儿穿好衣服走到窗前一看,高兴地呼喊:“下雪啦!下雪啦!我们要去玩雪啦!”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实景飘飞的雪花。他拉着我的手,迫不及待要出门去。

金顶听雪

云上杜鹃
天已经全亮,我们一家子便走出宾馆赏雪玩雪。金顶寺赭红色的院墙下,雪白得让人心静。石板路、石栏杆、石阶,瓦檐屋顶,松树柏树栗树,全都覆上了一层洁白的雪。山下的游客还未到来,夜宿金顶的游客不多,所以路上、院中的雪都非常洁净。小姐弟俩打起了雪仗,打着打着,冷不防就开始“攻击”我和妻子,于是一家人便开开心心“混战”了一番。小儿觉得戴着手套不尽兴,干脆把它脱了,堆雪人、滚雪球,欢笑声像雪一样洁净。
游道穿过一片树林,女儿使劲摇动树干,白雪便簌簌落下,那声音,仿佛能荡涤世间所有疲惫的尘埃。
云上杜鹃
索道的缆车缓缓上升。我在奇险峻秀的鸡足山中,在云雾缥缈的悬崖峭壁上,徐徐飘向山巅。
鸡足山巅,一场浪漫的杜鹃花事等着我前去赴约。
此时,宾川鸡足山十里杜鹃长廊的花事,在朋友圈中曼妙地灿烂,艳羡许多人的眼睛,我便是其中最向往的一个。许多人都到不了杜鹃长廊,一则地势奇险,在九重崖之上的山巅;二则还没有开辟正式游道,驮马走过的古道苔藓斑斑,坎坷难行,如遇雨雾天气,易迷路。也许正因如此,才更加诱人!
七月,多情的雨水将整座鸡足山浸润得青翠欲滴。山林间飘来的鸟鸣声,水灵灵地在心魂的耳膜上轻颤,崖壁上的苔藓吸足甘霖,将千万年的故事滋养得生机勃勃。
“疑泛轻舟碧海中,不知身在翠微里。”这么优美的文笔,出自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散文家徐霞客之手。且不说鸡足山厚重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佛教文化和人文内涵,仅此一句,鸡足山迷人的生态风光便可见一斑。
鸡足山的魅力,三言两语是无法说清的。徐霞客一生先后两次上鸡足山,在山中长达半年之久。鸡足山是徐霞客一生游历的终点,也是《徐霞客游记》的终篇之地。
我在翻阅《徐霞客游记》时,未发现他对鸡足山杜鹃花事的记录。但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初九的游记中,他对如今鸡足山十里杜鹃长廊的所在地做过详细的记述:“又上里余,再登一冈。其冈西临盘峡,西北有瀑布悬崖而下,其上静庐临之,即旃檀林也。东突一冈,横抱为兰陀后脊,冈后分峡东向,即狮子林前缀之壑也……”旃檀林、狮子林一带,是鸡足山高山杜鹃最盛的地方,可惜寒风凛冽的正月,花期最早的大树杜鹃(映山红)也还在沉睡。有点遗憾,徐霞客没赶上杜鹃灿然开放的时节。
缆车送我们上了山巅。在本地非常熟悉鸡足山的导游带领下,穿过索道站的后门,我们走进窸窸窣窣的雨雾中,走进禅意绵绵的旃檀林。断断续续的细雨,沾衣不湿,正好。雾也不太浓,在古道两边的林间弥漫。
“吾是寻常木,愿在旃檀林。”这是佛经里的一个比喻,意思是说,普通的一块木头,把它放在旃檀林里,久而久之也会浸染檀香。杜鹃本来也是普通的杜鹃,只因它长在灵山、开在灵山,在我们的眼里心里,就变得不同凡响。
一株、两株,粉色的、紫色的、白色的杜鹃,随着薄雾向眼帘飘来,就像古琴悠远却又不可抗拒的乐音。此时正在盛开的,是小杜鹃(灌木),开得袅娜而婉约,纤纤如玉女。导游介绍说,大树杜鹃(俗称映山红,乔木)早在干旱缺雨的三四月间就开了,开得热烈而洒脱,似在为纤弱的小杜鹃开路打前站,为召唤雨水快点到来。
间杂在古树林里盛放的杜鹃,被缥缈的薄雾轻轻抚摸,就像在仙境中嬉戏玩耍的一群仙女。雾气散开,可以看见三五成群;雾气聚拢,眼前慢慢就只剩一株,一枝,最后是一朵,与你深情地对视。我拍了一小段微风带雨的紫杜鹃发到朋友圈,称“遇到小仙女啦”。有朋友打趣:带回来,养在家中。我说,怎么能呢,仙女只能在仙境里。
我曾经到过贵州毕节市的百里杜鹃长廊,那里的杜鹃挤挤挨挨,中间很少掺杂其他树木,开起来的时候,一个一个的山头似火燃遍,特冲击人的视觉。而鸡足山的杜鹃,是间杂在古树林间,开起来,缥缈而婉约,仿佛能轻轻拨动你心中隐藏已久的古琴。
思绪回到鸡足山巅。此时的旃檀林,花在雾中,人在雾中。这缥缈与灵动,真让人流连忘返。我愿此境一刻,胜过人间千万。
编辑手记:
当大部分地方还被冰雪覆盖之时,在神秘的云雾缭绕之中无量山已经迎来了早春的场景。《无量山行记》记录了作者行至云岭山脉无量山系中的几段难得的旅行体验,该地域独特的地理气候和人文历史为其刻画描写带来丰饶的资源和背景,品读文字,仿佛一阵来自无量山深处的清风吹来,我们都心生惊喜和感动。在洱源茈碧湖,有个白族村落掩映在万株梨树之中,背山面水,乘船穿湖便可诗意抵达。《“世外梨园”入画来》的作者故地重游,登岸仔细探寻故人故事,梨园村在日益增强的环保意识中,洋溢着安宁静谧的和谐景象。密祉从前是马帮人的异乡,是一个有岁月痕迹的小镇。还因为花灯文化和一曲著名的《小河淌水》让这里蕴含着浓厚的艺术气息。这片与月亮流水紧密相连的地方能让人在山水与人情中流连忘返。我们不妨走进《徜徉密祉的悠长时光》一同度过一段绵长温柔的时光。趁季节正好,寻访山色,《情醉鸡足山巅》描绘了冬夏两季的山顶图景画卷,倾听一场冬雪,赴约一场花事,这些属于山顶景色的浪漫美不胜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