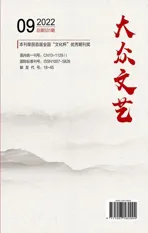传统“勇”德及其当代价值*
2022-05-17董艳艳
董艳艳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伦理型文化,道德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与规范。它蕴含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中。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内涵丰富,美德是道德文化中的精华,也是社会和谐、民族发展、国家富强的动力与保证。
“勇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民族危难时刻,“勇敢”总是能鼓舞士气,激励人们战胜困难。古代文献尤其儒家文献中多有关于“勇”的论述,“勇”德是儒家“三达德”之一,也是儒家道德观念中的重要德目。儒家传统“勇”德内涵丰富,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疫情常态化的新国情下,我们更应当将“勇敢”之美德内化于心,形成道德行为的自觉,发展好自身,保护好小家,守护好大家。
一、传统“勇”德的内涵
儒家“勇”观念的发展是逐渐完善的,孔子、孟子、荀子都曾阐述过“勇”的内涵。《论语》中论“勇”多与子路有关,孔子对“勇”的诠释体现在对子路之“勇”的教育中。子路在入孔门之前就是一个有勇之人,“好勇力,志伉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好勇,总喜欢逞勇,有时却行事过于鲁莽。侍奉孔子时,子路也是一副刚强的样子,与众人不同,“闵子骞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论语·先进》)。孔子经常与子路探讨“勇”的问题,他批评子路好勇的表现,如个性张扬,出言不逊,口无遮拦,争强好胜等行为,但肯定他敏锐果决的风格。子路曾经问孔子“君子尚勇乎?”孔子说:君子以道义为上,君子如果勇敢而不讲道义就会犯上作乱,小人如果勇敢而不讲道义就会成为土匪强盗(《论语·阳货》)。
综观《论语》中对“勇”的阐释,孔子对“勇”的看法主要表现为三点:一,认为“勇”的基本特征是“不惧”,“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面临危难而不畏惧,是“勇”的本质特征。孔子常将“仁”“知”“勇”并提,并将“勇”作为成就完美人格的要素之一,已然是将“勇”纳入了德性修养的范畴。二,“勇”要以仁义为前提,“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左传》中已有关于“义勇”的论述,“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谓之勇”(《左传·文公二年》),“周仁之谓信,率义之谓勇”(《左传·哀公十六年》)。《国语·周语中》也有“以义死用谓之勇”。以“仁”“义”为出发点的“勇”才是孔子所认为的“真正的勇”,即“勇德”。三,“勇”要以礼为规范。子贡问孔子有没有厌恶的人,孔子回答“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子贡也谈道自己厌恶的人“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论语·阳货》),“不孙以为勇”正是无礼的表现。《国语·周语中》中郤至谈道自己在晋楚鄢陵之战的功劳时说“吾有三伐;勇而有礼,反之以仁”。《礼记·聘义》曰“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以“仁”为出发点,以“礼”为规范,内心“不惧”才是孔子所提倡的勇德。在孔子“勇德”思想的教育下,子路慢慢屏除了其莽撞、好斗的个性,由单纯的“血气之勇”转变为儒家的义勇,既包含勇力的体能特性,又包含不惧牺牲,遵守信义的精神特质。
在春秋时期道德失范的环境下,孔子对“勇”的认识带有道德重建的意味,社会政治、经济、农业等各方面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面对的困难不再集中于自然灾害和战争。困难的多样化也促使“勇”的职能和内涵发生着变化。“不惧”之精神不仅在战争、政治、外交等国家大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个人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因此,孔子将“勇”纳入了个人的德行修养之中,成为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之一。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勇德”思想,认为“勇”的主要特征是不惧牺牲,“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万章下》)。孟子进一步将“勇”区分为“大勇”和“小勇”,小勇是“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下》),大勇是文王、武王之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下》)“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反对好勇斗狠的私勇,认为这样的行为会危及父母,是不孝的表现,“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逸周书·官人解》有“高言以为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称其说,以诈临人:如此,隐于廉勇者也”。虚张声势的勇猛强悍,并不是真正的“勇”。“勇”不是狂妄自大、轻率鲁莽、故作粗暴;“勇”要懂得进退,讲究策略。那种喜欢表现血气之勇,贪图从祸乱中捞到好处的“勇”被认为是小人之勇,是不被提倡的。孟子对于“勇”的阐述,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孟子曾经谈道北宫黝和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认为北宫黝能够不畏惧身体的伤害,不畏惧诸侯的强权,孟施舍能够不畏惧敌人的强大兵力,他们也算得上勇敢了,然而真正的大勇在于“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如果拥有正义,即使面对千军万马,也要勇往直前。“有行之谓有义,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所贵于立义者,贵其有行也;所贵于有行者,贵其行礼也”(《礼记·聘义》)。孔子所强调的“义勇”在孟子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荀子对“勇”做了更详细的解释,他分析了社会上各种形式的“勇”,并将这些行为分为四类: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和士君子之勇:“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荀子·荣辱》)。前三者皆是荀子所批判的“勇”,不辨是非、不懂礼义、凶猛暴戾,即便有与“勇”相似的外在特征(不惧危险和死亡),也不能看作是真正的勇敢行为,“悍戆好斗,似勇而非”(《荀子·大略》)。《左传》与《晏子春秋》中都有对这种“似勇而非”行为的批判,“畏强凌弱,非勇也”(《左传·定公四年》),“介人之宠,非勇也”(《左传·文公六年》),“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晏子春秋·内篇》)。无论是逃避强者,欺侮弱者,还是凭借别人的宠信而报私仇,都被认为是“非勇”的表现。“勇”作为一种德性,应当是以善为目的,充满正能量的行为。以发泄私愤为目的的斗勇,并不属于真正的勇敢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对国事无益,还会破坏社会秩序。所以,要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威武强大,就必须鼓励“勇德”而禁止民间私斗。荀子认为“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荀子·荣辱》),并且认为这种行为是令人憎恶的,“疏知而不法,辨察而操僻,勇果而无礼,君子之所憎恶也”(《荀子·大略》)。
对于“非勇”行为的否定,剔除了不属于“勇德”性质的特征:恃强凌弱、凶残狠辣以及蛮横好斗等,使儒家“勇德”的内涵与外延更加清晰。《晏子春秋》曰“勇士不以众强凌孤独,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晏子春秋·内篇》)。真正勇敢的人不会凭着人多势强而欺凌无依无靠之人,“勇而无惮”的行为“是天下之所弃也”(《荀子·非十二子》)。“刚毅勇敢不以伤人”(《荀子·非十二子》)唯有重死持义的士君子之勇,才是真正的勇敢,即“勇德”。荀子更进一步从“勇”的价值的角度将“勇”分为三个层次:“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荀子·性恶》)。荀子“三层次说”深化了“勇”的内涵,上等的勇敢,能够为天下人谋求福利,能够屹立于天地之间而不畏惧;中等的勇敢,能够礼貌恭敬,重义轻财,不惧权势,伸张正义;下等的勇敢追求私利,安于祸乱,不辨是非,逞强好胜。下等之勇即涵盖了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和小人之勇等行为,是被荀子所批判和否定的行为,中勇和上勇则是荀子所倡导的行为。“上勇”已经具有理想人格的意义,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体现,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风范与气度。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提倡后天的教化作用。“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因此,荀子认为血气刚强、勇猛暴躁可以以礼来调和,“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荀子·修身》),这种治气养心之术最直接的办法是按照礼去做,最关键的是得到好的老师。
综上所述,儒家对“勇”的认识比较全面。他们指出“勇”的本质是“不惧”,“不惧”的对象并没有局限于战争,而是针对一切人们所面临的危难;真正的“勇”即勇德,要以仁义为出发点,以礼制来规范,“勇而不中礼,谓之逆”(《礼记·仲尼燕居》);“勇”有类型和层次之分,凶残暴虐、蛮横逞强等看似勇敢的行为,其结果是对他人和社会的危害,因此是被否定的“勇”;“勇”可以培养,最大的“勇”是内心的坚定和刚毅。儒家将“勇”纳入了道德的范畴,并将“勇”与“非勇”做了明确的区分,将“勇”由一种外在形式的表现提升到心灵品质的培养。
二、传统“勇”德的当代价值
古代社会,“勇”德不仅适用于战争、政治、也适用于社会生活中,它不仅是一种具体行为,也是一种精神品格。远古神话中的英雄都具有“力量强大”“不畏牺牲”的特点,这虽是人们的美好想象,却也留下了远古先民真实生活的痕迹。私有制产生后,“勇”与人类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战争的决定因素,而“不惧死亡”就成为勇敢的标志。战争中为国捐躯是为了正义和高贵目的的死亡,这种勇敢行为的目的是善。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农业、文化的发展,人类生活更丰富,“勇”适用的范围更广泛,由战争中对将士的要求和评判发展到生活中对男性的评价,甚至影响到女性对男性的审美。有勇之人也因而受到各国统治者和贵族的重视,“勇”更是一度成为选贤举能的条件。
各种不同身份的人都有不同的“勇”之表现,这些具体的“勇敢”行为因人们所面临的矛盾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表象。“勇”是人类战胜困境的气度,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生之磨难的无畏,这是人们应具备的精神品格,各种不同形式的“勇”归根结底都是这种精神品格的体现。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选取了七十余位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将他们视为武士道精神的代表。其实在梁启超心中,武士道不是具有某种身份的人,也不是某些具体的行为表现,而是一种昂扬向上、积极果敢、无所畏惧、不苟且、不服输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是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待世界的态度。
孔子曰“勇者不惧”(《论语·宪问》),蔡元培说:“勇敢者,所以使人耐艰难者也”。高德胜认为“勇敢可以这样描述:为了‘肯定’善的、美好的价值和事物,经由审慎的思考和判断而‘否定’自身的恐惧,经受由此带来的痛苦。”由此可见“勇”的本质就是不恐惧,对于所有可能造成恐惧的危险因素不恐惧,比如战争、危害、痛苦、艰难、孤独、耻辱、疾病、死亡等等。时代、社会环境、身份、性别、价值观等因素使“勇”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形态表现,作为德性的“勇”一定是以善为目的的行为,是为了善的目的克服人类本能的恐惧,而不是对一切都无所畏惧。“道德的终极的起源和目的是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增进每个人的利益”。
简言之,“勇”是面对恐惧的心理态度和行为表现。这种恐惧可能来自外界,也可能来自自身,“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便包含着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因而能够克服自我心理上的恐惧,也属于“勇”的表现。“勇”观念的发展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一个不断丰富,不断演变的过程,从形态表现到概念内涵都有变化,但其对于善的选择和肯定的本质并未改变。当今时代,灾难、战争不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威胁,英雄与圣贤已经退出了人们的生活领域,但来自生活的压力、挫折、困难却成为我们最大的威胁,甚至使我们产生自我认同的危机,导致心理与精神的疾病。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不需要来自战场的勇武之力,不需要克服死亡的恐惧,我们更多的是要克服心理的恐惧,拥有坚毅的品质和行动的勇气。在时代的变化中,“勇”的内涵不断丰富,“力气”“力量”等原初特征逐渐减弱,“果断”“不惧”“刚毅”“坚定”等特征不断增加。语言中,“勇”所涵盖的不同意义,也渐渐被其他词语所代替。
王剑宇、胡文彬在《伟大的中国精神》中,书写了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华民族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中国精神,它们是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铁人精神、女排精神、抗洪救灾精神等等。这些形成于不同时期的民族精神,其内涵丰富,包含了爱国、民主、艰苦奋斗、不惧牺牲、勇于战斗、众志成城、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团结协作等内容。回溯历史,那些曾经名垂青史的仁人志士,曾经力挽狂澜的英雄豪杰,曾经无私奉献的人民公仆,在他们身上都体现着中国精神。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正是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精神的光辉,也正是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精神的传承。而“勇敢”就是中国精神的核心要义。
中国精神不只是一种民族精神,也包括个人品格。自2003年以来开播的《感动中国》栏目,被称为中国人的精神史诗。在节目历年的颁奖词中,勇敢、大勇大智、智慧、胆识、果敢、勤奋、爱国、无畏、无私、顽强拼搏、友善、博爱等词语屡见不鲜。无论是各个时期所倡导的民族精神,还是当代媒体所赞美的个人品格,其中都包含着与传统“勇”德相似的元素。“中国文化精神发端于伏羲,积蓄于炎黄,大备于唐虞,经夏、商、周三代而浩荡于天下,继之以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以至今日,绵延赓续了五千年乃至七千余年”。“勇”观念产生于春秋以前,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人们道德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有着普适性价值。
今天,我们所提倡美德教育以及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都有“勇敢”的内容。复兴中国文化,弘扬中国精神,是时代的必然需求。任何时代都需要道德的规范和引导,传统“勇”德的内涵及其延伸出的“精神之勇”,依然可以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将赋予它更为丰富的内涵。每个人都需要精神的支撑,也都需要美德的滋养。“勇敢”作为一种精神品格,关乎自我的调节与成长,更关乎自我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当前较为复杂的道德环境下,增强对美德的社会认同及自我认同,既需要加强道德教育和道德的自我修养,更需要社会环境的改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倡导传统美德,继承传统美德的积极意蕴,发展出新的内涵,应是当前道德建设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