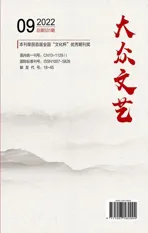一朵“迷人”的“恐怖”之花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恐怖与崇高
2022-05-17张忠喜
张忠喜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00)
一
小说《献》塑造了一个美国南方女子如何沦落为“活死人”的形象。主人公爱米丽是一位贵族的独女,自幼家父严管厉教,一辈子寄生于南方传统思想阴影之下,性格怪僻。后来,父亲死后,爱米丽对北方小伙荷默一见钟情,但却无法与其天长地久,并最终选择毒死荷默与尸骨共眠走完余生。在《献》中,恐怖和恐惧无处不在,美国作家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H.P.Lovecraft)曾说过“未知”是恐惧的来源。未知即不可预测,当小说故事情节不断展开,某种未知恐惧也不断到来,对小说中的主人公而言,他(她)可能变得不断紧张,失去理智变得癫狂,而读者可能经历一种“异质审美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怖恐惧也是一种美,也是一种崇高。康德说崇高需发生在“判断者的内心中”。实际上,他强调了人的主体性,人们“被扔出了自我感官的局限”并且抓住了自己内心的理性的崇高性,达到了认知的自由,这即是陈榕教授所指的“崇高的理性维度”。在小说《献》中,标题上的“玫瑰”就代表着一种“未知”,随着故事不断地展开,读者的想象力充满了使人屏气凝息的恐怖气氛。“玫瑰之争”一直持续到今天,因为小说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献一朵玫瑰花,但是小说读完读者却会对这朵缺失的“玫瑰”如痴如醉,痴迷不已。有学者认为“玫瑰”暗指荷默,这个曾经给她窒息腐朽的生活带来新鲜芳香的人,他曾带给他无限的勇气,使她面对镇上人的闲言碎语仍“把头抬得高高(high and mighty)”,但是荷默最终的背弃如同带刺的玫瑰一样扎伤了爱米丽,她杀死了他,永远的占有了这朵玫瑰,但也从此终结了自己“追求芳香四溢”的玫瑰爱情梦,玫瑰凋零了,但是爱情却在“死亡中得到了永生”。还有学者认为按照西方传统,人死了献上玫瑰理所当然。玫瑰可代指该镇居民的叙述者“我们”在讲述故事时对爱米丽所表达的敬意和感情。“玫瑰”也可以是爱米丽本人,她是美国南方传统的化身,也可能是小镇人心中不死的“南方玫瑰”。玫瑰也可能是作者福克纳献上的。福克纳在评价爱米丽时说:“我同情她,并借此致意,递上一朵玫瑰花。”在对玫瑰进行语意探索的同时,读者们会产生各种复杂的情感,玫瑰给人们一种忽近忽远的距离感,让人们不断感受到它带给人们的恐怖迷人的崇高感。一种恶心带给人们的愉悦感,这种愉悦感让人又感到难过。当人们理解了爱米丽,也就不那么恨她了。爱米丽的一生是悲惨的,可怜的,人们同情她。作为一个正常的女性,她能在那样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不断自由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顽强地表现她的人性,作为读者心理上是认同的,这种心理距离是安全的,虽然她选择了极端的方式获得了自己的“爱情”,虽然这是一朵“滴血的”玫瑰,虽然这让人们敬而远之,尽管这朵玫瑰有“恐怖”之处,但是它仍旧“迷人”。
二
人们不禁会问,这种“恐惧”的崇高感是“崇高”的本意嘛?康德所谓的“消极的愉悦”是什么样的崇高呢?谈道崇高,要从朗吉努斯谈起。朗吉努斯的崇高论有“五个要素”。但他的崇高似乎与“恐惧”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仔细思辨后会发现,朗吉努斯认为“崇高论的第一要素是思想性,但是也没有轻视情感的重要性”。后来,崇高论真正进入了美学范畴,于是出现了一批研究者诸如伯克,康德,席勒,利奥塔等。然后真正把恐怖恐惧与崇高关联起来的要属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伯克(Burke)。他认为恐怖要成为崇高需要具备这样的要素:“人类只有在面临恐怖的对象而没有真正危险,感到强烈的自豪感时,才感受到崇高;恐怖是崇高的主要效果,但是并非所有恐怖之物都能被感受为崇高”。换句话说,崇高来源于心灵所能感知到的最强烈感情(感情单因说),它也是不断关注痛苦,危险和恐惧的自我保持的情感,因此伯克的崇高论主导原则只能是“恐怖”。此外,伯克和康德都认可崇高能够引发不同寻常的愉悦的快感,但是前者认为这种感觉来源于主客体之间的审美距离而后者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愉悦,是我们的认知思维的无法把握之痛。一个是情感论,另一个是理性论,正如陈榕教授指出这种情感中的痛感也是一种审美,也是一种对生命力的肯定。正因为如此,伯克的崇高论才为18世纪英国哥特小说的发展添砖加瓦,指引了方向。小说《献》被誉为经典的哥特式小说,它吸收了传统英国哥特小说的诸多要素,也有了美国哥特小说的特色。这篇哥特式小说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便是死亡,在福克纳的作品中我们还能找到很多例子。死亡是恐惧心理产生的来源,而这也恰恰是伯克崇高论中的重要元素。小说以爱米丽小姐的葬礼开始,又以她的葬礼结束,“死亡”构成一个闭合圆形结构,让读者对死亡的印象颇深。小说中提到的三个人物的死亡更是强化了小说主人公爱米丽的悲剧命运。
首先,爱米丽的亡父(也包括爱米丽)象征着衰落死亡的南方,那些“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而爱米丽恰恰又是这样南方的产物。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南方社会新旧价值观,文化历史观,新旧社会秩序相互碰撞。时代前进了,而爱米丽却抵制时代进步,不承认不接受变革。她的思想与其外表亦极为相似:僵死,固执。虽然时代有所变更,可是爱米丽仍然墨守成规。她不肯接受父亲的死,父亲的死即是一种永生。一些研究者认为爱米丽的父亲如同“恶魔般的存在”,他是南方父权神话企图造就“南方淑女”的典型代表,亦是南方魔鬼清教思想的代言人。对父亲而言,爱米丽变成了“毫无力量把握自己命运的私有财产”。爱米丽的父亲就是一个高傲而自私的人,他让她失去了一个正常女人想要的生活。父亲长期禁闭的控制让爱米丽成了社会的“弃婴”,她的生活时时刻刻笼罩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她身心都“发育不全”,畸形满满。她没有办法与人正常的沟通交流,也没有办法对这个陌生的变化世界做出最积极的回应和适应。父亲对她的影响更是深远。父亲死后似乎也阴魂不散,他生前对爱米丽百般控制,他死后更是幻化为某种精神枷锁,对爱米丽的思想牢牢束缚,使其终生无法摆脱。因此,父亲的死爱米丽是完全无法认可和接受的,她甚至拒绝掩埋父亲的尸体。更可悲的是,爱米丽继承了父亲的一切;尤其是她父亲那傲视一切的性格(high and mighty)。父亲对她的影响,彻底改变了爱米丽的生活。她对父亲的情感是复杂的,既爱又恨,既想百般依赖又想奋力逃脱。父亲的死终于给了她解脱,她终于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生活了。可是他却被留在了父亲唯一留给她的财产——一座大房子里。她似乎像是中了魔咒,身心都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她被囚禁在这里,不能自已,她无法承认父亲的死,她终于疯癫了。她那象征着南方权贵不断衰落灭亡的父亲似乎正紧紧地抱着她,她因此而孤独,压抑,忧郁以致后来变得疯狂而变态,她的父亲制造了恐怖的场景,而爱米丽成功的遗传了它。
伯克认为“强权”是引发恐怖感,催生崇高感的重要元素。拥有“强大力量和权力”的主体,会对他人的生存构成威胁,由权力引发的暴力带给弱者强烈的痛感,后者将不可避免地“生发生存的危机感和毁灭的恐惧感”。爱米丽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拥有大权的父权制家长,他恶魔般的存在爱米丽的一生,他带着旧传统和社会的“武器”,折磨着爱米丽,让她不断产生焦虑,无助,抑郁等痛感,伯克式的恐惧油然而生,爱米丽变得毫无抵御和抗争力,不断被父亲操控,逐渐丧失理性,成了死神的俘虏。
其次,荷默彻底“杀死”了爱米丽,他的死诡异而令人惊恐,直到小说最后人们才知道是爱米丽杀死了荷默,也直到最后人们才知道荷默死在了爱米丽的家里,直到最后人们才知道这些年荷默去了哪里。小说一开始就提到爱米丽“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在小镇人们心中,她该是“南方淑女”-谦恭、隐忍、温柔、忘我,但是她却打破了这种传统。她孤高倨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和自主意识”。父亲去世后,她开始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也许是怕于孤独,也或许是对父亲无声的抗议。她心里也许在默念:去他的清教妇道观,极端父权制,见鬼去吧。她既要与社会相连,又要保持个性独立。但是,这种对峙状态最终让她打破了甚至失去了和谐,凸显了痛感。小镇上的人们痛了,他们不停地再说“可怜的爱米丽”。再后来,他们听说爱米丽买了砒霜“可能要自杀了”。又过了六个月后,人们再次见到了她,她的头发已经“灰白”,直到她去世都是这样。再后来,她再也不出门了,令所有小镇上的人们感到惊讶的是,荷默也消失了,他们开始同情爱米丽。
爱米丽的后半生就是在那个“父亲留给他的唯一的全部财产的”大房子里度过的。她对这座房子既爱又恨,既熟悉又陌生。哥特小说总是习惯性地把故事设置在经典场景例如居住场所。梁悦在《从恐惧感的宣泄到思想实验:西方恐怖小说研究》一文中写道:“当‘不同寻常’的事件发生在这个让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家),我们则感到意外和震惊和不安(无家)”。在小说《献》中,爱米丽逃进了小镇,但是小镇是封闭保守的,迫于压力,她又逃进了那个“大宅子”。但是这个大宅子也是封闭陈旧的:它被描述为一座“破败,丑陋,除了老仆人,至少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过的”宅子,宅子里有“阴暗的门厅”,“笨重的家具”,光线暗,尘封的气味扑鼻而来,空气阴湿而不透气,这种崇高客体的恐怖氛围营造了小说中这样的恐怖情景:整座宅子就像一座坟墓,而生活其中的是像“狄金森”一样的“活僵尸”。苏耕欣在《哥特小说-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文学》一书中写道:“封闭往往与罪恶形影相伴,非因即果。”的确,长时间的封闭,一个人的身心都将受到严重束缚,很容易找不到发泄的出口而扭曲变形。
在小说《献》中,爱米丽关在那个大房子里,缺乏正常的社会关系,没有母爱的滋养,去世父亲的阴影,被拒绝的爱情,小镇人们异样的眼光等一切让她喘不过气来,她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她的心灵严重扭曲。这种人为的封闭与世隔绝不仅丝毫不能压抑欲望,反而将人性引向另一极端扭曲。爱米丽以自己极端的方式(毒死恋人)永远地留住了荷默。爱米丽毒杀了荷默,成全了自己的玫瑰梦,也永远得到了自己爱的人,而在人们面前,她的“圆满爱情”玫瑰却是血淋淋的。也许她因为得到了荷默依然桀骜不驯骄傲自豪,但也许她也后悔忏悔自己做错了,从此封闭自己,凝固时间,守护着幻想中永恒的国王,陪着荷默的尸体度过余生。
人们的痛感或者说恐怖感会因为小说的情节发生转变,从最初的担忧焦虑慢慢地放松平静甚至获得一种满足感。也许这既是一种消极的愉悦吧,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也激起了人们心灵所能感知到的最强烈感情。痛苦感和恐惧感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弱小渺小。当人们能征服并且能够驾驭时,人类力量的强大则体现出来,随之强烈的自豪感和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当这种痛感产生的时候,人们会认识到自己和客体之间存在安全距离,自己不会被伤害,因而愉悦感自然产生。但是我们要明白“这种崇高的愉悦主要来自精神层面”。《献》呈现给我们的是爱米丽的恐怖之家,那个充满死亡的阴森的大宅子,不断把爱米丽推向绝望疯癫之境,小说中的人物以及读者不由自主生发惊恐感和痛感,这些造就了《献》独特的伯克式崇高美学效应。
三
爱米丽走了,她留给我们更多思考,她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个人命运悲剧。而且也是一部个人与历史,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庭相互纠缠的悲剧。爱米丽的悲剧也是美国南方女性的悲剧。掩卷而思,我们会问是什么使她从一个淑女变成了毫无人性的恶魔?答案是生活,生活中多种矛盾和不满,多种压抑和痛苦。爱情是美好而令人向往的,玫瑰是迷人的,因为它是爱的象征,但是死亡的爱情就是一朵凋零的玫瑰,它不再有芳香而是滴着鲜血的、让人感到恐怖的。伯克的崇高论也让我们认真审视小说中和生活中的“恐惧和恐怖”,不断地去思考人性,虽然他的理论在后来也遭到批判,但是透过福克纳的文本,这种旧南方传统,思想和文化连同爱米丽本人显现出了最“恐怖”而又“迷人”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