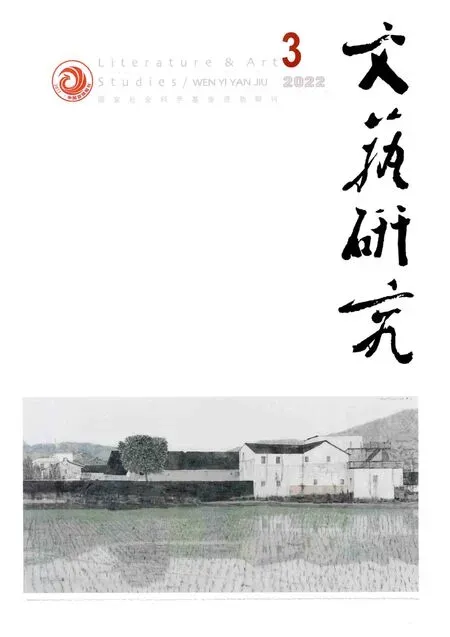贝拉·巴拉兹的动觉姿势电影理论
2022-05-12徐亚萍
徐亚萍
引 言
当代电影研究者一般将贝拉·巴拉兹的《可见的人》(Der sichtbare Mensch,1924)和《电影精神》(Der Geist des Films,1931)视为“经典电影理论”,即从媒介特性角度为电影的艺术和社会价值建立合法性的理论。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后占主导地位的语言符号学传统(关注电影的意指系统),经典电影理论关注媒介间的差异,在艺术传统和历史哲学的视野中,思考电影的性能对审美活动和普遍经验的影响。在巴拉兹看来,电影媒介之所以构成一种新艺术,在于它调整感知惯例,让人有可能更灵活地适应创造性进化的整体趋向。活动影像技术的可见功能,取决于人作为生命有机体的独特感知,即肉体性(本能、需求)和非物质性(感受、意识)的结合。在后电影、后媒介危机和重构电影价值的背景下,这启示我们要从感知活动的角度把握媒介的物质性转型。
格特鲁德·科赫(Gertrud Koch)认为,巴拉兹的电影理论之所以特别,首先是因为他在系统考察电影时提供了关于内在经验的一手材料。巴拉兹从自己身体内部的感知、感受、意识等纵深维度出发,以默片的姿势为基准,观察、描述、反思电影与书籍、绘画、舞台剧等文化形式的区别,以及电影技术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的过渡,从中揭示技术形式与生命的关系。在他的论述中,默片演员对身体运动的控制与电影的特写、摄影调度、视觉联结相结合,放缓了观者感知活动的持续时间。因此,“电影姿势”不仅是对象(表情、行走)也是形式(有节奏的运动),形式唤起习惯性和反思性感知的交替,即“电影微相术”,观者随着运动而持续感觉身体内部的触觉表面,把握过程性的现实。
电影姿势和电影微相术的提出,呼应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历史语境:机械论向生活世界渗透,而活力论从自我组织而非机械决定的角度理解生命有机体的特性。早期电影和电影理论承载了机械和生命之间的张力。1880年,英国医生查尔斯·巴斯蒂安(Charles Bastian)首次界定了“动觉”(kinesthesia)这一概念,即“运动”(kine)的“感觉”(aesthesis)。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尚未发展出系统研究躯体感觉的科学知识,但根据卡丽·诺澜(Carrie Noland)的考察,20世纪初的社会学、现象学已经开始重视身体的内在感应和外在具身姿势,甚至预见了20—21世纪认知神经科学的某些新发现。虽然巴拉兹没有明确将电影姿势界定为动觉姿势,但随着电影的机械运动而变化的内在感受和意识,是他理解电影特性的基本材料。
姿势唤起身体对运动的感觉。对于使用影像探究人体知识的19世纪欧洲现代医学而言,这是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材料,在20世纪初的大众电影中,这种科学探究意识被娱乐好奇心覆盖。巴拉兹试图揭示潜在于娱乐之中的认知进化,即“创造性的享受”。在效率管理理性利用感官运动机制推动工业合理化生产、异化人们的感知和行为的背景下,巴拉兹将创造性的感知视为对抗异化倾向的文化方案。从巴拉兹的角度检视创造性感知与技术形式的关系,对于克服我们当下的异化具有启示价值。
一、形式作为问题:巴拉兹的思想语境
在达德利·安德鲁的正典分类中,巴拉兹的电影理论属于关注电影人为性的“形式构成传统”和“形式主义理论”。现实主义、照相写实论强调电影有能力提供非中介的现实,而形式主义理论关注电影的建构性,尤其是电影的技术变量(摄影、剪辑、声音、色彩、表演等)和性能(陌生化、反常化、变形等)为审美活动制造的阻力和对日常自动感知的打断。矛盾的是,在安德鲁看来,巴拉兹之所以在电影理论史上占据了一个耀眼的位置,恰恰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坚定的反模仿论者,甚至即将踏入现实主义:接近技巧(如展示手势的特写)就是接近现实(被忽略的身体运动)。这意味着形式和现实是咬合的。
安德鲁认为,落脚于形式的揭示性是巴拉兹的自我矛盾。但这实际上透露了形式的多义性,因此有必要在巴拉兹的语境中重新认识形式的内涵。在与巴拉兹有交往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日常形式重复已知,获知未知则需要使用技巧对被呈现物进行变形,中断感知连续性。因此,尤里·梯尼亚诺夫(Yuri Tynianov)批评巴拉兹只关注“可见的人”“可见之物”等“再现的物质”,忽视了将对象转变为功能的“意义因素”(如景别、照明)。“可见的人”被误解为纯粹质料,体现了形式的双重性:电影最显著的性能在于对事物的模仿,即机械复制,同时,电影的模仿也是操纵现实,因此电影天然地具有创造力。电影形式的揭示性包含了复制和操纵,这使习惯和意识交替:在一个人认同于电影的连续体时,他也能有意识地体察技巧性。在巴拉兹看来,电影形式对这种交替状态的鼓励具有文化和历史意义。
马尔科姆·特维(Malcolm Turvey)认为,对于新技术和新感知的追求体现了巴拉兹的现代意识,这源于科学技术、工具理性大规模渗透进人类的生活世界、尤其是感官领域时,欧洲浪漫主义传统对这种倾向的批判。在20世纪初的现代性语境中,新感知为欧洲知识精英提供了一种克服文化危机(工具理性对主观维度的占领)的方案。对巴拉兹个人而言,文化危机最早表现为民族国家和工业现代性的认同危机。巴拉兹出生于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匈牙利的边陲,青年时代在中欧都会辗转游历,因不满于落后保守的贵族官方文化对社会的限制,产生了通过文化变革推动整体变革的意识。
在青年巴拉兹看来,找到合适的文化形式能够解决广泛的异化危机。在为文化形式赋予意义方面,巴拉兹和卢卡奇分享相似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历。他们都曾游走于德国思想家的社交圈,也曾共同创作戏剧、撰写评论、参与匈牙利共产党的文化工作。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党派斗争或社会运动,而是复兴艺术、哲学等直接诉诸感知的形式,因为“新鲜健康的社会”取决于“更好的人”。乔治·马尔库什(György Márkus)指出,青年卢卡奇关注小说、戏剧等文化形式,是因为它们有可能弥合日常与真实、心灵与体制的对立。在卢卡奇看来,生活是机械力量主宰的制度化、僵化的世界,这构成了不真实的存在状态;而心灵是真实的存在,包括个性、创造性、自我体验等。心灵回应生活的方式是形式,形式将多样混沌的事物和事件组织成有意义的结构,艺术形式选择质料、廓清生活中的混乱,因此有可能克服自我和世界的二元对立。对巴拉兹来说,作为心灵和生活之中介的形式应该是民间的、流行的,即符合自然需求的。
《可见的人》和《电影精神》将心灵与形式的关系具体化为感知与运动的关系:活动影像的运动形式经由感知转化为情感、意识。心灵不仅是卢卡奇意义上的被机械力量异化的个性,更是创造性进化意义上的蝶变一般的生命活力。电影形式的价值在于推动生命的蝶变,它提供的与其说是新艺术,不如说是为了感知新艺术而进化出的官能。因此,技术变革有着积极的内涵,因为感知将与技术形式共同进化。1918年以后,巴拉兹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将电影视为新的流行白话,试图借由电影增强普遍的创造性适应力,进而推动社会的转型。
巴拉兹的生命进化论视角源于齐美尔和柏格森。1906年,巴拉兹就读于柏林大学期间参加了齐美尔的美学课程。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最早由齐美尔译介到德国,巴拉兹对柏格森的吸收,既源于齐美尔在课程中对柏格森的讨论,也来自1911—1912年巴拉兹短暂停留于巴黎时与柏格森的直接交流。齐美尔认为,形式对生命而言,既是载体,也是限制,生命在不断流动中创造用以拓展自身、使自身可见的形式,但形式在产生后脱离生命的流动而僵化,生命必须不断创造新形式来代替僵化的形式。柏格森认为,形式的创造性源于有机体的本能和直观,有机体并不只是自动对环境做出反应,也可能进行有意识的活动,即直观:“直观指的是变得无功利、有自我意识、能够反思对象并且无限拓展对象的本能。”直观不同于知性,仍是感知活动,但是具有反思性。直观的对象不是某个定位点,而是感知的拓展,即潜在性被带入现时并产生将来倾向这一过程性现实,这种只能通过内部经验把握的过程性本体即绵延。绵延是内在的运动、变化、时间,这是电影中“可见的人”的非物质内涵:类似音乐对位,潜在的过去和将来在现时相互渗透,整体的生命冲动在个别的内在纵深运动中发挥作用,克服物质和肉体重量(实用性),构成创造性进化的整体。
肉体的运动变化(如肌肉用力产生紧张)可以唤起审美感知中的绵延,但柏格森并没有细究肉体性。出于批判抽象化倾向的目的,他在讨论艺术形式和审美感知时刻意忽略了形式的物质性,模糊了感知的多层面。保罗·艾肯森(Paul Aitkenson)认为,从生命哲学角度发展审美理论,亟需探讨“物质性姿势”,即物质、造型和肉体的相互作用如何让不可见的生命变得可见。在巴拉兹看来,活动影像提供了独特的物质性姿势,让心灵重新变得可见,这将弥补柏格森忽略的层面。
1919年秋,匈共政权解体,巴拉兹流亡奥地利维也纳,开始为政治日报《今天》(Der Tag)撰写电影专栏,以务实的方式涉足电影。这些专栏文章构成了《可见的人》的主要内容及其第二人称讲说性的、“清晰而谨慎”的修辞风格。搬到柏林后,巴拉兹加入了魏玛德国的文化复兴潮流,不仅为左派刊物《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撰写电影文章,而且参与了大量电影文化宣传和制作活动。在《电影精神》出版后,巴拉兹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因此不得不在纳粹上台后移居苏联。1945年,巴拉兹回到解放后的奥地利,出版了《电影理论》(Iskusstvo Kino),其中大量观点源于《可见的人》和《电影精神》,其英译本是“二战”后英语电影学界认识巴拉兹的主要来源。
二、电影姿势:表情与行走中的动觉专注
在巴拉兹的论述中,电影姿势既包括在屏幕上显现的姿势,尤其是面部肌肉的伸展收缩和肢体的动作,也包括观者内在的模仿性运动,比如随着特写、摇拍或剪辑视角的切换,观者会产生“我在人群中穿梭,我飞起来,我潜下去,我加入旅程”的动觉感受。巴拉兹之所以重视表情和行走的电影化呈现,是因为这两种姿势在日常状态中本就连续且有节奏,体现着过程性现实中相互渗透的多样状态,经由视觉形式呈现的有技艺的律动姿势,设定了接受的过程,鼓励感知者对运动轨迹持续投入触觉、动觉上的注意力。
以巴拉兹最推崇的丹麦女演员阿斯塔·尼尔森(Asta Nielsen)为例,在电影里,尼尔森看向窗外时,眼睛、嘴巴周围的肌肉逐渐放松、调整,表情从最初的恐惧、震惊变成犹豫、疑虑、急切、希望、审慎、愉悦、幸福、狂喜,观者和她同步(甚至先于她)意识到,向她走来的不是灾难而是意中人。为了描述实际上不可分的经验时间,语言设置了急切、希望、狂喜等代表质变的定位点,以便我们意识到纵深过程的多样性。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在巴拉兹看来,文字表达的是断音,而内在经验是连音、复调、和弦等复合体,各种质性状态是渗透交替的。能控制表情的演员是有意识的经验者,能让潜在的品格在感知中可见。比如埃米尔·强宁斯(Emil Jannings)在扮演奸商时,既展现邪恶吸血鬼的特征,也加入天真的、令人同情的细节,从而并置了潜在的善与实在的恶。面部表情作为复调意味着(基于跨媒介、互文本、前电影的)记忆中的潜在形象与屏幕上的实在形象相互渗透,影响感知者的判断。
巴拉兹有意识地使用比喻性的非固定词汇描述面部表情的连续变化,传达有机的内在感受,唤起读者对过程的警觉,尤其是频繁使用音乐比喻,如“对位”“泛音”“慢板”“快板”“渐强”等,电影姿势因此带有了音乐的绵延属性。音乐是柏格森用来说明其绵延理论的原型,聆听音乐时,听者的注意力被强迫性地切换,日常生活的物质限定被悬置。相比于自然的声音,音乐的声音更有力地影响我们,因为自然的声音符合感知惯性,而音乐的节奏和拍子“唤起感受”。这是巴拉兹将电影视为“运动和有机连续性构成的时间艺术”的内在原因:电影与音乐都是有节奏的运动形式,在我们占据电影运动的节奏时,我们获得了对运动倾向的感受,从而克服光学对视觉的限定,进入感知的纵深过程。从肉体可供性(affordance)角度而言,这是因为适应某种节奏时,运动更省力,正如形式主义者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指出的,跟着音乐的节拍走路或者在热烈交谈中行走,比没有节奏时更轻松,因为“行走的动作从我们的意识中消失了”。
(2) 权重的计算考虑了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两种权重计算方法,并且通过熵值对两者进行加权组合,充分利用样本数据,增加了权重的科学性,进一步提高了评价模型的准确性。
巴拉兹将默片演员的行走视为“最重要且非常特殊的电影化姿势”,这是因为电影不仅通过机械复制保留了日常行走的连续节奏,而且通过技艺和技巧,使其在感知中显现出更强的紧张度,从而唤起身体间的联结。巴拉兹的四个关于电影中的行走的例子,揭示了生命适应技术而拓展的自我组织活力。第一个例子是阿尔弗雷德·阿贝尔(Alfred Abel)在《魅影》(The Phantom,1922)中扮演的小公务员在街道上独自步行,巴拉兹看到了存在于他自身的危险、他的内在创伤。阿贝尔的行走与阿基里斯的步伐一样,是自为的内在经验,区别于知性通过外在表征划定的客观长度。活动影像的机械复制性能够为无法言说的内在经验提供表达条件,但这区别于语言表征。

第三个例子是《归家》(Homecoming,1928)的一组同景别相溶(dissolve)镜头。主人公的双脚被置于视觉中心,实际的行走时间被压缩为三分钟的屏幕时间,在观者看到双脚外观逐渐改变(鞋子破损、赤脚、流血)时,三分钟的镜头时间又被拉伸为“我们感到数年过去了”的感知时间。这不仅说明“电影的物质”(the substance of film)是身体技艺与特写、摄影调度和视觉联结等技巧的结合,能够使内在经验在感知中变得可见(三分钟唤起数年),而且说明克服阻力一心一意行走的韧性、意向性,尤其能呈现和唤起动觉专注。电影中的意向性移动,让生命秩序(意志、自觉的行动)和肉体秩序(自动机械运转)的张力变得可见。
第四个例子是在旅行和探险主题的游记电影中的行走。长途跋涉不只是吸引力景观,它作为意向性移动决定了形式(叙事动机和发展)。巴拉兹认为,这些行走体现了生命对形式的主导、生命和形式的嵌套,电影因此成为“生命的艺术”。因为跋涉中的新生命经验反馈进入形式,电影形式与流变生命共同进化、递归发展,形式不再是对过程性本体的快照式截取,而是过程本身。
三、电影微相术:身体的能动取景
对巴拉兹来说,在电影中重新可见的不是梯尼亚诺夫所谓的“再现的事物”,而是被习惯和肉体需求抑制的种种潜在性。电影姿势提供的动觉专注,让我们从原始观众变成创造性享受的主体,这是因为惯性辨识活动被反思性感知渗透。这种反思不是理智,而是将潜在带入现时,影响现时和将为的意向。不同于科学度量或知性分析,反思性感知构成直观,让我们从具体中压缩出共相,从而重塑我们的判断。艾肯森认为,视觉艺术达成直观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模仿不可分的整体(如风景画),二是通过变形(如点彩、漩涡)唤起观者的动觉感受,观者借此想象世界在创作者直观中分化和整合的张力过程。而电影有复制和变形双重性能,可以将两种直观同时纳入,使辨识和反思的交替更集中、活跃。在巴拉兹看来,这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即电影微相术。








在巴拉兹看来,带有文字印刷文化陋习的观众和制作者,用光学原则理解电影,排除了视觉感知中的触觉、动觉,这反过来巩固了文化政体。不符合习惯的电影调度虽然能让我们脱离惯例,但需要观者费力克服阻力。有意识的重复操演可以将动觉专注变成身体的需求、形成新的习惯,电影的商业理性为习惯的重塑提供了经济条件。但是,新技术和复杂技巧不断出现,或者让制作趋于保守,或者使感知更费力,加之社会政治的动荡,实现创造性进化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紧迫。
四、回到内在经验:姿势论的比较





结语:动觉姿势的方法论启示
巴拉兹的动觉姿势电影理论揭示了电影的性能(复制和变形)和姿势控制技艺在调节内在的过程性现实方面的力量:感知被强迫性放缓,这为身体的能动取景提供了契机。反思与习惯的交替构成了身体内部的姿势,即内在的动觉专注行为。基于此,电影研究、文化研究、媒介研究需要重视多层次的肉体性(感知可供性、习惯、有意识的活动),并借此重新理解经验的内涵:物质性经由肉体性转化为非物质性的过程性本体。因为动觉专注是对身体内部姿势的意识,研究者需要重视第一人称内观的材料价值,关注身体里面的意向轨迹。
媒介化的经验取决于成像技术和姿势控制技艺对触觉距离和动觉专注时间的调节。活动影像作为时基媒介,推动了主动合成共相的活动和感知技艺的进化。唤起律动姿势的形式与生命咬合、嵌套发展,是理想的形式,这为理解媒介生态提供了一种生命哲学视角。自然主义的电影本体论在强调电影的表征时,往往脱离身体内部的触觉连续性、全身的张力分布和身体间的律动交感。后电影状态让我们更容易看到,电影的危机实际上是自然主义离身观念的失效。
形式可以唤起感知者对潜在行动的选择,这使实在行动变得不可预测,这种不确定性是创造性进化的条件。这为思考结构和能动性的问题提供了一种非决定论的资源:在时基媒介为身体提供的犹豫迟疑的时间中,具身活动有可能改变意义,个别的响应行动有可能调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