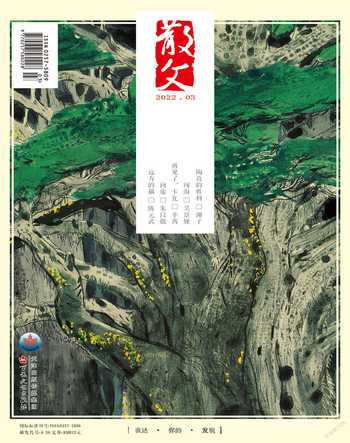三声狗叫
2022-04-30周蓬桦
周蓬桦
雪橇犬灰娃
在热炕上睡了一个长觉,睡到自然醒,伸了个舒服的懒腰,而乌力早已起床,牵着他养的雪橇犬到河边溜达去了。远远地,能听到乌力呵斥狗的声音:“嗨!哪儿去——回来!”透过木窗棂,可以看见那只名叫“灰娃”的白花雪橇犬在雪地上撒欢,倚着一株岳桦树捋毛蹭痒,一会儿又一溜小跑,在结冰的河湾留下一串爪痕。
火炉把室内烧得暖融融的,窗户上树影滑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把尿壶拿出去倒掉,这黑釉老瓷器制作的物件端在手里有种异样,想这东西有几十年没用过了,而在林区冬天的山里过夜,它又神秘地派上了用场——它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冬天:夜黑咕隆咚,我被一泡尿憋醒,吸到鼻孔里的是一股煤烟味儿,顾不得睁开眼,一双冰凉的脚摸索着找棉鞋,感觉触到了炕下的尿壶,把那东西朝脚边拉近,急急地撒下一阵响亮的雨声;过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放松和愉快。当然,没有瞄准目标的情形时有发生,一夜发酵,弄得满屋都是尿臊味,早晨醒来,第一件事是要挨母亲的一顿斥骂……
此刻,我手里提着尿壶,仿佛提着一壶童年的记忆,辛酸而又有些许甜蜜。抬眼,看见满山枯枝朦胧,百里山林已经被白雪抚摸过了,通体散发古意,活脱脱一幅黄宾虹笔下的山林雪野图,与我的故乡鲁西平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哦,是谁让我来到了这片风雪呼啸的山林地?这神秘莫测的命运,这陌生而又亲切的地理。
我时常想,人和某个地域的缘分,恰如人和物的缘分,以及人和狗的缘分一样,既神秘又有因果联系。比如昨晚,啃着新出锅的热气腾腾的野猪肉,乌力向我讲起了他的牧羊犬:那年夏天,他在巡山时误入一片原始森林,在一处水塘边发现一幢木屋,乌力踩着厚厚的腐殖败叶悄悄走近,又停留脚步经过一番观察,断定这是某一部族的猎人后代留下的,数十年前禁猎令后,他们大多更弦易辙,靠种植草药和养殖鱼虾为生,由于长期独处山林,他们早已习惯了自由散漫的日子,也放弃了融入外部世界的想法,便选择在森林茅屋过完一生。他们是山林中的悲伤的寄居蟹,在经历数十个春夏秋冬过后,回归泥土,自然消亡。
乌力走进这幢被废弃的茅屋,推开虚掩的木门,竟然看到破败的屋舍内还保留着主人生活的面貌:屋梁上悬挂的红灯笼,土灶前的干柴草,桌子底下装有大米的瓦罐……令乌力惊讶的是,铁锅台上的一把小葱居然还没完全枯萎,剥掉一层葱皮,露出新鲜的葱白,乌力咬了一口,满嘴的猛辣味道。这说明屋主不久前还在这里生活,每晚点亮灯笼。是什么让他丢弃了自己热爱和眷恋的山林?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主人究竟去了哪里?都成了谜团。乌力知道在森林里,类似的荒屋有很多,他本人无意探究,因为不会有结果。可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却隐隐地听到哪里有一丝微弱的呼吸声,夹杂着若有若无的呻吟声,顿时警觉起来。起初,他以为是躲藏在某处的狐狸,找了半天,在屋后发现一个草垛,草窝里居然瑟缩着一只奄奄一息的狗!它全身沾满草屑和土灰,像一个灰不溜秋的小怪物。乌力用木棍拨弄它,竟然没有任何反应,它已经虚弱得没有一点力气了,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乌力断定这是一条失去了主人的雪橇犬,这真是一个生命力顽强的小家伙,不知是靠什么意志活下来的,看样子像是生了重病,怕是坚持不了两天。乌力决定尝试救它,就从屋内找了一条破麻袋,打算把它背下山。
一路上,乌力背着病狗,一颗流星在夜空滑落,他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向山神祈求护佑,不要遇到虎狼和棕熊,不要让蟒蛇缠住了他的脚。最后,凭借一支指南针的引领,他走出了这片森林。
把狗背回家后,乌力到河中汲了一桶水给它洗澡,熬了点小米汤喂它,它瑟瑟地抖着身子,不肯吃。乌力找来屯子里的兽医独活大叔前来诊治,独活大叔即便在夏天也戴着白线手套,他连声惊叹,说这条狗命真大,因为它身上生了好几种病:皮炎、外耳炎、下痢、心丝虫病等等。失去主人后,它在森林里像个孤儿,承受了几个月的风雨雷电,靠吃草虫子活了下来,如果不是碰巧遇到乌力,恐怕只能撑一两天了。
独活大叔走了,留下一堆救狗命的药。从此,除了每天的巡山采药,乌力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了雪橇犬身上。一个月后,这只命大的雪橇犬终于恢复了体力。让乌力印象最深的是立秋那天,狗跑到河岸上,对着远山发出一阵汪汪的吠叫——这是生命的叫喊呀!他原本在茅屋里拿一盆水往身上冲凉,听到狗叫,激动地跑出门,跑到河岸上,扑倒在地,一把抱住了狗,在草地上痛痛快快地打了个滚……此刻,那只恢复了健康的狗承受着乌力的爱抚,从嘴里发出一阵模糊不清的呜哇声,只见它从眼角往下淌泪。乌力当即给它取了名字:灰娃。嘿!灰——娃!这小小的雪橇犬像刚出生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一个新家。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灰娃就像是河岸上的小白桦树,似乎一夜间奇迹般长高长大,很快成了一条闻名乡野的雪橇犬。
概括而言,原因有两条:一是它拥有一副野狼般英俊的外表,但比真正的狼可温驯多了,白花皮毛油亮光滑,总是警觉地高高竖起耳朵,一双漂亮的灰蓝色眼珠,在黑夜里也闪着光芒;二是它聪明且善解人意,能听懂人话,除了看家护院,两年来乌力已经教会它许多难度极高的本领,比如它能记住许多屯里人的名字,某次乌力借了屯里人的麻绳,由灰娃叼在嘴里去还,圆满完成了任务。某次乌力做饭,往锅里贴粗粮饼子,灰娃居然摇着尾巴帮忙拉起了风箱……在乌力眼中,灰娃除了不会说话,什么都会,智力上像一個年幼的孩童。
令他没想到的是,屯里人围绕着这条狗,进行了一些艺术加工和编排演绎,风一样传播开来,神乎其神,有人甚至扯到狐仙身上去,说灰娃是狐仙成精降临人间……乌力听了,只是摇头笑笑,并不多作解释。
一天,他牵着狗从山里归来,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他的茅屋前围满了人,老幼兼备,有人对着柴垛前的狗窝磕头,有人点燃了纸钱,风一吹来,弄得满天都是纸灰,像翩翩飞舞的虫蛾。
此后,类似的事情还时有发生,都被乌力用极其温和的方式处理妥当——除了无边呼啸的山林,他也太爱屯子里的乡亲,不忍用生硬或粗暴的态度对待他们。他知道山凹屯子里的人都善良,只是文化水平有限,对事物的理解能力不够,尤其是一些老人,习惯用陈旧的思维解读一切,一有点风吹草动,便祈求神灵的护佑。“其实,”乌力对我说,“人们都想多了,世界哪有那么复杂?”
我表示赞许地点头。尽管乌力出生在神秘的山林里,而且父母双双早逝,他却依靠自学和接收外部世界的信息而绕开了各种蒙昧,这也是我们之间能够建立友谊和对话的缘由。在他眼里,这条雪橇犬和世界上的狗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只不过略显聪明就是了。重要的是,雪橇犬是他的生活伙伴——帮他拉柴,和他一起上山采货,也时常和他怄气,陪他度过冬天的漫漫长夜。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暴风雪下,地动山摇,树枝断裂的声音四下响起;而茅屋内炉火正旺,火光映照着乌力清秀的脸,一绺黑发遮住了右眼;那只雪橇犬偎依在他的脚下,伸长了舌头,打着哈欠,摇着尾巴……
三声狗叫
我见过狗追流星的情景——那天晚上,阔大的雪野一片洁白,蒸腾的雾气从河边缭绕升起,夜游的鸟和蝙蝠似乎飞满了夜空。突然,唰唰唰——三颗流星呼啸着划过天际,一颗接着一颗,落在了不远处的雪窝里。当时,我愣住了,因为我从未见过流星以这样的方式降落,仿佛從天空落下三滴明亮的泪水,是神灵点亮的三盏灯笼——我早就听说,白山一带的流星很小,像粒粒萤火虫,捡起来拎在手里,可以当马灯。当然,这只能是传说。
而流星的每一次降落,都惹得机警的雪橇犬驻足仰头,顷刻后一路狂追,身后雪沫飞溅。
“汪!汪!汪!”
随着三声狗叫,沉睡一冬的白山和错落有致的屋舍被骤然唤醒,先是屯子里的狗跟着叫,接着是远处林中藏匿的狗也叫起来。一时间整个山野一阵骚动,叫声此起彼伏,像过春节放鞭炮,又像野鸭扑通扑通地跳入河中,生灵们都睁大了机警的眼睛——那些流浪的野猫和野獾,藏在树洞中的浣熊和松鼠,松枝上的啄木鸟和白嘴鸦,灌木丛中的红狐,柴草垛里的黄鼠狼,以及泥土中冬眠的蛇和蜷缩成一枚枯叶的土鳖虫。
此刻,它们都翻转身体,全神贯注,侧耳谛听,像人类迎接节日那样,迎接三声狗叫。
这些大地上的野性生灵啊,对声音、气味和天气变化有着天然的敏感,哪怕只是一点微小的动静,也逃不过它们的耳朵、眼睛和鼻子——它们是天才的美食鉴赏家、星相学家、气象预测工程师、房屋建筑师和高尖端的地形学家。
以形体微小力量薄弱的蚂蚁为例,在夏天的树荫里,一只小小的蚂蚁,其头部、触角、胸部和前脚的胫节都含有听觉器官,能够感受数十米开外的声音振动。它们的触角除了有精确的味觉、嗅觉和听觉之外,其触觉更为敏锐——触角上密布短短的触毛,触毛的根部与发达的神经末梢相连。长白山脚下的著名蚁类,分红黑两种,力大耐寒,即便是百年前火山爆发,岩浆滚滚,万兽逃亡,虎狼尸横遍野,却也没能将其消灭殆尽。
由此可见造物主是多么公平——蚁类虽小,小到被其他物种视而不见,但正因此,它们拥有生生不息的庞大家族,已经在地球上繁衍亿万年之久,而与之同时代的种种巨兽猛兽,一度猖狂到不可一世,却早已灭绝,只剩下博物馆里的一具具骨架。
比较之下,人类的整体文明尽管发达,但感觉系统堪称迟钝,即便进入科技时代,依然在诸多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付出巨大代价。尤其要命的是,人类的免疫和抵抗能力更在飞速下滑,活得越发娇贵,冬天怕冷,夏天惧热,春天乏力,秋季消沉……这是长期生活在象牙塔中养成的“城市病”。
再看读书人与饱学之士,大多都表示厌恶城市。可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又都选择往城市里跑?为何对勤劳的乡民们抱有歧视?为什么甘愿过一种“蛆虫式的生活”,甚至甘愿在城市的“坟墓”里沉沦?
人类被时光追赶,但并不是向前跑,而是朝一个东西莫辨的无间方向跑。人们把身体放置在相似的容器里,被时间驱使得团团转,便觉得生命的意义在丧失,人之存在变得可有可无。因为真正有效的时间,不再属于人本身。
在这个关口,每位思想者或大地赤子,都应该到山野中来居住一段时间,穿上草鞋,戴上斗笠,披上蓑衣,迎接风雨的沐浴,体验一下另一种人生滋味。要弯下腰身,放下板结的旧有经验,运用精密逻辑,进行一次深度田野考察,做一番调查研究。从原生态中汲取精气,详细了解每一株树的生长过程,细数每一道年轮中储存的信息;去探访每一块石头与每一株植物的形成,它们与这片森林的关系;熟悉众多生灵的日常活动、食物生态链和居住环境,接触和抚摸一下潮湿的泥穴、古老的山洞和风雨中飘摇的鸟巢。
观察自林中冉冉升起的太阳,看光线穿越枝杈,照亮树身的伤疤。
当然,除了以上,这里还有大规模的流星雨,还有三声狗叫后苏醒的森林:河流解冻,春天再度来临,林间遍开野花。乳白色的炊烟袅袅被风吹远,蓝天徐徐降下圆号般的深沉旋律,群山遥相呼应——这是大地奏响的一支古老沧桑的乐曲。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