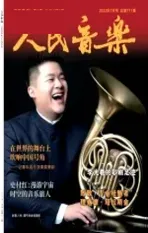音乐史学的有声媒介研究与中国戏曲之未来
2022-04-29李淑琴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馆员任思博士的专著《芳韵绝音——梅兰芳1920—1936唱腔艺术衍变研究》,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2022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鉴于该著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领域中所具有的某些新意,恰与笔者平日在教学与研究中的某些认识契合,特借其出版之机会撰写此文,以求教于各界同仁。
一、文化转型与学科背景下的选题
19、20世纪之交,西学东渐大潮中的风云人物梁启超,在历经维新、办报、讲学,大力提倡变法改良、文学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后,晚年转身沉醉于国学的故纸堆中。同时代西乐东渐的三员主将,同样在经历了东洋求学和投身新式学堂乐歌运动后,不约而同地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曾志忞投身京剧改良、李叔同皈依佛门、沈心工潜心古琴。中国文化,可以说,在这般的中西选择中获得新视角下的重新审视,拉近了与西方音乐文化对话交流的距离,也令自身焕发出新的生机。
20世纪80年代以降,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使国人切身感受世界不同文化成为可能。21世纪以来,日益发达的信息传递手段更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往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且让中国文化成为了全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正所谓拉力越紧,张力越大;眼界越开,自我身份认知的欲望越強。经过一个时期的极目远望,如今令人欣慰地看到,同百余年前开放后的回归一样,回归民族传统文化的潮流正在形成。而在音乐领域,这一文化转向已取得明显成效:创作界从观念到技法上的回归已带来音乐风格、样式上的悄然变化,尤其通过民族器乐创作展现出的具有自身独特性的作品,成为音乐文化回归的风向标;在研究界,转向自我的趋势近年也日趋明显,以往以西方音乐文化为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学习西方、研究西方、消化西方的作曲技术理论、西方音乐史学和音乐美学界的学者们,在各自的学术背景下纷纷推出的中国音乐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而为中国音乐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机;而对于本就以中国音乐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也出现了转向的迹象。
事起本世纪之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界展开的“重写音乐史”和同时期在更广范围展开的“回顾与反思”两场大讨论。针对当时学界出现的“不大赞成新音乐传统”甚至否定这一传统的潮流,以及另一种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和论著“只需大略讲讲甚至可以不讲古老传统音乐的发展”的观点,音乐史学耆宿冯文慈先生在2001年中国音乐史学会上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前者忽略了作为“新学”组成部分的新音乐业已扎根中国社会的历史原因;后者则对中国古老传统音乐文化的深厚积淀估计不足。由此提议,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实际教学与研究中,“两个传统并存”和“古今衔接”应该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冯先生所说的“两个传统”,一为“清末学堂乐歌以来大约百年新传统的音乐文化”,一为“先秦以来古老传统的音乐文化”。他认为,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两个传统并存是客观存在,应该在教学与研究中“并存并重”。冯先生所言的“古今衔接”包含双重含义,一重意指20世纪以来接受西方艺术音乐影响的中国新音乐与古老传统音乐文化这“两个传统”的相互关联、彼此衔接;另一重意指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在教学与研究内容上,与同以中国音乐为关注对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有关内容的衔接。①
冯文慈先生的发言在史学会上曾引起很强反响,更被上海音乐学院陈聆群教授认为是“重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正确的突破口”②。尽管两位前辈的倡议在当时业界荡起了一波涟漪,但20年过去后的今天,在实际教学与研究中的反应却显得有些“光打雷不下雨”,所见成果甚微。究其原因,依笔者浅见,固然与中国传统音乐种类浩繁,各地各民族音乐发展情况不均衡,以及由此为音乐史角度的研究带来诸多实际困难有关,也与过往音乐史在对待中国古老传统音乐问题上过于受限于中国传统音乐学科民间音乐“五大类”的思维定势有关。就此,笔者曾在拙文《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中写道,若想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新发展进行有效的史学研究,有必要打破这一思维定势,“而将重点放在那些在近代发展成就突出,具有近现代特征的剧种、曲种和乐种上,从中考察流变,总结新发展之规律”③。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之所以在对中国传统音乐新发展的研究上举步维艰,在笔者看来,还存在另一个现实问题。这一点,在十几年前的一次中国戏曲学院学科论证会上笔者曾经谈及:当下的学科分类,以戏曲为例,与音乐处在分离状态,无论演出机构里的艺术家,还是教育机构内的师生,抑或展示研究成果的期刊杂志,戏曲均隶属戏剧领域,属于中国戏剧家协会。如此,虽然强化了戏曲的文学、戏剧地位,却令戏曲音乐的研究处于尴尬境地,进而造成戏曲音乐研究与中国音乐史研究渐行渐远的现状。
纵然,研究上的各自为政与客观因素有关,然而在当今网络发达的信息化时代,这一客观因素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任思博士的专著《芳韵绝音——梅兰芳1920—1936唱腔艺术衍变研究》,即是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角度做出的新尝试。
这是一部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善的著作。鉴于戏曲音乐研究与音乐史研究分立的客观现实因素,笔者作为任思博士在读期间的指导教师,在选题基本确定后,经历了一次与作为戏曲的代表性剧种京剧界音乐同仁们的接触过程,并先后得到中国戏曲学院李晓天、费玉平、海展等教授的指导。④
经过这一过程,加之曾经与戏曲理论界前辈何为教授、余丛教授的短暂交往,让笔者领略到当今戏曲界学者们的开阔襟怀,也证明了打破学科壁垒,共同推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是完全可行的。只有音乐史学界与戏曲音乐界同仁们的通力合作,彼此支持,才能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对戏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才能适应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使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理想得以真正实现。
二、作者情况及该著的特点
任思之所以以梅兰芳唱腔衍变为选题,首先是基于前述学科背景,希望借博士论文写作机会做一些创新性的尝试;另外,客观上,梅兰芳先生的艺术成就具有既和时代紧密关联,锐意出新,又有深厚传统传承,悉心守护的特点,且留下的相对丰富的音响已经诸方整理得以公开出版,为研究提供了条件;再有便是基于作者之前的教育背景。
在笔者看来,前期的积累对于博士阶段的论文写作至关重要。任思本科、硕士均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接受过中央音乐学院体系内相对完整的教育,这些都无形中为这一选题做了准备。从本科论文《石家庄丝弦戏历史发展研究》(2009年)开始涉足戏曲研究,硕士论文《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二胡音乐作品研究》(2013年)在本科论文历史梳理能力训练的基础上,进一步尝试将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分析方法运用到二胡作品的分析中,这些积累成为其博士论文选题的前提条件。
在笔者看来,任思的研究成果在以下几个方面展现出了较为突出的特点:
第一,史学研究,重在严谨求真,丰富扎实的史料工作,是通往求真目的地的起点。该著在前人梅兰芳唱片史料梳理、梅兰芳京剧唱段乐谱出版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所有相关唱片进行了校勘,再凭借经过专业训练的敏锐听觉,根据唱片,对乐谱进行了补充和校正,为全文进一步的分析、论述打下了基础。此外,文中还佐以文字史料,这些史料对梅兰芳唱片的灌录过程、唱片与演出的呼应关系以及在唱腔音乐设计方面的想法进行了补充。在集中于理论阐释的第五章,文字史料进一步扩展到社会、文化,团队和个人,使全文呈现出史料工作扎實丰富、精良系统的特点。
第二,历史角度的京剧研究已有了丰硕的成果:戏曲通史中的皮黄戏与京剧史、戏曲音乐史内的京剧唱腔衍变史、现代戏曲中的京剧现代戏发展史以及京剧史、京剧唱腔源流和新发展等,成果不一而足。这类成果从宏观层面揭示了京剧在整个戏曲史中的位置和在近代以来的新发展,在帮助人们认识京剧上功不可没,也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起点。在微观个案研究上,以往的京剧唱腔研究比较集中于对某一具体唱段的唱词结构、旋律发展、板式变化维度的分析,这些分析加深了对京剧音乐的认识,也为历时性的唱腔研究积累了可兹借鉴的方法。与以往或宏观或微观的研究成果相比,任思的论著选择以梅兰芳鼎盛时期唱腔艺术的衍变进行微观历时性研究,时间范围限定在从梅兰芳灌录首批唱片的1920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16年的时间,从历史学范畴看范围是狭小的。另一方面,在借鉴以往京剧音乐研究从旋法、板式、调式、结构、伴奏、唱法、唱词关系入手的基础上,该著进一步聚焦于音乐性得以集中展现的润腔、拖腔、伴奏音乐的分析阐释,在研究的空间上也似受到了严格限制。之所以如此选择,首先基于梅兰芳艺术改革“腔新有度”、细节上求变的艺术理念和实践,同时也力图从深度上揭示梅兰芳唱腔艺术的衍变轨迹。
由于上述研究对象在时间、空间上的限定,带来该著研究方法上的新尝试,其中比较突出的在于借鉴了文化阐释学理论中的“深描”方法,全文不仅对梅兰芳唱腔艺术中的润腔、拖腔、伴奏音乐这些具体现象进行微观细读式分析,更为重要的是,运用“深描”手法,动态地揭示出其衍变的实质和意义,总结出梅兰芳唱腔艺术“趋渐丰富,繁中有简”的特征。因此,“微观细读、层层深描”成为该著的又一特点。
第三,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然而,历史视角的研究却始终苦于音响的缺失,因此被业界人士自嘲为“哑巴音乐史”。现代科技的发展,近代唱片业的出现,使音乐不再稍纵即逝,而固化于特殊载体之中。京剧唱片是伴随中国唱片业成长的历史见证,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兰芳艺术生涯的鼎盛期,恰已形成规模。得益于记录了梅兰芳16年中的演唱音响,使后人对其唱腔艺术衍变的研究有迹可循。“任著”即是从唱片所记载的可听可感、活生生的有声音乐入手展开的历时性探讨,再辅以与梅兰芳前辈与同代京剧表演艺术家灌录的历史唱片的纵横比较,使音乐史角度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从文献、考古、图像等无声间接载体变为记录着音乐信息原貌的有声媒介,改变了研究中“哑巴音乐史”的遗憾。
为有效获取唱片中的音乐信息,作者运用计算机音频测试软件对润腔中的倚音、颤音、波音、落音、断音进行量化分析,对演唱速度与节拍、力度与发声进行图形化展示,再配合以谱例、释文和作者的听觉体验,展示了可听、可读、可感的立体化效果。更为可喜的是,对于读者而言,作者与出版社合作,将文中涉及到的梅兰芳1920—1936年间珍贵历史唱片音响剪切编辑,扫码可听,使梅兰芳唱腔艺术在鼎盛时期的渐趋丰富圆润和委婉流畅的衍变轨迹,从书面阅读变为了有声可感。
第四,尽管该著主体五章中有三章集中于微观分析,但并不意味全文仅停留在细碎分析层面。宏观上,作者不仅对京剧早期唱片进行了梳理,对梅兰芳唱腔艺术的衍变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还对其成因从社会、文化、团队、个人不同层面加以剖析,最终提出了自己对京剧未来发展的看法。因此全文的特点还在于微观分析与宏观提炼的平衡。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该著在行文上的考量。由于中国古老传统音乐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留下了许多形象生动、口语化明显的专业术语和表述习惯,但是,也由于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而导致读者或研究上的不解,甚至歧义。如何即保留这些传统术语,又体现行文上的学术化表述,作者在该著中也做出了一些尝试。
三、音乐史研究与中国戏曲的未来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生活发生了全方位的巨变,音乐自不例外。音乐的巨变,尤其体现在传播方式上。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媒介的不断推出,颠覆了传统同时空下面对面的表演和聆听,而这种改变,恰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任著”通过唱片所提供的音乐信息对梅兰芳唱腔艺术进行的研究,使冯文慈先生提倡的“两个传统”“并存并重”的倡议得以实现的可能,尤其对于探究中国古老传统音乐在近代以来的革新与固守具有启发意义,并提供了可兹借鉴的新方法。联想到笔者另一位学生孟乔的论文,曾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有声电影中保存的民族器乐音响的挖掘分析,探究民族器乐的发展变化轨迹,⑤从而加深了对民族器乐在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改革前原貌的了解。尚若在此基础上,结合50年代以来灌制的大量唱片及其他有声资源,再辅以或传统、或新开发的研究手段,一部生动可感、可信可解的中国近现代民族器乐发展史便可跃然纸上。
由此给笔者带来启示,即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音乐文献学、古谱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相比,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有声音乐新媒介是近现代音乐史的独有现象,它不仅包括唱片、有声电影中记载的音乐信息,还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上的音乐信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发展已经形成材料丰富、形式多样的面貌,蕴含着极高的研究价值,加以新方法的开发引进,假以时日,未来完全可以建立起有声音乐媒介学研究专题。
全球化的当下,中国的民族音乐在几代国乐家们的不言放弃、勇于超越中看到了曙光,不仅活跃于国内音乐舞台和人们的音乐生活中,在国际乐坛上也有望以成为一种独具中国文化身份的音乐样式。中国的戏曲,在国内有着更为广泛的受众,汇聚着更为深层的民族记忆,承载着独特的民族审美情趣,在当下世界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中,以京剧为代表的传统戏曲能否像梅兰芳那样“移步不换形”,在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后迎来艺术的鼎盛时期,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期待的问题。也许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更大的勇气,采用更为多样的方式,或“移步不换形”,或换形不移步,抑或移步亦换形,只要能够像几代民乐人一样,大胆摸索,勇于在演出市场的实践中寻得更生,戏曲便有机会迎来自己的新曙光。
如同百年前的梁启超、曾志忞、李叔同、沈心工等人的回归,为传统音乐文化提供了焕发新生机的土壤一样,戏曲的更生离不开台前表演艺术家们才能的发挥、各界的关注,也离不开不同背景的学人们的研究与支持,任思的《芳韵绝音——梅兰芳1920—1936唱腔艺术衍变研究》正是青年学者的新尝試。中国的戏曲艺术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相对于中国戏曲的艺术成就,此项研究仅属开始,希望作者继续努力,不断精进,早日向学界奉献出研究新成果,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音乐学人加入到戏曲音乐研究的行列中来。
①详见冯文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9-11页。② 陈聆群《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音乐艺术》2002年第4期,第59-63页。
③ 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19页。
④ 费玉平教授、李晓天教授对该著的帮助,作者已在书中第五章述及,详见第240-243页。
⑤ 该文部分内容详见孟乔、李淑琴《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中民族器乐独奏音乐形态分析》,《乐府新声》2019年第4期,第82-88页。
李淑琴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