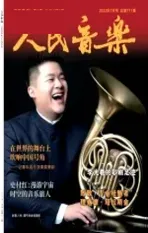塔拉斯金、音乐与我们
2022-04-29洪丁
一
2022年7月1日,美国音乐学家理查德·塔拉斯金(Richard Taruskin)因病溘然离世。此前的5月16日,我收到最后一封塔拉斯金发来的电子邮件,他言及自己确诊患病,医生开具了处方,身体正慢慢恢复但精神很差。他嘱我耐心等他几天,因我受梁晴老师委托,请他为“塔拉斯金对话中国音乐学者”写几句话。这是由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筹办,以塔拉斯金为主题的系列学术活动,本拟自7月却延续至年底,包括读书会、研讨会以及最重要的“对话”环节。塔拉斯金没有明说他所患何病,然而几周后仍未见他的消息,我的心情也一日沉似一日。终于,他允诺的寄语再也无法送达,许多想要问他的问题再也不会得到答案。音乐学的世界失却了一副鞺鞳大声,一种淬砺思想。而我失却了一位可敬、遥远又莫名亲近的朋友。
在塔拉斯金去世几个小时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其中转引音乐评论家亚历克斯·罗斯的评价,称塔拉斯金为“当世最重要的古典音乐作家,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报刊界”。2005年,塔拉斯金的鸿篇巨制《牛津西方音乐史》问世,出版社为该书创建的网站上将其称为“我们这个时代其中一位最杰出、最具争议的音乐学家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发展所作无与伦比的叙述”。时间再回溯十年,罗伯特·摩根为塔拉斯金的获奖著作《斯特拉文斯基与俄罗斯传统》写的宣传语称,“(这本书)将确立塔拉斯金为全世界最杰出的20世纪音乐学者”。贯穿塔拉斯金的职业生涯,他的名字与著作就时常伴随着此类“最高级”的评价。他以宏观的视野和深厚的学识对当下的音乐实践及其绵延的历史与学术思想进行着鞭辟入里的分析,始终站立于音乐学研究的最前沿。
在最初的震惊和悲伤渐渐平复后,我犹豫着是否动笔写篇纪念文章。一方面,对于这位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音乐学界其中一位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我们的了解确实显得匮乏。尽管上海音乐学院在2017年举办了以《牛津西方音乐史》为主题的研讨会,相关文集也随之出版;尽管他的文章偶尔可见中文翻译,他的议论也间或出现于国内有关西方音乐史学与表演理论的研究中。①然而,对于他的学术研究整体性的译介仍付阙如,他的观点也因此常常在未经充分考察下被质疑、被误解。但另一方面,我的文章如果是针对他的整体学术思想,以我对其把握程度而言,挂漏与顾此失彼恐怕在所难免,这样概述性的内容也很容易陷入对已有评价的重复。我的犹豫最后在“对话”与“回忆”上释然。回想起最初向塔拉斯金提出这场与中国学者进行对话的建议时他的欣然与雀跃,他是多么渴望与远方的中国学者们对话。如今,虽然计划中的交流再也无法实现,但对塔拉斯金这样一位坚持学术对话者而言(他也因此时常被贴上“好斗”之类的标签),一位相识的中国学者在中国的音乐学语境中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思考,无论如何肤浅或零散,也许仍然是个不错的纪念方式。
二
纵览塔拉斯金的学术研究,他的成就大约可以被归为如下几个方面:1.西方音乐史及史学研究;2.俄罗斯音乐;3.有关“历史本真表演”运动的论辩;4.对形式主义作品分析、理论及美学学说的批判;5.面向大众(包括音乐专业及非专业人士)撰写的音乐评论。在这些广阔的研究领域中,塔拉斯金采用“批评”(确切地说是“文化批评”)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這不仅彰显于上述第三至第五项本质即为音乐批评的研究中,也为他的音乐史写作增添了主观色彩。②批评在本质上可以说是概念化的逆向实践,意味着能够呈现不同的视角及观点并做出判断与评价。塔拉斯金将文化批评纳入他的历史书写,这种主观视角使读者产生一种强烈的在场感。翻开《牛津西方音乐史》距离我们最遥远的第一卷第一章,结尾两节的标题分别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它如何开始?”“据我们所知的,种种开端”。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哪部音乐史著作如此凸显“我/我们”,让读者如此真切地回到过去,随作者在时空中穿行。事实上,将塔拉斯金的音乐史与过去三十年间用英语写作的同类著作相比较,真正使之区别的并非如塔拉斯金所批判的,后者大多为“风格的概览”③,而正是这种主观视角的批评笔法。但塔拉斯金的主观视角并不妨碍其研究中的历史客观性,这一方面得益于他对于史料(特别是一手资料)无与伦比的把握;④另一方面则源自他对于史学家之任务不同于批评家的清醒认知:呈现(乃至揭露)史实,建立联系,并解释其因果。塔拉斯金结合文化批评的历史书写方式,与在“重写音乐史”大讨论中,冯长春老师所呼吁的“个性化音乐史写作”有异曲同工之妙⑤,这也启发我们反思自己的音乐史书写。
塔拉斯金学术研究的重中之重无疑是俄罗斯音乐。他的博士论文以俄罗斯1860年代“宣扬中与实践中”的歌剧为研究对象,详尽检视了这个俄罗斯歌剧发展史上的关键节点。随后四十年间,塔拉斯金以俄罗斯音乐为主题先后出版了一部专著以及四部文集,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文集《受诅的问题》,也以考察苏联音乐学中围绕文化社会学方法的争论终篇。⑥此外,塔拉斯金还为格罗夫音乐辞典撰写了超过160名俄罗斯音乐家的词条。但是,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为塔拉斯金贴上“俄罗斯音乐专家”的标签,那将很容易忽视他在这方面研究中更为宏观的批评视野(正如在他去世后许多纪念文章中有意无意间所做的那样)。仅举一例,塔拉斯金不惜以近一千八百页的篇幅探讨“俄罗斯时期”的斯特拉文斯基,追踪其音乐是如何根植于俄罗斯文化,受到俄罗斯民间音乐、前辈以及同辈俄罗斯作曲家(如尼古拉·罗斯拉维茨)以及俄罗斯文学、视觉艺术的影响。如此,塔拉斯金不仅揭露斯特拉文斯基在成为西方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后刻意淡化自己的音乐渊源,将自己包装为绝对音乐(因此更具“普世价值”)的代言人,更重要的是拷问了自律论音乐美学如何让人们趋之若鹜,成为价值判断的依据。⑦除史实研究外,塔拉斯金的俄罗斯音乐著述。在整体上可以说是以俄罗斯音乐为特定案例反思整个西方音乐文化,其目的并非要将俄罗斯音乐提升至与德奥音乐相抗衡的两极之一,而是批判了将德奥音乐默认为音乐正统的思想。事实上,这也是塔拉斯金在论述19世纪意大利、法国及东欧国家音乐时的一个基本命题。
塔拉斯金的俄罗斯音乐研究对中国学者也具有另一重意义。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始于冷战后期,随着柏林墙的消失,对立阵营因敌意产生的刻意屏蔽逐渐(至少暂时)解除,以塔拉斯金为代表,英美学界对俄罗斯音乐的研究弥补了曾经的忽视,在过去三十余年间成果颇显丰硕。而几乎是同一时期,苏联音乐学在我国曾经达到的权威与影响力则逐渐削弱,以至于不少年轻学者对相关内容与方法感到完全陌生。塔拉斯金的相关研究或许可以促发一部分中国学者重新与之连接,那曾是我们学术历史的一部分,今日的学者应能以今日的目光重新审视。
如塔拉斯金所言,《牛津西方音乐史》开始并且结束于“事情中间”。而在五卷正文中第三卷第八章(该章标题也刻意简化为《世纪中叶》),塔拉斯金标注了现代西方音乐历史观念的起点。19世纪中叶,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经由布伦德尔(Karl Franz Brendel)进入西方音乐史的写作当中。这种观念视历史终极目标为人类自由之实现,其历史演进则是这一理想与现实条件的辩证进程。黑格尔式历史主义以黑格尔本人未必认同的方式为西方音乐注入(或强化)了如“解放”“革命”“自由”“进步”“创新”等含义。与此同时,另一种由叔本华而来的“为艺术而艺术”美学思想经由汉斯立克为西方音乐的自律论奠基。这两种原本相悖的思想在20世纪合流,成为西方音乐现代主义(实则为升级版的浪漫主义)之根本。塔拉斯金批判的“创作谬见”(作曲家意图至上论)、对抽象的作品概念的神话、“文本字面主义”(唯乐谱论)、音乐普世主义、技术进步论等皆基于此。
对塔拉斯金而言,上述两种思想都通往了乌托邦。他的批评是要使西方音乐重新回到社会生活当中,重新连接音乐与我们。塔拉斯金以雄辩的语境式写作揭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虚妄,论证了他的核心观点:音乐不可能与社会现实区隔,将自己禁闭于自律的空间。⑧这无疑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⑨同时,塔拉斯金一方面承认自己与部分“新音乐学”学者的研究,正是德国与苏联音乐学在1920年代所实践的,一方面提醒我们注意这些实践与极权主义灾难结果之间的关系。⑩对于历史主义隐含的决定论,他不惜在“京都奖”的获奖致辞中以大篇幅生动描述自己学术生涯的种种意外,甚至不惜以“苏联的解体并非不可避免”进行反驳。
在塔拉斯金那些看似尖锐甚至“霸道”的批评背后,其实有着颇易跨过的“免责门槛”。塔拉斯金在学术界引发的第一场争议是有关“历史本真表演”的早期音乐表演运动。在长逾十年的一系列文章中,塔拉斯金论证了该运动实践的与其自称的相反,实际上是一种现代风格。但塔拉斯金并不反对这种表演实践本身,他甚至认为称其为“本真”也无不可,他所反对的是通过宣扬“历史本真”而主张唯一性的权威;尽管被调侃为“殴打理论家的人”,但塔拉斯金并不拒绝理论与分析,他曾受到申克理论的启发,著述中也充满了细致入微的作品分析,他所反对的是教条(即强加)的理论,是对“先入之见和学院式强制性判断循环论证”的分析;即使是德国唯心主义美学,塔拉斯金也并不视之为“眼中钉”,认为只要我们明白那是属于德国特定时期的思想,而非普适于所有民族的所有音乐之真理即可。塔拉斯金的“门槛”,阻拦的是强化音乐等级观念的“中心”“主流”“权威”,它们指向了通往极权主义的乌托邦,而他所维护的是多元的声音、多元的文化(即使是在西方艺术音乐文化中)。塔拉斯金著述中鲜明的批评与包容态度,使我们能够透过他雄辩的论证、难以企及的知识厚度以及辛辣犀利的文字,读出一位性格直率、情感丰沛的学者形象。
三
率真与感性也正是我与塔拉斯金相识过程中对他的性格最直观的感受。我与塔拉斯金相识于2014年9月在比利时鲁汶举行的第八届欧洲分析会议上(EuroMAC)。这是欧洲最大型的音乐学术会议之一,塔拉斯金应邀为大会作闭幕演讲,他的长期“对手”赫尔曼·达努泽(Herman Danuser)则担任了开幕演讲。因为规模庞大,会期内每日均有至少八个“平行会场”。因此,在20日上午的“分析1950年以来不可分析的艺术音乐”会场上,当塔拉斯金落座于后排我的身旁时,我更愿意将这种小概率事件解释为冥冥之中的注定。我像追星般请他在我的会议手册上签名留念,并开玩笑地说要拿去给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伙伴们吹嘘。数年后,当塔拉斯金收到我寄去的“上音”研讨会文集时,他的兴奋溢于言表。仿佛是主题再现般,他在邮件中直言要拿文集去向他的朋友们炫耀。
鲁汶相遇后我们并无联系,然而其后几年间,似乎又在冥冥之中,我总是沿着他前一年的脚步,前往不同城市参加学术活动。2018年10月,在维尔纽斯第46届波罗的海音乐学会议上我们再次相遇。这次会议的主题为“文化变迁与音乐批评”,塔拉斯金应邀为大会作了题为《李斯特的问题,巴托克的问题,我的问题》的主旨演讲。他围绕巴托克,以一贯敏锐的观察,批判“20世纪政治加密的伪美学,无论是以纯粹民族传统的名义,还是以社会正义的名义,抑或是以审美自律的名义,都破坏了艺术音乐的创造与接受”。相较于在鲁汶时,维尔纽斯这场会议的规模要小得多,全程没有平行会场,这使得学者们得以相聚一堂进行更充分的交流。我的宣讲从史料的角度分析了20世纪中国的音乐批评与政治的关联。印象中现场讨论颇为热烈,塔拉斯金除提出有关避难的犹太音乐家问题外,他尤其注意到我展示的《音乐小杂志》封面。这本由李叔同在日本创办的中国近现代第一本音乐杂志的封面上印着一小段《马赛曲》。塔拉斯金好奇背后原委,惭愧的是我对此完全没有准备。但在茶歇期间,他对我提到的一个观点颇感兴趣,我谈及苏联在所谓“赫鲁晓夫解冻”中对日丹诺夫文艺政策的松绑,或许对我国50年代后期文艺政策有着微妙的反作用力,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蝴蝶效应”。
维尔纽斯一别,我再无缘与他见面,过去四年间仅保持着电子邮件的联系。至我询问他的病情而未收到回音的最后一封邮件,我的电子邮箱中留存着59封往来对话,成为我对塔拉斯金最真切的记忆。我向他介绍了《牛津西方音乐史》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进展,他高兴又意外,因为他对此居然一无所知;我把“上音”研讨会的日程、题目翻译给他,他惊异于国内学界有这么多学者对他的学术抱有热忱;我提及将会翻译他的霍洛维茨文章,他关心地问我是否了解犹太人的受诫礼(bar mitzvah);他曾多次关心我在疫情中的情况,又曾不无沮丧地说:“我本以为中国会是(2000年)秋天最后一个可以到访之地,但現在看来你们正在爬出泥沼,而我们正在陷落!”讨论到他的新书《受诅的问题》时,他一方面用“意图谬见”(intentional fallacy)为由,拒绝回答我询问哪些问题值得尤其关注,一方面指出已出的一篇书评“如老生常谈,没有杀伤力”,另一篇则“不切题”。大多数时候,我在邮件中都对他恭敬有加,但偶尔也夹带着异议。我曾暗示他对于吉姆·萨姆森的批评过于严厉,他急切地抗议:“但吉姆和我是最好的朋友!他足够成熟,不会认为这些争辩是针对个人,我希望别人也不会这样想。”再回首,我多么希望自己对他少些对长者的恭敬,而多一分学者间的交流。我本以为将来还有许多机会和他讨论,但事与愿违。
每每想到塔拉斯金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准备与中国学者的对话时,我的内心就五味杂陈。2019年,在研讨会文集出版后,梁晴老师开始计划邀请塔拉斯金访问“上音”事宜。年底,我与梁晴、甘芳萌、徐璐凡三位老师商量好大致方案,并得到杨燕迪老师的认可,开始向学院打报告。我们甚至和塔拉斯金确定好了次年10月的访问时间(他计划把行程压缩到一周,为了赶回美国进行大选投票)。然而这一切都因疫情戛然而止。今年初,我们几人与邹彦、鲁瑶两位老师再次商议,决定无论如何先在线上实现交流。塔拉斯金否定了线上讲座的形式,但认为对话形式“意外的好”。他甚至笑称:“我可能不是你们希望的那样全知,但我会坐稳了等待大家的猛攻。”
按计划,我们将从7月开始举行一系列读书会,接着向学者们征集问题,在博客上与塔拉斯金进行“对话”。2022年7月1日,计划中的第一期读书会由何弦老师领读,顺利展开;同一日晚间,随着大洋彼岸传来的噩耗,原本的计划再也无法完成。今天,当我写下这篇散漫的纪念文章时,“对话塔拉斯金2022”读书会已经举行至第13期,来自世界各地超过六十位学者参与了对谈,其中不乏对塔拉斯金观点的质疑。我想,假如塔拉斯金在另一个世界看着我们,他会特别关注那些反对和批评的声音。我想他会有一种混杂的情绪,一方面会为无法亲自回击而懊恼,但另一方面,也会为他所希望引发的思考和对话的实现,在那个世界感到欣慰。
① 国内有关塔拉斯金的学术研究在2017年的研讨会后呈现出井喷之势。在此之前除偶尔提及外,较为重要的议论集中在有關《牛津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路、塔氏对“历史本真表演”运动的批评以及他与阿伦·福特有关音级集合理论的论战上,分别见孙国忠、杨燕迪,“西方音乐史研究”,载杨燕迪主编《音乐学新论——音乐学的学科领域与研究规范》第四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89–90页;徐昭宇《演奏型态的分析与音乐意义的追索——从“原真演奏”引发的音乐释义学方法思考》,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柯扬《本真表演的质疑者——理查·塔鲁斯金与丹尼尔·里奇-威尔金森观点之比较》,《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6那年第32期,第104–112页;王中余《阿伦·福特音级集合理论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研讨会文集见杨燕迪、梁晴主编《塔拉斯金:何为真正的音乐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19年版。有关塔拉斯金的中文翻译,见李超楠《译著〈音乐之危:以及其他反乌托邦的文论〉及其书评》,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论文中选译了塔拉斯金文集《音乐之危》中的前言、跋以及八篇评论文章。此外,由多位学者合作,全套《牛津西方音乐史》的翻译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之中,不久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② 这与塔拉斯金长期为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等撰写音乐评论不无关系。
③ Richard Taruskin, "Introducti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Vols. 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④ 塔拉斯金除博士论文外的首部著作,正是一本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至20世纪下半叶的音乐历史文献汇编,见Piero Weiss and Richard Taruskin,Music in the Western World: A History in Documents,Schirmer Books, 1984。
⑤ 冯长春《历史的批判与批判的历史——由“重写音乐史”引发的几点思考》,《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1期,第24–31页。⑥ Richard Taruskin, "A Walking Translation?" Cursed Questions: On Music and Its Social Practic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0.
⑦ Richard Taruskin, 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 A Biography of the Works Through Mavra, Two-volume S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⑧ 也许对于塔拉斯金这一观点最具象征性的表达来自他的几部文集封面。在时而清晰时而重叠的五线谱上浮现出生活中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音乐之危》的纽约世贸中心、《论俄罗斯音乐》的莫斯科瓦西里升天教堂)、雕塑(《俄罗斯音乐在国内与国外》的莫斯科“工人与农场妇女像”)与装置物(《受诅的问题》的纽约“倾斜的弧”)。在塔拉斯金即将出版的文集Musical Lives and Times Examined: Keynotes and Clippings,2006–2019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23)中,与五线谱叠置的是一块3500年前胡里安人的泥板,刻有据称世界上最早记录的旋律。
⑨ 查尔斯·罗森称塔拉斯金的研究方法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见Charles Rosen, "Modernism and the Cold War," Freedom and the Ar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46;安妮·施莱弗勒指出东德与苏联音乐学对塔拉斯金的研究产生影响,见Anne Shreffler, "Berlin Walls: Dahlhaus, Knepler, and Ideologies of Music History," Journal of Musicology 20 (2003): 523。
⑩ Taruskin, "A Walking Translation?" ,其中塔拉斯金也提及對于“新音乐学”的态度:“新音乐学很快就走错了路,从社会文化研究转向幼稚的诠释学,这导致它以惊人的速度老去。”
Richard Taruskin,"All Was Foreseen; Nothing Was Foreseen," https://www.kyotopriz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7/2017_C.pdf, 最近访问日期:2022年11月16日,下同。
塔拉斯金在这场论战中的相关文章收录于文集Text and Act,Essays on Music and Perform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ichard Taruskin, "Unanalyzed, Is It?" Cursed Questions, 257.
Richard Taruskin, “Speed Bumps,” 19th-Century Music 29/2 (2005): 198.
塔拉斯金的发言后以“Unanalyzable, Is It?”为题,收录于 Cursed Questions;达努泽的发言则成为其2017年的著作Metamusik中的一部分。
后发表于Richard Taruskin, "Liszt's problems, Bartóks problems, my problems,"?Studia Musicologica?58, 3-4 (2017): 301-319.
两篇书评分别为:
Nicholas Kenyon, “What Matters in Music?”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20/12/17/richard-taruskin-what-matters-in-music/ 以及Philip Bohlman, "Cursed Questions: On Music and Its Social Practices by Richard Tarusk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 2021, 74(2): 431–435。
[项目: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编号:19PJC052)]
洪丁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