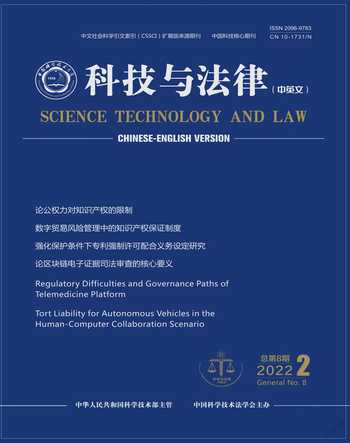互联网企业数据不正当竞争一般条款适用逻辑之辨
2022-04-26何敏马诗雅
何敏 马诗雅
摘 要: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互联网企业间数据竞争纠纷频繁发生。《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一般条款的适用在解决数据纠纷中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法院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解决互联网企业数据竞争纠纷案件中缺乏体系化的逻辑结构。一般条款的适用存在其内化的逻辑结构:首先,应当以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列举的行为作为逻辑前提;其次,应以“四要素”作为适用一般条款的逻辑主线;再次,将比例原则作为逻辑关联,辅助判断涉案竞争行为的性质;最后,在上述判斷基础上推导出逻辑结论。
关键词:数据不正当竞争;一般条款;逻辑结构;四要素;比例原则
中图分类号:D 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9783(2022)02⁃0054⁃09
引 言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突破和融合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数据增速符合大数据摩尔定律,大约每年翻一番。庞大的数据量及其处理和应用需求催生了大数据的概念,数据日益成为企业乃至国家的重要战略资产。在实践中,数据产品本身已经成为市场交易的对象,具有实质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网络运营商早已将数据产品视为自己的重要财产性权益以及核心竞争力[1]。美国政府更是将数据比作是“未来的新石油”“数字经济中的‘货币’”“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2]。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发展要素,但数据在不断丰富的同时,也给司法带来了极大挑战。企业之间对数据的争夺愈演愈烈,数据不正当获取与利用行为也愈发频繁。无序的竞争严重破坏了健康的商业秩序,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通过梳理与研究近十年的互联网企业间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可以发现,对数据纠纷类案件,法院更倾向于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来解决纠纷。“大众点评诉百度”“新浪诉脉脉”等案件都是适用一般条款解决企业间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典型案例。学界也有诸多学者对于适用一般条款解决数据竞争纠纷表示认可[3]。
然而,司法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存在诸多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一般条款)作为兜底性条款,其特点为原则性、概括性。由于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条款的构成要件和适用逻辑,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解读和适用第2条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存在体系不明、逻辑不清的问题[4]。因此,如何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解决互联网企业间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已成为实践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此背景之下,笔者梳理近年来互联网企业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的相关判例,归纳法官在该类型案件中适用一般条款的逻辑思路,省思与剖析一般条款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中一般条款的具体适用逻辑,以对司法实践形成统一的审判思路有所裨益。诚然,近几年已有不少学者对数据竞争的规制进行了广泛研究,但结合现阶段司法实践,通过系统梳理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逻辑来解决数据竞争纠纷的文献依然鲜见。
鉴于此,本文将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应对互联网企业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的现有审判标准,分析如何更为准确地理解和恰当地适用一般条款,并提出一般条款在数据竞争纠纷案件中的适用逻辑,旨在为司法实践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审判思路。
一、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一般条款的适用逻辑不清
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可以发现,近年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来解决互联网企业间数据竞争纠纷案件的相关裁判高达399件之多1。从时间方面来看,2012—2020年间,企业间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数量呈逐步上升趋势,并从2015年起,其相关案件数量呈跨越式增长。
从外部环境来看,互联网企业间数据竞争纠纷日益激化,由相同领域内的数据竞争已经转向为不同领域间的数据竞争,由单一领域发展成为综合平台间的竞争,这些新型竞争行为给司法裁判带来了挑战,但与此同时也为一般条款的适用奠定了现实基础。立法者无法预测将来会出现何种新的竞争行为,不断更新的竞争手段也无法穷尽式列举,因此立法采取了“概括+列举”的组合方式,即除《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章中明确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外,其他暂时无法明确或预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交由一般条款来解决。正是由于一般条款的原则性与概括性,给了此类新型竞争行为以法律适用的空间。
分析检索所得的案件可知,虽然目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处理互联网企业间数据竞争纠纷案件的比例颇高,但是法院在该条款的具体适用逻辑上并不统一。
为防止一般条款的滥用,最高人民法院在“海带配额”案2中给出了指引,该案中确立了适用一般条款的3个要件:其一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章未对该种竞争行为作出具体规定;其二是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因该种竞争行为受到实际损害;其三是该竞争行为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而具有可责难性。针对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部分法院采取了同样的裁判思路,如在“淘宝诉美景”案3中法官判定:首先,判定美景未经许可擅自获取、使用数据的行为不属于法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由一般条款规制;其次,认定美景的行为损害了淘宝公司的竞争优势;最后,指出美景的行为破坏了既有的商业模式,扰乱了数据行业正常的竞争秩序,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
然而,在“汉涛诉百度、杰图”案4中,该案法官将第一要件由探讨“涉案竞争行为是否应当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规制”转为探讨“涉案双方是否存在竞争关系”。其首先认定百度公司与汉涛公司存在竞争关系;其次指出百度公司抓取利用大众点评网数据的行为损害了汉涛公司的利益;最后判定百度搭便车的行为具有不正当性,构成不正当竞争。
在“微梦诉淘友”案5中,该案法官考虑互联网技术形态与竞争模式与传统不正当竞争的差异,在沿用“海带配额”案中确立的一般条款适用逻辑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3个要件:涉案竞争行为所采用的技术手段确实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涉案竞争行为破坏了互联网环境中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从而引发恶性竞争或者具备这样的可能性;对于互联网中利用新技术手段或新商业模式的竞争行为,应首先推定具有正当性,不正当性需要证据加以证明,且其认为只有在满足上述6个要件的情形下才构成不正当竞争。
此外,还有个别法院似乎摒弃了“海带配额”案中确立的3个要件,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行为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之上。“谷米诉元光”案6中,该案法官仅通过事实判断,认定被告元光公司大量无偿使用原告米谷公司的数据信息,有非法占有他人无形财产权益,为自己谋取竞争优势的主观故意,判定被告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由上述分析可知,目前上述司法实践中,我国应对互联网企业间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尚未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在适用一般条款解决这一问题时,仍未达成一致审判意见。
二、数据不正当竞争适用一般条款的核心要素思辨
梳理一般条款在解决互联网企业数据竞争纠纷案件中的适用逻辑,首先需要厘清该条款中“竞争关系”“商业道德”两大核心要素的内涵与外延。互联网企业数据竞争形式多变,传统的直接竞争关系已经无法规制跨行业竞争问题,应当扩大竞争关系的内涵,以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作为认定标准。商业道德可借助行业自律公约、技术规范等客观要素来辅助判断。
(一)应当对竞争关系做扩大解释
传统意义上,竞争一般均是发生于同业竞争者之间对于交易对象以及交易机会的争夺,故此,竞争关系为发生于同业竞争者之间的关系[5]。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竞争的形式不再拘泥于同行业之间的竞争。互联网环境下,竞争关系的认定标准成为理论界以及司法实践界争相讨论的关键问题。
目前,学界对于竞争关系认定标准的主流观点认为,竞争关系有直接、间接之分。直接竞争关系即同业竞争关系,其强调同一经济环节的竞争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且竞争对手是特定对象而非不特定对象[6]。间接竞争关系并非一个标准的法律概念,而是针对经济领域内非直接竞争关系的直观描述[7]。间接竞争关系针对的对象不要求是特定的,表现形式上要求对竞争对手造成间接损害抑或是直接损害消费者或其他经营者的利益。从本质上来说,间接竞争关系是因应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催生的新概念,用于弥补直接竞争关系限制范围过于狭隘的不足,合理扩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范围[8]。
互联网经济背景下,竞争形式的多元化更是对打破直接竞争关系的限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存在于商业活动范畴内的竞争关系当属于该法的调整范畴[9]。严格将竞争关系拘泥于同行业间,将很大程度上限制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同业竞争仅仅是市场竞争一部分,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规制全部不正当竞争行为[10]。互联网企业致力于用户注意力的争夺,创新竞争和跨界竞争已然成为业界常态,从服务性质或者服务类别来看,它们之间可能不具有同质性,但由于其在市场竞争中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或者关联关系,则可认为其存在竞争关系[11]。
司法实践中,随着新型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增多,法院也逐步突破了传统直接竞争关系范畴的限制,转而通过寻求间接竞争关系的认定来解决纠纷。“大众点评诉百度”案7中,大众点评网站与百度地图的经营方式虽有所不同,但二者面对的是同一用户群体,法官认为,即使双方的经营模式存在不同,只要双方在争夺相同的网络用户群体,即可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腾讯诉奇虎、奇智”案8中,法院指出,原告腾讯所涉猎的即时通讯市场及被告奇虎所代表的安全软件市场并非同一经营范畴,但在其各自经营过程中为更大范围地锁定用户,采用相同的经营模式,从而出现用户群体交叉重合,据此,法院认定二者存在竞争关系。
综上,传统的直接竞争关系的认定标准存在限制范围过于狭隘的缺陷,已经无法切实解决当下棘手的互联网企业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理论与司法界均倾向于扩大竞争关系的认定范围,借助间接关系的认定来解决问题。
(二)应借助客观标准判断商业道德
长期以来,司法实践借助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来规制新型竞争行为,其中“商业道德”标准是判断行为正当性的核心所在,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具体体现。商业道德因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条件及文化传统而凸显出不同的道德内核,互联网领域的商业道德趋于有多种判断标准9。法官通过结合个案对一般条款中的商业道德加以解释,解决了大量的互联网企业间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一般条款的弹性,商业道德参考标准也随之丰富。
司法实践中,行业自律公约似乎已成为评判行为是否符合商业道德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奇虎诉腾讯”案10中,法院将行业自律公约视为行业一致遵循的规范,并以之作为认定商业道德的重要依据。“百度诉奇虎不正当竞争纠纷”案⑪中,法院也同样肯定了行业自律公约的重要性,指出《搜索引擎行业自律公约》是由有行业影响力、占据多数市场份额的企业在行业协会的组织下达成的行业共识,反映了行业公认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在缺乏法律明确权利义务边界的情形下,将行业自律公约作为判断行为是否符合商业道德具有合理性。
此外,行业技术规范也是认定商业道德的指标之一。在某些新型商业领域,比如说互联网领域中某个行业,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甚至是行业自律公约,此时行业主体会依靠技术规范来维持行业内的规范运行。最典型的技术规范即目前互联网行业惯常采用的ROBOTS协议,是一种用于规制网络爬虫获取网站信息的文本文件[12]。在“百度诉奇虎违反ROBOTS协议”案⑫中,法院结合专家陈述意见以及涉案ROBOTS协议的审查结果指出,在我国互联网行业,ROBOTS协议案已经成为网络平台遵守的一项行业基本准则,应当将ROBOTS协议作为公认的商业道德对待。
与此同时,法院还创设了诸多一般条款司法裁判规则来辅助评判行为是否符合商业道德。其中,“协商通知”程序处理规则以及“三重授权”原则较具有代表性。这两个裁判规则或是对现有行业规则的认可,或是对互联网行业经营原则的构建。
“协商通知”程序处理规则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百度诉奇虎违反ROBOTS协议”案⑬中创设的新规则。该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奇虎公司违反百度公司设置的ROBOTS协议,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抓取和复制百度服务器内容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针对这一问题,法院开创性地提出,搜索引擎服务商与网站服务商就ROBOTS协议发生纠纷时,应当遵守“协商通知”程序处理规则。该规则强调,搜索引擎服务商认为网站ROBOTS协议不合理时,应当向其提出修改协议,准许其抓取信息的请求。网站经营者在收到请求后,如果拒绝修改,则应当在合理期间内书面告知搜索引擎服务商拒绝的理由。搜索引擎服务商认为拒绝理由不成立的,双方可以向行业协会或自律公约签订机构陈述意见,由相关执行机构先行调解。无法达成一致的,可以诉诸于诉讼。
“通知协商”程序处理规则为解决互联网企业ROBOTS协议纠纷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模式和司法裁判规则。纵观判决,该规则的核心内涵在于肯定了ROBOTS协议作为公认的商业道德的合理性。违反“协商通知”程序处理规则,擅自抓取第三方数据的行为不符合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
“三重授权”原则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新浪诉脉脉”案⑭中创设的新规则。淘友公司经营的脉脉平台与微梦公司经营的新浪平台同为社交网络服务提供者,存在竞争关系。淘友公司在合作期间抓取新浪微博用户的职业信息与教育信息超出授权范围以及在合作期满后,仍然使用新浪微博用户信息,缺乏正当理由,存在主观恶意;另一方面,淘友公司未取得用户许可获取并使用涉案非脉脉用户的相关新浪微博信息违反了《开发者协议》的约定,一定程度上破坏了Open API合作开发模式,同时也未能尊重用户的知情权及自由选择权,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具有不正当性。据此,法院明确指出,在Open API开发合作模式中,第三方通过Open API获取用户信息时应当坚持“用户授权”+“平台授权”+“用户授权”的三重授权。
“三重授权”原则实质上是从三个层面细化了诚实信用、商业道德:“用户授权”强调平台搜集用户信息时需要获得用户同意,在用户授权范围内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若违反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平台授权”强调第三方应用从平台获取用户信息时,需要与平台方签署《开发者协议》,获得平台授权许可,擅自抓取平台信息的行为有违商业道德;“用户再授权”强调第三方应用不仅要获得平台方的许可,还要征得信息所属用户本人同意,以确保其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符合商业道德”本为抽象的主观标准,但随着司法实践的丰富,商业道德的判断标准也越發具象,行业自律公约、行业技术规范、法院创设的法律规则都成为了判断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的重要标准,给解决企业间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以指引。
三、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一般条款的适用逻辑厘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为解决互联网企业间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提供了可行性,然而该条款的具体适用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标准。综合司法判例及部分学者的主张,本文归纳出切实可行的一般条款具体适用逻辑:首先,将反不正当竞争法未对某种行为作出明确列举作为适用一般条款的逻辑起点;其次,将双方存在竞争关系、经营者对数据产品享有合法权益、行为具有不正当性、行为对市场竞争造成损害等四要素作为逻辑主线分别进行判断;再次,将比例原则作为逻辑关联,辅助判断涉案竞争行为的性质;最后,在上述判断基础上推导出逻辑结论。
(一)逻辑前提: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列举的行为
一般条款始于德国,其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弥补成文法无法穷尽式列举的漏洞,为立法的滞后性提供解决空间,允许法官在个案中援引该条款,结合立法宗旨进行价值补充。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范围时,采用的是列举配合兜底概括的模式,除在第2章中明确规定了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外,另在第2条中规定了兜底性的一般条款,对未在第2章中明确列举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损害市场竞争秩序等行为进行了规制。
一般条款的实质功能就在于其搭建了竞争法规和其他非法律标准沟通的桥梁,当通过市场结构、竞争机制等竞争法的内在判断要素不能对经营者的行为作出准确认定时,引入伦理标准、习惯标准、道德标准等非法律标准进行解释,便成为司法实践的应有之义。
现阶段,数据竞争行为并未被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所列举的具体模式之中。随着数据在企业经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据竞争的纠纷不断,企业间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急需规制。在此背景之下,应当将数据竞争行为纳入一般条款的规制范围。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条件的适用并非行为正当性的判断标准问题,而是着眼于法律关系的处理,这一法律关系的确定,有利于一般条款的适用。
(二)逻辑主线:一般条款“四要素”的判断标准
1. 双方存在竞争关系的判断
竞争关系又叫市场竞争关系,是指市场主体之间在竞争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13]。是否应当将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作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逻辑起点一直颇具争议。有学者认为从保护消费者的立法目的出发,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竞争关系的判断是次要的[14]。在“酷米客诉车来了”案⑮中,法院也认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与具有竞争关系的商品或者服务本身的市场份额占有率并不具有直接关系,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评定标准是竞争方式是否符合同业者遵循的商业惯例、是否违背公认的商业道德。
然而,也有学者对“将双方存在竞争关系作为适用一般条款的逻辑起点”持支持态度,认为竞争关系在案件审理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殊地位[15]。将竞争关系作为法律适用的逻辑起点,与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扩张保护非但不冲突反而契合了这一发展趋势,使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不再囿于经营者身份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促进正当竞争、维护正当市场竞争秩序方面的作用[16]。如前文所述,司法实践也更倾向于将分析竞争关系作为开启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大门的钥匙。
竞争关系在分类上可以分为直接竞争关系和间接竞争关系。直接竞争关系的认定包含3点基本要素:其一,商品的可替代性;其二,竞争对手的性质;其三,竞争者所处的经济环节。从所处的经济环节这一角度来看,直接竞争关系是处于同一经济环节的经营者之间的制约关系[17]。其不足之处在于竞争范围过于狭隘,难以解决新型不正当竞争纠纷。
作为直接竞争关系的补充,间接竞争关系应运而生,不同于直接竞争关系中特定的竞争对手,间接竞争关系的竞争对手往往具有不特定性。间接竞争关系实则并非一个标准的法律概念,而是对经济领域非直接竞争关系的直观描述。在该类案件中,法院一方面明确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在阐述理由时,没有认定二者属于相同行业或者相同经营范围,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认定。
间接竞争关系是法官应对新型竞争行为,尤其是互联网企业间数据竞争的突破性创新,在解决网络环境中的新型竞争纠纷案件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仅应当将违反禁止性竞争法条款的直接竞争关系纳入其规制范围,而且还应当将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以主动进入争夺交易机会和直接侵害消费者或公众利益等方式构成的间接竞争关系也纳入其中[18]。
2. 经营者对数据产品享有合法权益的判断
目前,依据数据获取方式的不同,互联网领域的数据大致可以被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直接获取的用户信息;二是依据群体行为产生的用户信息之外的原始数据;三是原始数据经过加工后形成的数据产品[19]。其中,前两类为直接数据,第三类为间接数据。
针对直接数据,其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遵循用户信息的合同约定或者相关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对其不享有直接的财产权益。而对于数据产品,其是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算法,經过深度分析过滤、提炼整合,以及匿名化脱敏处理后而形成的预测型、指数型、统计型的衍生数据。数据产品虽源于直接数据,经过深度开发与系统整合,最终呈现给消费者的数据内容,已独立于直接数据之外,是与网络用户信息、原始网络数据无直接对应关系的衍生数据。网络运营者对于其开发的大数据产品可享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性权益。
网络数据产品的开发与市场应用已成为当前互联网行业的主要商业模式,是网络运营者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与核心竞争力所在。网络经营者对其加工处理所得的数据产品是否享有合法权益需要从两个维度加以判断:一方面,网络运营者数据获取行为经得用户授权同意,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另一方面,其研发的数据产品有效提升了经营水平,改善了营商环境,为广大消费者带来了福祉。与此同时,网络运营者在数据的获取与整合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根据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其通过将原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数据附着以自身劳动,从而对劳动行为产生的数据产品取得合法权益。
3. 行为具有不正当性的判断
结合目前搜集整理所得的判决来看,当前司法实践中对竞争行为是否具备正当性,主要从两个纬度入手加以探讨:其一是从道德纬度加以分析,即竞争行为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其二是从效果纬度加以分析,即经营者正当的商业模式是否因竞争行为而受到侵犯。
长期以来,商业道德标准作为诚实信用原则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化身,摇身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帝王条款”,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处理竞争纠纷案件时,均将是否符合商业道德作为认定行为正当性的重要标准。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传统商业道德标准也随之颠覆,相较于传统商业模式的稳定性,技术革新为商业环境增添了不稳定因素。商业道德往往需要行业共同体经过长期反复实践方能形成,而数字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网络行业实难为具体商业道德的形成提供土壤。
商业道德本身具有抽象性、多元性等特征,司法实践中也往往难以具象化,因而法官解释在案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由于不同的法官对道德标准理解的不同,甚至可能得到结论完全相反的判断。实践中,尽管法官试图借助行业自律公约、行业技术规范等指标来具化商业道德,但公约的形成往往需要时间的打磨,其也仅是参考标准之一,并仍留有主观空间,无法完全避免法官主观臆断的风险。
在商业行为、竞争模式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下,司法实践对竞争行为的正当性无疑需要进行调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似乎为判断行为的正当性明确了方向。该条款强调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仅要规制市场竞争秩序,还需要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兼顾消费者的利益。具体而言,即将行为所引发的市场效果作为判断行为是否正当的主要标准。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损害市场效果的行为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破坏他人经营的行为;另一种则是未经许可利用他人经营的行为。对于破坏他人经营的行为,其行为的不正当性自然不言而喻。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法院在分析行为的破坏性时需要将行为放置于互联网企业特有的商业模式框架之中。“微博诉饭友”案⑯中,复娱公司抓取新浪微博后台数据后在其运营的“饭友”APP中进行直接展示,该行为使“饭友”APP用户无需注册或登录新浪微博账号即可查看新浪微博全部内容,影响了新浪微博用户协议的履行,破坏了新浪微博数据的展示规则,且对新浪微博的该部分内容构成实质性替代,分流了微梦公司的潜在用户流量,妨碍、破坏了新浪微博的正常运营,构成不正当竞争。对于未经许可利用他人经营的行为,其行为的不正当性在于不劳而获,也即通常所说的“搭便车”行为。在“大众点评诉爱帮”案⑰中,“爱帮网”未付出劳动、成本,直接利用技术手段大量复制“大众点评网”的数据内容,并以此获取商业利益,此种行为则属于明显的“搭便车”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4. 行为对市场竞争造成损害的判断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不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市场竞争损害的界定较为宽松,除非有相反证据,损害了经营者的利益就往往昭示着市场竞争遭受到了损害。毋宁说,任何经营者在行使模仿自由权、使用和借鉴他人劳动成果的同时,都必须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以正当的手段和方式来行使此项权利。经营者不当利用他人劳动成果的,将会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构成不当利用之不正当竞争行为[20]。
需要注意的是,损害尚需达到实质性损害的程度。此处所强调的实质性损害包含两个层面的要求:首先,行为与损害之间需要存在因果关系,也即损害是由该竞争行为造成的;其次,损害不仅包括直接经济损失,还包含间接损失,就数据竞争而言,经营者的损失可以包括交易对象的分流、竞争优势的丧失及预期利益的减损。以“淘宝诉美景”案⑱为例,美景公司擅自获取并利用淘宝公司“生意参谋”数据产品的数据内容,以此获得商业利益,截取原本属于淘宝公司的客户,导致淘宝公司的交易机会严重流失,损害其商业利益,削弱其市场竞争优势。此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淘宝公司遭受到了实质性损害,美景公司的行为损害了市场竞争。
(三)逻辑关联:借助比例原则考量涉案竞争行为的性质
比例原则旨在考察不同方式(行为、手段)对两个相冲突利益(原则、目的、价值等)的各自影响,从而选择能够最大程度上同时兼容两种利益的方式[21]。比例原则作为处理利益冲突的工具,目前被广泛地应用于处理各类法律纠纷。互联网企业间数据不正当竞争涉及经营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及市场竞争秩序等多方利益的冲突,适用比例原则的分析框架对竞争行为进行考察,可以有效弥补一般条款适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反不正当竞争法乃行为禁止性法律,即以“负面清单”形式规定了何种行为不能做[22]。其中,禁止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多个条款中均有所体现,并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彰显其法律价值。从中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致力于经营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及市场竞争秩序等多种利益的保护,当这几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就要求裁判者能做到足够公正。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公正,就是合比例;不公正,就是破坏比例。”[23]
事实上,司法实践中,法院已经开始逐渐有运用比例原则的意识,其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百度诉奇虎”案⑲中提出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正是比例原则思想的具体体现与应用。“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的提出者石必胜法官指出,该原则包含三层含义:(1)不干扰,即互联网产品或服务不得相互干扰,否则可能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或不正当竞争责任;(2)非公益不干扰,即在有些情况下,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干扰是可以免责的;(3)公益且必要的干扰才可能免责,即使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才实施干扰行为,如果干扰行为不是必要的,也要承担责任[24]。从中可以看出:第一层含义确立了互联网产品和服务不受干扰的利益;第二层含义将公共利益的考量纳入其中;第三层含义要求干扰手段以公共利益为限,不可滥用,要具备必要性,符合狭义比例原则的要求,即为实现特定利益所造成的不利益,原则上不能超过其所欲维护的利益[25]。
数据竞争形式纷繁复杂,一般条款的适用过程中难免会忽略竞争关系所涉及的部分群体的利益,比例原则要求在综合考量经营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及市场竞争秩序等多方利益边界的基础上,确定行为的正当性。比例原则思想的适用可以有效纠正一般条款适用过程中的价值偏差,保证裁判者作出更公正的判决。
(四)逻辑结论
由于互联网企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目前尚未被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列举的“负面清单”当中,因而解决此类纠纷满足适用一般条款的前提要件。梳理逻辑主线,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需同时满足四要素的判断标准,即明确双方存在竞争关系、经营者对数据产品享有合法权益、行为具有不正当性、行为对市场竞争造成损害。其中,双方存在竞争关系为逻辑起点,由于互联网背景下企业数据竞争模式具有多样化的特性,跨行业竞争屡见不鲜,因此,竞争关系并不囿于直接竞争关系,双方存在间接竞争亦可认定竞争关系的存在。在确定双方存在竞争关系的基础之上,依次判断经营者对涉案数据产品是否享有合法权益、涉案竞争行为具有不正当性、市场秩序是否因涉案竞争行为而遭到破坏。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行为被判定满足四要素也不可妄下定论,还需要参照比例原则,综合考量消费者、经营者、市场等各方利益,至此,得出公正合理的逻辑结论。
结 语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在解决互联网企业间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弥补了立法滞后性的缺漏。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已经初步形成了规制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逻辑思路,即首先确定案件当事人竞争关系的存在,在此基础上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案件审理的大前提,结合个案事实,判断行为是否损害经营者合法利益,是否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是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但是,这一逻辑适用的过程中存在诸多缺陷,个案中,法官的主观臆断占比依然很高,针对不同案件,法院采取的审判依据不尽相同,一般条款缺乏统一有效的适用路径。统一一般条款的适用成为现实亟须解决的问题。
互联网企业间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属于一般条款中明确列举的行为模式,以此厘清法律关系。一般条款的具体适用需要以双方当事人存在竞争关系为前提,竞争关系应当做广义理解,竞争双方存在相同的交易对象即可认为双方具有竞争关系。在行为正当性的判断问题上,商业道德标准具有较高的主观臆断性,道德含义理解的本身即具备多样性,且道德评判标准往往具有滞后性的特点,难以承担评判企业间数据竞争这种新型竞争行为的重任,应当逐步将商业道德标准调整为更为客观的市场效果标准。
此外,市场竞争中往往涉及多方利益,一般条款的适用中,法官需要秉承比例原则的思想,在综合衡量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再对竞争行为的正当性进行评判,以此保证案件判决的公正合理。
参考文献:
[1] 徐海燕,袁泉. 论数据产品的财产权保护——评淘宝诉美景公司案[J]. 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8(20):83-89.
[2] 马化腾. 数字经济——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7.
[3] 薛其宇. 互聯网企业间数据不正当竞争的规制路径[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4(12):62-68.
[4] 谢晓尧. 在经验与制度之间:不正当竞争司法案例类型化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89.
[5] 李胜利.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竞争关系和经营者[J]. 法治研究,2013(8):49-54.
[6] 焦海涛. 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中的实用主义批判[J]. 中国法学,2017(1):150-169.
[7] 王永强. 网络商业环境中竞争关系的司法界定——基于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的考察[J]. 法学,2013(11):140-147.
[8] 陈兵. 互联网经济下重读“竞争关系”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意义——以京、沪、粤法院2000—2018年的相关案件为引证[J]. 法学,2019(7):18-37.
[9] 宋旭东. 论竞争关系在审理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J]. 知识产权,2011(8):43-48.
[10] 王艳芳.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竞争关系的解构与重塑[J]. 政法论丛,2021(2):19-27.
[11] 祝建军. 网络不正当竞争侵权成立的考量因素[J]. 人民司法,2019(10):4-9.
[12] 张平.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及其适用——搜索引擎爬虫协议引发的思考[J]. 法律适用,2013(3):46-51.
[13] 种明钊. 竞争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1.
[14] 谢晓尧. 竞争秩序的道德解读——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M]. 法律出版社,2005:85.
[15] 王永强. 网络商业环境中竞争关系的司法界定——基于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的考察[J]. 法学,2013(11):140-147.
[16] 郑友德,伍春艳.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十问[J]. 法学,2009(1):57-71.
[17] 刘继峰. 竞争法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4.
[18] 郑友德,杨国云. 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竞争关系”之界定[J]. 法商研究,2002(6):64-69.
[19] 薛其宇. 互联网企业间数据不正当竞争的规制路径[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4(12):62-68.
[20] 邵建东.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07.
[21] 兰磊. 比例原则视角下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解释——以视频网站上广告拦截和快进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为例[J]. 东方法学,2015(3):68-81.
[22] 邱本. 论市场竞争法的基础[J]. 中国法学,2003(4):94-106.
[23] 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943.
[24] 石必胜. 网络不正当竞争认定中的公共利益考量[J]. 电子知识产权,2015(3):31-36.
[25] 胡杰.刑事诉讼对物强制措施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77.
Thoughts on the Application Logic of the General Terms of Unfair
Competition in Internet Enterprise Data
He Min, Ma Shiya
(Scho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data competition disputes among internet enterprises in China occur frequentl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in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solving data disputes. The court lacks a systematic logical structure in applying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to solve the data competition disputes of internet enterprises.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l clauses has its internalized logical structure: firstly, it should take the acts that do not belong to the acts explicitly listed in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as the logical premise; secondly, "four elements" should be taken as the logical main line of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l terms; thirdly,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should be used as a logical connection to assist in judging the nature of the competition behavior involved; finally, the logical conclusion is derived based on the above judgment.
Keywords: unfair data competition; general terms; logical structure; four elements;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猜你喜欢
杂志排行
科技与法律的其它文章
-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Issu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Related Services as a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onetary Encryption in China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Security
- Tort Liability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in the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Scenario
- Regulatory Difficulties and Governance Paths of Telemedicine Platform
- 我国录制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制度定位、完善思路与建议
- 聚焦“5G+智能”时代:数字出版著作权法治理困境及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