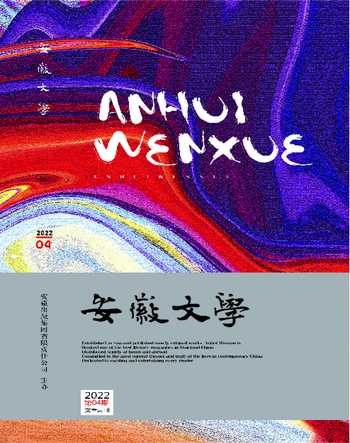疙瘩寨的美丽传说
2022-04-19袁良才
袁良才
詹文格的身材无疑是同他的财富成正比的。当某一天他突然像一只企鹅从劳斯莱斯后车门挤出来的一刹那,我们的身体不由地缩小了,从心里感叹:过去那个“詹文革”不复存在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对他不得不保持“望星空”的姿态。
然而事实说明,我们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詹董事长好像并未嫌弃我们,而是弄了一辆豪华中巴一股脑把我们这些发小拉到县城最奢华的大酒店,让我们见识了人的日子居然还可以这样过。詹文格(不知道他啥时候改了名字)送我们这帮东倒西歪的家伙返回到村子里时,差不多是夜半时分了。
大伙儿散伙时,詹文格独独留下我和二狗,詹文格超乎清醒地说,你俩,陪我,去蜈蚣岭看看。
二狗闻言,酒都吓醒了,妈呀!半夜三更的,去蜈蚣岭?
我的酒意一下子被激得更浓了,那地儿,恐怖着呢!传说鬼戽沙,青天白日去还得壮着胆子喔!
詹文格不屑地啐了我俩一口,长那玩意没有?自顾大步朝前走去。二狗和我对视一眼,老大不情愿地跟了过去。
蜈蚣岭位于村后不远处的小山包上,花花的月光照着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墟,夜风吹得草叶“沙沙”地响,树林里还有什么怪鸟在叫,像一个撒气漏风的喉咙里发出的空洞的笑声。
物人两非,别梦依稀!詹文格粗笨的身体里竟然会吐出这么细腻雅致的语言,这里,失落了我最纯真美好的初恋,埋葬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艰难而美妙的旧时光。
旺财,二狗,你们还记得这里当年是干嘛用的吗?詹文格诗人般感喟一番后,冷不丁转过身子,目光如炬,盯视着我俩,嗓音陡然提高了八度问。
育种室。我说。
不对!是牛栏。二狗说。
都对,都不对!
詹文格仰望着金黄烙饼似的月亮,抡圆了一只胳膊大声纠正道,那是后来。蜈蚣岭,最初是知青点!
在我和二狗有点蒙圈的当儿,詹文格显然很有点生气,呼吸也粗重起来,不到半个世纪呢!岁月的泥瓦刀把啥都抹平了?
詹文格看样子是个拎得起放得下的人,他的呼吸渐渐平稳匀和起来,那么,梁红梅,你们总该记得吧?
在我俩再一次更深地陷入懵懂时,詹文格不失时机地提醒道,就是那个满嘴安庆口音的那个?
我和二狗电光石火般,把那段早被时光的尘埃湮没无迹的陈年旧事一下子从脑海里打捞了出来。
梁红梅还是我爸开手扶拖拉机从公社接到疙瘩寨来的呢!
同来的有三个人,两女一男,胸前都戴着大红花,脸上洋溢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浪漫主义的幸福甜蜜的微笑。一个姑娘就是梁红梅,另一个姑娘叫吕佩玉。男知青看上去很木讷,戴着瓶底似的近视眼镜,乡亲们都管他叫“四眼儿”。
那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涌上了蜈蚣岭,聚拢在知青点一溜土墙瓦顶平房前面,说说笑笑,指指点点,詹文革的父亲麻子队长还点燃了一挂鞭炮,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硫黄的好闻的香味。麻子队长忙着指挥大家给知青们搬行李,收拾房间。真比过年还要喜庆、热闹。
我记得大伙儿散去时边走边议论,啧啧声扯歪了一张张嘴巴:
那个叫红梅的安庆姑娘真俊俏,说话跟唱黄梅戏似的,好听。
那个叫佩玉的合肥姑娘跟她站一块,一高一矮,一瘦一胖,一白一黑,一个像煞了千金小姐,一个活似使唤丫头!
詹文革在人群里看热闹时,两只金鱼眼让人担心随时会从眼眶里掉出来,他痴痴地只盯着梁红梅身上看,还咕嘟咕嘟很响地咽口水。这时他撵着大人的话把子叫道,不!应该这样说,一个是白雪公主,一个是灰姑娘!
有人拿詹文革开起了玩笑,莫不是你个臭小子看上了白什么公主?你爸是生产队长,权力大得很,可要让你爸照顾好白什么公主喔!
人群哄笑开来,半大小子詹文革一下子脸红到了脖子根,匆匆逃遁。
这以后,詹文革一俟放学,就拉着我和二狗有事没事往知青点溜达。要么在房前屋后瞎转悠,时不时地扯開嗓子唱歌,或鼓着腮帮使劲吹柳叶哨子,要么在知青点门口探头探脑,见到人就“哧溜”一声慌不择路地跑开。
我们倒是看清了,两个女知青住一间屋,屋里整饬得真干净,似乎还香喷喷的,窗户上糊了一层白报纸。四眼儿的房间从窗外看一览无余,一床,一桌,一凳,潦倒得可以,还显得乱糟糟的。
他们并不自己开伙,麻子队长安排他们轮流到社员家吃派饭。
知青们到谁家吃饭,哪怕是个穷得滴尿的超支户,也提着篮子到镇街上割点猪肉,买几块豆腐、豆干,让知青吃得直吧唧嘴,连说“好吃,好吃”。
那时候的乡下人实诚,宁愿苦自家,也不肯亏客人。他们把城里来的年轻学生当成客,说,待不长哩!待一天是单的,待两天是双的,娃娃们娇嫩,又正在长身体哩!吃饱了不想家。
詹文革对我们说,灰姑娘和四眼儿都是沾了白雪公主的光!梁红梅到哪家,哪家就亮堂了,看着欢喜!
我们疙瘩寨有句俗话:麻子点子多。詹文革的父亲麻子队长似乎有点狡猾,但心眼儿不坏。有可能是詹文革背后撺掇的(他是个惯宝宝),有可能他屁作用没起,开社员会时麻子队长清了清嗓子,拿腔作调地说,谁个不是娘生爹养?城里娃细皮嫩肉,吃不得苦,我们大家伙一人省一口,养这三个小花狗。我寻思,让梁红梅就在疙瘩寨初小当代课老师,教文革、旺财、二狗他们,四眼儿嘛记工分兼仓库保管员。佩玉嘛……也分个轻巧事干。
社员都没啥意见,热烈鼓掌通过。
后来,是吕佩玉去当了代课老师,梁红梅让她的。梁红梅执意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参加生产劳动。
但她也没能如愿,她被公社知青干事马光成抽去参加了公社文艺宣传队,巡回演出革命样板戏。一般是早出晚归,还是住在知青点。
马光成是县革委会主任的“公子”,经常背着老婆孩子干些花花事,是远近出了名的“骚牯牛”。他调梁红梅去宣传队就没安好心。
那天,马光成单独辅导梁红梅排“李铁梅”的戏。休息时,梁红梅要马光成讲故事。马光成喷着酒气说,今天不讲故事,我打个谜语给你猜。梁红梅说,好呀!马光成说,石坝街,十八号,关起门来轰大炮!梁红梅使劲猜,猜不出,那模样更妩媚动人了。马光成气喘渐粗,我来轰给你看!梁红梅顿悟,猛地抓起身边的红灯,高唱道,今日起志高眼发亮,讨血债,要血偿,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担!我这里举红灯光芒四放——马光成一激灵,只好悬崖勒马。
这一切,都被躲在外面的詹文革、二狗和我看见了。
梁红梅到哪个地方演出,詹文革就领着我和二狗窜到哪个地方,说要“保护”白雪公主。他总是挤在舞台最靠前的位置,一对金鱼眼鼓得很凸,盯着台上的梁红梅半天一动不动,喉咙里咕嘟咕嘟地响个不停。我和二狗早把戏听得耳朵起茧了,我俩就蹲在地上打“鳖”。
事实上,詹文革和我们一样对戏曲狗屁不通,他不是看戏,是看人,只看一个人,梁红梅!
几乎每看一场戏,他都会在中途胁迫我和二狗去附近的人家或地里去偷桃子、枣子或山芋、萝卜什么的,然后他藏在口袋里爬上后台去“孝敬”梁红梅。这小子跟他麻子爹一样,就是点子多,难怪他日后会成大老板!
詹文革跟我们吹嘘,说梁红梅有一次感动得亲了他的腮帮子,好香好痒,害得他好几天没洗脸。
梁红梅扮相好,唱功好,出身也好,所以都是演的英雄人物,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平原作战》里的赵小英什么的。
一次,不知怎么演起了《白毛女》,梁红梅自然是演喜儿,马光成演黄世仁,当黄世仁除夕夜去杨白劳家要拿喜儿抵债时,詹文革气不过,金鱼眼变成了火焰喷射器,他偷偷从口袋里摸出皮弹弓,填上石子,“嗖”的一声射上台去,把个“黄世仁”打得头破血流。在台上台下一片慌乱之中,詹文革带着我和二狗溜之大吉。
詹文革还做了一件丑事,只有我和他妈知道,连二狗也不知道。
一天,詹文革又领着我在知青点门前瞎转悠。詹文革的眼睛突然闪闪发光了,原来是梁红梅走出来,在屋檐下的竹竿上晾晒了一件白色的衣物。梁红梅见到我们两个小屁孩,粲然一笑,奖赏我们一人一颗奶糖,然后匆匆走了,是去公社文艺宣传队。
詹文革鬼鬼祟祟地凑到知青点门口,见四眼儿和灰姑娘都不在,转回身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扯下竹竿上的那件白色衣物,揣进衣领里,气喘吁吁地带我跑进附近的小树林,取出来一看,嘿!咋有这么短的小背心?这是干啥的?詹文革好奇地问我。
我哪知道?我想伸手捏捏小背心,詹文革粗暴地将我的手打开,你也配摸!
詹文革把这件小白背心贴在鼻子尖上闻了又闻,用手摸了又摸,成心馋我似的。后来他把小白背心拿回家,不小心被他妈发现了,被他妈一顿好揍。你个讨债鬼!咋把人家城里姑娘的奶兜兜偷回家?不学好,造孽哟!
文革妈连夜把白背心给梁红梅送回去,说,衣服让风吹到草窠里去了,我收工路过,捡到的。
詹文革变得越来越老成,越来越忧伤了。
有一天放学后,他把书包抡在地上,我和二狗也把书包扔在地上,我们坐成了一团。詹文革皱着眉头,向我们公布了一个重大发现,我感觉到,四眼儿喜欢上梁红梅了!
我们咋不知道?二狗和我抓挠着后脑勺,如同课堂上面对一道难解的算术题。
你没见四眼儿每晚都候在知青点门口,踮着脚尖等白雪公主回来吗?詹文革很肯定地加重了语气,最近他边等边吹上了口琴,那曲子好忧伤,听得我爸妈直掉泪。
那么,你该咋办呢?我们能帮你什么忙呢?我和二狗朦朦胧胧地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爸说,万事皆天定,半点不由人。缘分缘分,谁有缘谁有分。
然而,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出现了。
一天晚上,知青干事马光成居然打着手电送梁红梅回来了,梁红梅边走边小声地嗔骂,别动手动脚的,谁要你送!四眼儿的口琴声戛然而止,天地间仿佛窒息了。
宁可好了四眼儿,也不能让猪拱了嫩白菜!我和二狗慌忙伸出手来接着,生怕詹文革的眼珠子掉地上。
第二天一早,村子里就爆炸性地传开了:蜈蚣岭不干净,鬼戽沙哩!把马干事吓了个半死!
这以后,都是四眼儿接送梁红梅了。
再后来,知青们陆续返城了。
四眼儿招工回了省城,吕佩玉当兵走了,剩下梁红梅一个人,公社文艺宣传队也解散了。她白天去学校代课,夜晚独自复习功课,听说要恢复高考了。
梁红梅常常在夜里哭,但她的哭声都被夜色吞没了。她不知道,詹文革、我和二狗在黑暗中陪护着她。
梁红梅又是大哭一场,不过这次是抑制不住兴奋激动的哭,她考上大学了!
但梁红梅高兴得早了,公社知青干事马光成不给她签字盖章,不签字盖章就走不了人,上不成大学。伤心的哭声刺痛着詹文革少年的心,詹文革“请”来了他妈。
文革妈问,姓马的凭啥不给你盖章?
梁红梅红了脸,哭得更凶了,最后咬着耳朵对文革妈说了。
文革妈把大板牙咬得咯嘣响,骂道,这个骚牯牛!闺女,你明天去趟公社,答应他,让他明天夜里到知青点来。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有办法对付他!梁红梅急着去上大学,胡乱地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晚上,按照文革妈的吩咐,梁红梅去麻子队长家跟文革睡,文革妈睡在了知青点。
梁红梅让詹文革和她睡一头。詹文革怎么也睡不着,他闻到了一种淡淡的似有若无的幽香,他后来对我啧啧道,不像八月桂那么冲人,也不像栀子花那么呛鼻,那香味真好闻,闻了像喝醉了酒似的。对了,是兰花香。人身上怎么会有兰花香呢?
梁红梅突然说,冷,好冷,弟弟抱着我。詹文革就抱住了梁红梅,两个人都仿佛打摆子似的抖。
詹文革的手不小心碰到了梁红梅的胸,詹文革就顺势捧住了。梁红梅让他捧了一会,轻轻地把他的手移开了,梁红梅说,弟弟,属于你的那只苹果还很青涩,等它长大长熟了,风一吹,就会落在你的怀里。说这话的时候,“姐弟”二人眼睛里都闪着泪花儿。
那天晚上,马光成居然来了,他居然不怕“鬼戽沙”!
文革妈拿到了公社签字盖章的表格,梁红梅“扑通”跪在了麻子队长两口子的脚下。
四眼儿和梁红梅到底没能结合在一起,四眼儿娶了吕佩玉。
梁红梅一直单着,终身未嫁,脑子还有了点毛病。
她考取的是上海戏剧学院,她执导过不少很成功的戏,她后来成了一位很有名的戏曲导演,鲜花和掌声一路伴随着她,如果不是她后来亲自既编且导且演了一部戏。
詹文格听说那戏叫《恋之殇》,给她招来了很多麻烦。那部戏找不到赞助商,她就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积蓄。未曾想,戏没公演就被叫停了。
那是一部什么样的戏呢?詹文格好奇地探问过业内权威人士。
怎么说呢?《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你看过吗?意大利电影。说的是一个纯真少年对于一个成熟女性的朦胧恋情。当然,我只是打个比方,也许,并不恰当。
怎么会这样呢?
这些是詹文格在几十年后蜈蚣岭知青点的废墟上告诉我们的。
我这次回来,是在老家县城开办一家红梅剧场!就请你俩负责。
在我和二狗惊得嘴巴里能塞进一个拳头时,詹文格大声说,这部戏终于可以公演了,我拿到了它的首演授权!为了忘却,也为了纪念。
下半夜了,万籁俱寂,露水把我们坚硬而又柔软的心打得潮乎乎的。
想哭。
责任编辑 老 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