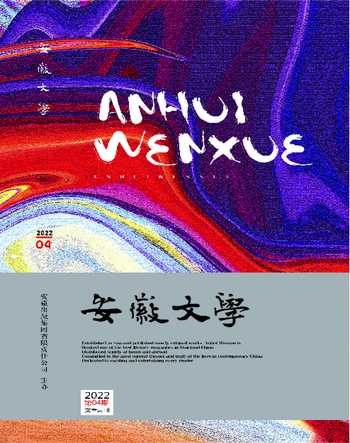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
2022-04-19张伟
张伟
在对《老嘎斯汽车司机》说长道短之前,让我们先揆诸小说史,看看小说的前世今生,发展走向。小说起源于神话,嗣后有志怪,唐代称传奇。神、怪、奇,顾名思义,早期的小说是以炫新猎奇为能事,从而满足、取悦读者的。神话,是先民无力对抗自然时幻想出一种超自然的神奇力量,射日奔月,移山填海,人类的伟大抱负,人类的本质力量,在这里得到了虽说虚幻却无愧于“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充分表达。志怪,志者,记述也;怪者,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也。干宝《搜神记》里的故事,粗陈梗概,情节离奇古怪,荒诞不经。传奇,得名于晚唐裴铏小说集名,无奇不传是也。虽然仍在传写奇闻,但已由鬼神怪异之事,变而为多瞩目于现实题材。经宋代的话本,一步一步走来,小说成为明清两代的标志性文体,伴随着诗、文的衰落而逆势生长,凸显崛起。我们看到,这期间有一条清晰的轨迹,即一个逐步落地的过程,一个越来越忠实于生活、贴近生活的过程,直至伟大的现实主义经典《红楼梦》诞生。不是说精灵古怪就不好,明代也出现了《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还跻身于四大名著之列。清代也有《聊斋志异》问世,花妖狐媚,说神道鬼,短篇之精粹,后世之范本。我们意在描述小说之大势所趋。“传奇”之名,到了明代,就不再是小说,而是戏剧的称谓了,这也就意味着,小说的一部分功能,让渡给倾力组织矛盾冲突的戏剧了。电影的逼真的写实性,对戏剧的虚拟性假定情境,又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早期电影的话剧腔,如于是之、谢芳主演的《青春之歌》,今天的观众听起来,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所以才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影与戏剧离婚一说。
在我看来,《老嘎斯汽车司机》问题正是出在作者想剑走偏锋,出奇制胜,却由于对时代的隔膜,对笔下人物把握不准,片面追求传奇性而导致作品失真。十九世紀中期,恩格斯批评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指出其“恶劣的个性化”,要害在于“对偶然性人物的既空空洞洞又非本质的特征不厌其烦地去描绘”,拉萨尔虽然在观念上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把这些字句写在了序言里,而在创作实践中却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
小说讲述的是“我岳父”余本超的故事。核心事件就很八卦。我不否认,在那个刚刚结束战争的年代,在寒风呼啸的大西北,流传着很多这样的传说,但多是捕风捉影、添枝加叶的,民间传说大都是这样形成的。为了把故事说圆,让人信服,也得把残缺的部件补上,一传十,十传百,集聚众人智慧,越来越丰满,同时也与真相越来越相去甚远。“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段子手口耳相传,聊以解颐罢了,拿这样的传说来写小说,且作为情节骨架,理当慎之又慎,弄不好会穿凿附会,漏洞百出。
“我岳父”是一个油田物探队的卡车司机,是从部队整体转业到油田工作的。战争让女人走开,大西北的油田亦然。可是,没有女人,这小说怎么能写得活色生香呢?不仅要有,还得是非同寻常的。于是,“我岳母”便作为不等边三角形中的一角出场了。小说给我们画了两个相重叠的三角形:首长——女学生——岳父,是一个;女学生——岳父——吴秀英,是另一个。岳父对首长有救命之恩,首长却凭着位高权重,抛弃了妻子,娶了岳父钟情的女学生(后来的岳母)。有了这个端口,后面的出格、离谱,就节节攀升了。如果说,那时许多首长都喜新厌旧做了陈世美,影视剧已反复演绎过,不足为奇,岳母究竟是爱首长还是爱岳父,就是一笔糊涂账了,是我理解能力差看不明白,还是像流行歌曲唱的,“这就是爱,糊里又糊涂”?当岳父冒着傻气去问首长的新媳妇男女性事时,得到一耳光。小说给出的解释是,因为这个女学生喜欢岳父,却被首长娶了,这一耳光是借机报复。如此说来,她是爱岳父的。工友拿岳父和女学生开玩笑,被岳父打得鼻青脸肿。可见岳父深深爱着女学生,这份感情不容亵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吴秀英),岳父不为所动,依然痴爱着女学生。可是,首长自杀了,女学生因此痛不欲生自杀了两次,难道她爱的是首长?下文交代,岳母常打小时候的妻子,“是把对大队长(即首长)的愤怒转移到了我妻子身上”,分明是怒而不爱嘛。当首长以副指挥长的身份出现在大庆时,岳母又想“跟副指挥长和好”,要把岳父推给吴秀英,“好大鸣大放地追副指挥长去”。最终她到底还是投入了首长的怀抱,真是莫名其妙。写她三心二意,举棋不定,也可以,生活中也有这样没主意的人。但小说塑造人物形象,不仅要写出他做什么,更要写出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这才是小说家的真功夫,是金圣叹推崇的“气力过人处”。
女学生的行止已经很混乱了,作者还嫌戏份儿不够,又请出一位神经大条吴秀英。老百姓把物探队的十面红旗偷了,岳父心生一计,谎称测量仪能看清几千米以下石头缝里有没有石油,当然也能勘察红旗的藏匿之地。吴秀英信以为真,她已把红旗做了内裤,身体的秘密暴露无遗,哭诉无法做人,接着便是以身相许。虽稀奇古怪,却也事出有因,合情合理。但后面的情节就有失理据了。吴秀英何以百折不挠,终生迷恋岳父,不可理喻,理由不充分,故事不可信,编造的痕迹太重,人物也显得苍白而没有血色。
首长就像作者手里的玩偶,没来由地让他跳井自杀,继而下落不明,女学生便成了“我岳母”。这里有个小复杂,倒值得肯定,岳父母婚后五个月产下“我妻子”,因而其生父还是首长。已经消失的首长,“又奇迹般地在大庆出现了”。“奇迹般地”,显然作者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不打自招了。写小说,不是凭空制造奇迹,而应该写出性格逻辑和情理依据。后来首长又被关进去了,需要他出场时,又像不死鸟一样飞落在江汉。来无踪,去无影,“被驱不异犬与鸡”。简直匪夷所思。
小说来源于生活,优秀的电影又改编自小说,这是过去很多年都不变的“二次转换”,几乎成为一条铁律。可是,这些年似乎变了,小说跟着电影电视剧跑,而不再是尊重生活的诚实创作,小说作者轻慢地玩起了电影思维。推拉摇移,在没有一点铺垫、读者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推出一个大特写,把读者一个趔趄撞出老远,这就是所谓的视觉冲击力吗?这篇小说也是如法炮制,人物任意驱遣,场景随意转换,西北——东北——中南,空间大跨度挪移。讲“我岳父”的陈年往事,讲着讲着就跳出来已然成年、身为导演的“我儿子”,因为这里需要他导一部电影,才能接续得上。当年的68个炮眼,吴秀英种了68棵杏树,长成一片杏林。这让我联想到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当高仓健饰演的岛勇作出狱回家时,那一面缓坡上,飘扬着一片暖暖的、杏黄的手帕,那份盎然的诗意,在温暖了主人公的同时,也点燃了广大观众的激情。而我想说的是,电影这样的艺术处理方式,生硬地塞进小说里,就未必合适了。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里说:“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这句话,就像一句谶语,逾千年而警示今人。构思新奇,可能着实让作者激动,可是,写出来,落实到文字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检视这篇小说,从人物性格、人物心理到人物关系,都存在着很多疑点,粗枝大叶地浏览一过,也能满足一下读者的好奇心,世上还有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而以评论之眼仔细端详,就会看出破绽来。金圣叹在小说评点中强调,情节的传奇性必须有现实基础。“何等奇妙,真乃天外飞来,却是当面拾得。”(《水浒传》第41回批语)“陡然插出奇文,令人出于意外,犹如怪峰飞来,然又却是眼前景色。”(《水浒传》第54回批语)经典作家的创作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借鉴。
责任编辑 黄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