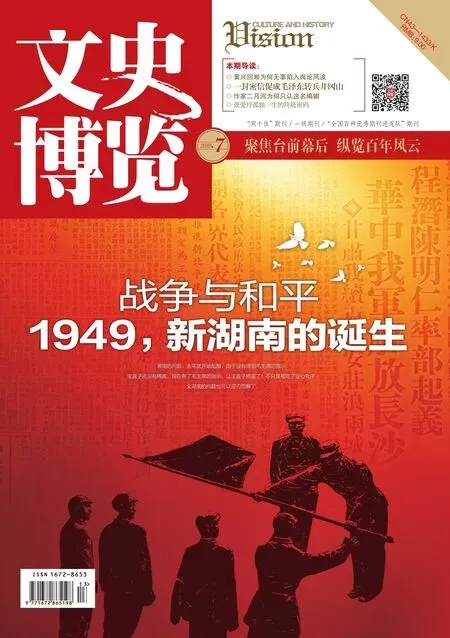我在知青点偷看文学名著
2019-12-15
1966年我14岁,小学毕业。10月上旬,我所在的四川平武县城关镇组织动员首批知青“上山下乡”,我报名参加。中旬,我们40名首批男女知青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来到与北川县片口乡接壤的马家公社前锋大队高山上的大渠园生产队插队落户。
我们这批知青,家庭出身绝大部分是“黑五类”,父母在“文革”初期,先是被批斗,随后被陆续赶下乡劳动改造。
生产队曾队长的女婿赵远河给我们腾出4间瓦房,依次是厨房、女宿舍、堂屋、男寝室,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家。白天,我们和社员们一起劳动,晚上吃了饭,有的在堂屋火塘边烤火,有的上床靠坐在大通铺的马灯下学“毛选”、背“老三篇”或学唱“样板戏”和“语录歌”,10点多钟,便熄灯睡觉。
那时我渴望阅读一些中外文学书籍,然而在知青点只有马、恩、列、斯、毛的书。元旦回县城,我到新华书店去买文学书,却一无所获。店里售书的女同志告诉我,因“破四旧”,国内很多著名作家和翻译家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们的书也被定性为宣扬封、资、修的“黑货”和“毒草”,已被列为禁书。
过了元旦,我从县城回到知青点。一天晚上,大队通知我们开批斗会,批斗的是一名1964年到我们大队插队的“黑五类”知青。因他在知青点公开阅读《燕山夜话》、巴金的作品,以及傅雷、查良铮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被人告发。我当时就想,这些书是从哪里来的?过了一段时间,有天晚上,我半夜起床上茅房,看见有五六个年龄大点的知青在昏暗的马灯下看书,看得如痴如醉。我心想,累了一天,已是深更半夜,是什么好书使他们这样入迷?
一天下午,我们在离知青点不远的山坡上干活,我借故回到寝室,在他们枕头下翻找,结果发现他们枕头下的铺草里藏有不少文学书籍,书的封面都用旧报纸包装,并用毛笔写上“毛选”或“马、恩、列”著作等字样,其中“正大个儿”(知青正常翔的外号)的铺草里藏有七八本名著。
有天下午收工,我身边只有“正大个儿”,于是我向他借书看。开始,无论我怎样求他,他都不借。我知道,他根本不信任我这个家庭出身“红五类”的小弟。于是我对他说,如果不借我,我就到大队告发他。他顿时害怕了,说,只要我发誓为他保密,他就把书借给我。此后,我得以经常从他那里借古今中外的书看。
时间长了,“正大个儿”觉得我这个人可靠,于是就把其中一些秘密告诉我。原来,知青点其他人阅读的文学书都是从他那里借到的。“正大个儿”1965年高中毕业,因家庭出身地主,政审不合格,未考上大学,一直在家待业。他的大哥是县文化馆的馆长,平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县文化馆的阅览室看书。人手不够时,大哥就叫他帮忙并把阅览室和书库的钥匙交给他。“破四旧”时,县城大批文学书被红卫兵查抄烧毁,他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冒着风险趁混乱陆续将阅览室和书库中的100多本文学书偷拿回家藏起来。插队落户时,他带了十几本书到知青点看。后来每次往返县城,他都要带上十几本书。
在插队的几年时间里,我不仅阅读了屈原、李白、茅盾、老舍、巴金、郭沫若等人的文学作品,还阅读了但丁、拜伦、雪莱、裴多菲、普希金、海明威、高尔基、巴尔扎克等人的著作。那是一段生活艰苦但心里充满阳光的日子,是我青春期最美好的时光。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开阔了我的视野,陶冶了我的情操,净化了我的心灵,对我的健康成长以及后来的人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