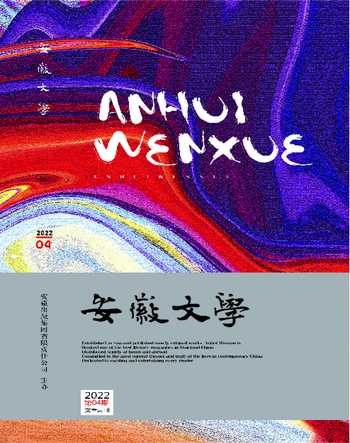老嘎斯汽车司机
2022-04-19余述平
余述平
人活着不一定是为了明白,活着,多么简单而粗鄙的事,我的老岳父,一个在祁连山出生的,不知道铁和事物如何向下的人。他一辈子活的,争取像一个鸟样。
他一辈子都在找一个鸟巢。
但悲伤的是,他做过巢的每一棵树都死了。
他有一年给我说过,榆林窟才是中国壁画的精华。我不懂,我是个历史虚无主义者,我当时想,你就是一个司机,纵横天地了为的只是一辆车。
我跟他女儿恋爱的时候,他把我们分拆成了灯泡、车头、方向盘、车厢和轮胎。我生气了,我说,她不是零件,她是雪莲。
我跟他女儿恋爱,老想加油,私奔。
因为他给女儿找男朋友定了一个规矩,他必须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司机。
而他,永远板着甘肃苍劲有力的脸,他说,老子看中你妈的时候,对着祁连山脉,跪拜了一年四季。
我当然知道,一个辽阔地方出生的人肯定愛吹牛。
我岳父是一个油田物探队的卡车司机,部队转业,张复振的队伍,石油历史上最著名的石油师,毛泽东主席亲自下达的转业命令。他们在陕西汉中集结集训后,就兵分几路往西北更远的西北进发了。他的目的地是冷湖,到了冷湖,他被分配到物探队当了一名嘎斯卡车司机。地道的苏联货。能开一辆地道的苏联嘎斯卡车,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当时录取的标准不光是你开车技术娴熟,还要长相仪表堂堂,政治立场过硬,在大是大非面前,行得正,站得稳,蚊子钻进眼珠里去了也绝不眨一下眼。我岳父本来是给首长开车的,但他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开车喜欢驾驭威猛雄壮的大家伙。他说他虽然没有多少文化,离一个完美的文盲几乎只有一个约等于的距离,但一个有追求的人,他内心里是不能没有格局的。首长当然想把他留在身边,他喜欢我岳父,是因为我岳父至少替他挡过五次子弹,这么出生入死为你挡子弹的部下,你用大太阳的视野满世界寻找也是难以找到的。
我岳父风华正茂的那年在汉中训练,他看中了一个女学生,首长对他说,你给我听着,等你进步了,提干了,混了一官半职后再想这球上的事。我岳父听了首长的话,那个年代的人都听领导的话,不让想球上的事,那就用努力工作这根皮带把形而下的这裤裆勒紧就行了。但后来已经有了老婆的首长把老婆休了,娶了我岳父看中的那个女学生。我岳父气坏了,从此他明白了,这恋爱也是讲究战术的,领导就是领导,解放裤子皮带的水平都比普通人高明些,你不服也得服。
没有了爱情想法的岳父,把身上的一股劲都使在了嘎斯汽车上,他说他一直把嘎斯汽车当作一个女人来热爱。物探队不会把嘎斯汽车像小媳妇养在闺房里,它要四处去野,要像个荡妇疯疯癫癫满世界跑,越是人迹稀少的地方,越来劲,越放肆。物探队是干什么的呢?现在的农村小年青甚至是城市青年,他们无论多么新潮,大概十有八九不知道物探队是干什么的。物探队是油田开发的先头部队,全称叫地球物理勘探队,他们可是共和国一支精良的工业队伍。二十世纪中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以老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卡中国的经济脖子,企图通过各种封锁将红色中国扼杀在摇篮中,其中石油和钢铁是他们控制的重中之重。没有石油,你机器转动不了,飞机飞不起来;没有钢铁,就没有其他工业的材料,你做什么都没硬度,都是软塌塌的垃圾。所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说,你给我五百万吨石油和五百万吨钢铁,我可打赢任何世界战争。这支队伍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带着专业化仪器长年奔波在茫茫戈壁滩、山区和沼泽地,他们天南地北,纵横驰骋。这石油有点日怪,不在城市的地盘之下苟且,专往荒郊野外、人迹稀少和生存都很困难的地方钻,你不使出十八般武艺,它就一直黑着脸在地下藏着不见你。你庞大的物探队把身体里的炮放完了,也是对着空气放空炮,加上那个时候的勘探不像现在这么先进,连卫星都搬来助阵。那个年代的物探,就像男人让女人怀孕,除了打铁自身要硬外,运气还是要有的。地球就是一个复杂结构,石油就是一个诡异的黑珍珠女人或黑寡妇,你和她的相爱注定要击穿厚厚的岩层,和她在深深的封闭圈轰轰烈烈地举行一场隆重婚礼。有的感情太丰富撞击太猛烈,就要冒出烈焰产生井喷。所以也有人说,石油人一生就是在迁徙中一次一次举行婚礼,他们是在征服和拯救被岁月囚禁了无数年的女人。物探队是个野外队,家是养不下他们的,也就是这个原因,女人们不是自身有了问题是不会嫁给他们的。嫁给他们,等于嫁给了空房子、空床和空被子。
我岳父爱嘎斯汽车这个媳妇是爱出了大名的,这个雄壮的女人不是谁都可以驾驭的。我岳父喜欢干净纯粹威猛的女人,这苏联老大哥的嘎斯大卡车符合他的审美需求,他自从拥有它以后,就不爱住职工宿舍了,恨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睡在嘎斯汽车上。跑野外,车子是不可能不脏的,但晚上一回来,他不是先吃饭,而是先把车洗干净。领导和工友劝他先吃饭,他们说,这车反正明天又要脏,你洗它干嘛!我岳父生气了,他说,我要让它天天像个新娘,难道你们喜欢一个邋邋遢遢的媳妇?
物探队的人嘲笑他,说我岳父想女人想得走火入魔了。我岳父盘弄这老嘎斯汽车,经常盘弄到深夜一两点,第二天,他是第一个到集合地点的。他站在嘎斯汽车车头的踏板上,注目着东方。那个年代的人,都向往东方,他们有一句口头禅,太阳永远从东方升起。他们还有一句话,东风一定会压倒西风。车头上的小红旗在我岳父的耳边飘扬,所以每天灌进我岳父耳朵里的声音一定是高亢有力正能量的。他站在车头的踏板上,像个贴身警卫守护着老嘎斯汽车,他们一点都不老,他们比新婚夫妻还崭新。他行注目礼一直等到物探队的人们来装工具装设备,这时,我岳父像个老婆婆开始唠叨了。
你轻点行不行?放个东西像丢原子弹似的。
你衣服多少个世纪没洗了?别把我们家嘎斯弄赃了。你个狗日的别把身体往嘎斯上靠。
你,你,你,别把测量仪直接往车厢里放,这会把嘎斯刮伤的,垫个垫子什么的,让嘎斯和测量仪两个人都舒服些。
有年纪大了的结了婚的老师傅说,你没结过婚,还尽开黄腔。
我岳父一脸无辜地说,没有啊,我说的都是事实,什么叫黄腔?
老师傅说,你问问大队长新媳妇就知道了。
大队长就是我岳父那个团的首长,大队长媳妇就是我岳父看中的那个汉中女学生。
我岳父真去问大队长新媳妇了,汉中女学生当即给了他一耳光,她说,你连耍流氓都不会,还叫个什么男人。
物探队后来流传一个说法,汉中女学生借机打击报复我岳父。他们私下认为这个汉中女学生还是喜欢我岳父的。
挨了一个女人打的我岳父的人生很快就被颠覆了,他对所有的女人都没有兴趣了。至少他表面上是这样,而且物探队的所有人都认为他是这样。因为有一次,队伍作业完后休息一会,大家盘腿玩纸牌,谁输了,脸上就被炭笔画一道鬼符,输两次,就画两道鬼符,运气不好的,脸上就被鬼恶贯满盈地全部占领。后来,几乎每个人都是一脸鬼符后,大家你瞪着我,我瞪着你,活生生一个魔鬼的世界。有个当了魔鬼的工友拿大队长新媳妇和我岳父开了玩笑,我岳父当即把那工友掀翻在戈壁滩的石头上。他把那可怜的工友骑在自己胯下,一顿猛揍。暴风骤雨之后,那工友就辉煌地鼻青脸肿了。
我岳父为此在物探队做了三次深刻检讨。
那一年,物探队到祁连山的一个山脚下做勘探工作,山上住了不少人家。
当物探队的各种车辆一路搅起漫天灰尘,浩浩荡荡开进山里的时候,村民们全都跑出来看稀奇了。
那个年代,看见个汽车就像看见了外星人和新鲜事物, 他们看到这一长溜的车队,以为又要发生战争了。
物探队一干人马在山里一字摆开,钻眼,埋雷管,放线,隔一百米就插一个红旗。各种设备依次各就各位,手持广播这时开始广播了,老乡们,我们是石油物探队,到这里不是打仗的,而是来为祖国寻找石油的。等一会我们就要放炮了,请大家以红旗为界限,不要近距离围观,一定要撤到安全区。
负责警戒的工人监督老乡们撤到安全区以后,他们也撤离了。我岳父得天独厚,一个人爬到车头上坐着看风景。每一次搞地球物理勘探的作业时,他都像一个大人物一样坐在车头上,这是他的特例,谁也不能共享。
在确定安全以后,指挥员把手中的红旗一摇,大喊一声,开始,放炮。操作员按下电路开关,电流通过埋设的电线迅速到达事先打好的钻孔里,引爆那里的雷管。雷管爆炸,从钻孔里喷出一股黑色泥柱。就这样一路的雷管都依次爆炸,整个山野都回荡着隆隆的炮声,鸟从树林里腾空而起。
一个多小时后,收线员开始收线,他们将黑皮软电缆线一圈一圈收起来。我岳父还站在嘎斯汽车车头上,像个避雷针一样架在那里。这时,鸟开始回归山林,山野一片寂静,我岳父站着睡着了。
工人们和技术人员在天黑之前都陆续收工回来,他们把仪器和电缆线装上车,我岳父又开始来劲,叉着腰叫工人装车时要小心轻放。工人们已经习已为常,谁也不理他,我岳父唠叨基本上是对空气唠叨。使用了一天的工具肯定是脏乱差的,不可能不把车厢弄脏,我岳父唠叨也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唠叨。
物探队在祁连山作业了半个月,每到一处,都有一批粉丝老百姓跟着,勘探作业十分顺利。但收官之作出了一点小纰漏,那一天,老百姓把十面红旗顺回家去了。
怎么办呢?这十面红旗也是生产资料,公共财产。作业队长把情况用电报的形式发给在基地的大队长,大队长下了死命令,必须把十面红旗一面不少地追回来。队长找到当地的领导,他们口头承诺都挺好,但回去后只是转了一圈就回话,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顺了红旗。
队长一筹莫展,号召大家想办法,他说,谁追回一面红旗就奖励一碗红烧肉,另加白酒三两。
有了这个重奖,大家纷纷进山破案去了,他们还没有进村子,就有人吹了口哨,紧接着村里的狗倾巢而动,扑了出来。可怜的物探工人们狼狈不堪地撤了回来。回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一脸噩梦,好像刚从地狱里虎口脱险。
我岳父是少数几个没有进村的人,他站在嘎斯汽车车头想了一天一夜后,终于想出了一个比天才更天才的想法。他叫上队长,说他今天要当总指挥,所有人包括你队长也要听从我调遣。队长回他说,搞不成,老子罚你关禁闭。我岳父说,只要按我的方法办,一定可以马到成功。
我岳父叫队长把测量仪架在嘎斯汽车车厢上,车厢门全部放下。他叫队长拿一个嗓门大的高音喇叭,高音喇叭他自己拿着放进驾驶室,再叫工人们把那测量仪保护好,然后他开着车向村子进发。
车子开得很慢,似乎在蛇行。
我岳父把车停在村口百米的地方。车停好后,他从驾驶室拿着广播喇叭跳了下来,然后爬上车厢,他叫工人们在测量仪身边散开,他自己一个人站在测量仪后面。他再次嘱咐大家要表情严肃,不要瞎吱声,一切以他的口气为准。大家都退到挨车头的车板上靠着,看我岳父究竟要使出什么幺蛾子。
我岳父打开广播喇叭,他清了三下嗓子后就开始对村里喊话了,各位老乡请注意,各位老乡请注意,我是物探队的革命大喇叭,现在我要跟你们对话广播了。我们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到了你们这块风水宝地,就是来为祖国找石油的。如果这里有了石油,你们家家户戶都会红火起来,富起来。老乡们,同胞们,我们都是阶级兄弟,大家热爱红旗可以,但这红旗是我们的生产资料,不是废品。因为下一次勘探工作少不了要用它,请暂时替我保管它的乡亲和亲人们把红旗还回来,我们将不胜感激。
我岳父口若悬河一个人鼓噪了半天,还是没有一个人把红旗送回来。队长急了,他对我岳父说,搞政治思想教育,老子比你有经验得多。别这么温柔地扯犊子了,给我滚开,我来。
我岳父没有让出自己的位置,他当仁不让地拿着高音喇叭,他对队长说,你哪里好玩到哪里去。我岳父他自己觉得很有信心,他还在拿着高音喇叭循循善诱讲着道理,他心里有数。他看村子人都出来了,他们集中在一个高坡上看热闹。
高坡上人头攒动,这时,我岳父立即开始转换演讲风格了。他用手指着自己面前的测量仪说,乡亲们,亲爱的同胞们, 我们这支勘探队是一支科学装备的队伍。大家看看我面前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神奇的千里眼,它能看清楚几千米以下石头缝里有没有石油。大家把红旗藏在什么地方,我们用它一探就知道了。我们今天迫不得已才搬来这个神器,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只要把红旗还回来了,我们不追究你们任何责任。半天,我们只给大家半天时间,过了这个时间,那我们只好动用这个设备破案了。
工人们扭过来,捂住嘴巴想笑,队长用脚轻轻踢了一下我岳父的屁股。
乡亲们从没见过这种设备,但他们一想,这设备能看见地球深处的石油,那还有什么不能看见呢?还是把红旗还给物探队得了。
九面红旗陆续被送还到了物探队,但黄昏的时候,还有一面红旗没人还回来。队长说,收兵,一面红旗不要算球了。
正准备鸣枪收兵的时候,一个大姑娘找了过来,她很焦急的样子,手上没有拿任何东西。她问物探队,谁负责看这个千里眼。我岳父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脯,他说,是我,干嘛?
这个大姑娘长相真不错,只是穿的衣服有点陈旧。她说,这千里眼真的什么都能看见?
我岳父说,地下几千米的石油隔着那么多石头都能看见,你说说它什么不能看见?
我岳父话音刚落,这个大姑娘就蹲在地上哭了起来。队长和工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劝大姑娘,你哭个啥?大姑娘哭得更来劲了,我什么都被你看了,你叫我今后在村子里怎么做人?队长和工人们更加稀里糊涂,不知所云了。队长毕竟是个领导,头脑反应的比一般人当然要快些,难道是有人背着他,偷偷溜进村庄把人家大姑娘睡了?他厉声喝道,谁干了坏事,他娘的给我站出来。
这时村子里的人也围了过来,物探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认自己对姑娘干了坏事。队长把姑娘扶起来,他对姑娘说,谁干了坏事,你大胆指认,我替你做主。姑娘害羞地用手指了指测量仪,然后又指了指我岳父。
队长问,这个,那个,一个是设备,一个是人,他们是怎么欺负你的?
大姑娘说,还有一面红旗是我拿走的,我今年是本命年,正好用它做了一件红内裤。他说千里眼什么都能看见,他看了我穿的内裤,也就把我身体的秘密都看了,你们叫我今后怎么在村里做人。
老乡们有人喊道,对,找他狗日的负责。
我岳父站在那里哭笑不得,他自己导演的戏砸了自己的脚。
队长也是哭笑不得,他又不能当着村民们的面,把事情的真相捣鼓破。他只有顺着来,敷衍一下,到时候屁股一拍,溜之大吉。他对大姑娘说,我们赔一桶柴油给你行不行?
大姑娘摇头。
让他在你们家劳动改造一个月行不行?
大姑娘摇头。
那我们干脆把他交给公安局去处理行不行?
大姑娘急忙喊了起来,不行,肯定不行的。
队长说,那你说怎么办?
大姑娘说,我要他对我负责,他把我看了,我就是他的人了。
村民说,两个选择,一是叫他留下来做女婿,二是叫他把吴秀英这女娃带到油田去。
这个大姑娘叫吴秀英。村里人说吴秀英是他们村最漂亮的姑娘,也是全村最穷的姑娘,要是家境稍好一点,她何必拿你们的红旗做短裤。
我岳父一下子就像一头驴被丢进大海傻到家了,他的一张脸比死驴脸难看一万倍。
队长拍了拍我岳父的肩说,你个好小子,照单收了呗,艳遇啊,十八辈子打了灯笼都遇不到的好事。
我岳父不表态,因为他心里一直还装着另一个女人,就是那汉中女学生,物探大队长的新老婆。
队长对村里人说,乡亲们回吧,我们留吴秀英吃饭,商量一下这事如何处理。
晚上大家喝酒正酣的时候,我岳父偷偷一个人开着他的嘎斯汽车,甩下一众人马回了油田基地冷湖。
回到冷湖油田基地的时候,物探队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我岳父的老首长现在的大队长跳了井,人被从井里吊出来的时候,血肉模糊,医生都摇头表示没救了。后来,他在军代表的护送下去了兰州,从此下落不明。
在祁连山的那支物探队三天后回到了冷湖,跟随物探队一起回来的,还有那个把红旗做成了内裤的大姑娘吴秀英,她带了一大袋子的生活用品来投奔我岳父了。
吴秀英到了油田后,队长给了她一套石油工作服,他叫吴秀英到公家的大澡堂先洗澡,梳妆打扮穿上新工作服后再去找我岳父。
队长用心良苦,他想撮合这门姻缘。
吴秀英一个人洗了半天澡,直到洗出一身的细皮嫩肉,方才罢休。她穿着石油工作服走出澡堂的时候,整个物探队沸腾。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大院,吴秀英是他们见过的最美的姑娘,即前不见古人,也后不见来者。他们都说我岳父有艳福。
队长带着吴秀英到单身宿舍找我岳父,没找到。
我岳父其实就在大队长家里。物探队的人一谈大队长就谈虎色变,谁也不敢去大队长家问候他老婆。因为据军代表说大队长是畏罪自杀,全物探队只有我岳父一个人去了大队长家。
那个汉中女学生自杀了两次没死,都被我岳父救了下来,那段日子,他一刻不停地盯着汉中女学生。
队长是在大队长家找到我岳父的,队长说,吴秀英来了,你去见见她。
我岳父甩頭丢下一句话,不见。他现在整个心思都在汉中女学生身上。
队长说,人都来了,好歹也是要见见的,这是政治任务。
一说政治任务,我岳父身子骨就软了。
见面安排在队部,背景墙上是毛主席语录,吴秀英坐在毛主席语录下,一脸的光芒万丈。但我岳父似乎是一根死木头,这光芒根本点燃不了他。这历史性的会见以失败而告终,他没有答应吴秀英做他的媳妇,全物探队的人都深为惋惜。
队长带着吴秀英视察检阅了物探大队没结婚的小伙,吴秀英一个都没看上,她说她一辈子只喜欢我岳父。她不埋怨我岳父,说我岳父一时鬼迷心窍,被那女学生蛊惑了,他迟早一天会找她的。
吴秀英没有回祁连山,她临时住在冷湖,靠打零工养活自己。她的目的就是等我岳父。
我岳父选择了和汉中女学生在一起,两个人没举行任何仪式。五个月后汉中女学生生下一个女婴,这个女孩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汉中女学生就是我岳母。我岳父其实不是我真正的岳父,我真正的岳父应该就是那个畏罪自杀的大队长。
我妻子出生的时候,吴秀英专门带了老母鸡和鸡蛋去看望。第二天,她就伤心地离开了冷湖,回到了祁连山的村庄。
我妻子一岁的时候,我岳父和汉中女学生双双要求参加大庆石油会战,他们一家从大西北支援到了大东北。
本来故事到此可以结束了,但世事确实难以预测。我妻子五岁的时候,吴秀英又找到大庆来了,她是通过好多层关系才找到我岳父的。
我妻子是个独生女,不对,我岳父跟汉中女学生没有孩子,不是我岳父不想要,而是汉中女学生不想生。据我妻子讲,她父母经常吵架,主要是说我岳父偏袒调皮的她。我妻子小时候特别野,经常无原则地欺负男孩子。我岳母的教育简单粗暴,她用她们家祖传的一把竹尺敲打我妻子,把我妻子敲打的体无完肤。我岳母对我妻子有仇似的。我岳父后来有一次告诉我,我岳母其实是把对大队长的愤怒转移到了我妻子身上。
吴秀英是听说了我岳父和汉中女学生关系有点紧张的消息后才赶到大庆来的,当然也跟她自身情况有关。
这一年,我岳父的首长,物探大队长(我真正的岳父)又奇迹般地在大庆出现了,而且当的官更大了。他的身边有一个更年轻貌美的女人,他现在是副指挥长。你们想想,我岳母不气晕才怪。
我岳母想跟副指挥长和好,但副指挥长的女人把保护措施做得滴水不露,这防火墙高大耸立,汉中女学生插翅难飞。
吴秀英在大庆油田找到我岳父的时候,我岳父愣住了,他问你来干嘛?吴秀英还是那句话,你把我身子都看了,你要对我负责一辈子。我岳父无语,他说,你看中家里什么了你拿走。
吴秀英带了一麻袋的杏子给我岳父,她说这杏子是她亲自种的,她种了六十八棵杏树。她说她从冷湖回家以后,受到全村人关注,村里人都认为她已经是我岳父的人了。吴秀英回村以后,常常望着物探队留下的炮眼发呆。她在村子仔细转了很多圈,数了物探队打了六十八个炮眼。后来,她在每一个炮眼里种一棵杏树,这六十八个炮眼像神灵似的,让每一棵杏树都成活了,而且全部茁壮成长。以后的日子,吴秀英把这六十八棵杏树当成她和我岳父的孩子。
我岳母对吴秀英的到来欢欣鼓舞,她向吴秀英保证,我把余本超还给你。余本超就是我岳父的名字。她想把我岳父尽快推销出去,自己解放了后好大鸣大放地追副指挥长去。
吴秀英相信了汉中女学生的话,就在大庆不明不白地干耗着。
后来他们没有离成婚。过了几年,那个副指挥长不知什么原因又被关进去了。这时候,在江汉平原上又开始了一场石油大会战,我岳父岳母带着我妻子到了湖北的潜江。
吴秀英不是石油职工,她又只身一人回到了祁连山的村庄。
过了好多年后,我岳父收到了吴秀英的来信,她还一直把我岳父称为她的男人。她说她得了腿病,再也跑不出祁連山的村庄了,她只求求我岳父每年给她写四封信,春夏秋冬各一封。与她的信一起到达的,是一大箱杏子。此后,我们家每年都能收到吴秀英寄来的杏子,她寄的杏子又大又甜。
我岳父满足了吴秀英的要求,每次同时汇款十元。吴秀英一直没有结婚,村里都说她的男人在油田,是个牛皮哄哄的嘎斯汽车司机。
是的,我岳父余本超从冷湖到大庆再到江汉,一直是个完美的彻头彻尾的工人阶级。那辆嘎斯汽车他一直开着,直到退休报废。
我岳母最终还是离开了我岳父。
人生最不能琢磨的就是命运。有一年,我岳母经过五七干校,她听见有一个人在喊她。她转过身,发现喊她的那个人曾经是她丈夫,也是我岳父从前的首长,物探大队长,副指挥长。这个人有着惊人的生命力,像个坚强的不死鸟。我岳母不顾一切地扑进了这个男人的怀里,这个落难的男人在江汉并不孤单,他有汉中女学生甜蜜的温暖。
我岳父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给了汉中女学生鸟击天空的自由。他的条件是,你们不能把女儿带走,因为女儿说,你们带走她,她就死。我妻子选择跟我岳父共命运。
汉中女学生最终跟领导回了北京,不过她命薄,有一年被一辆肇事小车撞死了。
我妻子长大后就懂事了,学习成绩始终都是油田同年级第一名,她考上了武汉大学,和我做了同学。毕业后不久,我们结婚了,也很快有了一个儿子。儿子最爱听他外公讲油田的故事,儿子长大后成了一名电影导演。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妻子带我到江汉油田接受我岳父面试的时候,他对我比较满意地说,你要是能开嘎斯汽车就好了。我说,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跟你学开车。我经过我岳父严格的训练,终于拿到了能开大卡车的驾驶执照。我是我们武大第一个拿到顶级汽车执照的学生。我拿了汽车执照后,他把他的汽车让我开出去过了一次瘾,他还有些不放心,坐在副驾驶位置监督我。我开得很稳,他说,现在路上没人,连一只蚂蚁都没有,给我开野点。我听了,一下子把油门轰到底。
我们一直想把他接到武汉养老,但我岳父不干,他说他舍不得那辆嘎斯汽车。那辆嘎斯汽车被他安放在一个废弃的车间里,车间里只有这一辆嘎斯汽车。他在这车间设了岗哨,他就是门卫,谁也不能进来。车间外的空地上,我岳父种满了花花草草。那辆嘎斯汽车至今还是油光发亮,马达还可以启动,但车是不能上路了。有时,我岳父启动它,只是想听听老嘎斯雄壮的声音。
我岳父八十岁了,他依然每年给吴秀英写四封信,汇款金额变了,是每次两千元。我们家每年在杏子成熟的时候,都能收到吴秀英寄来的杏子。
我儿子知道他外公的故事后很感兴趣,他立志要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特别是那个祁连山的吴秀英奶奶,更是主要表现的角色。
筹拍期间,我接到了老岳父的电话,他说,吴秀英快不行了,我们一家去给她送下终吧,这是她最后的要求,我必须满足她。
我岳父还说吴秀英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要我开着那辆嘎斯汽车进村接她。我那辆嘎斯汽车早就报废了,它上不了路,你们说说,怎么办?
我问儿子导演怎么办,他说,问我就问对了。我筹拍这个电影几年了,让我外公开着嘎斯汽车去村里找吴秀英这场戏就是这部电影的高潮。我已跟俄罗斯大使馆联系过,我把老嘎斯汽车的照片发给了他们,他们已经复制了一辆,明天就运到武汉,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景真人实拍了。
这辆嘎斯汽车当然不能由我岳父驾驶,我儿子亲自驾驶。但首先我岳父在出发时必须做个驾驶的样子,然后我儿子把照片传给照顾吴秀英的亲人。十天后,嘎斯汽车开到了吴秀英村庄的山脚下,这时,我岳父说,这最后一节路,我亲自开。本来按正常速度,我们三天就可以赶到吴秀英家,但我岳父说,慢一点,我们在路上多一天,吴秀英就会多盼望一天。吴秀英那边的亲人也说,你们一天没来,她就一天不会瞑目。
我岳父开着嘎斯汽车到了吴秀英的家,我儿子的摄影队伍也跟着。
我岳父下车的时候,村子鞭炮齐鸣,全村都沸腾了,他们等这一刻等了半个多世纪。
吴秀英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她对我岳父说,你终于回家了。
我岳父连连点头,去扶吴秀英,吴秀英靠在我岳父的身上,周围的人一片抽泣声。
吴秀英劝大家,好好的,你们哭啥?
然后,她对我岳父说,我想坐坐你的嘎斯汽车。
我们一起把吴秀英扶到副驾驶室上,我妻子在她旁边照顾她。
我岳父亲自开车。
吴秀英在驾驶室特别开心,像个羞涩的女孩。
我岳父问,秀英,车往哪里开?
吴秀英说,你们当年物探队放炮的地方。
我岳父把嘎斯车开到当年施工作业的地方,只见那儿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杏树林。
我们一家人和剧组簇拥吴秀英和我岳父走进吴秀英的杏树林。
一年后,吴秀英离开人世。
我岳父没有回湖北,他還住在祁连山的那个村庄。
我儿子也把嘎斯汽车留在吴秀英的杏树林里,现在它是一座爱情博物馆。
创作谈
小说是要生长记忆的,它与种子有关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小说不能过多地纠缠于描写人物关系,甚至有些结局就是虚无。我期待小说理想的模式是,让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颗形象的种子,它们替我们呼吸,奔跑,瞭望,然后生长出一棵记忆之树。好的小说就是一片森林,无论幸福和苦难,万物都不会停止歌唱,我觉得小说的任务就是你让笔下的人物都获得一种生命的力量。
要实现这种生长和记忆的文学当然很不容易,可以肯定的是,复制生活和草率处理生活都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当下,空转的文学比比皆是,安于现状的写作永远是没有出路的。我个人认为,实现文学的记忆,生长,直到成为一颗形象的种子,其路径应该是这样的:一是实现人物的历史深度,二是故事的历史深度,三是想象力的历史深度,四是语言的历史深度。这四个深度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以历史为坐标,好的小说这四个元素缺一不可。
我曾在石油系统工作二十多年,我写作的青春时代也在那里,直到现在我除了两次在武汉过春节外,其他都是在油田过的春节。现在我离开油田二十年了,我的脑海里老浮现在油田一次野外作业时,一位老师傅给我讲的一个关于红旗的故事:一个物探队到某山区物理勘探,作业完后,工地上的几面旗帜被老乡拿走了。那年头,山民们没文化也没见过世面,油田人用勘探仪糊弄老乡,把红旗追回来了。这个故事如果复制和简单处理,它也会是一部有趣的小说,也会留下稍许的历史印痕。我觉得这么写肯定是浪费这个题材了。于是我把这个故事的历史空间拉长了,让它充满皱褶,挣扎,焦虑,痛点,当然更多的是有执着,理解,爱。我这么做就是想把文学的空间打开,让现在的年轻人,看到我们前辈的奔跑和呼喊。
做到这些了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值得这么做。
责任编辑 黄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