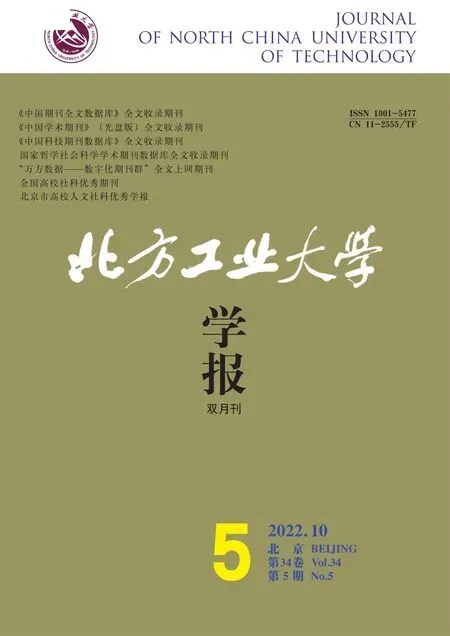春秋盟礼之“信”探析*
2022-04-16罗军凤
罗军凤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710049,西安)
盟礼本属周代礼乐制度。 《周礼》设玉府,掌管盟会之物;戎右掌辟盟之役,司盟掌盟载之法。玉府、戎右、司盟这些职官都是天子所设官职,掌管王室与公室、公卿、诸侯之间的盟礼。 《礼记·曲礼下》郑玄注:“聘礼今存,遇、会、誓、盟礼亡。”[1]周王室盟礼,与遇礼、会礼、誓礼一样,均已失传。 《左传》《国语》等文献记载的盟礼不是周王室与诸侯或卿大夫的盟礼。 王室东迁之后,周沦落为普通诸侯国,周与诸侯之间的盟礼已失王室盟礼的本义。 周初设盟礼,是为解决王室与诸侯之间的猜疑、嫌隙,周天子仍保有神权、王权,但春秋时期,周天子的神权、王权均已失落,盟礼上增设“交质”这一仪节,尤其是王室卑微的象征,不能再用周王室礼乐制度来解释。 学者分别讨论盟礼和交质,却未将二者联系在一起。[2]本论文以“周郑交质”一事,论述春秋盟礼的新变化,并分析《左传》君子曰对盟礼之“信”的阐发,以补前人之未备。
1 盟礼的特点
先秦典籍中的“盟”,均为盟礼。 汉唐注疏对“盟”的解释多种多样,侧重各不相同,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种:第一,指向盟礼“杀牲歃血”这一重要仪节,以此与“誓”相区别。 《礼记·曲礼下》:“约信曰誓,莅牲曰盟。”[3]《周礼·秋官》“司盟”郑玄注:“盟,以约辞告神,杀牲歃血,明著其信也。”[4]《说文解字》《文心雕龙》还具体指出盟礼所用牺牲和器物:“诸侯……十二岁一盟。 北面诏天之司慎、司命,盟,杀牲歃血,朱盘玉敦以立牛耳。”[5]“騂毛白马,珠盘玉敦,陈辞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6]
第二,指向盟礼的礼义“信”,以盟礼取信于双方,以防“将来”之不信任,此与“诅”相区别。《国语·鲁语》:“夫盟,信之要也。”[7]《穀梁传》曰:“盟者,不相信也,故谨信也。”[8]《淮南子》“周人盟”高诱注:“有事而会,不协而盟。 盟者,杀生歃血以为信也。”[9]《说文解字》:“《周礼》曰:‘国有疑则盟。 诸侯再相与会,十二岁一盟。'…… 盟,古文从明。”[10]《周礼·春官》“诅祝”贾公彦疏:“凡言盟者,盟将来;诅者,诅往过。”[11]盟字从“明”字得其义,盟礼之后双方不再安藏祸心,一切摆在明面,以防将来之患。
第三,指向人神之间的约束机制,假借鬼神以约束不守信用的一方。 《周礼·司盟》郑玄注:“司盟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12]《春秋左传正义》引杜预《春秋释例》:“盟者,假神明以要不信。”[13]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周初即有“盟诅之礼”,即“盟礼”。[14]《释名》:“诅,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15]盟礼是郑重其事在鬼神面前立盟,若有违背,则由鬼神降凶于人。 盟礼由鬼神施加惩罚于人,这一点,盟礼与会礼相区别。
根据“盟”的前两种解释,一是点明盟礼的仪节“杀牲歃血”,一是解释盟礼的礼义“信”,不免让人迷惑:何以杀牲歃血这样的行为能取信于双方,而且能防患于将来? 所以要解释盟礼,必须深入到古人的社会心理,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盟于鬼神,就可以致信,就可以达成两国之不疑?“盟”的第三种解释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假借鬼神的威力,对人形成约束。 考察春秋时期的盟辞,我们更能深入理解人神之间的约束机制。
僖公二十八年,王子虎盟诸侯,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若诸侯不拥戴王室,那么鬼神就会杀其身,亡其师,灭其国,且祸及子孙。 成公十二年,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盟于宋西门之外,盟曰:“……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晋楚两国世代相好,如有违背,就会亡师灭国。 襄公十一年,诸侯伐郑,郑与诸侯盟于亳,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 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氏,踣其国家。”盟书上列四项不该做的事、四件该做的事,若有违誓,所有的天神、山川之神、诸侯的祖先,都可以诛杀违盟之人。 鬼神的权力很大,不仅可以诛杀订盟之人,并可以祸及军队、国家、家族、百姓。 鬼神的约束是盟礼得以奏效的重要保证,故云“使不信者必凶”。 “盟礼”背后潜藏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鬼神有超人的能力,对人世间的人事有惩罚能力。 如果不相信鬼神能惩罚人,则盟礼失去约束力。
终春秋之世,盟礼“杀生歃血”的仪节未变,把“信”作为礼义这一点未变,但人神之间的约束机制却发生了极大变化。 盟礼在人神约束之外,加入了“交质”这一环节,这是春秋时期的大变革,《左传》以“君子曰”之口阐述了盟礼不可用质、盟礼重归于人神之信的主张。
2 盟礼“交质”的出现
至于盟礼的仪节,除了“杀牲歃血”之外,先秦文献及三礼未有更多仪节的记录,唐代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第一次详细讨论,[16]今人多引用、补正,踵事增华。 学者陈梦家结合考古资料,考证春秋盟礼的仪节有十步:为载书、凿地为坎、用牲、盟主执牛耳、歃血、昭神、读书、加书牲上、埋书、藏盟书之副于盟府。[17]山西侯马盟书遗址是春秋盟礼的历史见证,坑内有璧、璋等玉器,和牛、马、羊等家家畜骨骼,尤以羊为多见。 无论是考古,还是传世文献,盟礼皆无“交质”一事。
然而,参加盟礼的双方“交质”是盟礼在春秋初期的大变革,也是盟礼的大破坏。 《左传》记载隐公三年周郑交质,这一事件最易忽视的环节是盟礼。 为方便论述,兹将《左传》隐公三年“周郑交质”与“君子曰”之文录于下: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 王贰于虢。 郑伯怨王。 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 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 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 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 秋,又取成周之禾。 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 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 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锜釡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 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18]
周、郑两国交质,必有盟礼在先。 《左传》君子曰反对盟礼交质:“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杜注:“通言盟,约彼此之情,故言二国。”[19]明确指出周郑二国盟,清《诗义折中》:“春秋之世,人君有与其臣下盟者。 观周郑之交质,则王之盟其臣可类推也。”[20]亦谓周郑交质时有盟礼。
《左传》有盟礼之外附加“交质”的记载,虽然没有成功,但可以证明“交质”附加在盟礼之上。 哀公八年,鲁国欲与吴国盟,唯恐吴国不听从鲁国,鲁国以景伯为质,请求用吴太子为质。杜注:“鲁人不以盟为了,欲因留景伯,为质于吴。既得吴之许,复求吴王之子以交质。”[21]鲁人“不以盟为了”,于是提出“交质”,吴人不愿意出质王子姑曹,最后交质不成,只举行了盟礼。
春秋时期,盟礼出质的现象时有发生。 马非百《秦集史》谓周郑交质之后,“诸侯交质,遂成为国际交涉之惯例。”马氏统计交质事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凡六见焉”。[22]马氏统计有误,“交质”说亦不成立。 所谓“交质”,其所列举六事,只有五次出质,如晋太子圉为质于秦(僖公十七年),郑子良为质于楚(宣公十二年)、齐公子强(宣公十八年)及太子光(襄公元年)为质于晋,蔡昭侯使其子为质于吴(定公三年),都是单方面出质,而无“交质”;而哀公元年越王勾践行成于吳,并未出质。 诸侯之间每每盟礼后出质,或因质而求盟。 如宣公十二年“潘尪入盟,子良出质。”宣公十五年“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宣公十八年“齐侯会晋侯盟于缯,以公子强为质于晋。”成公二年,楚师侵卫,“公衡为质,以请盟,楚人许平。”这些都说明了“质”与盟礼关系密切。 可以说盟礼出质,成为国际交涉之惯例。
本文所论交质,更能说明盟礼的变革。 除隐公元年周郑交质之外,还有文公十七年晋郑交质、昭公十三年宋元公与华亥交质。 晋国合诸侯而与郑国有隙,晋“行成于郑”,当有盟礼,最后晋郑二国交质。 宋元公与华亥是在盟后交质。 可见,春秋交质都与盟礼相伴而行。
2.1 《左传》君子曰强调人神之“信”
不仅“周郑交质”背后的盟礼被忽略了,在明清评点中,《左传》君子曰以“信”为主旨,亦多被误解。 《左传》君子曰论及多个范畴,如“质”“礼”“忠”“信”“恕”,纠缠缭绕,在明清《左传》评点著作中,众多评点家认为君子曰以“质无益也”为主题句。[23]清末学者林纾《左传精华》论君子曰所论不在周郑交质的“质”,而是在“质”之外,欲“发明一义”:
后人读此篇,以《左氏》不主君臣之义立论,而以“质之无益”为言,似为失辞。 不知古人作文,皆以发明一义为言,……君子曰下一段,夷犹淡施,风致绝佳。[24]
林纾否定君子曰的主旨是“质无益也”。 至于君子曰所发明之义,林纾并未点明。 本文认为,隐公三年君子曰所欲发明之义在开篇第一字——“信”。 “信”是一个概念、范畴,《左传》有意将其措置于周郑交质之事后,是因为“周郑交质”是春秋时期第一次在盟礼中加入了“质”,违背了盟礼的本旨“信”。 君子曰以“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句开始,以“昭忠信也”句结束,实际上以“信”为始,亦以“信”为收束,其议论始终不离“信”。 隐公三年君子曰第一句便拈出“信”作为论述范畴:“信不由中,质无益也。”“信”不能不发自于内心,而“质”无益于“信”。 第二句指出依“信”而行“礼”,不需要“质”。 第三句,论述如果内心有“信”,祭祀鬼神可以是微薄之物。 第四句反问,依“信”行礼,何须用质? 第五句,指出“信”之义隐含在《诗》之义当中。 总之,“信”存于“礼”之中,而非“礼”之外。 此礼,即二国之盟礼,而“质”,不是盟礼应有之义。 乾隆时期学者李绍崧已发觉君子曰的主旨是“信”。 “篇中屡用‘信'字驳‘质'字。”“究只论‘信' 之得失。”“‘信'字是谋篇主脑,为‘质'字劲敌。”[25]君子曰排斥“质”,重申人神之“信”,冀复归于盟礼的本来面目。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指出盟礼要出自真心。 盟礼杀牲歃血以祭神,这些仪节均用以表内心的诚信,求信于鬼神。 在鬼神面前,如果没有诚信,鬼神是不会帮助他维系盟礼的约束作用的。 《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郑国大夫说:“要盟无质,神弗临也,所临唯信。 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临之。”[26]《春秋左传正义》引服虔云:“质,诚也。”郑国大夫子驷、子展指出若要鬼神照临,那么人必须有两个品质:一为诚(“质”),二为“信”(人言之信,信守自己的承诺)。 这两个品质实际是一个,即相信鬼神。 惟有真诚地相信鬼神,才能使鬼神照临。 惟人相信鬼神的约束力,盟辞方才有效,鬼神的惩罚才会降临在当事人中的另一方。 郑国大夫所说“要盟无质”,是指当年晋郑盟,晋卿士庄子强迫郑国接受自己所拟的盟辞:“唯晋命是听”,这样的盟辞并非出自郑国真心。 所谓“要盟”,即出于胁迫、而非出于内心意愿的盟礼。 郑国大夫相信,“明神不蠲要盟”。[27]杜注:“蠲,洁也。”明代学者刘绩解释道:“神不以要盟为洁而临之。”[28]晋人要挟郑国订盟,鬼神不会让他如愿。 盟礼要起作用,主要在于在人通过诚信,与神建立可靠的“信”,盟礼是人在鬼神面前达成契约。
春秋时期,诸侯屡盟,《诗经·小雅·巧言》讥之:“君子屡盟,乱是用长”,认为盟礼失信是天下大乱的根源。 桓公十二年一年之间,鲁公与宋公多次会盟,宋没有与鲁和解,却与郑伯盟,鲁遂帅师伐宋。 《左传》君子曰评论鲁宋之间会盟无信,并引《诗经》为证:“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襄公二十九年,郑国诸大夫盟于伯有氏,郑大夫裨谌引用《诗经》“君子屡盟,乱是用长”谓郑国大夫之盟是“长乱之道”。 襄公三十年,郑伯又与其大夫盟,《左传》君子曰认为郑国的盟礼如此频繁,将使“郑难不已”。 春秋时期无信之盟比比皆是,盟礼中鬼神对人的约束力转弱,故出现“交质”的极端例子。
当鬼神的约束力减弱的时候,主盟之人便用数量(寻盟)加以强化。 昭公十一年,晋与诸侯会于厥慭;昭公十三年,晋又合诸侯于平丘,欲寻盟。 周天子之卿刘献公认为没必要:“盟以厎信。君苟有信,诸侯不贰,何患焉?”此所谓“信”,即信守盟礼当中自己的盟辞。 《左传》哀公七年,鲁与吴盟,哀公十二年,吴欲与鲁寻盟,鲁国拒绝了。鲁子贡认为“盟,所以周信也。 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 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 若犹可改,日盟何益?”“盟,所以周信”杜注:“周,固。”“明神以要之”杜注:“要以祸福。”[29]盟礼通过鬼神祸福加身的方式强迫人固守诚信,归根到底,人在鬼神面前立盟,就意味着要信守自己立下的盟辞。 所以盟一而已,不必寻盟、改盟。 有人神之信,便可守住人言之信,不必用强权对盟礼加以干涉、强化。
综上,盟礼的“信”,有两层意思:首先,人言为信。 订盟双方皆需信守盟辞;人言若不信,则鬼神惩罚于人;其次,人神之信。 鬼神为诚信的人施加惩罚于不守信的人;若不诚信,则鬼神不临。 盟礼的最终归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 盟礼的神圣之处在于用一系列的仪式,动用鬼神,来约束人与人之间的“信”。 神高于人,但神为我所用。 神高于人,说明盟礼是信奉鬼神的时代特有的现象,是殷商巫鬼文化的遗留;神为我所用,则是春秋时期所遵奉的“理性精神”,此“理性精神”是礼乐文明超越巫鬼文化的根本特点。[30]
春秋时期,屡盟、要盟、寻盟、改盟屡见不鲜,皆因人不再信守盟辞;而人不信守盟辞,是因为不再相信鬼神的约束力,盟礼的社会心理机制崩塌了。 隐公三年君子曰针对盟礼“人神之信”的缺失,重申盟礼之“信”,而欲以“信”取代“质”。君子曰:“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
2.2 君臣“交质”破坏了君王的神权
“周郑交质”的核心事件是“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子狐、公子忽的身份不可忽视。 两人分别是周王和郑庄公的嫡子,在众多子嗣中,身份最为尊贵。 将嫡子送往对方的国都,以致造成“交互”“互通”的双边关系,若有战争或纠纷,都将对双方极为不利。 “周郑交质”使周郑两国在盟礼的鬼神约束之外形成新的互为约束的关系,而破坏了盟礼本有的人与神之间的“信”。
《说文解字》:“质,以物相赘。”“赘,以物质钱。”[31]段玉裁注:“质、赘双声,以物相赘,如春秋交质子是也。”[32]质的本义为以物作抵押,以换取钱,而以人为质,则为换取二国之间暂时的安宁。 周郑交质,《荀子》《穀梁传》等文献称之为“交质子”,即互相抵押嫡子。 《左传》宋尧叟注:“交质子以为信。”[33]清代学者讥周天子“以质为信,不亦懦乎?”[34]“周郑交质”指明这样的事实:周天子藉盟礼约束自己未将权力转移,以示好郑庄公,仍嫌不够,还要将王子狐作抵押,换取与郑国的相安无事,后来二国之间的安宁终究被葛之战撕得粉碎,最终以周天子身中一箭收场。 周天子曾经集神权、王权于一身,至春秋初年不仅丧失了神权,亦丧失了王权,甚至到了要用嫡子作抵押以换取郑国的信任的地步。
与“周郑交质”相似的事件是昭公二十年宋元公与华亥交质:
宋元公无信多私,而恶华、向。 华定、华亥与向宁谋曰:“亡愈于死,先诸?”华亥伪有疾,以诱群公子。 公子问之,则执之。 夏,六月丙申,杀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孙援、公孙丁,拘向胜、向行于其廪。 公如华氏请焉,弗许,遂劫之。 癸卯,取大子栾与母弟辰、公子地以为质。 公亦取华亥之子无慼、向宁之子罗、华定之子启,与华氏盟,以为质。[35]
宋卿华亥因害怕华氏被宋元公排挤、诛杀,先发制人,诱杀宋公子六人之后,劫持宋元公,与宋元公盟,并交质子。 宋元公、华亥交质与周郑交质的相似之处在于:第一,盟礼在君臣之间进行。 第二,盟礼与交质先后举行。 第三,双方抵押的是身份最为尊贵的子辈,包括“嫡子”,且抵押的人数一致。 华亥与宋元公交质,因为华亥一方有三个主谋,故质子三人;相应的,宋元公亦质子三人,包括太子及其母弟。 第四,盟礼顺应臣的利益,而限制君的权力。 以臣抗君,臣胜,君败。 君臣博弈之后,君臣关系导向盟礼并交质子,这是臣子的胜利。
君臣盟礼意味着君权的失落。 君臣原本尊卑不对等,盟礼降低君的地位与臣实行“亢礼”“敌礼”,这与西周王室设立的盟礼并不合拍。 汉代古文经学家认为周礼本有盟礼的设置。 许慎《五经异义》:“古《春秋左氏》云:‘《周礼》有司盟之官,杀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国有疑,盟诅其不信者',是知于礼得盟。 许君谨案:‘从《左氏》说,以太平之时有盟诅之礼。'”[36]孙诒让认为:“郑氏不驳,从许慎义也。”[37]许慎、郑玄等人支持《左传》古义,认为“太平之时即有盟礼”,大抵指西周君臣秩序井然之时,“凡国有疑”则盟。 《玉篇·子部》:“疑,嫌也。”[38]《一切经音义》:“疑,贰也。”[39]盟礼藉助神权,解决周王室与诸侯之间的“猜疑”“嫌隙”。 彼时,周天子具有宗族、宗教等意义上的绝对威权,周天子的世俗王权能亦能确保盟辞的应验,盟礼能使君臣回归原有秩序。 汉代今文经学认为上古无盟礼而春秋有盟礼,霸主在则无交质子,亦指出交质子伴随权力衰微而出现。 《春秋公羊传》:“古者不盟,结言而退。”[40]《春秋穀梁传》隐公八年:“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41]“五帝”“三王”指传说中的上古时期,人言为信,不行盟礼;“二伯”指齐桓、晋文所处的春秋时期,人们行诰誓、盟诅,藉鬼神巩固人言之信;天下无霸,则至于交质子。 王充《论衡·自然》征引今文经说:“要盟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德弥薄者,信弥衰。”改《穀梁传》“二伯”为“五伯”,其意仍是拥有霸权的诸侯。 孙盛注:“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质任之作,起于周微。”[42]也认为君王无强权,亦无强权(霸主)替代的时候,就会出现盟礼交质子的现象。
君臣交质亦意味着君王神权的失落。 春秋伊始,周天子用盟礼加质子的方式向郑国表明自己没有没有贰心;宋元公在被劫持的状况下,与华氏盟,故君臣盟礼,人君或多或少有被胁迫的意思,即所谓“要盟”。 臣子强迫君盟,却不大相信鬼神,因为臣本身并不具备神权,所以就不依赖神权,转而要求“交质”,以人为抵押,所谓“质之为言信也。 要盟无信,于是以人为质。”[43]盟礼而交质,君王依赖鬼神对人实施的约束减弱了,君王的神权也就被打破了。
春秋时期,交质不尽是交换嫡子。 文公十七年晋郑交质,晋国一方,赵穿、晋侯女婿公婿池为质,郑国则太子夷、大夫石楚为质。 与郑太子夷对等的是晋卿赵穿。 大国质卿而小国质太子,交质子变而为一方质卿大夫,体现出权力的不对等,亦是盟礼交质扩大化的表征。 而盟礼单方面出质,往往系卑弱者所为,也是权力不对等的反映。
侯外庐认为:“春秋霸主的盟约还有其相对的神圣性,而战国诸侯的‘人质'便成了危机的标帜了。”[44]春秋时期的盟礼有鬼神参与,固然有其神圣性,但春秋时期盟礼之外已交质,信用危机即已开启。 《左传》君子曰推崇并维护盟礼中的神权,要求重建人神之信与人言之信,重回盟礼的本真。 君子曰强调盟礼之“信”,是在信用危机的时代里,重建“信”的信仰。
3 君子曰引《诗》重“信”之义
隐公三年君子曰引诗之义,历来富有争议。清代左传学评点著作,如金圣叹《左传释》、冯李骅《左绣》,都发现了隐公三年《左传》君子曰引诗的怪异,其结构与全书体例颇为不合。 冯李骅《左绣》:“《左氏》引诗,大都先点而后注,此独先注而后点;又直写本文居多,此独撮举大意,盖点化之妙,此为第一矣。”[45]通观《左传》全篇,君子曰的格式大多先点明主题,再引《诗》来论证,此即“先点后注”;而此处的君子曰却是先引《诗》,而后点明主旨,此即“先注后点”。 加之《左传》引《诗》一般直接称引诗句,而此处却概括大义。这是此篇君子曰引诗的特异之处。 遗憾的是,冯李骅没有继续探究君子曰“撮举之义”来自何处,故不能由《诗》入手,分析君子曰的主题,不了解“忠信”的涵义。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谓《左传》引《诗》“不必尽依本旨”,[46]也是说引《诗》之旨与“忠信”无关。 引《诗》而无关主旨,那又为何引《诗》? 这种观点必然存在认识上的歧误。 本文认为,《左传》隐公三年君子曰标举《诗经》四篇篇目,诗义统摄在“忠信”二字之内。君子曰用《诗》之义,与《毛诗》之义相通。
君子曰征引的《采蘩》《采蘋》《行苇》《泂酌》四诗,都与“忠信”相关。 此“忠信”之义,与《毛传》、《诗》小序之义相通,取自春秋时期的共同知识库。 《采蘩》毛传:“神飨德与信,不求备焉,沼沚溪涧之草,犹可以荐。”意谓祭祀之人有“信”之德,故祭祀以薄物而神飨之。 君子曰以“薄物”为纽带,将《采蘩》《采蘋》的“沼沚溪涧之草”和《泂酌》中的“横汙行潦之水”引申至“信”之义,而与《毛传》相通。 君子曰又从《行苇》文本出发,由宴乐兄弟,得“忠”之义,与《诗》小序相通:“《行苇》,忠厚也。”简言之,君子曰征引《采蘩》《采蘋》《泂酌》等三首诗,用其“信”之义;征引《行苇》,用其“忠”之义。 对此,笔者有专门论述,[47]在此不再赘述。
君子曰征引的四首诗皆关乎祭祀。 盟礼与祭祀有相似之处,二者皆为人与鬼神的对话,对话的实质就是人和神之间的礼物交换。 祭祀物品越丰富,鬼神的回赠愈丰厚,物品与回赠是正比的关系。 只不过祭祀希冀鬼神的回赠,盟礼借重鬼神的惩罚。 回赠和惩罚,均为鬼神之职责。君子曰征引四诗,皆与祭祀鬼神相关,引诗人相信,即便提供的祭祀饮食微薄,鬼神亦能慷慨馈赠。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祭祀提供了与鬼神“慷慨馈赠”相对等的“信”。 同理,希望鬼神施加惩罚,也要送上礼物;如果人内心有人神之“信”,则无需贵重的礼物,鬼神也能助人得偿得愿。 祈求鬼神施罚,与祈求鬼神回赠一样,提供的祭祀饮食可以微薄,只不过特别需要以“信”作为祭品。盟礼交质,却反其道而行之。 当事人缺少人神之“信”,却以“人”为质,当作祭祀鬼神的附带条件,加重祭祀鬼神的筹码。 君子曰借祭祀以论盟礼,因为盟礼和祭祀一样,都讲求人神之“信”。
如前所说,君子曰欲发明之义为“信”,此“信”字在开篇第一字上,而在君子曰的末尾,却变成了“忠信”,似乎有跑题之嫌。 其实未必。“忠信”不是一个词语,而是“忠”和“信”的组合,“忠”特意针对周郑交质的“质”。 “忠”之义来自《行苇》之诗,为春秋乱世提供了兄弟燕饮、比射的欢乐场景,这算是从正面阐述了兄弟之间的正确相处之道:以燕礼宴乐之,而非“交质”以换取安乐。 可以说,二国之间有“忠”,便不会有“交质”的事情发生。 与现实中盟礼“交质”不一样的是,君子曰提出盟礼加“忠”的模式。 二国之间用人神之信约束,又用宴乐交好,可以确保两国关系不脱离正轨。
隐公三年君子曰终篇论述的“信”,否定、压制了“质”;而结句言“忠信”,则用燕礼代替了“质”,在二国盟礼之外,拓展出兄弟交接的燕礼来。 君子曰由周郑交质事件引申出来的,便是重建盟礼,辅以燕礼,这也就是君子曰所发明之义。二国交接,除了盟礼的人神之“信”之外,还当有兄弟交接之“忠”。 周、郑两国是兄弟之国,既有盟礼,也当有燕礼,方为全面。 “忠”是“信”的拓展,而非“信”的反面。
周郑交质这一事件表明,周天子的神权、王权尽失,受制于诸侯。 周郑交质未能阻止周郑交恶,盟礼交质不能挽救“信”的危机。 《左传》隐公三年君子曰认为唯有回归人神之信,方能有人言之信;唯有重建盟礼中的鬼神信仰,方能挽救“信”的危机。 《左传》君子曰的嘉言懿语,将道义礼信置于富强攻取之上,其风流文雅,为后世所向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