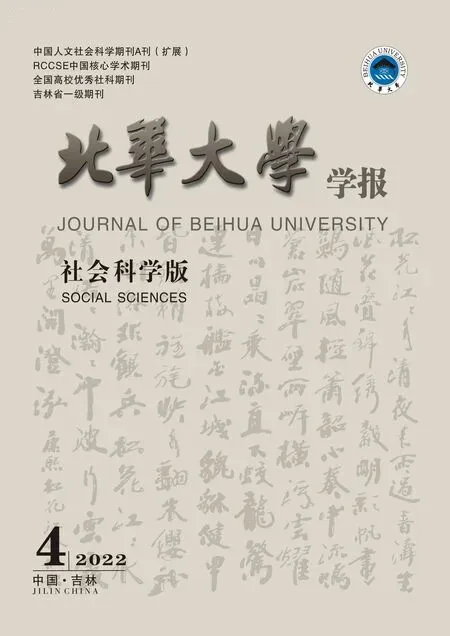从17、18世纪莎评看古典主义诗学在英国的瓦解
2022-04-16辛雅敏
辛雅敏
17、18世纪,来自法国的古典主义诗学盛行于整个西欧,但欧洲各国对其反思与批判也从未停止。在这一过程中,处处不遵守古典主义规则的莎士比亚无疑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思想武器。因此,这一时期的莎评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段反抗古典主义戏剧规则、解放戏剧创作束缚的历史。
一、早期莎评对三一律的挑战
1660年,查理二世从法国回国,成功复辟了斯图亚特王朝。以三一律为主要特征,来自法国的古典主义诗学开始在英国戏剧界广为流行。古典主义诗学在复辟时代虽然流行,但是英国剧作家和批评家们对待三一律等规则的态度其实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尊重三一律,认为这是戏剧艺术的金科玉律,因为古典主义者们认为这是古代戏剧艺术留下的瑰宝,而且他们认为时间、地点、情节的整一律确实能够让戏剧显得更真实,因此也更接近自然;但另一方面,由于有伊丽莎白时期戏剧的优良传统,在实际创作中英国的剧作家们又往往口是心非,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些规则,而这种矛盾也造成了一种现象,那就是英国人在理论上突破三一律的限制要比在实践上困难许多。
在德莱顿所生活的复辟时代,只有极个别的英国批评家敢于明确反对三一律。德莱顿的妻弟罗伯特·霍华德爵士(Sir Robert Howard)便是最早一批公开质疑三一律的批评家之一。早在1668年,在自己的剧作《勒玛公爵》(The Duke of Lerma)的《序言》中,霍华德在列举了三一律的规则之后说道:
为了说明这些规则如何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来影响戏剧诗,我将试图证明根本没有这回事。因为严格来说,如果在一个舞台上展现两个国家是不可能的,那么展现两座房子或两间屋子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同理,如果一千个小时或数年时间被压缩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那么五个小时或二十四个小时被压缩成两个半小时的戏剧时间也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都是一样的,没有程度的区别。[1]97
到了1702年,一位名叫乔治·法夸尔(George Farquhar,1678—1707)的喜剧作家和诗人也曾令人信服地反驳过古典主义诗学规则。法夸尔认为不应该迷信古代权威,因为当今的时代一点也不比古代逊色,那么凭什么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规则能成为不可改变的权威?况且,英国的戏剧是演给当下的英国观众看的,不是法国西班牙,也不是古希腊罗马,而英国的观众“不仅在地理上与其他地方隔绝,而且在身体的容貌和脾气上也与其他民族不同,甚至在政治体制上也异于他邦。”[2]因此,不同的戏剧目的带来了不同的戏剧手段。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与霍华德强调从想象的角度反对三一律不同,法夸尔无疑在戏剧批评领域预示了一种超越古典主义普遍人性论的历史主义思想。
虽然霍华德和法夸尔对古典主义诗学进行了大胆的批评,但一直到18世纪初,他们的观点应者寥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的英国就形成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无论改编与否,莎士比亚在剧场中依然被观众所喜爱;而另一方面,深受古典主义规则影响的批评家和剧作家们虽然也喜爱莎士比亚,也在莎士比亚身上看到了“自然”这样的优点(1)“自然”一词是17、18世纪的审美关键词,其内涵极为复杂。古典主义者强调摹仿“自然”,但这个“自然”主要指的是普遍人性和人类经验中的因果关系。17世纪早期,英国批评家已开始以“自然”标榜莎士比亚,但其口中莎翁的“自然”风格多有“浑然天成”的含义,具体所指比较模糊,到18世纪才逐渐有了对人性的忠实和对人物性格栩栩如生的刻画等内涵。关于“自然”一词在17、18世纪的具体含义,可参见阿瑟·洛夫乔伊的《作为审美规范的“自然”》(载阿瑟·洛夫乔伊《观念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但更多人则是看到莎士比亚身上各种各样令人难以忍受的缺点,而且这些缺点不断被人提及,反映了英国批评家们对待莎士比亚的矛盾态度。在古典主义诗学原则的影响下,当时的批评家们对莎士比亚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莎剧对古典主义三一律的无视,这反映了莎士比亚对戏剧艺术规则的无知;第二是莎剧的人物塑造不符合古典主义的“得体”原则;第三是莎士比亚对古典文学的无知(与第一点相关);第四是莎剧中的悲喜剧混合不符合古典主义的文体原则;第五是莎剧中各种超自然角色的出现和血腥暴力场面不适宜舞台演出;第六是莎剧语言上多用隐喻和双关语,含义模糊,不符合古典主义对语言明晰的要求,而且无韵诗并不是古典主义戏剧所提倡的诗体,等等。这其中尤其以前两个问题所引起的批评较多。
在如此众多的缺点被不断提及的情况下,纵使有个别批评家明确地将莎士比亚的“自然”和“不学”视为其优点,但仍然难以改变17世纪的英国批评界在整体上将莎士比亚视为一个文学品味低下的野蛮时代所留下的文化遗产的事实。此时的莎士比亚亟需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坛领袖来拯救其在古典主义思潮下岌岌可危的声望,而当时最重要的剧作家和批评家德莱顿恰恰就是在这时登上了莎评史的舞台。
二、德莱顿论莎士比亚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德莱顿显然在莎士比亚经典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1667年,德莱顿就与人合作改编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在这部改编剧的《序诗》中,德莱顿热情洋溢地赞美了莎士比亚,并明确将这位诗人的地位置于同时代的弗莱彻和琼生之上:
无师自通的莎士比亚第一次
将智慧传授给弗莱彻,将技艺传授给勤奋的琼生。
他像是一位君主,将法律授予臣民。[3]
结合德莱顿后来对莎士比亚的评价来看,这应该是他对莎士比亚最高的赞美。1668年,德莱顿出版了以对话体形式写成的评论著作《论戏剧诗》,这是17世纪的一篇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献,德莱顿在其中同样给予莎士比亚相当高的评价,其观点基本上为复辟时代乃至后来的18世纪莎评定下了基调:
在所有古今诗人中,他(莎士比亚)具有最广阔、最包容万物的灵魂。自然的所有意象总是在他面前展现,供他毫不费力地随意选取。当他描绘任何事物时,你不仅能看到它,而且能感觉到它。那些指责他缺乏学识的人实际上是给了他更大的赞美:他的学识浑然天成,他不需要通过书本去了解自然;他反观自己的内心,在那里发现自然。……他有时也是平淡无味的,他的滑稽机智流于俏皮,他的严肃变为浮夸。但是一旦涉及重要的场景,他总是伟大的;所有人都承认,一旦他有了一个合适的题材,他会超越其他所有诗人。[1]66-67
德莱顿在这里就明确地将莎士比亚的“不学”解释为他的“自然”,而且认为这是莎士比亚浑然天成的、不需要从书本得来的学识。在评论了莎士比亚之后,德莱顿又通过虚构人物尼安德之口,对鲍芒与弗莱彻以及本·琼生这几位英国本土剧作家也多有褒奖,但在将琼生和莎士比亚作对比时,尼安德提到:“我必须承认他(琼生)是更正确的诗人,但莎士比亚却有更伟大的智慧。”[1]69把莎士比亚与智慧(wit)联系在一起来区别于琼生的古典主义,进而为莎士比亚辩护,这也是当时批评家们的常见策略之一。
即便如此,德莱顿也远远没有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在德莱顿看来,莎士比亚仍然是一个野蛮时代的诗人,既有优点,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德莱顿对莎士比亚更细致全面的评论出现在1679年出版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序言》中,也就是《悲剧批评的基础》一文(2)《悲剧批评的基础》(The Grounds of Criticism in Tragedy)是这篇《序言》的一部分,是德莱顿自己提到的一个标题,占绝大部分篇幅。,而在这篇文章中,德莱顿的观点更倾向于保守。德莱顿在此文中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出发讨论了悲剧的情节和人物性格等问题,同时大量引述法国古典主义者拉宾和拉博苏等人的观点,并以这些观点来衡量莎士比亚和弗莱彻等伊丽莎白时代剧作家的作品,阐述其各自价值,并将两者进行了比较。
在谈到人物的情欲(passion)问题时,德莱顿这样批评了莎士比亚的语言:
他常常以辞害意,有时使得意思不可理解。我不愿说这样伟大的诗人分不清什么是膨胀臃肿的风格,什么是真正的雄伟;但我可以冒昧地说他那狂热的幻想常常使他超出理智的界限,或是铸造新字异句,或是硬把日常使用的字句粗暴地误用。[4]30
“以辞害意”(obscures his meaning by his words)是德莱顿对莎士比亚的一个著名指责,鲜明地反映了他追求语言明晰的古典主义立场。在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之后,德莱顿总结道:
如果把莎士比亚描写激情的夸张之词全部删去,而用最庸俗的字句来表现它,我们仍旧能够发现留下来的美丽的思想;如果把他的虚文都烧尽了,熔炉的底子里仍旧有着银子。……我们在一个更为文雅的时代继承了他(莎士比亚),如果我们模仿他的工作做得太坏,以致我们只摹仿他的缺点,而且把他的著作中不完美的东西变成我们作品中的优点,那是我们的过错。[4]32-33
直到全文的最后,德莱顿还在引用法国古典主义学者拉宾的观点来强调规则的重要性和幻想的破坏性:“只有依赖法则,虚构中的可能性才能保住,那是诗歌的灵魂。……但只以自己的幻想作为引导的那些诗人,他们犯过的种种可笑的错误和荒谬绝伦的事情证明:如果幻想不受节制,那么它仅仅是乖僻之物,完全不能创造合理而明智的诗篇。”[4]34强调规则而否定想象,强调通过符合理性的或然律原则来摹仿自然,强调语言的明晰而否定隐喻和多义,这是典型的古典主义诗学观点。17世纪的古典主义者们所欣赏的既不是莎士比亚的语言,也不是其想象力,而是其符合理性的摹仿能力和崇高的思想。不过,莎士比亚在其他许多方面显然并没有遵守古典主义规则。因此,古典主义者对莎士比亚的欣赏往往伴随着遗憾和惋惜,语言的多义和想象力的泛滥在德莱顿这里正是莎士比亚令人遗憾的缺点。
总的来说,年轻时的德莱顿对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更有热情,晚年的德莱顿更倾向于理智,也更倾向于古典主义。不过处在外来的古典主义原则与本土戏剧的民族情感之间的德莱顿始终是矛盾的。正如一位学者所描述的:“在这一页他好像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在一个层次,另一页他就陷入了冷冰冰的、讲究逻辑的古典主义。有时他为英雄剧辩护,有时他又用最刻薄的咒骂攻击它。他时常雄辩地表达对莎士比亚的热爱,但又多次对这位伟大的前辈抱怨个不停。”[5]德莱顿作为17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他对莎士比亚的矛盾态度也是那个时代的矛盾。但无论如何,德莱顿的那些热情洋溢的赞美还是为莎士比亚的名望带来了极大的提升,为日后莎士比亚代表英国文学对抗法国古典主义埋下了伏笔。
三、对三一律的进一步攻击
进入18世纪,与法国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对立以及伏尔泰对英国戏剧的评论所激起的民族情绪,让英国批评家们在18世纪中叶便开始有意识地与来自法国的古典主义诗学原则划清界限。1730年之后,古典主义诗学开始在英国不断走向瓦解。1736年,一位叫做乔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es)的牧师便认识到法国古典主义是一种束缚:
法国人(正如我们常看到的)用他们的批评原则平白给自己强加了一种奴役;当他们中稍有天赋的人带着这些枷锁写了一些悲剧时,只能勉为其难,弄出一些完全没有精神的作品。[6]68
不过斯塔布斯的批评还算温和,因为他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便在于,法国人有一种“关于合乎礼仪的错误思想和一种文雅的品味”[6]68。
1747年,演员和剧作家塞缪尔·福特(Samuel Foote)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总的来说,这些束缚(三一律)并没有影响这个岛上那些自由、富饶的居民的品味与天赋,他们不会在诗歌上再戴上枷锁,正如在宗教上一样。没有哪种政治的或文学批评的君主能再为他们立法。他们确实已经证明并不会由于能力不足而蔑视那些亚里士多德的规则(3)这里指的可能是琼生的大部分剧作和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们》《暴风雨》等剧,因为这些作品并不违反三一律。,而是因为他们在不借助其他国家帮助的情况下,便能够做到现有的成就。[6]222
福特在这里将英国批评家摆脱古典主义三一律的束缚与英国在宗教上的独立相提并论,其背后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政治指涉不言而喻。
1748年,学者和批评家约翰·厄普顿(John Upton)在《论莎士比亚》(Critical Observations on Shakespeare)中已经提到:“戏剧诗是一种欺骗的艺术,最优秀的诗人是那些最会欺骗观众的诗人,而最易受骗的人也是最明智的。”[6]296因此厄普顿认为,为了达到最好的欺骗效果,故事情节便是最重要的,因此,情节整一律是有道理的,但时间和地点的整一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为了讲好一个完整的故事,时间和地点一定会随之改变。厄普顿的这一观点显然与后来卡姆斯勋爵和约翰逊博士所表达的对三一律的看法基本一致。
到了1762年,作家和美学家丹尼尔·韦伯(Daniel Webb,1719—1798)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我们很容易发现,那些热衷于谴责莎士比亚忽视三一律的批评家们与承认他在情感表达方面的非凡能力与魅力的批评家们恰恰是同一批人。但我认为莎士比亚对三一律的忽视正是他的情感表达有魅力的原因。因为诗人如果没有被三一律所束缚,他就能创作出与他天才的活力相符的事件。因此,他的情感源于那些适合产生它们的动机:它们原初的精神恰恰源于此,正是这种精神克服了场景的不可能性,并在超越了理智的情况下传递给心灵。[7]519
同样在1762年,卡姆斯勋爵(Lord Kames)在《批评的要素》(Elements of Criticism)一书中从戏剧实践的角度反驳了时间和地点整一律,他认为希腊戏剧由于运用歌队,难以进行场景转换,因此不得不选择时间和地点整一律,而英国戏剧没有歌队,每一个场景的转换都可以有一定时间间隔,这就完全有可能让剧内的时间和空间比希腊戏剧更广阔,因为换景间隔的时间不需要等同于剧内时间。“这就意味着许多古希腊戏剧中不能处理的题材在我们的戏剧中都可以得以展现。”[7]496与此同时,因为有了换景间隔,观众也完全能够清楚地意识到真实的时间和地点与剧内的时间和地点是两码事,正如他们清楚地知道加里克并不是李尔王,舞台也不是多佛海滩一样。因此,所谓时间和地点整一律,完全是现代批评家对古代戏剧愚蠢误解的产物。
四、约翰逊博士的辩护
此后不久,著名的约翰逊博士在1765年版的《莎士比亚作品集》的《序言》中系统地反驳了三一律的不合理。约翰逊的观点本质上与卡姆斯以及这一时期的许多英国批评家类似,那就是反对时间和地点整一律,不反对情节整一律。但其实早在1751年,约翰逊博士便在另一篇文章中反驳了三一律:
批评家将戏剧的故事限定在数小时内,遵守这一规则似乎天经地义,其实毫无道理。……既然事实是戏剧必须要有引人遐想的余地,笔者就不知道想象的边界应该定在何处。假如一个人的思想不受机械批评观的左右,他很少会因为两幕间的时间跨度被延长而感到不悦;一个人假若能把舞台上的三个时辰想象为现实中的十二个时辰,二十四个时辰,他在想象比这个更大的数字时大概也会同样得心应手,这在笔者看来毫无荒诞或牵强之处。[8]122
这与他在《序言》中的反对时间和地点整一律的观点基本一致。不仅如此,约翰逊还鼓励作家要勇敢对抗权威和规则:
一位作家首要的任务是应当把自然与习俗分开来,将因为正确才被公认的东西与仅因为被公认才算正确的东西区别开来;一位作家不能因为想要标新立异而违背最本质的原则,同时也要知道有些规则是任何独揽文坛的泰斗都无权制定的,所以无需害怕自己会破坏这些规则,从而无法领略近在眼前的各种美好。[8]123-124
约翰逊在《序言》中花了大量篇幅对莎剧违反三一律的问题进行了辩护。他先是解释了古典主义者为何会制定这样的规则,因为地点和时间的一致性能够让观众产生错觉,从而觉得舞台上的表演可信,但他继而指出这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观众并没有任何错觉,他们从头到尾知道舞台不过是舞台,而演员不过是演员罢了。”[4]53如果观众能够想象构成情节的行动发生在不同的地方,“那么通过想象,时间也就可以加以延伸了。”[4]54因此,观众完全可以通过想象转换时间和地点,尤其在各幕之间的空隙更是如此。而戏剧之所以动人,是因为观众在情感上的共鸣,而不是因为绝对的逼真。从这种认识出发,约翰逊博士一再强调,三一律中只有情节整一律是重要的,时间和地点的整一律并无道理可言。应该说,约翰逊博士对古典主义诗学一致性原则的这种摈弃,正是他为莎士比亚辩护时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在为莎士比亚辩护之后,约翰逊也讨论了莎士比亚的缺点,不过由于他的辩护非常精彩,这些缺点便显得没那么重要了。总的来说,由于没有完全超越古典主义诗学原则,约翰逊对待莎士比亚的态度还是矛盾的,《序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约翰逊评论莎士比亚的名言,同时也最能代表他的矛盾立场:
一个准确和遵守法则的作家像这样一座花园,它的设计很精确,在那里面人们细心栽培了许多花木,它既有树荫,又有花香;莎士比亚的创作像一片森林,在那里橡树伸张着它们的枝干,松树耸立在云端,这些大树有时间杂着野草和荆棘,也有时给桃金娘和玫瑰花遮阳挡风;它们用壮观华丽的景象来饱人眼福,以无穷的变化来娱乐人的心灵。其他的诗人陈列出一橱又一橱的贵重珍品,这些东西制作得十分精细,打成各种样式,而且擦得发亮。莎士比亚打开了一座矿藏,它含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黄金和钻石,但它的外壳却使它黯淡无光,它所含的杂质却使它贬值,同时大量的普通矿物和它混合在一起。[4]61-62
“准确和遵守法则的作家”指的无疑是古典主义者,约翰逊在这里其实已经将莎士比亚和古典主义者放在了对立面,而且作了两个非常恰当的比喻,一个是花园与森林的比喻,另一个是橱窗与矿藏的比喻。如果我们看一看雨果在《〈短曲与民谣集〉序》中类似的说法就会发现(4)比较雨果同样的比喻:“请你以凡尔赛王家花园来作一个比较,花园里修饰得整整齐齐,打扫得干干净净,杂草都被刈除了……。请你把这个被人高度赞扬的花园和新大陆的原始森林作个比较吧!那里有高大的树木、浓密的野草、深藏的植物、各种颜色的禽鸟、阴影与光明交相辉映的宽广的通道……。在花园里,流水受制于人、违反原来的流向,神像也都显得呆滞……。天然的秩序都被破坏、颠倒、打乱、消灭了。在大森林中则相反,一切服从于一个不可更改的法则;似乎有一个上帝主宰着一切。……在那里,甚至荆棘也很美丽。”参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122页)。,约翰逊博士的这两个比喻离浪漫主义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在这两个比喻中,约翰逊认为莎士比亚是树林和矿藏,莎士比亚的美正如树林的“壮观华丽的景观”和矿藏中的“黄金和钻石”,但同时他又承认,树林中也有野草和荆棘,矿藏中也有杂质。而约翰逊找到的这些野草、荆棘和杂质还是揭示了他的古典主义立场,也是他与后来的浪漫主义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因为在浪漫主义者眼中,野草、荆棘乃至杂质本身就是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同样是美的。正如雨果所言:“不要把秩序和匀称混淆了。匀称仅与外表有关,秩序则产生自事物的内部,产生自一个主题的内部因素之合理安排。匀称是纯粹人为的形体的组合;而秩序则是神意。……匀称是平庸者的趣味,秩序是天才的趣味。”[9]不过应该承认,在古典主义诗学流行的年代,约翰逊博士能有这样的认识,已经难能可贵。
五、古典主义诗学的瓦解
在约翰逊博士反驳了三一律之后,越来越多的英国批评家站出来明确反对这种古典主义规则。这些新的反驳逐渐触及了古典主义诗学的要害,即普遍人性论和古典主义的自然观。1777年,英国博物学家、医生和批评家约翰·伯克恩霍特(John Berkenhout)在反驳伏尔泰对莎士比亚的指责时提到:
我读过的所有被这些三一律所束缚的悲剧或喜剧,没有任何一部不是做作、不可信和乏味的。……我越是思考这些希腊的三一律规则,就越是发现它们的荒谬。如果这荒唐的东西从未存在过,那么对英国戏剧来说真是极好的事。……如果自然中存在这样的三一律,那么莎士比亚这样如此熟悉自然的人早就应该发现它们。但如果一位剧作家想要完成戏剧创作的目的,自然根本不会给他规定这样的三一律规则。这些规则是无聊的发明,是可怜的蹩脚诗人的束缚。[10]158-159
1783年,苏格兰诗人和散文作家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在《道德与批评论文集》(Dissertations Moral and Critical)中认为:
遵守三一律在某些情况下无疑会让戏剧行动变得更可信:但它们对作家的天赋是一种巨大的束缚;遵守它们有时甚至比忽视它们还要显得荒唐。比如,如果某个戏剧描绘了一场阴谋,故事发生的场景是街道,那么如果遵守地点整一律,阴谋就变成阳谋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如果这时把场景换到私密空间里,显然就合理了许多。[11]226-227
紧接着比蒂几乎是完全复述了约翰逊博士关于观众的舞台想象力的观点:
但实际上,在戏剧中根本就没有批评家们所说的那种严格的或然性。我们从不会把演员真的当作他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也从不会想象自己置身于异国他乡,或者回到了古代:我们观剧的快乐来自其他方面,我们从这里知道,整个剧都是虚构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让诗人去严格遵守时间和地点整一律并不是创作的必要条件,而是一种机械的创作规则。[11]227-228
1789年和1799年,英国作家和历史学家威廉·贝尔舍姆(William Belsham,1752—1827)分别出版了《哲学、历史与文学论文集》(Essays,Philosophical,Historical,and Literary)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在此书第二卷中,贝尔舍姆同样认为三一律中只有情节整一律是有道理的,而且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时间与地点整一律的错误本就出自亚里士多德:
情节的整一或完美联系确实是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的,亚里士多德也常常提到其重要地位,但他没有意识到,时间和地点的整一律是来自希腊戏剧创作的特殊形式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这一点,即亚里士多德是否有不容置疑的资格来决定戏剧只能有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中只有情节的整一律是应该遵守的,如果诉诸理性而非权威的话,时间和地点的整一律有时可以被抛弃。[12]551
贝尔舍姆继而说道:“很明显,如果严格遵守这些规则,诗人的天赋便会受到束缚,变得捉襟见肘,情节的组织也会受到伤害。”[12]552可见,由于约翰逊博士在文坛的巨大影响力,18世纪60年代之后约翰逊博士关于三一律的见解已经成为英国批评家们的共识。此后,英国批评家们也越来越大胆,最后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三一律的源头亚里士多德,可以说完全与古代传统决裂。虽然个别古典主义诗学原则还被认为有必要遵循,但以三一律为代表的大部分古典主义原则在英国几乎已无立足之地,三一律也已被视为文学创作的束缚和人为设计的枷锁。
而早在1777年,浪漫主义莎评的重要先驱莫里斯·莫尔根(Maurice Morgann)便发表了著名的《论约翰·福斯塔夫爵士的戏剧性格》(An Essay on the Dramatic Character of Sir John Falstaff)一文。莫尔根在此文中认为,莎士比亚这位英国大诗人不仅已经超越了荷马,也超越了诗歌的立法者亚里士多德,甚至连亚里士多德也要在莎士比亚面前俯首称臣:
连他(亚里士多德)自己都会拜倒在他(莎士比亚)的脚下,承认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啊,戏剧的卓越权威!”他也许会说,“别把那些蠢人的无礼归罪于我。希腊的戏剧诗人被歌队的合唱所束缚,因此他们会发现自己无法做到对自然细致的描绘。我只看到这些剧作家的作品,不知道还有更广阔的视野,也不知道戏剧还可以将人类的天赋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相信了这些,我就知道一个更广阔的自然是可以达到的,这是一种效果上的自然,对它来说地点的整一和时间的连贯都无足轻重。自然屈从于人的能力与理解,在人的生活中勾勒出一系列的简单因果关系;但诗以惊喜为乐,隐藏她的脚步打动人的心灵,在不背叛自己上升阶梯的情况下达到崇高。真正的诗歌是魔术,而非自然;它是由未知的或隐藏的原因所导致的结果。我不会给魔术师制定规则,他的规则与他的能力是一致的,他的能力就是他的规则。”[10]171
在这里,古典主义诗学原则已完全瓦解,亚里士多德不仅拜倒在莎士比亚脚下向其表达敬意,而且承认自己对自然的理解有误,甚至亲自为莎士比亚辩护。于是,一种对戏剧的全新认识开始出现,更广阔的、效果上的自然取代了建立在普遍人性论基础上的自然,戏剧评论中的浪漫主义呼之欲出,而莎士比亚距离浪漫主义者们为他树起的神坛也只有一步之遥。
总之,以三一律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诗学在英国的瓦解与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重新解读息息相关。在这些解读中,古典主义的“自然”观念被重新定义,自然不再具有普适性,而是意味着个体情感的真挚与浑然天成的天赋;希腊罗马经典也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典范,而是特定历史语境中产生的特殊作品。因此,古典主义所信奉的普遍人性论开始瓦解,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思想开始出现。英国批评家们不再相信来自古代的规则,而是开始强调英国人的特殊性,而正是这种对特殊性的强调最终走向了浪漫主义对个体情感与独创性的崇拜,走向了文学批评中的印象主义和历史主义。因此,在即将到来的浪漫主义思潮中,莎士比亚终于成为反抗古典主义的一面旗帜,被全欧洲的浪漫主义者们推上了神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