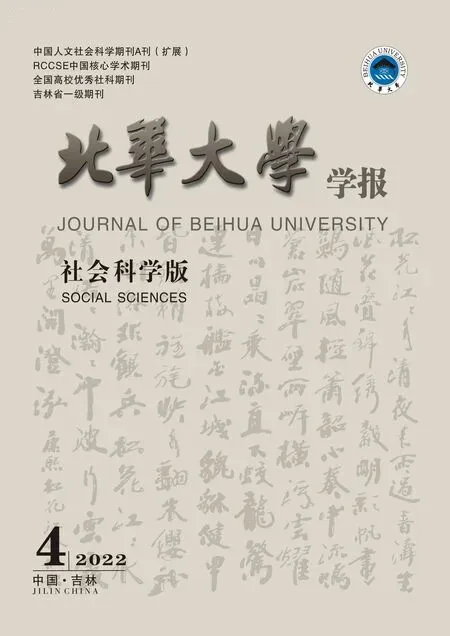阅读回甘
——黑塞书评中国古典小说
2022-04-16李昌珂
李昌珂 远 思
引 言
近当代德语文学中,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独步西东,是位中国元素在其作品中比比皆是、俯拾可见的“异质”作家。(1)黑塞对中国文学颇为热爱和了解,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如黑塞短篇小说《余国王》是《东周列国志》“幽王烽火戏诸侯”故事的一个翻版;黑塞童话《诗人》情节来自《列子·汤问篇》的“薛谭学讴”;黑塞赞美诗《献给女歌手婴宁》中有《聊斋志异》狐女婴宁显其芳踪;黑塞散文《克林索的夏天》多次吟咏李白的《对酒行》和《将进酒》诗句,还直取李白《月下独酌》的情景。参见陈壮鹰《赫尔曼·黑塞的中国情结》(《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2期)。幼时成长在多元文化的家庭环境里,这对黑塞后来与中国文化接触,并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深度了解具有重要影响。黑塞的父亲是出生在爱沙尼亚的俄籍德国人,母亲生于印度,外祖父长期在印度传教,外祖母也有外国血统。受这样的家庭环境熏染,黑塞从小就对外国文化持开放和接纳态度。他不仅受到欧洲文化的熏陶,也有东方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古老文化的影响,这对黑塞日后的文学创作、对“文化”的理解,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成年后,当面临危机和处于生活困境或是对喧嚣的时代予以拒斥时,(2)黑塞人生多舛,背负着很多危机,如因主张和平及遭遇婚姻危机等而承受很多压力,他前后接受过72次心理治疗。黑塞便想到借助东方文化逃离孤独与绝望。他先是对印度佛教“苦修”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又被中国文化深深吸引,甚至迷恋到不能自拔。1915年6月,在《新苏黎世报》上黑塞发表了《图书之年》一文,谈了他的藏书、读书情况,说他书房里有个角落专门置放东方书籍,先前放有中国的《诗经》《论语》《道德经》《南华真经》等,后来随着中国哲学、文学、民俗文化等方面书籍的不断增多,这个角落又延展出了一个“中国角”,那些中国书籍“让我思索和让我赏心悦目了难以计数的日子,近段时间里除了四卷本的歌德作品外,它们几乎就是我的每日读物”(3)本文对黑塞书评内容的引用,皆出自Hermann Hesse,Sämtliche Werke(汉译《黑塞全集》,Suhrkamp Verlag,2001—2007)这部《黑塞全集》尚无中文译本,所有引文皆由笔者译为中文。[1]461。
黑塞一生有六十余载在接触中国文化,首次与中国文化接触是在1907年。在这一年,他读了一部德译本中国诗集。读后惊奇慨叹不已,于是黑塞写了他第一篇感知和评价中国文学的文章。黑塞在文中感叹道:“读着这些优美的诗篇,我们仿佛徜徉在异域盛开的莲花丛中,感受到一种与古希腊、古罗马相媲美的古老文明的馨香。”[2]自那以后,黑塞不间断地与中国书籍进行对话,把很多时间用于阅读中国书籍、钻研中国文化上面。(4)据统计,黑塞阅读的中国书籍是同样也关注中国文化的托尔斯泰所阅读的四倍还多。参见詹春花《黑塞与东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页)。黑塞不仅通过读书为自己汲取思想资源和心灵慰藉(5)对此,黑塞曾自叙道:“我踱至书库的一角,这儿站立着许多中国人——一个雅致、宁静和愉快的角落。这些古老的书本里,写着那么多优秀又非常奇特地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在可怕的战争年代里,我曾多少次在这里寻得藉以自慰、使我振作的思想啊!”参见祝凤鸣《赫尔曼·黑塞的中国情结》(《中华读书报》2011年11月23日第18版)。,还写书评向社会读者分享心得(6)黑塞爱读爱写,一生写有书评三千多篇。各篇书评既是黑塞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个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推荐阅读。黑塞阅读了大量中国书籍,心中感想颇多,针对中国书籍的书评黑塞撰写了四十多篇。其中针对中国长篇小说的书评,有的写成专文,有的则是穿插在札记里的零散片段。这些书评,对德国乃至欧洲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了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黑塞的内心希冀:为欧洲人竖起一面文化的“镜子”,向欧洲人提供了解中国世俗风貌的文化视角,袒露中西文化交流的心迹,宣扬并期待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而斗争的“共同精神”。
一、为欧洲社会竖起一面“镜子”
那个时候,中国长篇小说的德语译介还比较罕见,在德国汉学家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翻译之前,德国人对中国长篇小说实际是知之甚少,除了《好逑传》 (1766),《玉娇梨》(1827),《花笺记》(1836),《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1843)及《平鬼传》(1923)等几部外,德国人对其他中国长篇小说作品基本是处于认知盲区。黑塞读到的德译本中国长篇几乎都是库恩翻译的(7)库恩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开始投入对中国长篇小说的翻译工作的,陆续译有十余部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在书市上曾掀起过一股不大不小的中国长篇热,库恩也因此一时声名鹤起。不过在翻译中,顾及到中西文化差异,库恩秉持一种以便于德语读者接受为出发点的“创造性叛逆”的基本态度,大量使用“归化”翻译方法,信马由缰,随心所欲,时刻对原文文本作删节、压缩或改写的处理,常常将原本中的话本套话统统删去,或是将情节里的应景诗词完全删除,总之不考虑严格遵循信译原则,更不追求呈现中国异质文化的审美魅力。凭借十分个性化的灵活译法,库恩译作在德语读者那里获得了较好的接受效果,所译中国小说最多的再版达二十多次,还被转译成了其他欧洲语言文本。。弗兰茨·库恩译的《好逑传》(Eisherz und Edeljaspis oder die Geschichte einer glücklichen Gattenwahl,18世纪有人翻译过)出版于1926年,是库恩翻译的第一部中国长篇小说。同年,黑塞读了这部译作,颇有感想,写下了书评:
……她(水冰心)的故事是一桩爱情故事,一桩在患难中互通情愫,又谨守礼教大防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保留了以理节情的社会崇尚,对我们这些生活在一个价值丧失、意义离析时代的人来说,没有比这种崇尚更显奇异,更值得让人思考的了。对西方读者来说,这部小说的重要读点不在于它的故事离奇和浪漫,而在于它传递的伦理道德,礼仪规矩,崇敬先祖和遵从权威的文化精神。这部表现家庭与爱情生活题材的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上也优雅洁净,清丽芊绵,讨人喜欢。[3]32
了解《好逑传》的中国读者知道,这部小说篇名取自《诗经》之《国风·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的“好逑”。全书标举儒家思想的“人伦不苟”题旨,讲述女主人公水冰心不顾闲言,暗地里接铁中玉来她家养病,二人产生情愫,相互倾心,又同处一屋“五夜无欺”,甚至明媒正娶后也“虚为合卺以守正”,最终御赐婚姻,终成“好逑”。从书评可以看出,《好逑传》给黑塞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并非因为它讲述的美好感人的爱情故事,而是它彰显出的风化教义让他心下一动。黑塞书评推崇这部小说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这部小说对所有欧洲人都有意义,他欲通过这部小说将西方的当前社会与中国的古代社会形成对照:竖起一面礼仪伦常的镜子,让西方人照照自己。
1935年,库恩译《好逑传》增加了数祯中国木刻插图后又一次修订出版。黑塞阅读了这个版本,并再次撰写书评言说见解。书评再次体现出黑塞对这部小说之于欧洲人意义的重视,依然有对照意识在场:
17世纪的这部小说,不知名的作者讲述了名教和心性、纲常和精神间的冲突。对故事里出现的一些大胆的努力和自主的作为,已经惯于无政府主义思维的我们觉得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出于礼仪和服从的举动而已。对我们而言,小说讲述的社会应当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理想状态的秩序。唯婚姻为人伦风化之首,当正始正终,决无用权之理,美丽又聪慧的冰心小姐如是说。[4]71
“冰心小姐如是说”,表明黑塞特别重视并再次通过书评向西方人推介西方人观察反省自己的中国文化视角。歌德也读过《好逑传》,认为这部作品表现出的中国人贞洁自持的伦理情操让人感慨万端,并与爱克曼如此谈论这部小说:
“特别是一部中国小说,我还在看,觉得它极为值得关注。……特别是写到一对情侣,虽交往已久,但洁身自好,即便是又一次不得已而在同一房间过夜,也仅有交谈而无身体的接触。书里有无数这样的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因为有各个方面的清规戒律,才使得中华帝国得以千年不衰,继续存在。”[5]
踵武其后,黑塞通过新书评再次强调《好逑传》塑造的中国人形象之于西方人的榜样价值和意义,与歌德所见略同。歌德和黑塞都在《好逑传》中品读出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都认为这是西方少见但又为西方所迫切需要的,这也正是这部中国通俗小说在西方流传两百多年的秘密所在。
二、为欧洲社会打开东方文化视角
1927年,库恩翻译出版了清初小说《二度梅全传》,不过库恩将书名改为《女子梅氏复仇记》(Die Rache des jungen Meh oder das Wunder der Zweiten-Pflaumenblüte),以期用吸睛的书名来吸引读者。这部小说讲述了梅、陈两家的悲欢离合,揭露了官场腐败和统治集团的内部争斗,情节曲折跌宕,是清代一部鲜见的将才子佳人的爱情婚恋与忠孝节义的正义事业结合起来的长篇小说。读了库恩译《女子梅氏复仇记》,黑塞撰写了书评:
这些天我一直在读两部外国作品,都写于以前的时代。……那部小说来自中国,名叫《女子梅氏复仇记》。它不属于世界文学名著之列,有些胡编乱造,不过可以把它当作是有关中国风俗、习惯、理想和思维方式的闲暇读物来读,因而令人喜欢。[6]63
黑塞所说“胡编乱造”,当是指这部小说中女主人公陈杏元被逼出塞和亲,路上跳崖自尽,被王昭君神灵摄回中土这类情节。中国小说源于传奇故事,发展成近代章回小说后,为迎合民间审美意趣仍讲究无“奇”不传。怪力乱神情节、场景穿插在小说中,实为中国古典小说一种典型审美范式。黑塞或许因不了解中国古典小说的这一特点而感到迷惑,认为这是作者艺术运思上的失当。的确,即便从今天的视角看这样的情节设置,也觉虚诞。黑塞书评虽不看好《二度梅全传》情节的“胡编乱造”,但却不指责、不抨击,而是论调温和,说这部作品为西方读者展现了中国风俗、习惯、理想和思维方式等而“令人喜欢”。书评,往往承担着撰写者自我宣言功能,表面上看是在对他人作品评骘品鉴,实际也是撰写者从自我主体性出发的一种“夫子自道”,即将自己的立足点、情感判断、价值观念、思考模式、情趣韵味等反映在对他人著作的评论中。黑塞以包容态度品评《二度梅全传》,让人窥见他对中国小说阅读的单纯期待,体现出黑塞对丰富多元的中国文化的兴趣与期待。
库恩也翻译了我国的《金瓶梅》(Kin Ping Meh oder die abenteuerliche Geschichte von Hsi Men und seinen sechs Frauen),1931年出版。译本中附有“译者后记”,介绍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其他人对《金瓶梅》作者的众说纷纭等内容。读了库恩译的《金瓶梅》,黑塞有评:
它不是我们知识中的那种表现智者或英雄的中国小说;它描绘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粗俗快活场景。荒伧、谑浪和淫猥之处甚多,也不比其他民族的同类作品写得幽默。然而这部流传了几百年的伟大作品自有它的魅力,这魅力在于它呈给读者一幅万象纷呈的市井生活风俗图。[3]206
虽然书评指出《金瓶梅》笔墨毫不娟洁,有人欲猥贱描写,但黑塞仍用“社会文化”视角打捞这部作品的意义,强调它的伟大价值在于它实为一部相当出色的、反映中国世俗社会世情风物的小说。了解《金瓶梅》的中国读者都知道,这部小说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活泼跳脱,人物思维和行为方式体现出的市井文化和朝代气质触手可及,是人们了解北宋市民社会和精神特征的一个文学典范。对黑塞来说,《金瓶梅》同样是一部可从中探视中国社会民俗的作品,与这部小说在中国文学里对世俗生活叙事的开创性作用十分吻合。一句“交给了读者一幅万象纷呈的市井生活风俗图”的评语,体现出黑塞对《金瓶梅》的观摄洞明。
三、捕捉到“真真国女孩子”
1932年,库恩翻译出版了我国的《红楼梦》(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此译本是个篇幅只有全本三分之一多一些的缩略本,(8)库恩的这个缩略译本是整个西方对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的首次翻译。书中人名多为音译,诗词基本删去,故事重新编排,全书被改成只有50个章回的篇幅。读了这部小说,黑塞在书评中写道:
阅读这部巨著既是一大乐趣,而且还获益匪浅。……小说里描述的中国,饱受历史遗留重压,已受到西方影响。故事发生在1700年前后中国最后一个皇朝的最初年代,所讲述的中国正在缓缓趋向没落,精神和道德已显现疲惫和停滞,不过古老文化积淀深厚丰富。佛教和道教,除了几句残留的通俗套话、咒语和迷信外,已所剩无几,和尚和道士几乎只是以蓬头垢面、歪斜不整的滑稽面目出现。伟大的神话仅还只是些肤浅的情节:人的命运是由祖宗和神灵在控制、安排和庇佑,必要时神灵还会以人的形象来到人间,奖善惩恶、拨乱反正。这些叙事道具增添了故事魅力,但也仅此而已,始终不过是迷信而非信仰,好在作品中对这方面的描述不多。如果说,在这部人物众多的巨著里精神的中国只还闪现着微弱的光芒,那么对其社会习俗的描写却是非常完美的。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小说通过对大观园里的社交关系、道德规范、奢侈生活、打情骂俏、讲究排场及受到礼教约束的心灵的描写而充分展现了18世纪的中国面貌。[3]332
一方面,古老的文化气象仍丰沛袭人;一方面,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已在缓缓趋向没落,两相映照,形成存在,是黑塞对《红楼梦》故事的认识。黑塞观察到小说所反映生活之明亮或幽暗,感受到小说所描写世界之辽阔或压抑,捕捉到小说所反映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之动机或隐秘,以书评方式呈现出来。可以说,黑塞书评是一头扎进一个正在没落社会的浮光掠影。由于翻译问题和文化差异缘故,黑塞无法深入理解《红楼梦》文学血液里流淌的“厌世解脱”的佛家观念或者信奉“循环论”的道家思想,评论《红楼梦》自然谈不上也无法做到深入到位,即便中国人也还没有谁敢说把《红楼梦》读透说清。黑塞书评让人看到,从了解中国文化角度进行阅读,仍旧是黑塞对中国小说流连忘返的主要原因。肯定《红楼梦》直抵中国社会风物样相的同时,黑塞书评也谈到这部作品在审美上的不足:
它说不上是一部经典的艺术佳作,写作技巧不脱成规窠臼,文本也未展示出精神意蕴的中国,没有以新的生动方式将古老的中国智慧显现出来。[3]331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其渊懿朴茂的人文情思和诗意葱茏的艺术标格,在整个中国古典小说文库里都令其他作品难以望其项背,黑塞之所以如此诟病《红楼梦》审美品质,可能是库恩的翻译手法和译文风格已使这部小说标志性的芳馨悱恻诗情画意被淡化抑或尽失之故,也可能还有黑塞自己初次阅读的深入程度不够,对中国文化了解有限等方面原因。可以确定的是,黑塞并未从此放弃《红楼梦》,而是继续徜徉在对其阅读里。第二年即1933年2月,黑塞又发表了一篇《红楼梦》的书评。这次撰写的书评显示黑塞对《红楼梦》的看法已大有不同,字里行间变化已起。黑塞赞扬《红楼梦》散发着朦胧迷离的气韵,称它是一部描写没落文化的杰作:
所有的宏大的中国母题再次呈现,构成风景。古代中国的伟大智慧、宗教与圣迹气息扑面而来,达到艺术灵性的通透。虽然作品中描述的所有世象都只是在淡淡地闪烁着光韵,仿佛是映照在环礁湖中,所有的描述世象都已在开始落败,充满了忧郁,有一种衰落与疲倦的情绪在将它们整体笼罩。这部巨著以精湛的技巧构建了荣国府和宁国府家族。人间命运是由彼岸的智慧大师在把控,必要时这些大师也会出现在人世舞台上。……我深知,即使有晚古的佩特罗尼乌斯那游刃有余之笔,也找不出第二个文学例子,以镜像将一种精疲力竭的文化描写得如此异彩纷呈,婀娜飘逸。[3]367
黑塞这次书评,以诗人之心感受《红楼梦》对现实社会的镜像,言辞之花自由绽放,宕开欣赏《红楼梦》描写大厦将倾的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的一笔:虽然它的退场已在悄然开启,但仍散发着文化光芒,像一个超越般的存在凝视着深沉的黑暗。这次书评并不表明黑塞对《红楼梦》已深谙其意,已深切感知并叹服其神来之笔,但可从中看出,黑塞阅读知微至微,从《红楼梦》的细微之处看到了中国历史深处一种重要情形春光乍泄,那就是曹雪芹笔下展现的中国已在睁眼看世界这样一个时代动态:
这个时期的中国不再完全自闭,西方已找到了切入口。小说提到了一个掌握了中国文字和诗歌艺术的欧洲金发女孩。[3]367
书评所言的“欧洲金发女孩”,应该是指《红楼梦》第五十二回薛宝琴讲她小时候见过的一个精通中国诗书,会讲《五经》,能作诗填词的“真真国女孩子”。《红楼梦》何以让黑塞再次撰写书评,也许正在于这个女孩。第二次撰写《红楼梦》书评的几个月后,黑塞为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第二部《儿子》德译本写了书评,开头是这样写的:
《红楼梦》这部18世纪初的伟大中国小说中有那么一个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而言很是让人在意的人物,一个金发女孩,一个西方姑娘,在中国生活了数年,喜欢上了这个国家,喜欢上了它的语言和礼仪,甚至能与中国上流社会女孩竞诗。读赛珍珠的作品,人们会不禁想到这个女孩。[3]399
站在西方与中国交集的坐标上阅读赛珍珠描写中国的作品,探究赛珍珠创作它们时的姿态,想象赛珍珠写下它们时的表情,琢磨赛珍珠对写作对象的心灵感受,在喜欢中国文化的层面上打通与赛珍珠的精神联系,这是赛珍珠的中国描写引发了黑塞的共鸣。用《红楼梦》里的金发女孩比喻赛珍珠之于中国的满怀情意和深厚因缘,这是黑塞的独具慧眼。应当承认,对中国读者来说,《红楼梦》里的“真真国女孩子”是个极易被忽略的人物,我们往往以为曹雪芹让薛宝琴提及这个女孩,不过是出于稀罕目的。即便在《红楼梦》对我们来说已不单单是一部文学经典,而是有许多民俗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有饮食饕餮们在其中探究当时生活、民俗、礼仪、服装、美食的今天,这个“真真国女孩子”也仍常常是在人们眼前一晃而过,并不会对她驻目关注。但是一个有心的外国读者却将这个女孩捕捉到了。黑塞之所以领略到《红楼梦》中的这个小小风景,是因为黑塞自己有积极参与文化交流的自觉与思考,因而“探秘”意识和发现力强。黑塞书评在赛金花作品和《红楼梦》人物间牵线搭桥,既是在赞叹赛珍珠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西中文化交流的贡献,也是把自己的西中文化交流之心、经验和心得予以巧妙印证。
四、心驰“共同精神”
库恩翻译的中国小说中还有《水浒传》,译本达800多页之厚,带有60祯中国木刻插图,1934年以《梁山泊强盗》(Die Räuber vom Liang Schan Moor)书名出版。次年3月,黑塞对其作了书评:
“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早在歌德和洪堡时代的人文主义德国就已建立和培植起来。地球是所有民族的共同家园,各民族之间就是兄弟姐妹关系,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学之间就是亲戚关系。通过对陌生者的亲切接纳,尤其是通过切贴的翻译,拓宽和丰富自己的语言和文学,感受一种终极的共同精神,这是歌德和德国理想主义者的一个美妙设想。这种态度当然从来就不是主流的,而只是很有价值的少数人的思想。在那个时候的德国,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在社会精英头脑中深深扎下了根,而在普鲁士,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一个犹太人要想成为大学教授却几乎是同样的不可能。不过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在德国不会消亡,人们乐见其今天还在生发作用。……当前又有一本中国古代民俗小说《水浒传》在德文世界里开启了它生命的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对译者和出版社为此所作的贡献)欣悦不已,我本人尤为如此,因为在所有的非欧洲国家文学中,没有哪种文学能像中国文学那样让我如此喜欢。[4]30-31
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书评中国小说时黑塞通常会说获得了文化阅读愉悦。这里引人注目的却是,黑塞书评是以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导入,并以该概念的哲学内涵提示西方读者要在来自中国的这部长篇小说中感受一种“共同精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能令黑塞如此心驰?黑赛接着写到:
这部伟大的英雄传奇读起来格外引人入胜,真叫人爱不释手。它是一部反叛者的史诗,梁山泊的众强盗是不折不扣的席勒式强盗:他们是高尚的叛逆者,他们反抗腐败的官僚统治,他们嫉恶如仇与歹人作对,他们为自己的胜利狂欢,他们折腾敌人不遗余力,将其打翻在地后仍要夺其性命。他们中的一个首领,……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强盗,而实际上他是天上的星宿,还要回到那里去。[4]31
用“席勒式的强盗”来评价《水浒传》的梁山好汉,称他们是反叛腐败的官僚统治的“高尚的叛逆者”,显然,黑塞书评所言“共同精神”指的是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而斗争的精神。这是一种在世界各民族文化里都存在的精神,席勒的剧作表明了这一点。一般来讲,作为中国读者的我们读罢《水浒传》这部小说,脑中留下的常常是一群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几乎每个人物都有他们的专属故事,因而对于国人而言,这部作品精彩之处常常在于它讲述的绿林英雄和风雷传奇,常常在于人物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和事件描写的跌宕腾跃,如金圣叹所言:“《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7]黑塞书评《水浒传》是部“反叛者史诗”,我们不能肯定他就是触摸到了这部小说内蕴的“撞破天罗归水泊,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抗争思想,就是萃取到了这部小说骨子里张扬的“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英雄气概,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于书中看到的是除暴安良、为民去害之英雄。“他们中的一个首领,……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强盗,而实际上他是天上的星宿,还要回到那里去”,这样的书评语言透露着黑塞对书中好汉的真情点赞。
马克思说:“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8]人的真情表现有其社会生活中的必然性要求。黑塞对中国文学的“抗争者”题材格外欣赏,有着似乎他乡遇故知的巨大共情,用歌德“世界文学”概念将梁山好汉们的山贼高义与席勒式的伸张正义强盗联系在一起。这一联系,打破界限,对《水浒传》的书评不仅传达着黑塞为犹太人仍难成为大学教授打抱不平,又显然成了他自己内心希望的一个隐喻,即黑塞希望西方社会也能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梁山泊强盗”出现。黑塞内心应该是怀有这个期待的,因为他生活在时代的泥泞中,为他所处的野蛮时代而焦虑。一战期间,黑塞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心中自有善恶,是少数几个没有卷入当时泛滥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狂热的德国作家之一,不断发表文章痛斥这场战争及其根源,却被污蔑为叛国。战后的魏玛共和国社会和政治动荡与混乱也让黑塞倍感失望,最终于1923年放弃德国国籍成为了瑞士公民。希特勒主政德国期间,黑塞被纳粹视为不受欢迎的作家,受到社会排斥。在这样的背景下,黑塞对《水浒传》阅读回甘,感觉它“真叫人爱不释手”,非常欣赏水浒人物的硬朗意志和抗争精神,也就不足为奇了。
1935年3月,黑塞再次撰写书评评论《水浒传》:
这是一本人物众多的章回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十三世纪的一群铤而走险的强盗的故事。读这本小说,就像是在观赏一幅哥白林织锦或古代东方图画。对我来说,历史的内容尽管也很有趣,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阅读让人感觉像在一个布局巧妙,充满奇观和惊险的超现实花园里漫步。与我们的天真的自然主义相反,在这里,遥远被拉到了身边,真实变成了镜像:事件镶嵌在古典人生智慧和宗教礼仪的繁复图案内,在一幅魔幻幕布的背后、在一面魔镜的背后发生和展开。孔子和菩萨端坐在事件上方祥云里。[4]41
黑塞这一书评,语言缥缈富有弹性,从亦真亦幻的视角观察小说审美特征,指出《水浒传》用了一定的超现实主义手法,行文很有黑塞风格辨识度。书评最后一句“孔子和菩萨端坐在事件上方祥云里”,不是书评语言妙笔生花的装饰品,而是黑塞对小说有其独到的体会。除了菩萨(九霄玄女)外,黑塞认为孔子也在《水浒传》故事中,这是他自己产生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他将自己的精神向往转换成了一幅中国式图案,以此图案告知西方读者:要从中国文化儒家思想角度阅读这部小说。我们知道,确有我国儒家思想在贯穿《水浒传》始终,那就是“忠义”伦理,但这个伦理却是梁山泊好汉们最后悲剧结局的一个缘由,比如他们的首领宋江,他那具有双重心态,徘徊动摇在抗争与招安之间,背着沉重精神枷锁的悲剧性格就源于此。不过,黑塞书评言“孔子和菩萨端坐在事件上方祥云里”,应该不是在暗示宋江命运之悲剧性,而是黑塞带着他的个人语境和西方世界的时下问题在寄托心灵,希望中国文化儒家思想登临高处,辐射西方。
因为黑塞这个时候对中国的兴趣已从老庄哲学转向儒家学说和佛教禅宗,因为黑塞在寻找一种能够帮助清淤排障的精神文化,因为黑塞置身的西方世界笼罩着没落的危机,因为黑塞身处的时代上空盘踞着“野蛮”的巨蟒,又因为黑塞不让失望和悲哀统治内心,而将忧患思绪化作能让他产生希望的文化寻找。可以说,黑塞之所以被译成德文的中国小说打动,是因为他从中发现了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他者”,一个他在寻找的中国。这个中国,是一个澄明的、净澈的、纯粹的、超然的精神信念、精神世界和精神空间,是一个形而上的精神价值,是一个寄寓了希望的精神背景,是一个意在让文明没落的西方人实现自救的精神意义指向,是一个用以对抗纳粹掀起的反文明逆行的精神力量之源。(9)这期间,黑塞在创作他的最后一部小说《玻璃球游戏》,黑塞在小说中融入了诸多中国文化内容以充实小说中描述的乌托邦设想。
结 语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9]可以说,在黑塞心灵里持续唤起惊奇和敬畏,把黑塞引向无限而实现了对身处现实的超越的,除了星空和道德律,还有来自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粲然大备,黑塞对它一直热情不减,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已然成了他的一种信仰。依照皮尔士的观点,信仰发生于现实需要,之所以能够平息现实焦虑,是因为它让人超越现实;信仰能够让人超越现实,又往往通过一种习惯性的持之以恒方式。[10]这些,正是我们可以在黑塞那里观察到的情形。黑塞说,阅读中国书籍,他感受到了很多想象奇诡、思辨超常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尤其是在煎熬的战争年代,我常在这里(笔者按:黑塞书房“中国角”)找到了使我慰藉和振作的思想。”[1]298黑塞道:“不懂中文和从未去过中国的我,在两千五百年后有幸在古老的中国文献中找到了自己设想的一种证实,找到一个精神的氛围和家园,就像我通常只是在由出生地语言赋予的世界中拥有它们那样。”[11]黑塞如此直接和坦诚地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骨髓的激情,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就是黑塞的一种信仰。
文化信仰下的黑塞中国小说书评,交织着热爱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意识。比如《好逑传》,中国人在这部所谓“正统小说”里看到的是纲常名教、金殿抡元、皇帝赐婚、珠辉玉映一类的陈旧落后现象和封建礼教对自然人性的阻碍压抑,对黑塞而言,它则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东西:书中的节制、孝道、秩序、公正、仁爱等美德伦理,正是以资西方人学习借鉴以实现文化自新、精神自救、走出没落困境和摆脱野蛮的理想范式。正因如此,在读到黑塞将那些对中国人而言是“未入流”的小说评价为“令人喜爱”的作品时,我们也被打动,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黑塞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里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与定位,感受到了黑塞仰望中国文化的心音和脉息,感受到了黑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思维火花的跳跃和闪动。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对黑塞的中国小说书评也不觉生发出阅读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