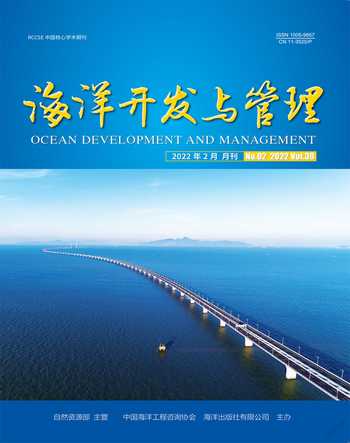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法律属性及其立法完善
2022-04-01杨未名刘飞琴
杨未名 刘飞琴
关键词: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水产品贸易;强制标志;捕捞许可;渔业法
中图分类号:DF413.4;F326.4;P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22)02-0082-06
0引言
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捕捞是影响渔业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为破解水产品国际贸易中的IUU 捕捞问题,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应运而生。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是指与水产品合法性标签的申请、核发和监督管理等相关的一系列规定,其政策目标是通过合法性证明标签对水产品捕捞行为进行合法或非法的区分,进而为水产品贸易和相关执法提供指引,其中非法捕捞的水产品将被禁止交易,同时不依法标注合法性标签或标注不合法标签的行为将被施加公法制裁。2015年美国《IUU 捕捞强制执行法》确定17类(涉及119种海关HS编码)处于风险中的水产品,这些水产品的进口商须向美国政府登记备案,其中对野生和养殖水产品分别要求提供相应的l7项和13项信息,包括捕捞品种、捕捞船只、捕捞地点、捕捞日期、捕捞重量和卸货日期等大量电子追溯信息[1]。目前包括欧盟、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等在内的60余个国家和地区均已实施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
为有力回应国际社会质疑,同时保障我国水产品加工业和水产品贸易的健康发展,我国自2010年开始实施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要求在进口蓝鳍、大目金枪鱼、剑鱼和南极犬牙鱼等高价值捕捞水产品时须提供合法捕捞水产品通关证明[2]。此外,截至2018年我国已在浙江、吉林、江苏和广东等地实行水产品溯源认证管理制度,由渔民自行在“渔港通”App上录入信息以识别其捕捞行为是否合法并获得相应标志码。
实践的发展推动相关立法进程。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渔业法草案》)在第三十七条和第五十二条新增对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规定,据此可以看出我国的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并不仅限于水产品国际贸易,而且扩展至水产品国内贸易。该规定不同于国际社会主要将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应用于水产品国际贸易的普遍做法,由此产生对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法律属性的争议,即其是行政认证还是行政许可抑或是其他? 其与既有捕捞许可制度是什么关系? 此外,《渔业法草案》的相关规定还存在实施程序和法律后果模糊等问题,亟待进一步澄清和完善。
1我国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立法现状和存在的不足
自2010年开始,我国分别从水产品进口和出口2個方向启动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实践,但有关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法律规范化进程却相对滞后。
1.1立法现状
在国际社会质疑我国水产品捕捞查验制度的背景下,我国针对出口欧盟的水产品专门发布《关于为输欧海洋捕捞产品办理合法捕捞证明的通知》[3],决定自2010年1月1日起为部分输欧水产品办理欧盟相关条例要求出具的合法捕捞证明的确认和加工厂声明的认可。为进一步规范输欧水产品合法捕捞证明制度,2011年我国《输欧海洋捕捞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由中国渔业协会远洋渔业分会以及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具体负责输欧海洋捕捞产品认证的初审工作,2017年我国发布相关办事指南。此外,可通过“中国输欧海洋捕捞水产品合法性审核单证查询系统”在线查询水产品合法捕捞证明和加工厂声明。
对于进口水产品,2010年我国《关于对进口部分水产品启用<合法捕捞产品通关证明>》[4]决定对金枪鱼和剑鱼等4类水产品启用《合法捕捞产品通关证明》。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海关总署公告第2146号》[5]进一步要求对从俄罗斯进口的大麻哈鱼和狭鳕等14类水产品实施合法捕捞产品通关证明制度。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海关总署公告第2157号》[6]决定实施《合法捕捞产品通关证明》联网核查系统,以有效防范和打击非法捕捞活动以及提高通关效率。从具体的实施程序来看,有关单位在我国申请《合法捕捞产品通关证明》时须提交由船旗国政府主管机构签发的合法捕捞证明原件,我国将重点审核合法捕捞证明所列渔船、签发人和签发单位在有关国际组织的登记注册等情况,必要时还会审核产品转运声明,审核后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签发《合法捕捞产品通关证明》并交予其办理通关手续[2]。
2019年《渔业法草案》体现我国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最新进展,主要规定在第三十七条和第五十二条。其中,第三十七条规定“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销售产品应当按照渔业主管部门的要求,填写产品合法性标签,载明船名船号、捕捞许可证、渔区、渔具等相关信息,并随渔获物流转。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收购、转载、加工、销售、进口没有合法来源的渔获物。县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监管需要向大中型捕捞渔船派遣观察员,对其生产情况进行记录评估。”第五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渔业、市场监督、海关等行政主管部门对捕捞渔获物的合法性标签进行检查。对于非法捕获的渔获物,应当按照职能查封扣押,并依法处罚。”
1.2存在的不足
由于我国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实践起步较晚,目前相关法律规定仍存在诸多问题。
1.2.1法律依据缺乏
上述通知和公告仅是规范性文件,其法律位阶和效力都很低,且规定笼统,未明确申请合法捕捞证明所需的材料、时间、费用和职责分工等具体问题,可操作性较差。《输欧海洋捕捞产品认证管理办法》仍停留在征求意见阶段而未正式出台,导致我国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在实践中缺乏系统的法律依据。2019年《渔业法草案》表明我国尝试补充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法律依据,但其能否通过审议尚且存疑,同时其中的相关规定仍存在实施程序和法律后果模糊等问题。
1.2.2法律属性不明
从既有法律条文来看,我国尚未明确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法律属性,相关立法者对其属性的认知也不一致。一方面,《输欧海洋捕捞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由中国渔业协会远洋渔业分会以及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具体负责输欧海洋捕捞产品认证的初审工作,表明立法者倾向于将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定位为行政认证;另一方面,2019年《渔业法草案》并未明确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法律属性,但从其第五十二条的表述中可知,水产品合法性标签由渔业、市场监督和海关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检查,捕捞渔获物如未附加相应的合法性标签将无法进一步被收购、转载、加工、销售和进口,从这个意义上似乎又可将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理解为行政许可。gzslib2022040123231.2.3与捕捞许可制度的关系不明
捕捞许可制度是指为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控制捕捞强度以及保障生产者的合法权益,由渔业行政管理部门依申请赋予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从事捕捞的权利或资格的许可制度[7]。该制度是针对特定人的一般禁止捕捞义务的解除,即只有被许可人获得捕捞许可证后才能进行捕捞,且被许可人应严格按照捕捞许可证所核定的事项和许可本身的条件进行捕捞。
对比捕捞许可证制度和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二者在规范内容上都涉及捕捞船名船号、捕捞地点、捕捞渔具、捕捞品种和捕捞数量等信息,而在实践中二者的制度功能是否存在重叠进而有重复处罚之虞以及应如何理解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渔业法草案》并未给出明确答案。
1.2.4能否扩展适用于国内贸易不明
在水产品国际贸易中引入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原因是国际法中存在“国家主权”原则,使得一国很难监管另一国的渔业执法情况,此时为确保捕捞水产品是由合法捕捞行为获得的,其他国家可要求捕捞者所在国政府出具合法捕捞的担保证明。而在水产品国内贸易中引入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上述法理基础显然无法支撑,因此其合理性存疑。
2关键问题: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法律属性
我国的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规则上存在诸多不足。而要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须首先解决其基础理论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明确其法律属性。
2.1水产品合法性标签的标签类型
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属于水产品标签[8],其实质是溯源认证措施,理论上水产品标签包括地理标志、生态标志和强制标志3 种。① 地理标志。1994年《TRIPS协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地理标志是识别商品原产自成员方境内或其境内某区域或某地点的标记,而该商品的特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在本质上可归因于其地理原产地”,我国属于地理标志的水产品标签包括长海海参、千岛湖鱼和砀山梨等。地理标志为水产品生产者提供商业信誉的保障,也为消费者选择优质产品提供可靠的信息途径。②生态标志。生态标志也被称为环境标志,起源于1978年德国启动的“蓝天使计划”,通常由生产者自愿申请获取,提醒消费者选购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较低的产品,促进生态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如国际海洋管理理事会和“海洋之友”发布的水产品认证标志[9]。1992年欧盟通过第EEC880/92号条例,出台生态标志体系。③强制标志。强制标志是指基于安全和健康等考量而必须在产品上附贴标签,否则产品不能上市交易或上市交易会受到处罚的认证标志。强制标志主要应用于工业产品,在农业领域目前有转基因食品强制标志,而在渔业领域尚未形成类似的强制标志[7]。
在实践中,水产品合法性标签的附加往往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当进出口商违反规定、不申请或申请后不按规定使用水产品合法性标签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采取强制性措施甚至是具有公法性的制裁措施。例如:英国法律规定在没有取得经过验证的捕捞证书的情况下进口渔业产品是违法行为,进出口商可能被起诉并被处以高达5万英镑(约合43万人民币)的罚款[10];《渔业法草案》第五十二条规定“对于非法捕获的渔获物,应当按照职能查封扣押,并依法处罚”。因此,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在法律上应被认定为强制标志。
2.2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和捕捞许可制度的关系
水产品合法性标签虽属于强制标志,但探究其作为制度本身的法律属性还须结合行政法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通常而言,申请人能否获得该强制标志须从捕捞主体、捕捞时间、捕捞地点和捕捞数量等角度来判断其捕捞行为是否合法,这便与捕捞许可制度在规范内容上存在高度重合,由此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界定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和捕捞许可制度的关系。
捕捞许可制度是为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和维护渔业生产秩序而准许申请人从事捕捞的行政许可。那么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是否也是行政许可呢? 结合上文分析,水产品合法性标签是行政部门在判定捕捞行为合法后颁发的强制标志,其判定标准主要參照捕捞许可证的内容,即只要申请人按证捕捞,行政部门均应授予其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可以看出,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不是授予相对人从事捕捞活动的资格或权利,因此其并非新的行政许可。
而后须回答的问题是,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是否属于行政认证?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定义,行政认证是指由政府认可的第三方认证机构证明某组织的产品、服务和管理体系符合相关标准、技术规范或强制性要求的合格评定活动,具有一定的自愿性。而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属于强制标志,且根据《渔业法草案》第五十二条,水产品合法性标签的检查机构是渔业、市场监督和海关等行政主管部门而非政府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在此前的实践中也是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为输欧海洋捕捞产品办理合法捕捞证明。因此,不宜将我国的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理解为行政认证。
那么如何在行政法层面认定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法律属性呢? 从制度功能的角度来看,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实际上是对有效实施(渔业捕捞)行政许可的监督手段,即行政部门在行政许可之后的跟进监管,具有强制性。在这个过程中,捕捞许可证是水产品合法性标签的实质所在,而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则是捕捞许可证的外在表征。捕捞许可证和水产品合法性标签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机动车的行驶证和牌照:交警可通过牌照判断机动车是否具有在道路上行驶的合法资格,而无须逐一核查行驶证;由于捕捞许可证不会直接表现出来,对于作为执法对象或交易对象的水产品,可通过水产品合法性标签来识别和证明其是由享有合法捕捞资格(捕捞许可证)的自然人或法人依法按证捕获的。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实质目标就在于解决捕捞许可证等行政管制类工具在应对IUU 捕捞时的失灵问题,即通过引入水产品合法性标签这样的信息规制类工具,改变执法和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从而提高执法和交易效率。综上所述,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是行政部门对捕捞行为是否符合捕捞许可制度的强制性行政确认。gzslib202204012323在此意义上也可得出结论: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最初被运用于水产品国际贸易,但可将其扩展至水产品国内贸易。这是因为IUU 捕捞的猖獗与行政管制的失灵不仅存在于国际贸易市场,而且广泛存在于国内贸易市场。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旨在规制捕捞行为而非其后续的销售行为,或者说销售行为的合法性取决于其前期捕捞行为的合法性。因此,无论是水产品国际贸易还是国内贸易,都不影响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适用。
3我国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立法完善
根据上文分析,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属于强制性行政确认。在当前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订的背景下,立法者应基于此统筹考虑完善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
3.1健全实施程序
《渔业法草案》第三十七条目前仅就水产品合法性标签的取得作出原则性规定,即“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销售产品应当按照渔业主管部门的要求,填写产品合法性标签”。据此,捕捞者在销售其所捕获的水产品时应申请和附加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并随渔获物流转。值得注意的是,此条的条文表述是“填写”,而未明确后续是否需要审核、谁来审核和如何审核办理水产品合法性标签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笼统的立法方式不利于制度目标的实现,尤其对于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这样的新制度来说,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制定具体和完整的实施规范。
由于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是行政部门对捕捞许可证的强制性行政确认,行政部门(可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应承担对水产品合法性标签进行审查、核发、登记、备案和监管等的责任,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订过程中增加水产品合法性标签的申请程序(包括材料、时间和费用等)、审核和颁发程序(包括职责分工、办理期限、信息共享和核查协助等)以及救济途径的相关规定或授权国务院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3.2明确法律后果
法律效果的实现有赖于法律规范要素的完整。明确违反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法律后果将有助于打击IUU捕捞,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渔业法草案》第五十二条规定行政主管部门“对捕捞渔获物的合法性标签进行检查。对于非法捕获的渔获物,应当按照职能查封扣押,并依法处罚”,然而这样的法律规定主要存在3项缺陷。①条文表述并未明确是否要对违反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行为进行处罚,因为其设定的处罚情境是“非法捕获的渔获物”。②即便立法者的本意是要对违反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行为进行处罚,在《渔业法草案》的法律责任章节中也找不到相对应的处罚条款。换言之,《渔业法草案》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依法处罚”中的“法”并不明确和具体,唯一相近的是第六十二条中关于违反捕捞许可证制度的处罚规定。而基于上文对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法律属性的分析可知,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和捕捞许可证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机动车的牌照和行驶证,理论上执法者可直接套用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对违法获取、违法使用或未使用水产品合法性标签的行为进行处罚,但此时亦可能存在对违反捕捞许可证制度本身的处罚,进而有双重处罚之虞。③根据《渔业法草案》第三十七条和第五十二条,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运行过程涉及收购者、转载者、加工者、销售者(既可能是捕捞者也可能不是捕捞者)、进口者和行政部门等多重法律主体,而《渔业法草案》并未有针对性地对其设定不同的法律后果。
对于上述问题,建议从3个方面進行完善。①明确对违反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处罚,并针对不同的法律主体设定不同的法律后果,包括查封、扣押、罚款、(情节严重时)吊销捕捞许可证和行政处分等。目前《渔业法草案》第七十九条“执法人员违法处分”中并未明确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核发水产品合法性标签的法律后果,因此建议在该条第一款中明确“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核发水产品合法性标签的,依法给予处分”,从而避免将其置于“兜底条款”中讨论是否给予处罚。②关注对违反捕捞许可证制度与违反水产品合法性标签制度的处罚衔接,避免因同一事项而对相对人进行双重处罚。③《渔业法草案》第三十七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收购、转载、加工、销售、进口没有合法来源的渔获物”,这意味着水产品交易的整个过程均须附加水产品合法性标签。然而其中的“转载”无法涵盖“运输”的所有环节,因此在法律修订时建议加入“运输”。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