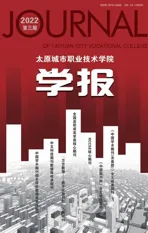技术中立视域下通知删除规则的纠偏与应然路径
2022-03-28胡自源
■胡自源
(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一、问题的提出
版权的历史是一部扩张史,而技术的发展是版权扩张的导火索[1]。版权学说理论及司法实务的发展与技术进步总是如影随形。随着互联网技术、新型商业模式的飞速发展,利益主体呈现多极化特征,多主体寻求版权保护及责任豁免的利益诉求给司法裁判带来许多难题。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版权制度的核心在于在最优激励与最优利用之间实现平衡[2]。一方面,通过版权法赋予作者专有权,以解决知识生产的激励问题;另一方面,又需对版权进行必要限制,以防止权利垄断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减少。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信息时代背景下的重要版权权能,其对高价值作品的交互式传播及社会文化事业的进步均具有积极意义。但技术的发展会使制度平衡产生动荡。而基于法律的内在生命力,通过新制度的创设又使利益的平衡状态得以恢复。通知删除规则(该制度称谓在我国学界并未答成一致,多数学者将其称为“通知删除规则”,但也有少部分学者将其称为“通知移除规则”“通知取下规则”“通知规则”“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规则”等)[3-6]的引入实属利益平衡机制在版权法领域的典型体现。
在司法实践中,通知删除规则持续发挥着以合作机制为基础的平衡功效,促进了网络产业发展和版权人利益保护两者之间的平衡。但传统通知删除规则出现了难以应对新型网络服务版权纠纷的趋势,算法版权纠纷、小程序版权纠纷、云服务器版权纠纷均可见一斑。均于近年审结的微信小程序案①及阿里云案②实属通知删除规则司法适用难题的典型。在微信小程序案中,一审法院对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主体进行目的性限缩,得出该制度仅适用于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及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而根据相关技术原理,微信小程序平台属于接入类网络服务,故最终将其排除在通知删除规则之外。在阿里云案中,一审法院认为《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适用于所有网络服务提供者,但阿里云公司并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二审法院认为,云服务器提供者无法对用户存储的信息内容进行控制,在技术上不应承担删除、断链等法定义务,且转通知可以成为适格的必要措施之一。
诚然,不断衍生的新型互联网技术及商业模式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技术与法律的相互作用更是版权理论的古老话题。法律的稳定性及可预见性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所以我们更应当考虑的是以现有规则合理解决新型网络服务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技术中立为对话起点,并以现有版权法律制度为依归,明晰通知删除规则的本质与时代新意,探索出具有普适性价值的解释路径以合理解决前述问题。
二、技术中立的适用现状与应然定位
应当明确的是,过于严苛的权利保护对作品传播及互联网技术发展等方面势必会产生消极作用。作品使用、传播及互联网服务带来过高的侵权风险,会抑制网络用户的创作热情及平台开发者的技术创新。过分强调版权人的权利垄断势必阻碍文化繁荣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故技术中立原则应运而生,成为版权法律保护的重要制度之一[7]。
(一)技术中立原则的司法适用现状
笔者以北大法宝为基础数据库进行穷尽式高级检索,共获取143份判决书作为有效样本案例(此次检索的关键词为“案由: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文书类型:判决书”“案件类型:民事案件”“全文:技术中立”)。通过深度分析,其中以技术中立作为被告抗辩理由的案件共115件,占案件总数的80.4%;以技术中立作为判决理由的共26件,占案件总数的18.2%;技术中立在抗辩理由及判决理由同时出现的共计2件,占案件总数的1.4%(详情参见表1)。

表1 有效样本案例
不难发现,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现状存在如下特征。
第一,适用前提模糊,被告往往对该原则进行笼统性适用。部分案件中被告认为技术中立原则与利益平衡原则属于并列的、调整法律价值目标的宏观性原则③。且在多数案件中,被告仅单纯地辩称其属于技术中立方,已经履行了较高的注意义务,但尚未充分证明其技术中立的具体表现及责任豁免的依据④。
第二,法院对该原则的适用存在随意性,缺乏统一的概念界定及适用标准。囿于技术中立原则在制定法层面的缺失,该原则对司法裁判人员丧失拘束力。正如前所述,在143份有效样本案例中,共有115例案件的被告以技术中立作为抗辩理由,但无一例判决对技术中立的适用与否作出具体解释。在以技术中立作为判决理由的案件中,仅有极少数判决明确解释了技术中立的本质,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迅雷网络公司诉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公司等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⑤,该案中法院认为迅雷下载软件属于下载工具,技术提供者不因其仅提供了该技术而承担责任。但技术提供者帮助、引诱用户使用技术实施侵权行为的,仍应承担间接责任。
(二)技术中立原则的应然定位
版权法上的技术中立原则发轫于美国1984年环球电影诉索尼案⑥。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法官提出技术产品提供者是否需要承担帮助侵权责任的前提在于该产品“能否被广泛用于合法的、不受争议的用途”,若该技术存在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则技术提供者无需承担侵权责任。申言之,即使技术服务提供者知道该技术存在侵权用途,也不能作出其具有帮助侵权故意的主观推定[8]。
但索尼案所创设的裁判标准并非以“侵权用途”与“非侵权用途”的比例为基础,而直接将产品具有“一种潜在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作为技术提供者责任豁免的充分条件[9]。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该原则为故意设计侵权用途但保留一种潜在合法用途的技术提供者打开了责任规避的大门。鉴于此,有学者指出,面对技术发展威胁版权人利益的现实,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受到了严峻挑战[10]。而后该原则又在实践中得以修正,逐步确立了以客观帮助行为与主观过错相统一的帮助侵权规则、以监管关系及获取直接经济利益为适用要件的替代责任规则⑦。其后又在Grokster案⑧中明确技术中立从不意味着脱离普通法中以过错为基础的责任规则[8]。由此可见,在比较法层面,即使技术中立原则缺乏制定法依据,但其在判例法体系下逐步发展并完善。
技术中立的真谛在于,因某技术被适用于何种用途难以预料,故不能仅因技术被用于侵权行为而对技术提供者科以侵权责任[8]。诚然,任何一项技术均有被适用于侵权行为的可能性。对技术提供者来说,技术中立无疑是技术创新的大宪章;而对版权人来说则不然⑨。但法律的制定必然要在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基础上实现技术进步与版权保护的平衡。因此,法律不应对技术本身作出价值评价,其管制的立足点仍是行为[6]。技术提供者是否需要承担第三人责任的核心在于其是否具有主观过错,技术中立的适用仍需以侵权法基本原理为依归。故司法实践中将技术中立作为“万金油式”抗辩事由的当事人实属对该原则本质的误读。
根据传统侵权法原理,基于主观过错对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提供帮助或引诱他人侵权的,成立间接侵权责任[11]。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技术提供方,其责任基础往往并非直接侵权行为,而是立基于其客观帮助行为使得损害后果得以延伸和扩大,但其最终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尚需对其主观状态作出价值判断。但基于网络侵权具有侵权主体匿名性、传播快捷性、影响广泛性和不可逆转性等特征[5],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状态的判断实属司法实践的难题。为明晰间接侵权的责任边界,通知删除规则作为版权人与技术提供者的博弈结果应运而生,在难以权衡的利益主体之间长期寻求着最优化的稳定状态。
三、通知删除规则的纠偏适用与时代新意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通知删除规则最早形成于美国。在早期域外司法实践中,版权人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对内容作品的权利监管义务;而网络服务商却认为事前审查义务对其来说不堪重负。基于此,《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应运而生,成为双方利益主体博弈过程的产物。通知删除规则是DMCA的核心,意即除事先知道具体侵权行为存在,网络服务商在收到权利人合格通知的情况下,及时删除被控侵权作品或断开相应链接,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11]。在美国的影响下,《欧盟电子商务指令》也存在类似规定⑩。
我国在借鉴DMCA的基础上,于2006年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正式引入通知删除规则。但基于不完全的法律移植,该制度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出现较多问题,择其要者:第一,该制度已逐步背离立法初衷,从合作性机制向对抗性机制转变[12];第二,何为网络服务商需采取的“必要措施”成为法律解释的难点所在;第三,由于替代责任规则在立法层面的缺失,单纯的定位清除措施无法适应新技术发展的风险。
(一)对合作治理理念的重申
通知删除规则的科学性在于其立基于合作治理理念[12]。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具有正外部效应,即知识生产者以外的人不付费或少量付费,便可获得并使用知识。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知识的正外部性尤甚,由此也导致了盗版猖獗、版权人创作热情降低等现象。所以在经济理性及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通知删除规则免除了网络服务商的事前审查义务,将发现侵权的任务分配给版权人。但就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该规则已然出现向对抗性机制转变的趋势——版权人大规模发出侵权通知,而网络服务商处于被动等待侵权通知的主体,仅机械化地完成定位清除等法定义务。有学者指出,不论通知删除规则是否有利于版权人,其最终目的仍是促进社会文化事业的繁荣[13]。故打击互联网版权侵权理应成为版权人与网络服务商的共同对话起点,两者之间进行版权治理的良性互动才是通知删除规则的应然状态。
(二)关于“必要措施”中“必要性”之解释
根据版权共同侵权理论,只有网络服务商主观存在过错时才可能承担帮助侵权的责任⑪。而过错在侵权法理论中存在故意和过失两种主观状态,其分别对应着“明知”和“应当知道”的立法表述。通知删除规则作为归责条款,其准确定位应作为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过错的判断方式[14]。基于此,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并采取必要措施成为其能否豁免责任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通知删除规则已然在技术发展的进程中嬗变成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规则。囿于技术的局限性,在立法初期,制定法将该规则的必要措施限定在“删除、断开链接”等定位清除措施。但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发展,新型网络侵权类型纷繁复杂,必要措施的适用必定需要弹性空间,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解释适用。必要措施的选取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自主判断、自主决策的领域,立法不应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此给出一个刚性规则[15]。但在实践中,有部分法院将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前提限定为——平台需对侵权内容具有控制力[6]。但从该规则的立法本意来看,前述观点实值商榷。如前所述,通知删除规则以版权人及网络服务商的相互合作为制度基石,以期共同应对网络版权侵权问题。而伴随着技术发展,商业模式呈现新业态。在根据相关技术原理判定网络服务商对侵权内容不具有控制力的前提下,并不能因此否认其不具有除“删除、断开链接”外的其他法定义务。正如有学者所言,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法移除被指称侵权作品的,并不意味着无需采取任何必要措施,而应当采取与其技术能力相适应的措施以体现与权利人相互合作的精神[11]。在学界,多数学者肯认“转通知”可以成为必要措施之一[11,16-20]。但也有少部分学者持否定观点[21-22]。在司法实践中,亦存在判决认为“转通知”可以成为适格的必要措施⑫。但笔者认为,在《民法典》实施背景下,“转通知”业已成为一项独立的程序性法定义务,其仅属网络服务商责任豁免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值得肯定的是,阿里云案的判决思路成为今后新型网络服务商所应履行注意义务并采取必要措施的典型范式。必要措施之“必要性”,即比例原则在通知删除规则中的嵌入,法官应当对被侵害权利类型、网络服务商的技术能力、技术可操作性等方面进行综合酌定,以适应网络服务的多样化、新型化发展。
(三)注意义务的现代化发展及替代责任的引入
需要明确的是,DMCA⑬及我国制定法⑭层面均免除了网络服务商事前版权审查义务。该立法精神体现了对网络服务商技术能力、治理成本、效率性及经济性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理应予以肯定。但技术进步及新业态的商业模式给传统平台版权治理机制带来挑战。版权侵权赔偿制度的不完善及版权刑事责任门槛较高等因素均导致法律对版权侵权问题吓阻力度不足[22]。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为解决前述问题,会结合其他替代性责任规则以修正网络服务商注意义务过低的现状⑮。
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网络服务商预防侵权的能力也在逐步加强。在实践中,腾讯公司的“视频基因比对技术”、百度公司的“DNA反盗版文档识别系统”、YouTube网站的“Content ID技术”等均使网络服务商承担部分版权审查义务成为可能。对于热播电影(电视剧)、经典歌曲、知名小说等具有较高流量的内容作品,网络服务商应当建立版权基因数据库,当网络用户在其平台上传之前,其应当进行部分事前审查工作,以防止未获得合法授权的作品在其平台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十条及第十二条也均对热播内容作品的版权保护义务予以特别规制。因此,事前承担部分版权审查义务可以成为网络服务商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且主观不存在过错的有效抗辩。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般性内容作品仍应免除网络服务商的事前审查义务,辅之以替代责任的引入以提高其应尽的注意义务。风险分担理论是替代责任的正当性基石,是一种比帮助侵权更为严格的责任规则[23]。在域外法实践中,该规则在DMCA相关条款③中有所体现,并经Napster案⑪、Viacom诉YouTube案⑯等经典判例得以修正并逐步完善。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十一条亦体现了替代责任的制度精神,该条强调了获取经济利益与网络服务商注意义务提高之间的伴随关系。在互联网服务呈现新业态的今日,网络用户的内容上传行为与网络服务商往往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所以,替代责任在我国版权法领域的引入成为规范互联网版权治理的应然路径。该问题在美国2020年召开的DMCA现代化听证会中备受关注,我国有学者在此背景下认为,平台商在收到侵权通知后不仅应承担定位清除的义务,尚需屏蔽侵权内容的再次上传[12]。因此,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重视通知屏蔽规则对替代责任的促成关系,充分发挥司法对新型网络服务平台良性治理的能动性。
制度既是博弈规则,亦是博弈均衡[24]。任何一项法律制度仅在使各方利益达到优化平衡状态时,才能成为一种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则。技术中立作为版权立法及司法所必须遵循的宏观性原则,是一种平衡技术发展与版权保护的长效机制。但应当避免的是披上技术中立外衣的侵权之实。法律不应单纯地对技术本身作出价值评价,而应将规制的立足点放置于侵权行为的判断。通知删除规则作为明晰网络服务商间接侵权责任的制度工具,应当伴随技术的发展充分焕发其内在生命力,为新型网络服务版权治理提供制度前提。
注释:
①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18)浙0192民初7184号民事判决书。
②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终1194号民事判决书。
③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 (2020)京0491民初31238号民事判决书。
④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民终3267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6882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23588号民事判决书等。
⑤参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民终2830号民事判决书。
⑥See Sony Corporation of America.Universal City Studios.Inc,.et al.464 U.S.417,1984:586.
⑦See RECORDS A M,Inc.V.Napster,Inc.239F,3d 1004(9th Cir.2001).
⑧See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Inc.V.Grokster,Ltd.F.3d 1154(9th Cir.2004).
⑨See Peter S.Menell&David Nimmer,Unwinding Sony,UC Berkeley Public Law Research Paper,No.930728.Date Posted:September19,2006.
⑩See Jane C.Ginsburg,Separating the Sony Sheep from the Grokster Goats:Reckoning the Future Business Plans of Copyright Dependent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50 Ariz.L.Rev,(2008):577-602.
⑪See Gershwin Publishing Corp.v.Columbia Artists Management,Inc.,443 F.2d 1159,1162(2d Cir.1971).
⑫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第83号指导案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知终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该案法院认为,将有效的投诉通知材料转达被投诉人并通知被投诉人申辩当属天猫公司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之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终1194号民事判决书,该案法院认为,在不适合直接采取删除措施的情况下,转通知体现了网络服务提供者“警示”侵权人的意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损害后果扩大,可以成为“必要措施”从而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达到免责条件。
⑬See DMCAξ512(m)(1),The US.Senafe Report No.105-190,at 44(1998).
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第八条第二款: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主动进行审查的,人民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具有过错。
⑮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18671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百度公司作为网络服务商,其注意义务并非仅限于删除链接等定位清除措施,还包括主动采取技术措施屏蔽关键词等。
⑯Viacom Intern.,Inc.v.YouTube,Inc.,676 F.3d 19,38(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