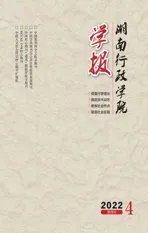论梁鸿“梁庄系列”作品中仪式的消解
2022-03-25颜光洁
颜光洁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仪式作为一种储存社会历史和记忆的抽象行为,以其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它的一系列展演过程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向。因为这种仪式展演在宗法色彩浓厚的乡村具有重要的规约性,是乡村人民重要的精神信仰,也是他们重要的精神归宿。但随着乡土中国的变迁,一些具有重要仪式性的行为逐渐淡化乃至消退,带有角色演绎和功能对接等重要职能的乡土仪式正逐渐被机械文明取代。
2021年1月,梁鸿出版了《梁庄十年》,在此之前,梁鸿分别于2010年和2013年出版了小说《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三部小说共同构成了梁鸿笔下的“梁庄系列”作品,为了解中国乡村的多元发展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在学界较多关注其作品中乡村发展前景时,其间隐现的人性书写不可忽视,仪式作为乡村赖以发展的重要行为,它的消解与乡村人民的精神图景变异密不可分。因此对“梁庄系列”作品仪式消解的分析能管窥乡村人民精神生态的发展,关注乡村文化的衰退和消亡,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向性。
一、仪式的解构:传统习俗的消解
当代中国的乡村正处于现代化浪潮的不断冲刷中,数千年时间形成的村落景观正在现代化潮水的洗涤中失去其原有的面貌。无论是贾平凹笔下的商州世界还是阎海军笔下的崖边村抑或是梁鸿视角下的梁庄,它们都在作家的叙述下反映出时代影响下乡村内部的变迁。而仪式作为一种民族志的存在,不仅具有储存乡村古老文化的载体功能,更是一个地区社会文化的缩影,以其独有的系统构造凝聚乡魂。但随着梁庄居民逐步走向城市,老龄化和幼龄化笼罩下的梁庄逐步失去原有的生命力,仪式作为当地重要的民间活动正在经历被简化、消弭直至意义弥散等一系列的解构过程。
仪式最重要的不是浅层次的信息交流,而是通过仪式的展演营造出一种娱神或通灵氛围,以其具有神秘色彩的行为构筑一个精神交流的场域,从而达到乡村仪式行为的目的。以姓氏和血缘为重要依据的梁庄自然是有其独特的宗族文化,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具有宗法文化色彩的婚姻、丧葬、娱神等乡土仪式。但随着梁鸿的多次返乡,以一个“归来者”身份重新审视乡土时,其间仪式的简化问题浮出水面,在梁庄系列作品中多次出现仪式的简化现象,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捕捉可以管窥现代化的高效率气息在乡村的隐现。
仪式在乡村地区既是一种传统文化也是一种乡村集体记忆,是世代流传下来具有积淀与传承功能的乡村志。丧葬、嫁娶等活动是一个地区重要的仪式展演活动,它象征着一个村落的迎来送往,但在梁庄地区,这些仪式正在被逐渐消解,丧葬习俗的简化便是较为具象化的一个代表。丧葬作为梁庄最具本土意味的仪式,是当地较为重要的一种宗族文化实践,无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民,还是外出务工秉持着叶落归根思想的梁庄人,都想在村庄买块地,盖个房子,能在作古之后有个安置棺材的地方,为自己谋个好的归宿。但在梁庄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出,当地已经有好几个将棺木安置在野外的例子,村里房子闲置腐朽后,只能将灵堂设在野外,而丧葬仪式的过程更是一减再减。如梁家贤生的葬礼“没有报小庙大庙,没有身穿麻衣白布的孝子和亲属,凄凉得很”[1],连酒席也是在德义家办的,而死于清立手下的虎子甚至连骨灰都无处存放。丧葬仪式中更多涉及功能性表演的部分被削减,那些蕴含亲属关系的环节也逐渐省去,仪式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环节正渐渐淡出视线。
仪式的消弭也是乡土中国较典型的一个现象,相较于上述丧葬等仪式的简化,另外一些积淀期较短,民间色彩不那么浓烈,且脱离了特定语境的仪式则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的命运。仪式在乡村能够提供借鉴与交流的场所,具有集体性和公开性,在这样一种客观条件下,仪式内部的沟通则显得合理合法。但随着乡村人口的减少和传统村落聚集的变化,仪式的消弭现象也成了梁庄系列作品中的要素之一。无独有偶,阎海军也在其《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中提到“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庄围绕人的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所固有的仪式正在逐渐被湮灭。由于外出打工,崖边从2000年到2014年,只举办过五场婚礼”。[2]作为一种社会认识性装置的仪式行为正携光阴远去,那些刻在民族基因里的特质终于在乡村内部结构瓦解后消失殆尽。
梁庄不仅外部村落形式发生了变化,内在的文化结构也濒临坍塌,仪式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是以人的现实生活和经验为基础的,因此仪式的简化也是在现实生活与经验中呈现的。作为一个族群或者说社群,梁庄的独特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聚居,梁姓在当地为大姓,邻居多少都是有点血缘关系的存在,所以“端饭”则是当地重要的一个年节仪式。因为以姓氏为依据的房屋群落已成废墟,而以此为依据的“端饭”习俗也自然难以重现。“大年初一的时候,每家都会做一锅大烩菜,依照辈分的高低,依次相互交换,最后每一家锅里都是一整个姓氏的饭。然后大年第一天的早饭才开始吃”[3]40这一仪式的目的主要是为家族内部提供一个可供交流的场域,暗示同一家族的人彼此团结,平时有恩怨难解的族人也可借此机会缓和矛盾。但现在这一仪式已经消失,其间隐现的社会事实是宗族血缘的凝聚力已不如从前,以利益为中心的乡村集团正在形成。虽然这些与社会机制相连的文化传统起着伦理规约、交流沟通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乡村人民娱乐设施的多样以及沟通渠道的便利,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交流色彩的仪式逐渐被淡化。
而这种仪式的消解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乡村人口的流失导致的人口结构失衡,从《出梁庄记》便可看出,乡村的青壮力为了谋求经济的发展,大多流向北京、青岛、内蒙古、广州等地,留下的多是妇女、小孩和老年人,而多数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仪式展演又离不开青壮年的支持,因此,不和谐的人口结构直接决定了很多仪式展演的困难;另一方面则是生活场域的变化,即乡村聚居形态的变迁,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乡村部落聚居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为中心的乡村建筑风貌,新的生活场取代了以往的种族聚居,乡村新贵们多选取优秀宅基地建房,原有居住模式被打破。因此,在这样一种乡村生存景态下,一些仪式不可避免地会主动或被迫消失,这也是乡村发展中必然经历的精神阵痛,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正逐步更新。
二、仪式的变迁:乡村信仰的变动
信仰与仪式作为文化结构的两翼与传统乡村的发展相辅相成,而宗教文化影响下的仪式更多与信仰相连,两相碰撞下,乡村仪式出现了与宗教信仰融合的趋势。宗教与仪式关系的讨论众说纷纭,但把仪式置于宗教内部进行分析的做法是神话仪式学派的基本观点,有关仪式的定义也阐述了二者关系:“通常与宗教或巫术有关、按传统所定的顺序而进行的一整套或一系列的活动。”[4]因此,从广义上说,仪式与宗教是相互包含的关系。从乡村发展的新面貌来看,宗教的仪式行为渐渐成了乡村中的新景观,传统文化中的仪式行为让位于宗教活动,而这种宗教仪式的内涵却发生了新变,一路向上的“善”不再是其核心,更多的是一种符号化行为,无关善恶,宣泄感情和纾解困乏的精神意义遭到消解,仪式和信仰的崇高性消失。
首先是外来宗教的传入致使精神信仰发生改变,乡村人民以往遵循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基本道德准则,村庄内部有自己的运转机制,这种朴素的道德观会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准则横卧在村民心里,鲜有人逾矩,因此村庄内民风淳朴,邻里和睦。但是,随着基督教等的传入,乡村新兴宗教的受众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以往蒙昧的老人向年轻群体扩散,传统的文化信仰与仪式则在无形中受到冲击。不仅乡土人民在走向都市,城市文化也在反向注入乡土,这种对外来宗教的朝圣不只是作为特例在梁庄盛行,而是嵌入到了中国的大部分乡土,如孙惠芬《生死十日谈》中调查访问的翁古城,作为一个小县城,其北大河边上赫然竖起了一座大教堂,为那些经历了自杀事件的受访者们在教堂里提供精神的栖息之地。梁庄亦是如此,如灵兰大奶奶们对宗教的疯狂追逐令人咂舌,她们甚至为了宗教事务放弃家庭,但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只是精神层面的疯狂。
其次是传统仪式行为的移位,一些具有民族志色彩的仪式被迫让位于宗教的朝圣,那些凝聚着民族生命色彩的仪式在宗教的影响下斑驳褪色,“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民间信仰与外来宗教被置放在同一空间内,我们可以此说明乡土文明是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与原生信仰剥离的。”[5]当这种原生信仰从乡土中被剥离时,原有的仪式内涵便被迫让位于新生的宗教。在梁庄地区,基督教是当地较有名望的宗教,自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一大批信徒,他们倡导信奉主,以今世的赎罪换来世的幸福。而履行宗教义务成了他们信任宗教的唯一路径,以往的出生、丧葬等仪式变成了基督教的洗礼和唱诗,每周的礼拜和朝圣占据了他们生活的空隙,原有的仪式行为被宗教的礼拜所切割,对教会的绝对信仰是他们公认的虔诚。
以往梁庄的红白喜事兼具放电影、唱戏等多种活动,作为全村人公开活动的事件,红白喜事的仪式是重中之重,死亡与新生的气氛笼罩着乡村,和谐与安宁是乡村的基本基调。但随着基督教等在乡村的盛行,传统仪式让位于基督教的礼拜以及灵魂安抚,一些信教人员的丧葬仪式让位于基督教的礼仪,乡村原有仪式的“生态型”平衡被打破。“通过民间信仰所反映的‘社会空间’,实际上‘全息’地反映了多重迭合的动态的社会演变的‘时间进程’。”[6]当民间信仰发生转变时,这种地缘性较强的仪式便会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而隐退,其背后的现实指向性也渐渐显现,即乡村生活空间的被迫压缩不仅表现在生活方式的变化,更显现于精神图景的异动。
最后是精神信仰的极端化。仪式作为宗教行为的重要载体承担着趋利避害的美好愿景,仪式的展演是为了娱神和安抚自我,但在梁庄系列作品中,我们敏锐地发现,宗教仪式逐渐呈现极端化和异化,向上的“善”被“利”驱逐,宗教的仪式行为只是“走过场”,流于表面。信仰理应是非功利的,如果带着某种利益的色彩信仰宗教则会本末倒置,要求付出与收获强行平等,或者迷失自我,都会导致这种仪式行为的异化和极端化。
遮蔽“自我”的信仰是有失偏颇的,以灵兰大奶奶为首的梁庄女性大多信仰基督教,她们或许并不能完全理解自己所信的宗教,对于《圣经》一类的文字读本更是一窍不通,每每问起总是啼笑皆非,但她们执迷于基督教的原因大多相似——能在教会里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作为梁庄里“芝麻粒儿大的命”,她们的存在一直为男性所忽视,甚至大多数人都不曾记得自己原有的姓名,只是“某某家”的一员。“但她们在其中找到了一种尊严、平等和被尊重的感觉,找到一种拯救别人的动力和自我的精神支撑,这是她们在生活中从来没有得到过的。”[3]234在宗教会所里,她们摆脱了传统身份对她们的束缚,不再只是某某家的一员,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这种心灵上的身份承认和被肯定满足了她们的需求,对宗教的信仰则会更甚。
然而正是因为她们与外界的交流过少,所以并不能掌握信仰的本质,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践行教义,比如疯狂地印传单、发传单,常年不着家,大量参加教会活动来证明自己对主的忠诚,过分讲究形式化。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一种自我安慰,并且具有一定的功利色彩,相信信主能发财,实际上是将自己向善的心给蒙蔽了,如文本中一个血的教训:一个老太太急着赶去参加教会,看见坑里漂着两个孩子却没有吭声,并且没有采取任何施救行为,等她回来发现,坑塘里溺毙的是她的两个外孙。还有一个令人唏嘘的事件是“明太爷救人”:“前几年有个妇女掉到水里,我跳进去把她救了,她不说感谢我,她说感谢主。日他妈,咱是清想不通。”[3]222宗教信仰的初衷是劝人向善,仁爱世人,但老太太却选择了参加形式主义过盛的教会活动而放弃了两条挣扎中的生命,这无疑是对宗教信仰的亵渎。将现实生活中的被拯救归功于神祗更是一种虚妄无知的表现,当生活与宗教本末倒置时,“自我”的本体则容易被遮蔽,信仰便出现了极端与变异的现象,善意被驱逐。
三、仪式意义的消散:光芒的暗淡
乡土中国的仪式具有传承性,与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传承出现断代时,仪式则有可能被中止或者出现变异即仪式的展演随时事而变。“长期以来,仪式一直被人类学家当作观察人类情绪、情感以及经验意义的工具,成为民族志研究中阅读和诠释社会的一种不可多得的‘文本’;比起日常生活中的‘秘而不宣’‘未充分言明’以及缄默的意义而言,仪式是较为集体性和公开性的‘陈说’,具有经验的直观性。”[7]而随着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仪式的展演也逐渐趋向现代化,而仪式所蕴含的神圣性却在现代化的步履中递减,那些原有的精神愿景正被人淡忘,仪式的神性光芒趋向暗淡。
这种仪式意义的消散一方面表现为仪式展演的现代化,仪式展演与当地的文化结构是有内在关联的,随着都市生活衍生品逐渐流入乡村,乡村的生活面貌也焕然一新,与之相关联的仪式展演也呈现出现代化面孔。仪式展演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仪式活动中所用工具的现代化、仪式展演时受意识形态影响过程的现代化,因此,在村落政治组织和抚育社群等的几方平衡下,在保证仪式的基本形态下,乡村的仪式展演的意义大多归于虚无。然而,现代化科技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传统的野性思想为前提,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所说:“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两种平行发展,互相制约又互相渗透的两种思维方式。因此指出人类社会是比照着两种思维方式进行的,如同自然界的‘野生’和‘园植’一样,思维方式也有‘野性’和‘文明’之分,而这两种方式是相互并存的。”[8]
仪式内部的横向性价值是强调仪式参加者或者整个仪式在特定社会中的平等,仪式展演的过程尽可能与原有的形式相差无几,维持动态性的平衡,宗族性的乡村更是如此。但以梁庄为例则可看出这种仪式展演的变异。丧葬是当地最重要的仪式展演活动,以往的报小庙大庙、孝子送行等活动被火化和汽车取代,传统的平等被打破,更讲究排场和面子,“现在农村兴这样,火化也讲排场,有钱人家还开一长溜小汽车,把亲戚们都拉去。回来再埋,再请吃饭。等于是花两回钱,费两回事。”[3]237以往是请一位在当地富有名望的通灵者进行整个丧葬活动的规划,包括哭丧、送行、孝子叩拜等一整套仪式,整个过程不涉及金钱上的影响,村里人不论远近亲疏一律给予帮助,且大家送葬的形式都是沿袭传统,没有特别突兀的方式。经济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交通工具等的更新,但丧葬仪式上的物品逐渐被现代化的商品取代,用小汽车鸣笛取代唢呐弹唱这样的方式则是将仪式中的平等彻底打破,致使乡村仪式的展演趋向异常化,这种讲排场拼面子的方式与传统仪式的初衷背道而驰。
“火化”代替“土葬”是在国家引导下的必然之举,出于生态问题的考量,火化更环保,但梁庄人民却在和这一政策的博弈下,使丧葬仪式出现了各种吊诡现象。政策的引导和入土为安思想在当地互相纠缠,金钱便成了其间最好的调节剂,交了钱即可在默许下偷偷埋掉,民间信仰和仪式被用作牟利的手段,传统的仪式和信仰被经济利益消弭,出现图解信仰的行为,并且这种僵化吊诡的状态带来的只能是形式的皈依。出于对逝者的尊重,梁庄村民将火化后的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里,指甲放在四肢旁,权当作一个完全人以表心意,但一抬便散了架,最后竟演变出钩坟、烧坟等恶劣事件,缺少对逝者的尊重和虔恪,是对民族心理的一种践踏,乡土社会中的仪式与信仰逐渐步向落日的余晖。
另一方面,仪式之所以具有民族志意味就是因为其展演的神圣性,是为了能获得一种精神的疗愈,但随着前文所述仪式的中断、异化以至消失,仪式内部所蕴含的神圣性也在与日消减。仪式在其创设的情景中会营造出一种神秘色彩给人以心灵暗示,让一些精神或者心理有障碍的人,通过这种仪式信仰来达到心灵慰藉的目的,同时以其公开性为民众提供纾解困乏的渠道。
祭祖是乡村里常见的仪式行为,清明节作为法定节日也是国家对这一传统的宣扬与继承,常见的是由一家之主带领全家人扫墓祭祀亲人,将自己对已故亲人的思念娓娓道来,同时也是一家团聚的好时机。如在作者母亲的墓前,有哥哥黑夜躺在那里倾诉时的孤独身影,有父亲手术成功时几个姐姐专门前去汇报的喜悦面孔,在作者的认知里,唯有这样才能算真正的隆重,母亲亦还是家庭“隐形”的一员。这种传统吊唁方式带来的心理慰藉是纯然的,当一家人聚在一起采取最古老的凭吊方式纪念时,乡村美好自然的一面跃然纸上。然而随着土葬的消失,以及乡村人民大多寓居外地,对乡土的牵挂也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凭吊方式渐渐趋向形式化,只是赶时间似的临时祭拜,尤其是隔代以上的血亲,相处时间的不足也决定了这种情感的淡然,传统意义上的祭祖已烟消云散。无独有偶,阎海军也曾发出过类似的疑问:“我们会是最后一代祭祖的人吗?”祭祖仪式的神圣性消失,读者从中获得的仪式感受也明显不足。“仪式是人类初年创造的一种精神性文化形态,它是由传统习惯发展而来,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并按某种规定程序进行的行为方式。”[9]当这种文化形态不再被新一代的乡村人民接受时,仪式神圣性的蒙尘则是题中应有之义。
“新乡土中国”的发展呈现出断裂现状,仪式的载体濒临短缺,随之而来的仪式感减弱则不可避免。乡村人口结构的不合理,乡土文明的多样化景观正在走向单一,如何在保持乡土文化自信的基础上重建民族文化是目前反思的重中之重。
四、结语
作为一个乡土中国的返乡者,书斋生活的经验和现实乡村生活的体验都有助于梁鸿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她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在身体和精神双重返乡的前提下,深入开掘乡村人民的精神图景,感慨城市对乡村生存空间的挤压。而仪式展演作为乡村重要的民俗活动,承载着重要的民族志意义,当这一神圣性活动逐渐淡出乡村发展版图时,乡土文明也隐现出了落日余晖。梁鸿的返乡还在继续,她对乡村的未来走向问题依然密切关注,梁庄只是整个“新乡土中国”的缩影,以梁庄为聚焦点,可以见微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