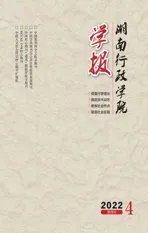当代乡村书写伦理困境下韩少功的乡村诗学的建构
2022-03-25廖小婵
廖小婵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乡村”是乡土中国现代进程中最广大的现实,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各种现代话语和文学书写中的巨型“他者”[1]。韩少功曾说,“这个时代变化太快,无法减速和刹车的经济狂潮正铲除一切旧物[2]”,而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文学的“根”应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韩少功对乡村文化的体悟,始于上山下乡的插队岁月。不管是《马桥词典》中对当地插队生涯体验的描述,还是《山南水北》中对山野自然和底层民间深刻的体察,还是在《长岭记》中充当“义务守夜人”与知青岁月的深情回望,韩少功都在重新厘清文学与乡村的关系,将乡村传统和现代文明、汉语和方言碰撞在一起,将“问题中国”转向了“理解中国”[1]。
尽管乡村书写都喜欢从作者和他者世界的接触讲起,但似乎再也没有发生像鲁迅《祝福》中“我”遭遇祥林嫂那样的“事件”。今天,农村的面貌和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但“祥林嫂”事件持续散发着意义。而这一偶遇被韩少功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主题和当代的日常现实来处理。乡土小说的展开始于作者对破碎瓦片般日记的清理、拼接、修补,就像一个义务守夜人守护遍地月光一般[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原则,对于今日在世界范围、历史长河中重新定位乡土中国、治理乡村生态环境、重塑乡村诗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
一、当代乡村书写的伦理困境
在以城市为主导的语境下,乡下人在城里人眼里是“愚”的: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也不是,司机向着那土老头,啐了一口:“笨蛋!”[4]10随着近代乡村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无法无视科技对传统人文生态(人情伦理)的消解与解构,以及对新的人文生态(物化伦理)的建构。乡村生态思想研究已成为“显学”,有对乡村生态危机和文化根源的反思,也有对乡村生态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探寻。21世纪以来,乡村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向人们提出从乡村出发去理解中国的重大课题。
(一)乡村发展下的认知错位
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正在产生着对于环境的压力并威胁着地球支持的生命的能力[5],正是资本控制下对乡村资源的疯狂开发与挥霍,导致了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错位,使得乡村书写失去了以往的活力和力量。
首先,乡村书写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就是发展书写的困境,即无法把握当下,无法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塑造出站得住脚跟的新型农民形象。乡村书写自诞生以来就与发展书写结缘,有时描绘的是乡村过去与现在的变化,有时呈现的是乡村主人公依靠自身、依靠自然所产生的价值和满足感,有时又是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使得乡村书写不再处于边缘地位。但当今乡村书写中引领一时的“朱老忠”“梁生宝”“江姐”“杨子荣”新农民英雄人物普遍消失,很多作品都以乡村的破坏和消逝为结局,乡村发展中环境破坏、资源消耗等弊端都显露出来:如莫言《四十一炮》中农村改革的冲突和裂变,格非《望春风》中江南乡村的演变,阿来笔下《机村史诗》中藏族村庄的发展流变。乡村发展的尽头似乎就是被现代文明所泯没。
其次,新的乡村现实问题越来越多,乡村变化也不断被记录和解释,但它无法被我们的认知所消化,所以一种无力感、衰落感就会蔓延开来。阅读当下的乡土小说会发现,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并未被有效地记载,或是所记载的都是读者所已知的。这样已知的作品并不像《活着》《平凡的世界》那样令人心潮澎湃,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乡村书写的整体现状。格非针对这一质疑发声,“有的读者批评我对当代乡村生活的问题没有提供多少借鉴的意义……我再次强调,描写当代的乡村社会的空间不是我的任务,也不是我要做的,我没法在小说里和读者讲它到底是怎么回事[6]”。这些质疑都说明作家没有做好面对乡土的变化的准备,进而导致作品直面历史和日常现实问题力度的削弱。当代乡土社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代,但它为何发展,何以发展都已经远远超过人们的经验范畴,那些涉及到乡村发展的本质根本无法在历史长河中找到原因。
列夫·托尔斯泰曾言,“(作家的责任)是经常地、永远地处于不安和激动之中,因为他能够解决与说明的一切,应该是给人们带来幸福,使人们脱离苦难,予人们以安慰的东西”[7]。乡村书写者应走出自身局限,扩大视野和题材范围,重新建构和定位中国乡村,处理好文学与乡村的关系。
(二)城乡解构下的人性物化
近年乡土中国城乡二元化的格局正被城镇化进程所打破。正如马克思所言,“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8]。在乡村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错误在于对大自然采取了对立乃至敌视的态度,破坏了人与乡村的生态关系、人与人的生态关系等等。其中,最为鲜明的表征是环境异化下的物质生命化、人的生命物质化。
第一,近现代以来,在西方先进城市文明的肆意渲染下,在中国反封建的大旗下,中国古代传统乡村文化不断被解读为“无知、落后、闭塞”的文化形态;农民被描述为自卑、落后文化的代表,并成为国民性改造的主要对象。费孝通提出, 乡村社会的生活形式表现为以伦理为标准和依据的“差序格局”[4]29。大量农村人口的迁徙和流动而出现的村庄空心化现象,不仅导致大批乡村文化精英纷纷远离家乡,也造成以乡村文化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空洞文化世界里的人们如何处理肉体和灵魂的分裂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当今的中国乡村社会正在由以年长者为主导的前喻文化迅速向以年轻人为主导的后喻文化过渡,年长者在乡村文化秩序中已被迅速边缘化[9]。而人性中的真、善、美又驱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自身身体与灵魂的分裂,其结果是促使人们陷入更加痛苦的精神境遇。
第二,当乡村不再是过去的样子,乡村发展也不再采用过去的方式时,作者对乡村发展经验的理解以及赋予这些经验重要性的方式遭遇了失效,这导致了发展写作的“伦理俘获”效应[10]。一直以来乡土小说除了要写出乡村的发展变化,更要强调人的主体性和力量感,乡村发展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和我们自身的力量,这似乎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十七年文学中,赵树理、柳青、罗广斌、杨益言、浩然等人的小说都充满了对劳动的赞美,对新型农民的赞美。但在1990年以后,单纯依靠劳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社会整合的任务从道德转移到了市场[10]。如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君子梦》《缱绻与决绝》《青烟或白雾》反映的是山东村庄的农民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展现了作家对新型乡村的不理解和不认可。所以村庄不再是被文学化的乡土空间,而是政策整合下政治话语的代表。于是,乡土作家一边适应乡村发展的话语,一边又对发展不满和批判,那么一种割裂感就会蔓延开来。
总之,中国乡村小说的叙事存在两个困境:一是在认知层面上,乡土小说作家并没有消化和理解新的乡土经验,对乡村地域性的理解存在严重的误区;二是在人的物化上,乡村重构书写似乎只能进行道德、怀旧以及伦理层面的补救,而非直面历史和当下现实。这种双重困境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书写的成就和发展[11]。
二、乡村书写者韩少功如何建构乡村诗学
乡村城镇化、现代化浪潮下,人们对于乡土小说的消极态度日益加深,很大程度是源于作者无法把握和认可当代乡村的时代变化,是对乡村发展本质把握得不自信。那该如何书写好乡村,新型乡村文化又该从哪里入手?
第一,寻找后乡村时代写作的路径,知识体系的更新是必要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乡土书写作家的创作理念在很多时候依赖于国家政策、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引。在资源匮乏的时代,生产和发展是硬道理;而到了今天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得人民群众对“软需求”的渴望日益加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是要求我们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当代乡村中国的面貌越来越多元化,旅游村、示范村、新型社区等层出不穷,于乡村而言是一种幸运,说明国家有意识地去反哺乡村;而对乡村书写者而言是困境,代表着“乡村”意义的解构、方向指引的缺失。但韩少功敢于正视当下的后乡村现实,其作品中有大量巫楚文化的方言俚语和风俗民情。如《长岭记》中写到当地口头禅是“鬼”“鬼咧!”或者是“好大一只鬼”;有关“世上有没有鬼”的争论,他们认为“火焰高”的人就看不到鬼,年轻的、读书的、城里来的人就是“火焰高”的人;在当地也流传着一个传说,五神庙中的五位神主与敌军大战,打退了日本人、美国人,保佑着世世代代村民的安全;在方言中称碘酒为“碘酊”,红药水为“红汞”,肥皂为“碱”,打死你、弄死你为“武死你”。同样,《爸爸爸》中也提及了一些落后却有趣的习俗,如骂人的时候在胯里摸一下,这样能增强语言的毒辣性;迷路的时候,要赶紧撒尿骂娘,据说这样岔路鬼就不会近身等等。于是韩少功用“武”“坨坨”“逞骜”“擂”等古老的具有湖湘特色的方言,“三根香结拜”“蚂蟥听水响”等风俗文化为乡村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更为重要的是,作家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传统巫楚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端,惟其如此,才能重新认识乡村的现代化发展。如关于“打裹包”的描述,家家户户带一张草纸或者一片荷叶来吃酒席,没吃完的就连汤带料打包回去。这一特别的农村习俗让人发笑又觉得无奈,“这哪是吃酒席,差不多是分猪潲吧……不无心酸:可怜天下慈母心![3]”70年代队里有收化肥(人粪)的习俗,化肥要按质按等级计算,所以常出现“前几天吹牛说他家条件好,长期是吃茶油、猪肉和面条的,后几天等队里收化肥的时候,就又换一套说辞”令人哭笑不得的场景。这些古老的、具有时代特性的农村习俗在现代乡村书写中显得滑稽可笑、无所适从。因此,在更为复杂的新型乡村框架中,需要更为宽泛的视角、敏锐察觉变化的能力,和直面新的现实景观的勇气。
第二,当代乡村书写并不缺乏关注现实的勇气,但缺少将这种关注提炼为本质的敏锐度和厚重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以人民为中心”为发展思想,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影响下,作家韩少功除了有精英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更有站在底层农民立场上的民间关怀、接纳和理解,以及面临乡村中国各种不适的审视和思考。作为汨罗长岭文化的“闯入者”,他用过滤的现代眼光发现了这片土地的落后和闭锁,同时也发现了这块土地上地方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如在作品中民众对待政治运动的态度是不满的,甚至本应自由的婚恋都逃不开以利益为驱动的“例行公事”:团支书李简书和戴铁香的恋爱关系,因为戴家的政治成分问题而困难重重;新来的公社书记“铁姑娘”本来是组织重点考察和培养的对象,但因为她爱抹雪花膏、烫刘海,展现出与传统“铁姑娘”截然不同的一面,导致前程阻力重重。作家正是通过年轻人的婚恋,将政治话语反驳消解,从日常、现实、人性多维度审视严肃的政治运动。虽然人们现实生活艰难,但闪耀的同样是干部、民众的人性光辉:桃林公社的书记“曹明天”捉到贼,反而担心起贼的生活起居,“我是你的书记,搞得你没有饭吃,是我的错[3]”;自己的煤要留给刘爹爹、四婆婆,还要多贴一点钱。面对人性的裂缝,韩少功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感,更多是从民间的视角平等地看待底层人民的艰难生存和落后思想。
第三,回归作家本位,同样也是必要的。当代乡村书写者大多属于乡愁派,但在书写过程中经常存在越位现象,即一边以理性主义自居,一边怀念逝去的乡村;一边认同乡村的变化发展,一边又不满发展过程中乡村的破坏。在情感上同情和亲切底层农民,希望平等对待不同群体;但又因为启蒙者的文化优越感作祟,无法用平等的姿态去保留和记载当地农民原始的生命活力。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新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乡土书写者韩少功尝试回归自己作家的角色和本分,不仅有对历史和日常现实的关注,同时也有知识分子理性的决绝、洞穿现实的能力,平静关注乡村命运的作家书写责任。韩少功的精神原乡是楚文化源远流长的湖南汨罗,游离于正统文化之外的方言土语、民俗风情在书写中营造了极具湖湘风味的美学效果。其中既有抛秧把田里的泥浆砸出一个个笑声和骂声的场景,也有育杉秧、捉肉虫和甲虫、捉鳝鱼、放鸭、赛龙舟等农村劳作娱乐场景的描写。另外,农民朴素的生死观——“木匠、砌匠、剃匠、篾匠死不得,不然大家不方便,好人也应该有点寿”,也被韩少功敏锐地察觉到,并把此提炼到生存哲学的高度——农民把一粒种子撒进土里,结出果实;把自己丢在地里,长出坟墓。而当作家面对当地落后的“牛顿是女的”“地球不是圆的”“婚闹”“打裹包”的思想和习俗时,放低精英知识分子傲慢的姿态是关键,平等地记载着这些令人发笑但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画面。若当代乡村书写不再流于表层乡愁情绪的宣泄,其实于乡土而言也是一次成功的回归,也能从乡村日常中发现充满人情和理性的中国。
三、新的乡村书写的文化出路
传统意义上的乡村逐渐走向“虚空化”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赵本夫《即将消失的村庄》直接以“即将消失”明示[12]传统乡村以及乡村民俗文化的时代结局。新世纪乡村书写的“新”,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且乡土中国的转型、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变化丰富了“新”的内涵。新时期如何理解乡村,已经成为理解中国、现实及世界最重要的视角之一。韩少功的《长岭记》聚焦于普通农民琐碎的日常生活,以新的历史眼光扫描和表现乡村农民的生存现实,重构地方文化和人文传统的认同。我们该如何为乡村找寻到曾经的意义和未来的出路?
首先,新世纪乡村书写的目的不是简单的历史复刻,而是基于新时代语境下探讨人与乡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真诚表现中国新农民的生活史、精神史和心灵史,以此重建对地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认同。韩少功的作品中既有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爸爸爸》的鸡公寨充满着国民劣根性的苍老遗传,丙崽是这个蒙昧社会的畸形产物;又有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处汲取力量的趋向,展现出被忽视的地方文化独有的活力:汨罗长岭大队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民风俚俗、观念情感从来都是一成不变的——打鼓打得是“凤点头”“狮子滚绣球”的花样,吃饭用的是剁辣椒或者干辣椒咽饭,叫小辈或同辈的昵称一般是一个字再缀一个“子”,把红薯叫作“肥”。这种仪式被社会和文化系统赋予一种特殊的规定性,也就是说许多仪式的功能是事先被规定的社会意义所预设[13]19。因为长岭人民所面对的是原始地方文化所规定的、参与者所认可的“神圣”,无论这种认可属于个人自愿还是带有集体强制性意味,迷信仪式的意义在形式之中和行为之前已经铸就和确定。对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来说,“文化记忆”主要以非文本的形式得以流传[14]。绝大多数的民族仪式属于某一个民族或族群历史传承的产物,即使是同一个民族或族群的人们也已经无法真正还其“原生形态”[13]5。在当今现代化语境下,我们要增强自身的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转身向乡村地域和历史叙事下汲取经验,努力找寻乡村人文传统的新鲜感,站在新的历史的结点讲好乡村中国的故事。而讲述乡村中国故事的主体,不只有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还有当地的乡村文化精英。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龙洞村创办的龙洞诗社,最初只是为了把爱诗歌的一群老人聚在一起,充实晚年生活,但慢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诗社。在龙洞,国事入诗,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设专栏传递正能量;村规民约也编成了诗,用吟诗作词这种传统又大众的方式,弘扬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农民诗社唱响了乡村文化之歌!
其次,“人民性”就是韩少功创作的活力。人们组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其根据在于他们以共同的或一致的思想方式看待神圣的世界以及与世俗世界的关系,在于他们把共同的观念化作共同的实践活动[13]74。很多乡土作家离生活很远了,但韩少功仍像候鸟一样飞回汨罗过起真正的乡村生活,主动去接近农民、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努力去填补新时代乡村生活的虚空。正如作家所言,“真正伟大的自我,无不富含人民的经验、情感、智慧、愿望以及血肉相联感同身受的‘大我’关切”[15]。因此,他在乡村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寻找湖湘巫楚文化魅力的同时,还能保持作家的本分,理性探索巫楚文化的荒谬怪诞,展现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例如,当时的乡村家长们根本无法理解“教育革命”的意义,对捡茶籽、扒松须、挖菜土极为反对,这导致学生辍学情况日益严重;哪怕是留在学校上课的学生,对新来的老师和课堂学习也全不在乎,睡午觉的时候也老是讲话和打闹。值得肯定的是,韩少功对底层人民的书写并没有从道德层面给予更多价值判断,而是尊重生活的质感,注重从生活的逻辑和民间的逻辑理解底层人的生存[16]。另外,作品重新复写了一些封闭落后环境中人的愚昧和乡村的迷信文明,散发出一种荒诞、神秘和魔幻的色彩:抢救一只误食农药的鸡,用剪刀剖开食袋洗一洗,再缝合起来,吹一口气,公鸡就活了;在农村不能打蛇,打死一条,明天会有十几条来报仇。作家对此是持理性警觉的态度,正如《爸爸爸》的结局,一个妇女走过来对另一个妇女说“这个装得潲水么”,于是把丙崽面前那半个坛子旋转的光流拿走了。韩少功对乡野巫楚文化的思考和批判,不仅增加了小说的历史感,也由此上升对人类生存样态的探讨[17]。
最后,农村类非虚构乡村写作依托的是“田野调查”类的工作方法,尽可能客观地记载乡村记忆,强调作者的在场。尊重差异、尊重他者,是文学和艺术的本性。因此,要给予乡村声音足够的话语空间和想象空间,呼唤一种新的乡村诗学——真正地探入事物深处和诗性思维,看到文化背后的生态、生活和灵魂。于是,当描写乡民面对城市文明涌入村落的心理时,作家用充满诗意的场景描写“天上星海,地上灯河,交相辉映[3]”,冲淡了乡民内心的局促不安。何为“诗学”,“诗”可以看作人类所有人文、社会活动的总和,而“学”指的是学科化。有人会疑惑将乡村写作学科化是否会造成其凝固化?其实不然,文学性是敞开与流动的,这种文学性、文化关怀的眼光有利于将人放在特定历史现实语境下的存在化和具体化,而这一切最终指向的是如何解答当代人的存在的困境。于是当代乡村写作所面临的,不仅是理性探索乡村地域人文传统的新鲜感,而且要求乡土书写者创造出新的乡村诗学和文化关怀。
因此,在新世纪中国乡村正发生剧烈的现代性变化之时,正如钱理群先生建议的“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和作家李洱所倡导的“重建小说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一方面需要作家进入乡村以感知的方式重新了解乡村生活;另一方面需要作家的智性参与,依托新农村生活的认知,重新找寻乡村书写的新可能。在今天以“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学与西方经验的一次自我身份的重新确定,是中国文学的一次自我觉醒与真正独立。
四、结语
中国乡村与乡土小说存在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当今乡村正面临着“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的社会转型,以“人情”为纽带的互助式乡村关系[18]的裂变,因此必然引发乡村书写的文学新变。而韩少功对“乡村诗学”意义的探寻,犹如一位虔诚的守夜人。他依托湖南汨罗的知青下乡经验所构建的乡村诗学,既是面对都市文明的个人选择[19],也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建构乡村生态乌托邦的勇敢尝试。他指向乡村书写这一命题,必然要承受绚丽楚文化没落的精神危机,甚至会存有王国维先生那样的“文化殉道主义”之感想。而作为乡土书写者,韩少功始终关注城乡的发展变化,既以农民的身份无声地抵抗乡村中国所面临的各种不适,又以作家的身份返回到湘楚文化的大地上,深度挖掘乡村楚文化背后的生态、生活和灵魂,发掘乡村与现代的双重陷阱,挖掘湖南楚文化的文脉结晶,将湖南人的历史沉思和精神归宿寄于山水又高于山水,旨在为乡村诗学提供一种新的书写方式。
在中国乡村转型的重要阶段,新的中国故事正在不断发生。因而,在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乡村书写要善于从社会转型和变革中汲取力量,社会的快速发展应当为乡土小说的发展注入更多的资源和能量,但如今乡土小说反而走入自我锁定的壁垒,这是重建一种新的乡村书写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