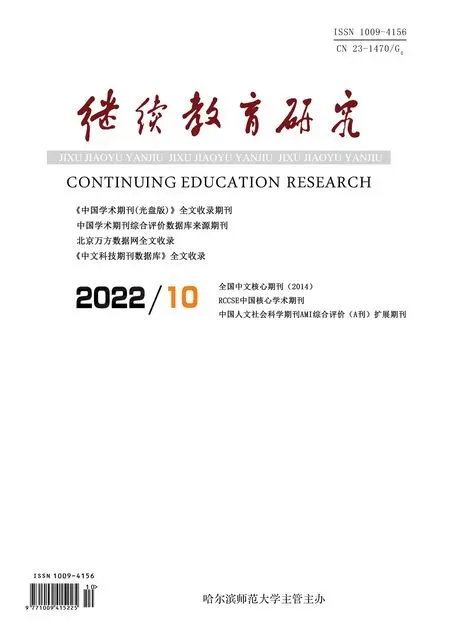“身教”与“身学”
——中日阳明学的教育启示
2022-03-24施敏洁
施敏洁
(浙江万里学院 外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一、引言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知行合一、做实干家”: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正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每一项事业,不论大小,都是靠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干出来的。新时代的中国教育就是要培养知行合一的实干家。
中国教育发展史延绵两千多年,要数儒家教育最为突出。自孔子作为第一位以教育立身的儒者开始,历代儒者都将教育作为自己的立身之基。因此,教育对儒家来说比创造思想学说更为根本,也只有从如何教育人的角度,才能更接近儒家思想之本真[1]。千百年来无数儒者身体力行的重要教育思想就是“言传身教”,它在人类教育史上独树一帜,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新时代教育事业中得到传承和发扬。
王阳明就是儒者中的佼佼者,他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和教育家。其事迹及所创学说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更是走出国门,在日本获得了特有的发展和运用。近年来,中日阳明学研究备受重视,围绕王阳明的生平及思想成就的研究,特别是从哲学视野开展阳明心学的研究最多,成果斐然,但从教育视域研究中日阳明学的偏少,已有成果中更侧重其德育价值,为培育我国公民道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理论支持,从教育主体——教师和学生的身体投入视角研究中日阳明学实践意义的并不多见。将主要从教师“身教”和师生共同实现“身学”这两个方面展开探索,以发现中日阳明学更多可借鉴的现实意义。
二、身体——教育的主体
何为教育?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上施下效为教,养子使作善为育。”所以,在教育中排在前面的是“上施下效”,教育的本质是以我们的生命唤醒别人的生命[2]。在学校教育中,可以说学生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熏陶出来的[3]。
在传统的现代教育思维中,往往更注重思维训练、心理研究,身体经常被主流研究排除在外,没能成为教育学的重要主题,也不是理论研究者的核心研究对象。直到20世纪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运动中,身体作为灵性化的肉体而受到特别关注,从而启示了身体在教学世界中的种种意义,显示了身体与教学关系的巨大价值[4]。教育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从获得知识到检验知识,再到运用知识,都需要亲身实践,才能学得深入,获得真知,造福人类。因此,教育必须重视身体的效用,让身体在场成为开展教学工作的前提。
身体是教育的主体。教学从身体出发但并不止于纯粹的肉体,教学活动的展开也不是纯粹的脑力活动,教师需要调动身体知情意行诸因素参与其中,学生需要身体的所有器官都参与学习探究,没有身体的参与,教学活动将流于空虚。身体在教学世界的行动是全面性的投入,是全身心的学习、理解、认同和转化的复合性过程。只有学生全身心投入地学习,才是真学,所领悟和体验的才是真知[5]。知识通过身体力行,感知环境于体验文化而得以发展,从而使我们开放心灵、感悟真理、启迪心智[4]。
从阳明学的教育思想看,王阳明基于“主行主义”的立场而提倡“知行合一”说,因此阳明学被世人称为“实践哲学”也不是毫无道理的[6]。阳明学注重身体的修行,强调实践的作用。身体即行动,身体即实践;学问即行,行即知。而教育工作中的“知行合一”,就是要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行动,来掌握知识,增长才干。阳明学并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而是强调实践的伦理学。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修己;二是治人[7]。结合教育实际看,修己可以理解为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时刻不忘提高自身修养,在言行举止中处处流露出严于律己、勤奋好学、“事上磨练”意志等优秀品质;治人就是指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行为示范和榜样引领,培养学生的良好品行和专业才能。
三、“身教”——教师育人
(一)“身教”的含义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解释,“身教”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做榜样”。“身教”的作用自古以来都广受重视,如汉代刘向 《列女传·鲁之母师》:“夫人诸姬皆师之,君子谓母师能以身教。”之后常以“身教”表示用自身的行为教育别人。陈世宜在《孟硕入狱不获探视诗以慰之》中提到“文字立教寻常耳,君独身教追如来”,对比了言传与身教的不同效果,更加突显了“身教”的作用巨大。
(二)“身教”的渊源
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教书需要言传,育人必靠身教。“言传身教”的组合最早出自《庄子·天道》:“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言传身教的教育思想源远流长、深入人心。在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第五伦传》中就有论述:“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可见身教高于言传早有公论[8]。即使放到现代高等教育领域仍然成立,因为教书只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只有依靠教师的行动进行示范引导,才能让育人工作卓有成效。《孔子家语》有云:“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教师在学生面前的任何行为都是教育,正因为如此,“身教”应该摆到更重要的位置,教师注重“修身”以胜任“身教”的意识和实践应该广为提倡。
(三)中日阳明学之“身教”实例
中日两国的阳明学者在创立和完善学说的同时,都承担了开馆讲学、教化众生之责。教育是阳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以身作则、师生共学更是诸多阳明学者的共性。
作为伟大教育家的王阳明,他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皆居绝顶,是明代后期影响很大的人物。他的道德事功堪为后人之楷模[3]。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该以他为榜样,努力向他学习,让自己成为一个明亮的发光体,吸引学生的追随。
王阳明一生颠沛流离,遭遇了诸多不顺,但每到一处,都不忘读书,钻研学问,并且在恶劣的环境中怡然自得、内心光明。这些自然流露的学者风范,都是他办学授课时的金字招牌,让各地的求学者,甚至是朱子学者慕名前来,在他的身边接受熏陶,提升学问。另外,正如其弟子钱德洪总结的那样,“先生立教皆经实践”[9]1232,王阳明各个时期的教学方法都是建立在自己先行亲身实践的基础上,所以教育更有力量,更显效果。如王阳明教育实践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鼓励学生立志,当志存高远。这可以追溯到王阳明自幼入私塾读书,在被先生问及“何为第一等事”时,他回答“做圣贤”。他的一生都是在努力实现“读书学圣贤”[9]1226的志向,因为只有立定志向,方能勤学不倦。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先做到,是谓“身教”的精髓。
再如“诸生责善,当自吾始”[10]376。王阳明提倡谏师和责善,也是从自己开始实行。他说:“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10]376“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若先暴白其过恶,痛毁极低,使无从容,是激之而使为恶矣。”[10]316王阳明不仅从精神上鼓励谏师、责善,还明确给出了可操作的方式和该规避的事项,引领诸生一起相互学习,彼此乐道。若教师一边言语中鼓励学生提出意见建议,一边神情行为中厌恶排斥谏言者,那“谏师、责善”都将销声匿迹,“身教”也无从谈起。
日本阳明学者中典型的“身教”代表当数中江藤树。藤树被尊称为日本阳明学的“开山祖师”。他是位堪称典范的思想家、教育家,作为“孝亲爱人”模范国民形象,其“孝敬父母”的言行被记载在小学的道德课本中,他曾经背着母亲步行,以这样的言传身教向弟子们展现“孝”的重要性。被称为“近江圣人”的中江藤树,其核心学说“全孝心法”不仅把孝道作为全部道德教育的核心,把孝道看作人类社会最高的道德准则,而且把它上升到哲学高度,看成是万事万物的根本道理和宇宙万物的本原[11]。藤树放弃武士身份,回乡照顾母亲,一边经营小酒馆维持生计,一边收徒讲学,用实际行动向弟子们表达了他的学术主张,即反对“口耳之学”。做学问不能仅仅记诵辞章,而应该全身心投入,明心修身,方能真正受益。孝道也是如此。抽象的理解和经典的诵读都不能达到真正理解,唯有亲自躬行,才能明白孝为何物。藤树的“身教”效果显著,不论身份高低,听课者在生活中用行动阐释了孝敬父母、拾金不昧的含义,一度传为美谈,从而吸引了更多的求学者投入其门下。
另一位知行合一的“身教”典型就是大盐中斋,被称作“行的阳明学”[12]。大盐中斋开办私塾,取名为“洗心洞”,表现的是阳明学中“洗去私利私欲”的思想。他把自家住宅设为私塾课堂,吸收包括武士、农民、医生等各类身份的人入学,讲授阳明学。在中斋的思想中,人之所以能在天地万物中自由地生存是因为发挥了良知的作用,要致良知,就应该“去人欲存天理”,而做到“致良知”,就实现了最好的生存方式。停留于口头说良知而不落实到行动,知行不合一,则会被人嘲笑[13]。他强调道德教育的目的,不限于“致良知”式的内求于心,而是要践行“为善去恶”的社会道义[11]。他曾经把自己的书籍全部变卖了来接济贫民,堪称是知行合一的典范。当他观察到当时武士的放任自流和商人的唯利是图已经让社会秩序极度不合理,超出了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就亲自起草了檄文,带领着300名弟子一起发动了起义。他们袭击武器库,并发射了大炮,震惊了全日本。在起义开始时,他首先做的是放火烧了自家宅院,为起兵造势。在与幕府军交战的过程中,大阪的街道都被战火包围了。就因为中斋“不为私利,只为遵循天理”的言行,虽然在起义中有大量民居被烧,但老百姓并不怨恨中斋,而是将责任直接归于幕府的腐败。尽管起义很快失败了,中斋最终也献出了生命,但隐退官员率领民众起义刷新了日本历史,开创了先河,其精神代代相传,最终促成了明治维新的成功。
四、“身学”——师生教学相长
(一)“身学”的含义
“身学”说由日本阳明学者冈田武彦所提倡,是他本人为学之道的总结。有学者将冈田武彦的学说归类为“身的阳明学”[12]。冈田武彦(1908—2004年)是当代日本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儒学特别是阳明学,是一位具有日本特色的儒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是对二战后日本社会及当代人类命运的反思和总结,对中国的教育也有借鉴作用。冈田先生对“身”的概念作了这样的阐释:
此身虽不过七尺之躯壳,其体虚灵不昧而内藏万里,外应万事,亘与古今,万物为一体。故学之要,致身尽焉。若能致此身,则不啻保全吾身命,亦可以化育天地,为万世开太平矣。盖致身也者,本体工夫。然体立而用达,学者须要兀坐,以培此身命之根也。[14]348
上文把儒家“致知”“修身”说融合演化,形成“致身”理念。“学之要为致身”,“身”者“心”也,故为本体,“致身”者爱身与尽心也,故为工夫。按照阳明提出的“本体工夫合一”的思路,可谓“致身也者,本体工夫”也。王阳明有诗云:“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15]于是故,最后冈田先生把自己的为学之道,归结为简易直接、平淡寻常的“身学”说:
自阳明子出,提倡良知之说,心学乃大明于世矣。曰良知二字,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体大思精,寰宇赓继相承,以是为本体工夫,则圣人之学致知尽焉,圣人简易之学于斯极矣。余谓天地万物会归于心,心归于身,身是心之本源,宇宙生气之充实处也,故曰学也者,身学也,致身尽焉,然初学者,宜兀坐以培其身命之根,应宇宙在手,万化生身,其功切至矣。[14]349-350
“天地万物会归于心,心归于身,身是心之本源,宇宙生气之充实处也,故曰学也者,身学也,致身尽焉”,既指明了“身学”的意义,也明确了与“心学”的关系。阳明学是体认之学、培根之学,是“身心相即、事上磨练”之学[16]。体认,即以体认之,所谓身体力行也,非止以智识认知也[14]344。“培根”即“培养根本”之说,其倡导的是“诚意”,到王阳明晚年时逐渐演化为“致良知”说[17]。换言之,做事也好,求学也罢,最根本的是内心的良知不被蒙蔽,具体采取的方式方法则为“枝叶”,“根”充盈润泽了,自然“枝繁叶茂”。成事向学之心足够笃定,必然能指导人们选择正确的方式方法,从而实现事业学业的长进。“身心相即、事上磨练”,表达的就是“知行合一”,“心归于身,身是心之本源”,“身者,心也”,身心本一体,“身学”与“心学”在名称上虽然有异,但内核是一致的。中国的阳明学具有理论与实践齐头并进的特质,但日本的阳明学则以实践为主。阳明学给日本思想界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有关“实践躬行”的内容[14]286,因此,阳明学在日本发展一两百年后,在冈田武彦的学说中形成“身学”之说属水到渠成之果。故“身学”的含义可以概括为:为学应爱身尽心,身体力行,超越智识,持续实践。
冈田先生在强调“身学”这一为学宗旨的同时,还将其付诸教育实践。他指出,在当今科学教育十分发达的条件下,要十分注重这种以“身学”为内涵的人文精神的培养,只有把科学教育和“身学”教育统一起来,才能培养出既“爱人”又“崇物”的新型人格[14]350。“身学”不仅是学者该有的治学之道,也应该推广到教育领域,让学生在求学的过程中以“身学”的要求培育“知行合一”。
(二)“身学”教育的意义
“身学”教育的目的就在于达到一种自然生命的“忘”的境界,也就是自然无为、顺人之天的境地。换言之,就是在教育的过程中磨炼自己的意志和才能,将理论付诸实践,反复尝试、反复改进,最后磨己而忘、践履而忘,而忘的境界又是为了“活泼泼地发挥人本来所具有的生命力,从而使人能够美好地生活”[14]350。这里的“忘”,意味着已经成为自觉行为,学习成为生活的必须,和空气、水一样不可缺少。作为教育的两大主体,教师和学生都应该通过“身学”达到理想的境界。
从本质看,教师和学生之间没有区别,都统一为学问的追求者。
习近平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对教师以身作则、不断学习作出了明确指示。教师需要有深厚的知识修养和文化品位,并需要不断加强自我修养,提升道德情操和学识水平。以崇高的师德为前提,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教师的基本素质,其中,知识是根本基础。知识储备不够,视野不够,在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更谈不上游刃有余。在信息时代要做好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先要有一桶水”已经不够了,国外教育家说过:“为了使学生获得一点知识的亮光,教师应吸进整个光的海洋。”陶行知先生也说过:“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好教师不是天生的,都是全身心投入教学管理的实践中锻炼成长出来的。
学生的天职是学习,如何学、持续学成为关键。教室里的理论讲授,不能代表学习的全部。学生的自主探究,创新型学习日渐成为学习的新模式,终身学习正在成为生活所必需。学校教育与产业教育、社会服务教育紧密结合,让更多的书本知识有了接受检验的机会,学生在社会中亲身体验过的反复尝试和不断改进,将进一步激发他们主动学习,加强和拓宽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以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学习不再被视作痛苦和强迫,而是忘我的投入,在学习中体验良好的效能感,实现个人价值。一切的学习,重点在于爱身尽心,身体力行。在智慧时代的大背景下,诚心实学,脚踏实地作贡献。
(三)中日阳明学者的“身学”理论与实践
王阳明思想的形成过程与阳明本人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密切相关,而其思想又是极为贴近生活的[18]。王阳明龙场悟道,是谓“身学”之典范。王阳明在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伸张正义、仗义执言而触怒最当权宦官刘瑾,被罚廷杖四十,并被贬谪到偏远落后的贵州龙场当驿丞。龙场穷乡僻壤,民未开化。流谪龙场的阳明,是碰到了千难万险并克服了它,才静坐修行的。在日夜反省的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顿悟,认为向外求理都是徒劳,自己的内心才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由此提出“心即理”的命题,并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其中的“吾性”,就可以理解为“我的良知”,而阳明所悟得的“良知”之体,后来又经过种种磨难,经受了反复磨炼。阳明的思想经过了几次变化,才提出了“致良知”说。因此,阳明学说来源于其本人经历,又在后续的经历中受到反复磨炼,才日渐精益,是“身学”的具体体现和集中代表。
另外,在王阳明的教育实践中,也处处体现出“身学”的宗旨。王阳明告诫弟子对待诽谤的正确方法就是加强自身修养。为学处事贵在加强自我修养、尽心躬行。内心认定不动摇,不为外界所干扰。环境无法改变,但可以改变自己。一旦自己从内心到行动都渊博谦恭并正直磊落、诚意洒脱,那些流言诽谤就不攻自破,而凭实力获得的认可,自身正能量必能辐射周围人,带动他们一起诚心实意做学问、干事业。
日本阳明学者中也不乏“身学”的代表。山田方谷是日本幕府末期有名的阳明学者,是一位活学阳明学于实际的实干家。他是德川幕府最后一位将军德川庆喜的首席老中(直属于将军的最高行政长官)、松山藩藩主板仓胜静的得力助手,是幕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智囊与辅佐。他在吸收阳明学的时候更注重学习王阳明的为人,他认为这样才是善学者。从王阳明的为人和做事上吸取其精神精华,来指导自己做学问和理国政。方谷以阳明的良知说为依据,认为若能独悟自得良知说之精髓,“则为仁、为义、为礼、为智,万变之条理随生焉”[14]155。方谷在松山藩推行财政重建、教育改革和军制改革,践行良知学说,仅用7年时间就为全国有名的贫穷藩松山藩偿还了10万两欠款,并为本藩挣得了10万两,堪称当时财政界的奇迹。不止山田方谷一人,多数日本阳明学者更看重阳明的为人处世,即他的实践性品格,并身体力行,以阳明为模范投身日本的社会建设与发展。
日本阳明学者吉田松阴的教育观特色之一是平等教育,在平等教育中潜移默化地传递“身学”理念。除了没有严格的师生身份高低规定以外,在教学方法上,以开放的精神协同研究,相互切磋,“师弟同门”是其平等教育的重要体现。松阴门下有个学生,立志学习诗文创作,但当时的松阴不喜欢诗文,认为诗文只是文字游戏,对人的上进没有任何好处,而自己也不擅长诗文,但他并没有拒绝这个学生,而是以实情相告,两个人决意共同学习诗文,在诗文的学习中松阴感悟到了伟大诗文的感人之处,改变了对诗文的原有成见[19]。在松下村塾的学习是一种对生存与发展的考量,学生不仅要博读经史子集,通晓文武两道,还需要洞察国内外时局,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社会性角色,在时空的社会舞台中找到自己,更好地塑造自己,最后贡献自己[20]。松阴虽然英年早逝,但在其30年的生涯中,在不到五年的教育活动里培养了高杉晋作、久坂玄瑞、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木户孝允等明治维新志士,这些门人在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吉田松阴执教的松下村塾改变了日本。可以说,吉田松阴的教育就是一个奇迹,这与松阴带领诸生实践的“身学”有着很大的关系。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与弟子的相互学习中育人育己,其力量不可谓不强大。
长冈藩家老——河井继之助,深得阳明学真谛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藩政改革。在18岁时便掌握了王阳明所教导的“知行合一”的精神。他认为,从学问中获得的知识必须付诸行动,并作用于现实社会,唯如此才算是真知识。因此,“知行合一”的精神便成为继之助的行为方式[14]163。他师从山田方谷,修业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成为一个能担当起长冈藩政的人,通过身心之磨炼,具备必须有的技能和才学。由于受到方谷践行的阳明思想感染,他在学问上活学活用,虚心聆听并体认相关改革的真知灼见。继之助将方谷奉为真正的老师,从方谷那里接受的是实用之学,用此学指导长冈藩的改革,使病入膏肓的长冈藩得以傲立群雄数年之久。继之助的“知行合一”精神,也是“身学”的另一种阐释,“身”即行,注重行动,在现实生活中反复磨炼,促使知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身学”的现实贡献。
知识之所以是力量,智慧之所以崇高,是因为他们是我们自己获得的,是我们在对自己、对宇宙、对生活经验的深刻体验中建构的[4]。通过自己的身体,将内心与他人经验努力进行联结,形成自己的理解,支持学习者在理论与实践、生活与体验的相互作用之间,不断实现自我世界的开拓壮大,这也就是“身学”的落地效用。
五、结语
正如孔子在总结自己教育生涯时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教育实践中,能让学生真正信服并追随学习的是他们所看到教师形象和行动,并不是纯粹的理论知识讲授。随着教育形态和理念的变革,人们对教师角色的理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教师已经从知识权威形象转化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相应的,“身教”在内涵上也有了新的解释,即不只是教师以身作则的单向度的意涵,还关涉其如何组织和调动在场者身体的感知觉、情意、行为等因素充分参与教学实践[5]。随着智慧型教育的普及,混合式教学、探究式学习成为常态,教室内外的学习形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技能和涵养,运用多种新鲜而活泼的方式让学生主动愉快地参与教学活动,师生共享学习的乐趣。
在中江藤树弟子——日本阳明学者熊泽蕃山的教育思想中,对教师论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教育不是用语言传达知识,说到底是教育者成长的过程。“学不可以已”,进而言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取得不间断、可持续的成长,才是教育的真谛。所谓“修己工夫和治人工夫都是必要的,通过教育改变他人与通过教育改变自己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14]151。这是对教育本质的同质概括。“身教”与“身学”,即聚焦于身体的“教”“学”双向活动,可以看作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在实践性上体现了统一。教育不是“口耳之学”,仅用语言传达的知识毕竟范围有限,效果欠佳。中日阳明学者的言和行,启示了“身教”与“身学”在新时代的重大意义。达到教学相长、共同进步,才是教育界的良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