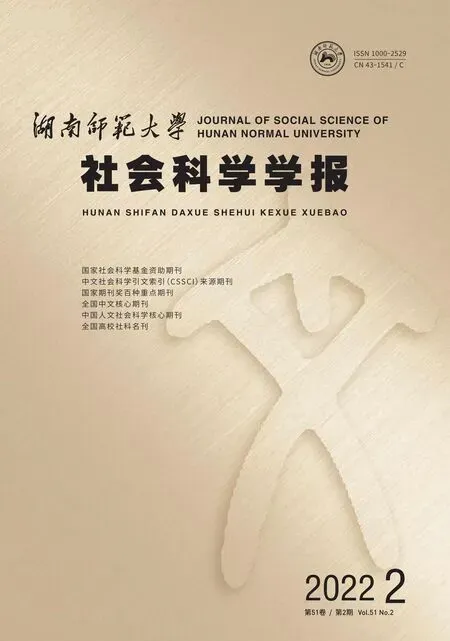京派文学的散文化与母语文学传统的新创化
2022-03-24伍丹
伍 丹
京派同人(创作者和理论家)到底包括哪些人?这个问题,学界始终没能达成共识。他们既没有正式结社,也从未发表过共同宣言,即使存在过的那些松散的文艺小圈子也没有特别密切的联系。然而,文学史始终将他们视为一个文艺群体,一个文学流派。对此,唯一能确认的一点是,他们都曾居留北平。“京都”的韵味和诗性熏陶了他们博大而纯良的气度和风骨,也促成了某种近似或共通的文学观,乃至文化观的形成。吴福辉在《京派小说选》中以是否聚集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周围为标准,认为京派同人包括“小说家:沈从文、凌叔华、废名、芦焚、林徽因、萧乾、汪曾祺;散文家:沈从文、废名、何其芳、李广田、芦焚、萧乾;诗人:冯至、卞之琳、林庚、何其芳、林徽因、孙毓棠、梁宗岱;戏剧家:李健吾;理论批评家:刘西渭(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朱光潜等”[1]。考虑到汪曾祺的文学成就基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可以不纳入对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的考量。本文所论述的京派文学和京派同人,皆着眼于20世纪30年代,即京派文学的经典时期。
如果把京派文学视为一种文学话语形态,而话语又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文本作为话语则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形态,每一次对其的阅读和阐释都是一次“完型”。伟大而卓越的文本更是表征出完全且恒久的敞开性状貌。鉴此,有必要对京派文学进行重新阅读和阐释或再一次的“完型”,即京派同人秉持将“语言”视为艺术生命的精髓之文学理念,再次发展了汉语言母语意蕴悠长且饱含诗性的文学样式。成中英在《中国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一文中指出了汉语言母语的“功能”:“语言的功能一是表意,不指谓世界,而是显示世界,一得真实,即弃语言;二是做审美对象,是表达形象和声音的图象,而不是直接掌握世界、传达意义的工具。”[2]
京派同人以对中国古典文化深深地眷恋,以对世界和人生理解的善意,用从容宽厚的文化心态,从理论研讨到创作实践一直都在努力传承着汉语言母语的文学之魂,其创作无不彰显着汉语言母语的“表意”和“审美”。他们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感兴式思维,又吸收了现代西方文艺的唯美主义和直觉主义,用满具个性的才情和诗意,立异革新、改进通变,形成了既具有现代气韵又独立自主的文学创作、批评体系,实现了母语文学的“新传统化”。
一、散文传统与母语文学正宗
京派同人最擅长的“文体”是散文。在坚守其文化自由主义和文学人道主义的前提下,京派同人不仅在感情上且在理智上创造性地传承、赓续了汉语言母语文学最具优雅性的一脉,即他们以趋近完美的散文写作传承了母语文学的千古文脉,呈现出“郁郁乎文哉”的博大气象。
京派同人几乎人人写散文,散文是与他们艺术习性最亲近的文类。他们以独特的个人风格和自觉的创新提高了散文的品位和价值,其独标高格的散文创作也让京派文学走向绚烂的顶峰。周作人曾将现代散文比作一条淹没在泥沙尘土中的长河,多年后终在下流被挖掘而出。虽然是一条历史中的古河,却也在重见天日时焕发新颜。当然,也只有在京派同人的创作中,周作人的说法才能得到佐证。1934年,沈从文返回故里,一路写下《湘行散记》,以一种活泼泼的民间味道,抒发着“无言的哀戚”。1937年,何其芳的《画梦录》以大学时期颇具实验色彩的抒情散文夺得《大公报》文艺奖中唯一的散文奖,而后师陀、李广田、废名、萧乾等陆续出版散文集。有意思的是,“汉园三诗人”以诗歌著称,依卞之琳的说法,他们在一起谈论较多的却是散文。可见,京派散文已为当时文坛所确认并趋向鼎盛。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虽然反对如“小摆设”般“冲淡闲适,抒写灵性”的小品文,却不得不承认到“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显然,散文小品的辉煌战绩和蓬勃发展与京派同人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文学传统以“诗文”并称,“诗”泛指诗歌,“文”大体指散文。古人称“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此“文章”正是前贤作为治国理政和价值实现手段的散文。在此意义上,散文正是汉语言母语文学之正宗,其以“文”为名,实践着“以文化人”的文化理念,扮演着文类之母的角色。王本朝在《白话文运动中的文章观念》中指出“‘文章’在中国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概念,曾作为书面文字专称,又被作为所有文体的总称,后又专指诗之外的骈、散文体,还经历了‘文’、‘笔’和‘古文’的分合流转,才形成诗文并列的格局”[3]。相对而言,传统文章比诗词的地位高、作用大,传统文人的命运与文章的关系也更为紧密,既有发奋著书、文以干禄,也有文字狱。朱自清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也提到,胡适在回答他人提问时,曾表明文字的作用就是表情达意,达得好、表得妙就是文学,故文学要有“三性”,即“懂得性”“逼人性”“美”。故,“文学只是‘好’的文章、‘妙’的文章、‘美’的文章罢了”[4]。
实则,“文学”与“文章”虽有交汇却又有区别,文学创作审美引导着文章写作,而文章写作形式规范着文学创作。当年周作人称废名小说之独特价值就在于“文章之美”。废名自是对“文章之美”有所好焉:“有一个好意思,愿公之于天下同好……那个意思其实只有一句话:我们总要文章做得好。”[5]此所谓“文章之美”的标准就是传统散文的文辞和趣味。
现代诗歌和小说在发展过程中与传统文学发生剧烈断层和割裂,而现代散文在传统散文的影响下,发展却比较从容和舒缓,京派同人的诸多散文亦展现出鲜明的古典审美情趣。钱基博曾以散文为中心建构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周作人亦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借助晚明小品散文解读“五四”时期的文学,更有研究者将散文与“纯文学”视为同类。陈平原曾指出,清末民初最早接受西方文论的学人,如王国维、黄人、周氏兄弟,皆推举“纯文学”之识见,缘于他们拒斥传统文学的“文以载道”。故而,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六朝的文章(散文)因抵御“载道”遭贬责,如今却因“纯文学”而受到重视。这也应和了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所见,提倡六朝文章的人一般没有“载道”之欲求,只追究文章的美质,因而容易获得为文的独立性,不受意识形态流变的拖累。
由是,京派同人的散文创作走的正是“纯文学”的路径,作品讲究的是意境、神韵、情趣、文采,无形地避开了“文以载道”,更鲜明地体现出母语文学擅长抒情、写意的本色。换言之,京派同人的散文之“纯文学”的意味,主要表现在母语文学创作的语言“艺术”上。
诚然,在建设现代国家、塑造现代国民的历史要求下,“五四”新文学提出了中国新文学的时代性课题:用文学的白话文运动构建起“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但在京派同人看来,“五四”新文学的理性观念过于粗浅,尤其是被胡适们一味推崇的“做诗如说话”的白话文学:它脱离了汉语言母语文学固有的内在韵律和美质。“不仅是反旧诗,简直是反诗的;不仅是对于旧诗和旧诗体底流弊之洗刷和革除,简直是把一切纯粹永久的诗底真元全盘误解和抹煞了。”[6]这为京派文学返归、持守母语文学本性提供了充足理由。如朱光潜在其《诗论》中所言,白话新诗因节奏和韵味皆匮乏而缺乏审美品质。新文化运动时期,各式西方主义、学说,各种西学思潮、理论先后传入中国。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新文学中,散文是汉语言母语文学血脉基因延绵得最纯正的一脉。沈从文在《阿黑小史·序》中以“乡巴佬”自居,自认其文字放弃了“善于用美丽漂亮语汇长句”的欧化语言,似乎“更拙更怪”,却也“极自然”。他在评“京派”作家的《论冯文炳》一文中,对周作人“清淡朴讷的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大为推崇,进而直言:“因为文体的美丽,最纯粹的散文,时代虽在向前,将仍然不会容易使世人忘却,而成为历史的一种原型,那是无疑的。”[7]观其创作,沈从文母语文学的语言造诣无疑是卓绝的。他以句短味永、清丽柔美,如诗似水、泻畅通脱,温厚明澈、灵秀飘逸的文字,提供了一种母语写作的型范。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将京派散文对母语文学的直接承续称之为“文艺复兴”。可以说,京派散文将语言形式和艺术情思完美交融,“它连接着民族深厚的散文传统”[8]。可见,京派散文的成功正是母语文学的成功。
朱光潜曾在《眼泪的文学》中批评巴金的创作并因此与之交恶,其本质实为不同文化背景和话语方式的纷争。巴金在《中流》上的回驳,同样体现了他特有的行文风格、充沛的激情与直率淋漓的表述。不止巴金,与左翼作家雄奇澎湃的气势和艺术夸张或审美夸饰不同,京派同人将情思、情蕴渗透于文字间,着眼于感发的思绪和想象。他们对散文化创作的灵活舒展特性的感悟,连同其作品语言格调的意境美、文采美、神韵美,始终带有一种雅驯和洗练。虽然不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却也称得上言简意丰、含蓄蕴藉。
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称沈从文为“文体家”,之后权威的文学史著作沿用了这一表述。实则,多数京派同人都可以担起这一称号。因为他们注重散文的文体艺术,其艺术创造极端趋近散文化:用散文的体制及基本精神贯通整个文学创作(包括小说),且在叙事散文、抒情散文、文学评论等方面都有艺术创新。或可以这样说,在京派同人那里,散文不仅是文学,它已经关乎文化与人生、哲思与审美。他们追求着“纯粹的美丽”[9],以妥当和完美的写作承接了母语文学的散文传统,各逞才情,娓娓挥洒着对乡情母语的眷恋缠绵。
二、散文式小说与抒情诗意建构
京派文学小说创作的“散文化”十分明显。母语文化如同天赐的本能,深深影响着京派作家的创作。他们运用并发展了母语文学叙述语言精练、含蓄和抒情的功能。在小说创作中,他们注重炼句的考究、情绪的渲染、叙述的空白化和结构的片段化,显示其小说创作的散文化倾向。
“京派同人属于一个颇为独特又极富创造力、兼有艺术追求和个性才情的文学群体。”[10]对于创作文类(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批评)的差异、区分,京派作家并不看重,他们看重的是对散文化创作内在张力的表现;反之亦是,京派同人是在不同文类中寻求精神叙述的统一、创造境界的统一。文学武在《京派小说与海派小说比较论》中直言京派小说具有“散文化”的艺术特征,认为京派小说淡化了传统的情节结构,抛弃了海派式的心理结构,而追求诗意的建构;其情趣氛围和意境的营造、传统绘画技法的融汇,更传递出一种隽永的意味,拥有一种时间向量上的延续力和渗透力。
如废名小说的散文化更多地表现为文笔的自然和思绪的自由,其文本始终流注着一种舒缓自如的审美情愫,叙述、结构、人物大都融解其间。尤其是,废名早期小说多有对自然景色的妙悟,于竹林、桃园等乡野景致中描绘出类似于“拈花微笑”的境界,从中洞见世间万物生命本体的跃动,表达对“个体生命的感悟和人生苦乐的思考”[11]。故其小说常深蕴玄思和禅趣。而师陀自言其小说创作,“这些东西有的像小说,有的像散文,有的却又什么都不像。”[12]他在《江湖集·编后记》中说,“我想用旧说部的笔法写一本散文体小说,每节都自能独立。”[12]这便是《果园城记》。这本系列性小说汇集了18篇“果园城”的人和事,写作创意是“一个小城的性格”。换言之,师陀依靠一个固定的地域空间“果园城”,将众多篇章组成审美叙事的整体。“果园城”作为共通的叙述背景,具有美学氛围极强的内在聚合力;同时,由于叙述可以在各种人物的行动和各类自然场景之间自由流转,读者也能随之走进“果园城”,感受到小城的荒凉与衰败、悲郁和忧伤。师陀就是以这样的旨趣和意绪写作,由此,既勾连又独立的篇章被融合在一起,共同的地域空间与相近的抒情格调映照生辉,从而完美地实现了对“一个小城性格”的型构。
再如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他自叙只有“平平的写法”,既无“中心”,也未“提高”或“拉紧”,虽描写尽力,但结构确是“疏忽”,进而得出结论“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13]。如《边城》,沈从文有意虚化故事冲突、情节起伏,甚至不动声色地用一种叙事者的“纪述笔调”平复情节的“演示性冲动”,而将热情给予了情境的渲染和世态的描摹。沈从文对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将“人和景错综在一起”的写作手法颇为钟情,“背景”向“前景”挪移,与“前景”混合,这一笔法同样为小说文本带来了“散文”的联想。他的《湘行散记》绝非一般的游记散文,它的重心更在于写人,写湘西的人物故事,亦可以视为散文式的小说。
当然,与叙事文学类型的小说以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为己任不同,“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孜孜以求的是人物形象的神韵和写意性,是取其神似以象征‘这一类’;而不是穷形极相或精雕细刻,不是力求形肖以坐实‘这一个’”[14]。在此种意义上,京派文学放弃了小说最重要的本质特点——叙事,而以富于生命情调的人物活动和虚实相映的情境完成了文本的叙述功能,由此变成了抒情散文或田园牧歌。
总之,京派小说家“为着诗意的丰盈,走上了抒情小说的途径,而也为着诗意,他们的小说以散文作为自己的装束,写得那类半是小说半是散文的文字,散文式的小说,也当然成了他们共通的趋赴”[8]。
严家炎曾指出,就讲究语言这一点“京派在中国现代各小说流派中也许是努力最多的”[15]。众所周知,汉语言母语文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独特美质的语言本色:重诗性传达,简洁自然,讲究文采,追求含蓄;赋予语言多重含义和联想功能,通过有限的形式到达无限的广阔世界。与小说的散文化相对应,京派作家充分运用并发展了母语文学叙述语言的精练、含蓄和抒情的功能。最具说服力的当属废名的小说。其长篇小说《桥》,故事层面的叙事时间几乎凝滞,情节铺展、人物塑造被大大压缩,而生活片段、细节被拉长、定格,一种兴味、一种气息、一种情趣弥散在整个文本空间,朱光潜称之为“诗境”“禅趣”。许道明在《京派文学的世界》一书中如此评价:“诗、散文、小说三种文体在他那儿犹如海洋中的三座岛屿,他们突兀在海面,而各自的脚根却在海底深处连成一片,在这片潜土上赫然镌刻着‘散文’两个大字。”[8]无怪乎有人将废名小说视为山水小品来解读。周作人亦盛赞废名小说是一种很有“意味”的文章。《桃园》《桥》《竹林的故事》出版后,周作人欣喜地为之写序,称“废名君用了他简练的文章写所独有的意境”[16]。这无疑表明废名小说有意识地走上一条为文造“境”的路径。
三 、“寻美式批评”与理论思维散文化
在理论性或批评性话语的建构层面,京派同人依然保持了散文化的思维态势。在传承和开发母语文学资源的基础上,京派同人创造了一种近似“美文”的、由感悟化思维所凝聚而成的批评(理论)文体风范。
朱光潜将批评家分成四类:“导师型”“法官型”“舌人型”“饕餮型”。“饕餮型”批评家“只贪尝到美味,尝到美味就把他的印象描写出来”[17]。从京派同人所秉持的批评理念以及批评风格可知,他们无疑是属于“饕餮型”批评家,亦即法国文学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所言的“寻美的批评家”。京派学生辈李广田在《文学的枝叶》中引用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最好的批评应该是描写的”来指陈“批评”的艺术创造性,而杨义则赞京派的理论文章都是“自然浏亮、从容潇洒”的。显然,京派文学的“寻美的批评”已由审美思维进入了理性思维,即把作品本身当作独立的对象进行欣赏和批评,以散文化的语言品赏小说的自然情趣。
正如朱自清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部极美的散文集,它步步引你入胜,断不会让你索然释手。京派同人认为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创造。李健吾强调批评家应该有“文笔、语言、文法”。他本人尤其喜欢蒙田的随笔,对其文章挥洒自如的风格赞赏有加。他在文学批评集《咀华集》中多次提及蒙田:“他往批评里放进自己,放进他的气质,他的人生观。”[18]《咀华集》可谓名副其实的“含英咀华”,行文下笔神似蒙田涉笔成趣的评述。其中的悟性的飘逸和灵魂的探险,以一种羚羊挂角般的审美机趣进入了批评的文本世界。可以说,李健吾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中炼铸出了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从而将自己活泼且灵动的艺术审美感受传达了出来。如他将读茅盾的文章比喻成“上山”,沿路皆是“瑰丽的奇景”,亦有“绊脚的石子”,而读巴金则如“泛舟”,一路“顺流而下”,几乎没有“收帆停驶的工夫”[19]。可见,他追求的是形象、抒情、比兴的语言特色,用一种情韵盎然的隐喻和近乎诗性的表述,传达出几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感受;其意在于保持阅读印象的原色原味,并通过随笔性的诗性语言以及随意赋形的结构,以直观的方式诱发读者关于印象的“印象”。就像他说:“《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八骏图》是一首绝句,犹如那女教员留在沙滩上神秘的绝句。”[19]在此,批评无异于一个心灵向另一个心灵的触碰,具有与散文作品一样的可读性。以此观之,其文学批评因文风洒脱、语言华丽、体制活泼,善用比喻、象征、类比,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文风格。
沈从文并没有成为文学批评大师,但也写下了大量的评论文字。相对于茅盾等人系统化、逻辑化的文艺评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更多的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感悟式批评。他评许地山“以佛经中遂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最散文的诗质是这人的文章”[20]。在此,沈从文已然轻松地从文体进入了作品的世界,以己之写作经验品鉴着文本的美,体味着创作者的情思。他的文学批评一如他的文学创作,重“文质”而非“析理”,摒弃逻辑而诉诸直觉,在飘忽朦胧中,用款款叙谈的描述性语言娓娓道出他的感受和体验。如他论鲁迅的文字“寒光闪闪,有投枪意味,中必透心。即属抽抒个人情绪,徘徊个人生活上,亦如寒花秋叶,颜色萧疏”。他认为鲁迅对于“当前”的“游离感”或“厌倦感”,与冰心、朱自清等“作品中无不对于‘人间’有个柔和的笑影”自然是“并无相同”的[7]。沈从文批评文体的语言有着强烈的心灵化表述风格,或独白或沉吟,批评中不乏轻灵跳跃的情感性话语,故其批评文字是情绪化的,亦是描述性的。在《论闻一多的〈死水〉》中,沈从文这样写道:“一首诗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故事、一点感想,应当是一片霞、一园花,有各样的颜色与姿态,具各种香味,作各种变化,是那么细碎又是那么整个的美。欣赏它,使我们从他那超人力的完全中低首,为那超拔技巧而倾心,为那诗人手艺熟练而赞叹。”[7]这是一种“轻盈、柔缓与灵动的美,这自非诗家功夫,乃批评所为”[21]。这样的批评性话语不就是诗意盎然的散文文字吗?其恣意挥洒的审美情思、随心舒展的才情灵性,正是京派批评话语“散文化”最显著的标记。
概言之,京派批评的散文化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结构和语体。在结构上,京派的批评文章大都松散自由,往往信笔而去、率性而为,宛如“思想漫游”和宗白华式“美学散步”,在漫游与散步中与读者形成亲切的对话氛围。批评者只需努力传达自己对作品的感受和印象,乃至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垒块;在语体上,京派同人使用一种感兴性、品味性、描述性的言语,以直觉感悟营造出情志和意趣交融的话语运行过程,“不判断,不铺叙,而在了解,在感觉”[19]。它传递的不单是批评对象鲜活的个性与生命气息,以及批评家自身的经验与精神气质,同时也是批评家自己被作品客体化的过程,更是作品被批评家主体化的过程。
如前所述,朱光潜指出现代文学批评史曾存在大量的“导师”式、“法官”式和“舌人”式批评,而真正把作品当作独立于作家、派系之外的美的对象,从而进行艺术创造的并不多见。而“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艺术”[22]。这便是京派批评存在的合理性。
简言之,京派文学彰明的是汉语母语(文学)“表意”和“审美”的两大本体功能。近年来由海外华裔学者(陈世襄、高友工等)发起、国内学界呼应并续接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议题,其本质就是对汉语言母语“表意”和“抒情”功能的审美化转述。“抒情”作为一种情感符号,在文学想象和实践里,其“情感”的“抒发”过程本就是语言的言说过程。不是作家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道说艺术(包括文学)。以往学界将沈从文、废名的小说冠以“抒情(诗化)小说”之称,言说的正是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现代性创化,即对汉语言母语文学的“新传统化”。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现代性创化”的实质不在“西化”而在对传统的“重估”,从而使“已丧失的传统价值得以回归到实际来”,其正是“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23],即一种现代性的创化。也正因为此,京派同人并未受限于某个特定的文艺圈子,作家内部因知识背景和审美倾向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在母语文化精神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下,也能自然融合,甚至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