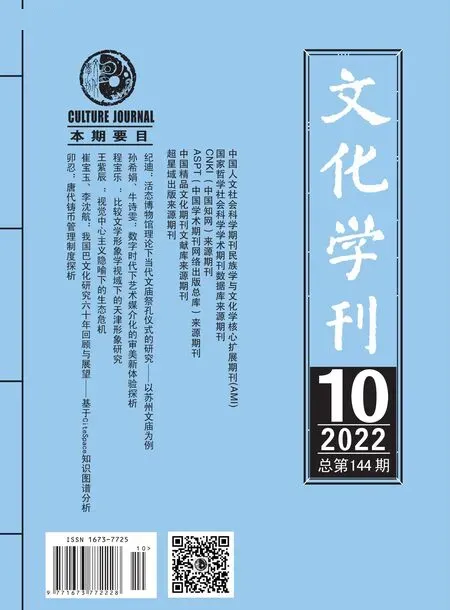差异化的解读重构
——论温索姆·皮诺克戏剧中的互文性
2022-03-23乔西汀
乔西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概念最初由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推广,指的是“任何一部文学文本事实上都是由其他文本以多种方式组合而成,比如这一文本中公开的或隐秘的引用与典故,对先前文本形式特征及本质特征的重复与改造,或仅仅是文本对共同累积的语言、文学惯例与手法不可避免的参与等方式”[1]。经过巴特、热奈特等理论家的进一步阐发与建设,互文性理论产生了广义与狭义的两种走向,前者指“文学作品和社会历史(文本)的互动作用”,后者指“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2]26。本文对温索姆·皮诺克的戏剧采取互文性研究,从戏剧创作的文化策略角度,探究少数族裔剧作家在主流剧场中平衡议题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方式。皮诺克戏剧中的互文性把文本向历史开放,引起读者对既定知识展开反思,使观众、读者和剧作家共同完成差异化的解读重构,有助于新的文学与剧场实践。
一、诗歌互文与身份启蒙批判
《道别》(LeaveTaking)是皮诺克的早期剧作,也是一部反映了她本人及家庭所代表的“疾风世代”在英国生存经验与境况的作品,1987年在利物浦剧场工作室首演后,又在同年于考文垂贝尔格莱德剧场、哈默史密斯抒情剧院再演。1995年,《道别》在英国国家剧院上演,标志着英国主流剧场对皮诺克的初步认可。
在《道别》中,作为一种连接英国黑人经验和白人观众的文化策略,皮诺克首先将经典英国文学元素《麦克白》融入了伊妮德(Inid)和薇芙(Viv)的对话。伊妮德在家中打扫时,薇芙挪用了《麦克白》第五幕第一场中麦克白夫人的台词。伊妮德享受说“莎士比亚”一词,并立刻模仿挪用。伊妮德在故乡牙买加接受到的是文化殖民教育,薇芙则是以英国人的身份接受本土教育,而这段对话反映了母女二人对英国文学经典文本创造性吸收和运用的能力。伊妮德移民到英国后被丈夫抛弃,靠清洁工作维持家庭,她的空间身份和社会角色没有闭合在传统家庭中,这为她和她的家庭教育也提供了开放和进步的可能。但家庭好友布罗德(Brod)的来访反而固化了黑人家庭中的男女分工,并且将薇芙的英国国民身份意识提前割裂。
这处不合时宜的割裂发生在布罗德、伊妮德和薇芙对民族英雄和身份的讨论上。当布罗德发现薇芙不能分辨非洲和加勒比时,他开始为薇芙讲述牙买加女英雄逃亡黑人保姆(Nanny of the Maroons)的历史,并说薇芙是保姆皇后的后代。伊妮德为薇芙辩护,认为女儿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但薇芙却背诵出了鲁伯特·布鲁克(Robert Brooke)的诗歌《战士》:“一具尸骨,生于英格兰,长于英格兰,育于英格兰,曾给他花朵让他去爱,给他道路让他漫游英格兰的身体,呼吸英格兰的空气,由故乡的水洗净,被故乡的阳光祝福。”[3]薇芙用诗歌中一战战士的形象确认自己的国民身份,这种引证使伊妮德也不确定如何接受,并成为了薇芙拒绝接受教育的导火索。
皮诺克抓住了《战士》和戏剧主题共通的国民身份概念,借助语境差异发掘概念内外的矛盾,批评了布罗德式的启蒙民族主义。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公民身份(citizenship)导向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启蒙’性质的民族主义”[4]。但在复杂的现代民族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中,个体不再具有启蒙主体论所相信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统一个体。皮诺克借助《道别》与《战士》的互文,将国民身份概念的矛盾调和于新的概念,即教育的时机,并指向了后殖民身份概念在实践中的问题。在与身份相关的理论中,杜波伊提出双重意识概念,霍米·巴巴提出身份的混杂性和流动性,吉尔罗伊则提出混合身份认同。但皮诺克设置的互文揭示了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即这些身份概念都忽视了意识与身份认同建立前的个体觉醒过程,以及外界影响因素可能造成的破坏。过早采取布罗德式的寻根“启蒙”方式会改变启蒙应有的性质,使以加勒比为根的启蒙民族主义尝试走向封闭、排斥、侵略。在中心尚未被完全认知的前提下,去中心化的身份认同教育甚至可能造成薇芙这一类人群的精神分裂。
面对复杂的身份建构问题,皮诺克不仅借助《战士》提出批判,还给出了家庭内的解决方案:剧末,尽管薇芙的寻根意识被外力提前启蒙,但伊妮德抓住了教育时机,给薇芙讲述了牙买加家庭的历史,既缓和了“疾风世代”及其后代之间的代际矛盾,也鼓励了薇芙继续丰富自我身份认知。剧内的薇芙和剧外的皮诺克都认识到,英国文学的国际化和教育的去殖民化都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自己也可以承担作为英国黑人的双重责任。薇芙有志于在大学学习种族研究,而皮诺克则持续投身戏剧创作,用剧作数量和质量的积累提升英国黑人剧作家在剧场中乃至社会上的话语权。
二、戏剧互文与差异符号化批判
《说方言》(TalkinginTongues)是皮诺克创作的两幕剧。剧中,英国黑人女性莉拉(Leela)在伦敦经历了婚姻危机与身份认同危机。新年过后,莉拉与朋友克劳戴特(Claudette)到牙买加度假疗伤,二人对跨种族交往的仇恨态度却被再次激发,从而伤害了白人女性凯特(Kate),并导致当地旅游服务员休格(Sugar)失业。此剧反映了英国黑人女性在20世纪90年代面临的性别、文化问题,于1991年首演后在英国多次上演,并先后被选入两部戏剧选集,是当代英国戏剧的经典作品之一。选集编辑林奈特·戈达尔(Lynette Goddard)提出,皮诺克的创作是“以《奥赛罗》为灵感,检视黑人女性对跨种族交往的态度”[5]。这种论证虽然维护了《说方言》的内容深度,但暗含了一个前提:新书写只有依附主流经典文学作品,才更具有被承认的价值。
对《奥赛罗》的讨论发生在第一幕第七场开头:众人即将离开跨年晚会回家。杰夫已经知晓妻子弗兰和他的朋友班特利发生了外遇,但未开口挑明,而是突然开始分析起《奥赛罗》中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的关系。这是戈达尔“创作灵感论”的来源。根据戈达尔的解读,对于黑人男性更喜欢白人女性这一可能,剧中的黑人女性们感受到恐惧与焦虑,并影响到她们的自尊心。但《奥赛罗》和《说方言》的互文分析不仅在于二者可能的共同之处、先后关系,也就是说,《说方言》并非对《奥赛罗》跨种族交往问题和对“嫉妒”情感的简单模仿、主题挪用或改写。作为一种策略性互文,皮诺克在《说方言》中安排《奥赛罗》的讨论有读者反应层面、文学史层面和伦理层面的深刻用意。
剖析《说方言》和《奥赛罗》的互文性,还需要从二者的差异入手。从篇幅与语境层面来说,《说方言》中对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的讨论仅出现一场,并不是贯串整部剧的关键线索。在讨论之前的第六场,杰夫明明已经知晓妻子有外遇,却只是通过暗示弗兰当晚和自己缺乏交流,并暗示弗兰像香水广告中在大雨中奔跑的女人,拐弯抹角地指责妻子的不伦行为。他又通过宣告自己修好了收音机,主张两个人应该放个假去湖区旅行,试图挽回已经失败的婚姻关系。杰夫对《奥赛罗》的分析,是他发觉弗兰心意已决后,与克劳黛特对话中的内容:“用奥赛罗的眼睛看看世界:被种族主义者包围,对年龄和外表神经兮兮,担心丢掉他的工作和头发。……他和苔丝狄蒙娜私奔,为的是融入白色世界,而她和他私奔,为的是离开那个世界……每个人都需要融入……他是最最需要融入的[6]。杰夫和克劳黛特的对话被一旁的弗兰打断,原因是弗兰听出了杰夫解读中的画外音: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影射的并非被背叛的莉拉和班特利,而是因追求符号化的差异而背叛配偶的班特利和弗兰。
《说方言》的故事设定于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现代社会,已经脱离了《奥赛罗》中的历史语境。互文性《奥赛罗》的存在是必要的,不是因为《说方言》回避不开布鲁姆式“影响的焦虑”,而是引发对《奥赛罗》和《说方言》的差异的思考本身就是一种以观众为目标的伦理策略。就形式而言,关于《奥赛罗》的讨论既不是元戏剧,也不是剧中剧,更不能代表剧作家或演员本人的观点,但这段评论打开了对经典戏剧作品的读者反应空间。
本雅明在分析布莱希特叙事剧时指出,在叙事剧为观众的参与准备的双重对象中,事件必须“能让观众在关键的地方根据自身经历加以检验”[7]。《奥赛罗》的阅读经历受到大量英国剧场观众的共享,易于引起感兴趣者的表态,而剧中的杰夫也是如此。杰夫是白人读者,但他对《奥赛罗》的认识并非陈词滥调的白人中心或《圣经》中心解读,也非如今已是新典型的后殖民阅读,而是具体的伦理环境使他认识到了班特利的错误伦理选择背后的原因。此外,这段评论也展现出早期英国戏剧中黑人形象对当代英国人的影响,并提示着观众,无论是黑人在英国的存在还是英国的跨种族交往,都不是当代社会的新现象,而是历史已久。
三、绘画互文与表征伦理批判
《火光与蓝光》(RocketsandBlueLights)是皮诺克于2018年创作的戏剧,并于同年获得阿尔弗雷德·费根奖(Alfred Fagon Award)。该剧于2020年在皇家交易所剧院首演,在三场演出后因新冠疫情停演,改以广播剧形式在BBC播出。2021年8月,此剧在英国国家剧院再次上演,其影像版本于11月上线英国国家剧院流媒体。多媒介、全球化的传播是皮诺克被英国主流剧场接受的另一重要里程碑。而评论界多聚焦于双线叙事中黑人女演员露(Lou)的遭遇,而鲜少关注另一主人公,即英国画家约瑟·马洛德·威廉·透纳(J.M.W.Turner 1775—1851)的叙事线。
《火光与蓝光》剧名取自透纳的同名水彩绘画。透纳以奴隶船为表现对象的系列绘画是贯串全剧的线索,透纳也是剧中多线叙事的主人公之一。在剧本创作早期,皮诺克通过阅读大量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对英国19世纪废奴历史中的时间漏洞和英国废奴的不彻底性产生了初步认识,发掘了英国废奴运动的时间阈限:从1807年英国国会通过《废奴法案》,到1854年先驱者号在马德拉岛被击毁,奴隶贸易并未彻底结束。《火光与蓝光》以上述时间线索和艺术史料为基础,选取了1840年这一时间节点,并在序幕就安排了对《奴隶船》的讨论。
在序幕中,美术馆中的露和艾西(Essie)两人因透纳的《奴隶船》而相识,两人针对这幅画提出各自的见解。争论之余,她们都认为透纳的创作是一种“赎罪”,并给出了同样角度的质疑:“为什么他要把这么丑陋的东西画得这么美?”[8]。以当今的“取消文化”来看,透纳也可能遭遇取消式的批判。然而,皮诺克借艾西之口强调,相比于盲目“正确”的拒绝,直面矛盾是观看者的重要任务和使命:“最初你弄不懂发生了什么。你必须看,真的看。你不能转过头去。”
皮诺克融合了历史与想象,重新塑造了透纳创作《奴隶船》《火光与蓝光》等作品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借助多线叙事,建构了跨时空、多族裔的表征责任共同体。通过想象“废奴主义画家”透纳在奴隶船上对黑人水手托马斯见死不救的经过,皮诺克提供了对透纳在艺术生涯中的知行不合一问题的多种理解方式。在想象中,对托马斯的愧疚唤起了透纳的绝对责任意识和作为艺术家的共同体情感,促使他创作出融入他者意识的《奴隶船》等作品。
然而,皮诺克并不只是从创作者的角度为透纳辩护,对《奴隶船》的讨论是批判当代艺术话语的入口。除了序幕之外,《火光与蓝光》中反复跨越时空的场景分属于两种艺术界,一个是1840年透纳所处的绘画界,另一个是2006—2007年露身处的电影界。皮诺克在戏剧中将两个不同时空的艺术界联系起来,共通的前提是她对于艺术界中殖民主义的认识:艺术表征的媒介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发展更新,但表征对象选择背后的殖民主义意识,其存在方式也顺应着时代变革而变化,发生作用的方式也更加隐匿。
19世纪中期以来,艺术批评话语建构并不断重构透纳的艺术家形象。1843年,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出版了《现代画家》的第一部分,促进了浪漫主义理论的绘画转向,也提高了透纳的声誉。到了20世纪,人们对透纳后期色彩创作的抽象性、创新性和具体技术都有了新的认识,透纳在艺术史中的地位也进一步加强。一部分研究者的关注点从图像的形式转向内容,关注艺术作品的被创作时的环境背景等,增加了艺术作品阐释的社会维度。这样的视角为透纳的《奴隶船》带来了新的解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画作可见属性与奴隶贸易历史上的联系。废奴史和艺术史建立起了协商关系,二者互相交换并补充文化文本,不断加强对透纳及其作品重要性的论证。废奴史为《奴隶船》的阐释填充了“宗”案的创作背景依据,为画作赋予了技法之外的意义。透纳则获得了废奴主义者的标签,不仅因为透纳创作了《奴隶船》等反映奴隶制历史影响的作品,还因为他和参与英国废奴运动的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等人有交往。据此,近年又有学者推测,透纳的创作也可能受到1839年再版的《奴隶贸易的历史与废除》(HistoryandAbolitionoftheSlaveTrade)的启发。1876年,《奴隶船》在拍卖中被爱丽丝·胡珀(Alice Hooper)购入,并在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展出至今,策展说明也将作品与废奴历史背景相联系。
通过绘画互文,皮诺克表达了对上述这些关联、推测和阐释的质疑,因为它们都满足了为透纳建构废奴艺术家神话的需求。皮诺克批判性思考的角度与2010年以来艺术评论界的表征伦理批评既有呼应,又有补充。艺术评论界关注的是表征对象和观看者的关系、《奴隶船》的审美化、商业化与奴隶制获利在逻辑上的相似性。而皮诺克关注的不仅是绘画本身,更是其创作者透纳与奴隶制历史互动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剧中另一条时间线上,皮诺克也借透纳传记电影的拍摄问题,批判以白人拯救者叙事为中心、忽视历史他者的废奴史表征伦理与实践。“对过去获得的认知基础越深,对当下的参与才会越出色。”[9]互文性为皮诺克将历史文本和社会现实文本并置提供了可行的文学手段,打通了经典艺术文本与戏剧文本的联系。《火光与蓝光》在与观众艺术经验构成互动的同时,通过互文讨论融入了后殖民、后现代伦理的阐释,从而引发观众对历史和当下的思考。
四、结语
一方面,皮诺克戏剧中的互文性继承了18世纪以来黑人书写中的批判性写作精神,也继承了英国戏剧的社会现实主义传统,不把戏剧停留在表现或再现愤怒的层面,而是以英国黑人的生活和艺术实践为基础,将诊断出的问题与艺术讨论交织,通过互文策略为观众打开思考和参与的空间。另一方面,皮诺克的戏剧也为不同时空的黑人发声,并为当代英国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指出可行的道路。结合经典作品、戏剧情境和社会问题的讨论重构了英国黑人的存在与思想经验,也加强了少数族裔剧作家作品内涵的哲理与智性。
对皮诺克的戏剧采取互文性研究,是以符号系统的共时结构取代了戏剧史的线性进化模式。一方面,互文性研究将作为书写符号的、高度稳定的戏剧文本从心理、社会或历史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发掘戏剧文本得以产生的话语空间。另一方面,互文性理论也为具有文化混杂性的观演关系和读者反应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从作为舞台符号的、高度变动的演出“事件”角度理解少数族裔剧作家写作的策略与思维,发掘作品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为跨文化戏剧的创作与戏剧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