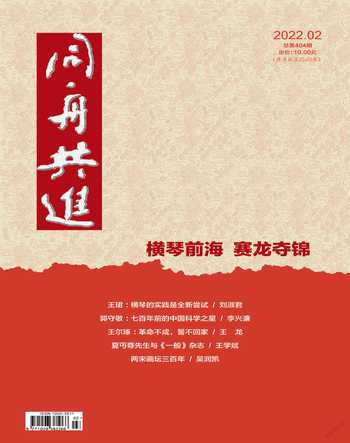张謇的情感世界
2022-03-23王斌
王斌
张謇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为建设“新世界之雏形”作出了不少开创性建树。而作为一位生活于社会巨大转型时期的历史人物,他身上同样无可避免地烙下时代的印记。这在张謇的婚姻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充满着新与旧、落后与进步、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观照张謇的婚姻情感生活,可以让我们更为立体地认识张謇,还原其有血有肉的一面。
张謇的情感生活可以追溯到他青少年读书时期。他的前半生,走过了30年漫长而痛苦的科举之路。年轻时的张謇在蹉跎考场之余,曾和几位女士萍水相逢,甚至与其中的“桐花女史”“触电”生情,有过一段浪漫之恋。“女史”这个词古已有之,意为知识女性。
早年张謇在家乡南通和南京等地拜师求学期间,结识了不少学友。同学间偶尔会组织文酒会,邀请一些略通文墨的知识女性陪伴助兴,张謇也会随大流参加。
千年秦淮河畔,文人墨客与歌伎才女之间,曾演绎出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情爱故事。1875年仲夏,正值情窦初开年龄的张謇在南京游幕和读书,秦淮河上画舫穿梭,佳丽如云,张謇在与一群同学朋友饮酒时,在一艘游船上与容貌出众的“桐花女史”不期相遇。
很快,两人有了进一步的交往。在张謇日记中,留下了他“写赠桐花联”,“同往桐花深处”等记录。又有一次,“桐花来,由窗外过……文园客方落寞无聊,不知其来之翩翩早也,故彼虽有洛神之流睇,我仍若夏统之心肠”。“桐花女史”让张謇深深着迷,几度交往下来,两人情感逐渐升温。这位长着“洛神之流睇”般眼睛的痴情姑娘,竟追随张謇来到他读书的书院。
后来,“桐花女史”慢慢淡出了张謇的生活,也从他的日记中渐渐消失。究其原因,他自责道“荒嬉已甚,岂忘三年磨折乎”,为了求取科举功名,张謇曾遭人要挟,陷入“冒籍风波”,打了多年官司才得以脱身。也许胸怀远大抱负的张謇想到了这些,才斩断了情丝。
1875年1月,张謇与家乡海门常乐镇邻村比他小三岁的徐端完婚。四五年前,两人订婚时,张謇母亲金氏就让媒人周婶去详细打听过未来儿媳的情况。徐端尽管和大多数同时代女子一样没上过学,却能干而稳重。周婶去徐端家提亲时,正是收获季节,只见徐端拿着杆称和账册,忙着向佃户收租,周婶与徐母谈话,徐端也不插嘴,是一个非常贤淑的姑娘。
徐家本来家境还算殷实,后因徐端的两个兄弟做生意亏了本,只得变卖家中田产。徐端请求家里把原来许给她的百余亩嫁妆田也卖掉偿债,还表示要放弃衣物、首饰等嫁妆。其时,张謇因“冒籍风波”赔了不少钱,债台高筑,家境困窘。张謇和徐端的婚礼也是张謇向亲友借钱操办的。
张謇儿子张孝若说,“我先母徐太夫人……到了我家以后,志趣很和我父相同,对于翁姑奉侍,异常孝顺。我父终年在外居幕奔走,每年年底才回来一月半月,有时竟不回来,家事都是她一手料理,使我父专心在外,没有内顾之忧”。和徐端结婚30多年,张謇绝大部分时间在外忙碌,前期是为了生计和仕途奔波,后来是为了创办实业等一系列事务而奔走,因而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很少。
张謇把父母起居、邻里往来等家中诸事都交给妻子。过门第三天,徐端黎明即起,穿上粗布衣服,问候公婆,把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有一次,为了调解邻居家的矛盾,徐端把自己的衣物典成银子,慷慨相助。婆婆金氏连连夸奖她是“贤妻”,张謇给她取字“倩宜”,意即秀外慧中,处事得体。
徐端持家有方,和张謇还有着共同语言,不仅为张謇解决了后顾之忧,而且她的体贴和鼓励常常给身心疲惫的丈夫很大的安慰。张謇说,“夫人虽未尝学文,而勤勉慷爽,出于天赋。方敝人之舍仕宦而求實业也,家事一委之夫人。遇极艰苦时,退而至家,夫人必有以慰其劳苦而勖其坚忍”。她十分支持丈夫的事业,并积极参与其中。1905年,张氏私立初等小学创办,徐端任校长;海门常乐镇重建颐生酒厂时,她出任厂长;张謇修造宅邸,她代丈夫督办工程;她还动员妇女名流为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募捐,自己带头捐建筑费500元、常年基本金1000元。
后来的张徐女校、南通育婴堂、幼稚园,都是根据徐端的遗愿创办的。张謇对她始终抱有敬意。在她去逝后的1910年,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市河岸新校开学,张謇莅临致辞时多次提到亡妻,说夫人当年“志愿甚雄”,日谋夜思,筹措经费,“欲女子师范养成,而各处女子小学次第而立”,乃“夫人之志,敝人义何容辞”。在张孝若眼里,父母夫唱妇随,“看见我父办学校,她也要提倡女学,就办了女师范,还在母家近边,办了一个小学校”。“她也很富于创造的观念,譬如在光绪末年她就发明女子着长袍,她先穿着,叫家人也照样做,不到一年,亲戚中的妇女都改穿长袍了。”徐端逝世后,“我父好像失掉一只膀子”。
对于徐端患病,张謇牵挂心头,四处为她请医治疗。生离死别前的那一幕,更是感人至深。1908年4月25日晚,徐端病危,弥留之际,张謇急匆匆赶来与之诀别。徐端已坐不起来了,只能示意让张謇抱她,还拉住丈夫的手,声音虽微弱却很是动情地说:“你待我不错,我也待你不错……”张謇俯身问她,有什么需要交代,徐氏声音细若游丝:“叫我如何说,我现在已说不来。”的确,一生恩爱即将就此诀别,千言万语又从何说起。她望着张謇,神色苍白,欲哭无泪,最后带着无限的眷恋逝于张謇怀里。
在给徐端的挽联上,张謇痛彻心扉地写下:“呜呼痛哉!三十五年贫贱夫妻,常将辛苦分磨蝎;几千百变忧危身世,甚矣摧伤况老鳏。”后来每年祭祀,张謇都会写下许多诗文倾诉对妻子的怀念。在自己的住所花竹平安馆内专门辟有“倩影室”,室内挂有徐端的照片,他常常独坐静对,以寄托无限哀思。
张謇一生娶过四个妾氏,都是徐端一手张罗、前后选定的。

徐端曾为张謇生过一个女儿张淑,却因惊风,不足百天就夭折了。后来,他们抱养了三哥张詧的女儿,“弱而慧”的娴儿在4岁那年也不幸患病而卒。为能延续张家香火,深受“无后为大”观念影响的徐端,先后纳进陈、管二妾,对此,张謇似乎不太情愿甚至反对,徐端便搬出公公张彭年来做张謇的工作。
不过,过门后的陈、管两妾仍未能生育,而从唐闸育婴堂领养的襄祖、佑祖则体质羸弱,且资质平平,难成大器。佑祖稍大后竟染上恶习,20多岁就死于肺病,襄祖患有骨癌,19岁即逝,这是后话。徐端为了能让张謇纳妾生子,“祷神卜筮,博访良家,尝单车晨出,风雪,夜逾半而返”,后来她索性一下子为张謇纳进吴、梁两位农家女为妾。
陈氏是张謇娶进门的第一个妾。在徐端的安排下,随庆军出兵朝鲜回来不久的张謇,在1884年春节迎娶了21岁的陈氏。陈氏身世坎坷,是张謇妻妾中命运最悲惨的一个,死后连名字也没有留下。在陈妾来归之初,张家陷入了又一轮困苦贫穷之中。张謇的日记多处留下“家中支绌”“家中乃奇窘”之类的记载。
1893年5月初,去江西贵溪看望在当地担任县令的哥哥张詧后,张謇回到海门常乐老家,当时夫人徐端、弟弟张警夫妇和侄子张亮祖皆病。后来,其他几个人渐渐康复,唯有陈氏久病不愈,并日呈凶险之状,几个月后便撒手人寰,时年不足30岁。次年,张謇考取状元、走向科举巅峰。张謇在日记中评价道,“自陈氏来归,于今九年,虽未有所出,而谨慎无过,能主中馈,内子甚赖之。即卒,家人咸惜焉”。可见,陈氏颇得徐夫人信任,在一家老小里人缘不错。
张謇纳娶的第二个妾是管氏。徐端见陈妾多年未有生育,1892年又为张謇纳19岁的管氏为妾。对于管氏,张謇的着墨更少。多年后,张謇在信中告诉友人,管氏“渐习奢好,与无知妇女往还,染嗜鸦片,诫之不悛。辄以己意出家,去而后白。恶甚而去之,求还不许”。管氏进门后也没有生育,徐端甚是着急,便继续张罗替夫纳妾,也许是管氏感到内心孤独空虚,染上毒瘾,难以戒除,后来遁入空门,吃斋念佛。
吴道愔是张孝若的生母。张孝若说,“我父到了将近四十岁还没儿子,她(徐端)很为着急。‘无后’是中国家族祠度最看重的一件事,也是妇人分内应该担心的一件事,于是为我父纳我母……”1894年3月,也就是在张謇考中状元的前几个月,张謇亲往南通乡下石港与好友议商纳妾之事,娶如皋吴道愔、梁曼容两女为妾,并行聘礼。
张謇在考中状元后不久,因其父辞世,守孝三年,遂于1897年才将吴、梁二妾迎娶回家。次年正月,吴道愔便生下张孝若。母凭子贵,她在张家的地位随之上升。1908年,徐端病故,吴道愔被立为正室夫人,掌管家务。对于吴道愔,张謇留下的叙述并不多。反而是张孝若对自己生母的描述极为详细,说她“助徐大夫人管理家事,很得器重。生我以后,抚育我受尽劳苦,自处谦谨,极有分寸……很知礼节,尤富于美术技能,凡家庭粗细工作无一不能”。她还“周济了许多贫苦的人,世俗妇女的习惯,她丝毫没有”。张孝若之子张绪武也印象深刻地说:“我亲生祖母吴氏端重庄严、美丽富态。她经常穿着自己设计的长长的连衣裙,穿着小脚皮鞋。夏天拿把茄扇,真是仪态万千。”
梁曼容是与吴道愔一起被纳为妾的。进门之初,她也颇为张謇看重,为她写下“曼容亦有言,天解从人愿”的诗句。在张家十多年,梁曼容没有生育,她和吴道愔分工明确,吴氏主要负责抚育亲子张孝若,梁氏负责抚养养子佑祖、襄祖。

而关于梁曼容的最终归宿,张謇在给友人的信中作过交代:“内子卒,一妾稍肆,好詈仆妪,不白主人,辄予人物,训之不悛,恶其专愎而大归之。”这里的“一妾”,指的就是梁曼容。梁曼容和张家矛盾激化,应是1908年徐端去世后,也许是因为一同进门的吴氏被扶正,梁氏心有不甘,在家里弄出口舌来,对张謇的批评和劝导不以为然,还以退为进地提出要回娘家奉养老母。
1909年4月,张謇同意梁氏的要求,并给她写了两封信,“一法家言,一慈善家言”,一封强调妇道家规,另一封强调做人要以慈悲为怀。不过,梁曼容回娘家后,仍喋喋不休地讲别人坏话,因“恶其诬也”,张謇又去信教训她,口气明显比上次重多了。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梁曼容再也没有回头。
在张謇的婚姻家庭观中,对名分看得很重。徐端是明媒正娶的妻子,张謇对她始终尊重,并留下很多赞美她的文字,每逢其生日,张謇都要纪念。而其他几个妾则没有这个待遇,除了在陈氏死后三年,张謇“附奠陈妾”外,管氏和梁氏均不知所终。
张謇晚年和沈寿(1874—1921)的交往常为后人所谈及。出生于“苏绣之乡”江苏吴县的沈寿,自创“仿真绣”,被誉为“针神”。1914年,张謇在南通创办女红传习所,40岁的沈寿应聘担任所长兼教习。
1916年11月13日,张謇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沈寿,“为沈雪君书联‘绣段报之青玉案,明珠系在红罗襦’”。这副对联的上、下两句分别出自东汉张衡的《四愁诗》和唐代张籍的《节妇吟》,显然,两句诗都隐含男女之情。
此后,沈寿不时出现在张謇的日记里,且频率越来越高。沈寿体弱多病,张謇在日记中留下“复病”“复不适”“又病”“渐癒”“忽晕厥,甚重”等诸如此类的几十处记录。特别是在沈寿去世前后的5个月内,张謇日记中与沈寿有关的内容占到1/3的篇幅,涉及她的病情、去世和善后等,流露出深深的不舍与思念之情。同时,两人书信往来频繁,如1918年3月24日至30日的一周内,张謇给沈寿写了5封信,从饮食、休息到请医看病服药,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心。张謇日记中最后一次出现沈寿,则是她殁后的第四年,即1925年3月1日:“至雪君墓。”

张謇亲自教授沈寿学诗,挑选了一些古诗编成《学诗读本》,开篇是一首情意绵绵的《越谣歌》:“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在两人诗词往来中,张謇笔下常会出现“比翼鸟”“比目鱼”和“鸳鸯”等一些极富情感意蕴的词,如他的《谦亭杨柳》:“记取谦亭摄影时,柳枝宛转绾杨枝;因风送入帘波影,为鲽为鹣那得知?杨枝丝短柳丝长,旋合旋开亦可伤。要合一池烟水气,长长短短护鸳鸯。”
而沈寿则是含蓄的,一方面,她借自已所写的诗《垂柳》,表达出“本心自有主,不随风东西”的态度,另一方面,她内心对张謇充满感激之情,在《奉和啬师谦亭摄影》诗中,她写道,“谁知六尺帘波影,留得谦亭万古心”。还以自己的青丝作线,抱病精心绣制了张謇的手迹“谦亭”。
沈寿患病后,张謇为她寻医问药,延请名医,确定医方,“亲伺汤药”。在病榻旁,沈寿口述,张謇记录,将沈寿的刺绣艺术经验记录整理为《绣谱》,“无一字不自謇出,实无一语不自寿出也”。1921年6月,沈寿在南通病逝,时年47岁。张謇把她安葬在和她家乡隔江相望的马鞍山南麓,亲自主持沈寿去世后大殓、过七、百日、生忌、公祭等各個环节的活动,还一口气写下48首怀念沈寿的《忆惜诗》,常常独自坐在沈寿墓前,直至夕阳西下。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