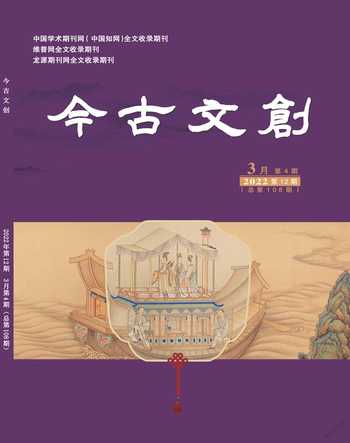梁启超国民教育思想的衍变
2022-03-22于海英
于海英
【摘要】19世纪末,伴随着西学东渐,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逐渐传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相碰撞而引起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实现中国近代化为目标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着救国救民的出路,并逐渐意识到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其中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以“新民”为理念,为当时的国民教育指明了方向。他在《新民说》中发表了一系列国民性改造的文章,对道德的公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关于公德私德的讨论,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对公私道德讨论的序幕。众所周知,梁启超的国民教育观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新民说》从《论公德》到《论私德》,他的国民教育观经历了从以公德为重到以私德为先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探索梁启超国民教育观的流变,以期为当今社会道德的建设提供一点建议和思考。
【关键词】梁启超;私德;公德;国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2)12-0059-04
基金项目:江苏师范大学2017年度博士学位教师科研支持项目(17XLW025)的阶段性成果。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深陷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各界开展了救亡图存的运动。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相继创刊《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并以此阵地广泛介绍西方新思想、新文化,与此同时大力倡导国民性改造,期待“新民”的诞生。他将救亡图存作为终极目标,致力于解放国民思想,塑造新型国民,开启国民智慧。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可以说离不开梁启超的努力。在清末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过渡过程中,梁启超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新民说》是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一系列文章,时间跨度从1902年2月到1906年1月。梁启超的《新民说》在近代中国国民精神的形成史上是一重要篇章。正因为此,学界对《新民说》的研究有很多积累①,研究内容涵盖《新民说》的各个方面,成果颇丰。
在《新民说》的一系列文章中,梁启超对如何塑造新的国民即新民,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公德与私德的关系也是其探讨的重要内容。《新民说》前期的1902年对公德的宣扬转而到1903年对私德的强调,可以说梁启超言论中关于国民教育的论述存在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本文试图以这一问题为出发点,分析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在公德私德的建构中前后相互矛盾的原因。看似矛盾的梁启超的思考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和谐社会发展可以提供哪些有益的借鉴?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探讨以上问题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德——一种道德革命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关于《新民丛报》的创刊宗旨,我们可以从《本报告白》中窥见一斑。《告白》中称:“本报取名《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 ②梁启超认为单纯的制度的变革并不能实现中国的根本性变革,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国人的精神的变革。梁启超基于这种现状认识,提出了智育和德育两张处方签。
面对中国生死存亡的危机,梁启超把“新民”当作中国的首要任务。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基于对戊戌变法的反思,意识到无国民的觉醒,建立近代民主国家只是空谈。而当时中国的民众恰恰缺乏的就是独立的精神和国家思想,基于此,梁启超将思索的中心转向普通国民的培养,也就是说如何塑造“新民”的问题。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了公德私德这一对概念③,对公德和私德进行了重新界定。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 ④(P660)。“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④(P660)“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 ④(P662)为此,梁启超指出“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新民出焉” ④(P662),在这里,梁启超提出“发明一种新道德而提倡之” ④(P662),梁启超还提出了“道德革命”的概念,可以看出,梁启超提出以一种道德革命的形式,即以公德为核心理念铸造新的国民。他在《新民说》中指出“中国之新民”应该具有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合群、自由、进步等能力,这些能力都是公德的具体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认为树立公德的目的就在于利群。这个理念贯穿《新民说》的始终。正如他在《论公德》的最后所指出的那样“本论以后各于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为纲,一以贯之者也” ④(P662)。这里的“群”可以理解为民族国家。⑤可以说“群”即国家思想的养成是梁启超国民教育观的核心所在。
梁启超在《新民说》初期的1902年提出以公德为重,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国民在公德上却表现得十分不健全,且国家意识淡薄,这与救亡图存的主旨极为相悖,因此基于这一现状,梁启超开始大力宣扬公德的优点。
如梁启超自己所说“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 ④(P657)。他强调群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强烈认识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然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需要每个国民能力的提升,所以说对梁启超来说“新民”就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那如何塑造“新民”?在梁启超看来首先要德性的更新。具有新的德性的国民才能真正实现救亡图存这一目标。而这里的“新德”首先就是公德的培養。“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④(P661),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对公德、私德的界定⑥,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注重个人修养和德行,而公德则追求群的完善和群中的个人“合群”的能力。“无私德则不能立……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 ④(P660)。梁启超认为“国也者,积民而成” ④(P655),国家是由国民组成,公德和私德都是个人不可或缺的品质。然而,梁启超同时也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偏重私德而轻视公德,“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 ④(P660—661),无论是“温良恭俭让”“克己复礼”,还是“知耻慎独”,儒家关于私德的教育已经很完善,然而以“束身寡过主义”为中心的传统儒家教育使得“我国民中无一人视国事如己事者” ④(P662),由此,提倡公德教育,才能新民,才能有新制度,新国家。
以上所述可见,《新民说》初期的1902年,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中国传统的私德教育已无法适应建立民族国家的需要,所以倡导道德革命,在国民教育重大力倡导公德教育,将培育公德作为新民的第一要务。
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论公德》对公德私德的讨论中,虽然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的旧道德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仍然认为仅用公德也并不能完全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没有私德的公德依然是空中楼阁,并没有否认私德建设的必要性。
二、私德——公德之根本
在《新民丛报》创刊之初的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公德实现方法的“新民说”的文章之后,1903年2月,应美国华人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访问。梁启超考察了当地华人的生活状况和美国的社会状况,他在肯定美国共和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也看到了其制度黑暗的一面,可以说梁启超此次访美,打破了他对美国共和制度的幻想,不再迷信共和。访美归来后的1903年8月,梁启超发表《论私德》,在文中他不再一味提倡公德,转而强调中国传统的私德对于国民教育的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为何访美之后,为何转而强调私德?梁启超在晚年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到自己的善变时说:“然其保守性和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⑦可以说梁启超对于自己思想的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然而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却发现他确有不得不变的理由。其原因可以归结为此次的访美之行,梁启超看到了新党的腐化堕落,从而放弃了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⑧。正如陈来所说,梁启超对私德的讨论,是由于一年多对政治领域的所见所闻的心得所引发,让他对道德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⑨梁启超访美归来,转向对私德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梁启超对“破坏主义”的反省
梁启超在1899在《清议报》上发表《论破坏主义》,认为“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认为破坏断不可免。然而梁启超面对一些革命者以“公德”名义践踏私德的言论和行为表达了不满⑩。看到一些革命者假借公德之名,而实则充满功利主义的心态,妄谈爱国而私德不彰,表达了极度的忧虑和失望。
访美归来后,梁启超认为中国应专注于建设,不能专言破坏。“破坏之必能行于今之中国与否为别问题,姑且具论。而今之走于极端者,一若惟建设为需道德,而破坏无需道德,鄙人窃以为误矣。” ④(P779),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放弃了之前激进的破坏主义,认为建设和破坏不可分离,两者都不能离开道德。
《论私德》文章发表之后,对于自己之前极力主张公德,以公德为重,现在转而重新回归到中国传统的私德,以私德为先。对于这一转变,梁启超自己做了如下的解释:关于私德,我们的圣贤论述详尽并且践行得很好,无需自己再费口舌,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举国上下打着公德的旗号,做出很多不利于国不利于群的事,鉴于这种情况,自己有必要对私德的重要性做出说明。
(二)国民教育并不能仅凭“公德”而成
梁启超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意识到他以培养国民公德为手段,改造当时中国的国民现状,实际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现实效果。他认为以公德来塑造国民,如同“磨砖为镜,吹沙求饭”,谈德育,虽然需要西方的新道德来补充,但前提条件是国民教育大兴之后,并非一朝一夕而成。现在仅凭新道德的输入来谈国民教育,只不过是一句空言。在这里,梁启超否定了在《论公德》中提出道德革命论,意识到西方的道德有其形成的社会原因,不能轻易把西方道德用在中国国民的身上以图改造国民的性格。
既然新道德即西方的公德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无法完成“新民”这一国民教育的任务,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梁启超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提出从我们固有的私德入手来改变现有的困境。梁启超在《释新民之义》中就曾指出,中国之所以在世界上存在于千年,是因为我们拥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淬厉”即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 ④(P714),如梁启超自己所论,想要铸造新的國民,必须以培养国民个人的道德为第一要义,私德是国民道德培养的基础,梁启超肯定了中国传统儒家道德在国民道德教育中的积极意义。
(三)以智育为重的德育教育对培养新民的德性收效甚微
梁启超认为,现在很多人提倡的道德教育,实则是“智育的德育”,所谓的德育教育实际上并没有摆脱智育的范围。“而名德育而实智育者,益且为德育之障也。以智育蠹德育,而天下将病智育,以‘智育的德育’障德育,而天下将并病德育”④(P722),中国德育教育的障碍在于偏重智育,实际是以智育代替德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梁启超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偏重智育而轻视德育。梁启超认为智育注重的是知识的积累,而德育是实践践行。他真正想要强调的是如何求学问,学做人。智识固然重要,但是道德更为重要。智识离不开道德,必须以道德为本源。道德是立人之本,只有以道德做内在的精神支撑,才能保证经世的动机和方向的正确。
(四)私德的培养——取诸阳明心学,“正本、慎独、谨小”
梁启超在《论私德》中,详细论述了私德之所以堕落,主要有专制政体之陶铸、近代霸者之摧锄、屡次战败之挫沮、生计憔悴之逼迫、学术匡救之无力等④(P714—718)原因,论证了坚持旧道德的合理性和强调培养私德的必要性。那么如何培养私德?梁启超依据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来论述“正本、慎独、谨小”的意义。
关于正本,他依据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抨击时下的功利主义思想,他从爱国的角度出发,认为那些嘴上谈爱国,而行动上却不爱国的人,不是真爱国,是“伪爱国者”,他们爱国论者的言行,充满着功利主义,名爱国,实在“济其私,满其欲”。这些人的爱国心被名利之心所侵蚀,没有下苦功夫修身。因此梁启超强调,培养私德本源在于正本清源,修身治心,在本源处消除功利之心,真心爱国。
关于慎独,梁启超依然根据“拔本塞源”论,以良知为本体,以慎独为致之良方。他所谓的慎独的方法,“必收视返听,清其心以对越于神明;又必举其本日中所行之事、所发之念,而一一反省之,使其正直纯洁之良知,不期而自然发动。” ④(P724)只有这样才能“涵养、省察、克治”。
在1905年出版的《德育鉴》中,梁启超对慎独的方法做了详细的论述。关于“慎小”,梁启超是针对小节无害论而提出“谨小”,“大德不逾闲,小德可出入,此固先圣之遗训哉” ④(P724),他认为大的道德原则不可违背,小的行为细节则不必苛求。
然而与此同时,他同样强调纤毫的险黠之心,最后可以发展为卖国的大节,也是需要注意的。他提出了“正本”“慎独”“谨小”三项德育修身的要领,作为本身勉励自己的内容,提供给大家参考。他希望人们能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古人嘉言作为修身的条目,自用自行,安身立命。
梁启超访美归来后的1903年,从公德为重转向私德为先,他开始重新审视私德的意义,故而写了《新民说》的第十八节《论私德》,对此前的公德说作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正,更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个道德结构和国民教育中的基础意义和重要价值,主张培养国民道德应以培养私德为先。
梁启超认为,私德败坏的原因并不在于对公德的过分侧重,而恰恰在于公德所需的条件尚未达到⑪,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梁启超对私德与公德的关系作了重新思考。他在肯定私德重要性的同时,在私德修养方面提出了“正本”“慎独”“谨小”三项主张。
三、结语
中国国民教育的近代化,伴随着与西方近代文明的激烈碰撞,但与此同时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纳入了近代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中,拥有这一特质的中国国民教育的近代化,在近代知识吸收的过程中不可否认有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对国家存亡的危机,梁启超认识到必须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新民说》中所体现的国民教育观,同时也反映了吸收西方文明的和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和摩擦。
梁启超在《新民说》初期,国民素质的提升是国家振兴和民族独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倡导道德革命,大力提倡公德教育,利群是公德教育的目标导向,以公德实现对新民的塑造。在公德与私德两者的关系上,梁启超主张无私德不能立,无公德不能团,然而在侧重点上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侧重私德教育,缺乏公德教育,因而体现以公德为重的一面。
然而以1903年访美为契机,梁启超放弃了之前激进的破坏主义,搁置公德,转向对私德的讨论,注重修身的私德成为他最为关注的焦点。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新民说》中对公德私德的道德讨论,爱国主义是梁启超国民教育观所阐述的基本立场。无论是利群的公德教育,还是正本溯源的私德之道,都体现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转型中的深刻思考,同时也体现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现实考察。
与此同时,梁启超的国民教育观深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在重拾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觉的今天,梁启超在如何处理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方面给我们的启示,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学界对梁启超《新民说》的研究成果分类,特别是国内学者的研究,具体可以参见邓铭英、王根的《梁启超塑造新民的道德路径及其现代启示》(《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4期)。笔者在这里简要介绍日本对于梁启超《新民说》的相关的研究。如狭间植树从梁启超执笔《新民说》时的历史状况出发,在强调日本所起的媒介作用的同时,对《新民说》加以考察。(狭間直樹「「新民説」略論」,见狭間直樹編『共同研究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の受容と明治日本』,みすず書房1999年版,第79-106页。)小野川秀美认为,梁启超从救亡图存的问题意识下,有必要对国民进行改造,主张通过国民的变革,来建立国民国家。(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2),平凡社2010年版,第74-81页。)阿部洋认为,梁启超的《新民说》为中国的近代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阿部洋「清末における国民教育観の成立:梁啓超「新民説」をめぐって」,见『日本教育学会大会研究発表要項』18,1958年8月,第23-24页)。野村浩一指出《新民说》的最初部分,最能系统地体现《新民丛报》的理念,梁启超1903年访美归来后立场的转换应该从思想的政治的维度进行考察(野村浩一『近代中国の政治と思想』,筑摩書房1964年版,第176页)。
②《本报告白》,《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③关于公德私德概念,吴宁宁认为梁启超是受了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影响。(吴宁宁:《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困境解读》,《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3页。)陈来认为关于公德私德的观点也受到边沁的启发。(陈来:《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文史哲》2020年第1期,第11頁。)
④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⑤对于《新民说》中“群”的理解,陈云度认为《新民说》中“群”既是社会、国家,又是使人聚合的能力。(陈云度:《善“群”成“己”:以〈新民说〉之“公德—私德”论为视角》,《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61页。)
⑥关于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论,陈来认为梁启超提出了区分公私领域,提出了有别于私德的公德,然而梁所说的公德大都是爱国利群的政治公德,而实质上并不属于道德,而政治道德压抑了私德的发展,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陈来:《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文史哲》2020年第1期,第5页。)陈乔见从美德统一性的角度,认为,从《论公德》到《论私德》,梁氏诚有“从公德到私德”之转向,但他自始至终都相信道德品性或品格具有统一性,认为私德与公德之间具有某种连续性和关联性。(陈乔见:《清末民初的“公德私德”之辩及其当代启示——从“美德统一性”的视域看》,《文史哲》2020年第5期,第37页。)蔡祥元则认为: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启蒙学者从公私德的区分出发,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蔡祥元:《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文史哲》2020年第3期,第5页。)
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⑧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219版。
⑨陈来:《梁启超的“私德”论及其儒学特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60页。
⑩李喜英:《梁启超〈德育鉴〉思想的现代价值》,《齐鲁学刊》2020年第5期,第26页。
⑪陈云度:《善“群”成“己”:以〈新民说〉之“公德—私德”论为视角》,《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64页。
290150078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