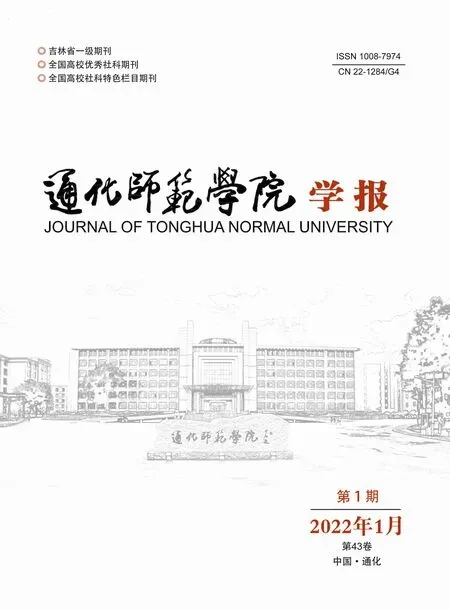《风土什志》中的《鹦鹉夜谭》研究
2022-03-18赵亚宏
赵亚宏,封 羽
一、《鹦鹉夜谭》栏目介绍
(一)《鹦鹉夜谭》的来源及译者
《鹦鹉夜谭》是刊载于李劼人主编的《风土什志》中的栏目之一,贯穿《风土什志》从1943年9月出版到1948年10月终刊的三卷14期。《风土什志》创刊号上的一则编者按揭示了此栏目的来源:
鹦鹉夜谭一书,原系波斯文体,书翰先生早岁游亚拉伯时,以重金购得,盖该书已成海内孤本也。全书包含寓言五十二,由一鹦鹉口中逐夜讲述,其情节离奇,故事动人,字句隽永,结构紧凑;故多诲人之言,其文学价值与“天方夜谭”相伯仲,堪称佳构。书翰先生幼即常游近东,精回藏及波斯土耳其语文,四十而后始习中文,今先生已八十余岁矣!以先生高迈之龄尤从事译作,其精神实堪钦佩!原译为文言文,经编者改译后,全文约三十余万字,将次第在本志发表。[1]
《风土什志》所刊载的《鹦鹉夜谭》故事,来源于刘书翰早年游历亚拉伯(即阿拉伯)时所购得的“孤本”。编者指明《鹦鹉夜谭》的故事构成形式、语言风格和文学价值,并向读者介绍促成其最终成型的两次转译。译者刘书翰精通外语,熟悉文本,具备稳固的知识结构和充足的翻译能力,将寓言由波斯文体翻译为文言文,此为第一次改译。编者又将文言文翻译为白话文,以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此为第二次改译。另外,《鹦鹉夜谭》的译者名单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为《风土什志》的第1期到第6期,此阶段译者只有刘书翰一人,署为“刘书翰译”;第二阶段为《风土什志》的第7期到第8期,此阶段译者加入了李劼人的秘书即主编之一——谢扬青,此时署为“刘书翰、谢扬青合译”;第三阶段为《风土什志》的第9期到第14期终刊,此阶段刘书翰和谢扬青应该对原文内容进行过编辑,所以署为“刘书翰、谢扬青编译”。
《风土什志》在创刊号的《征稿简约》中明言:“我们需要真实趣味的内容,我们需要描写生动的记事”[2]。“趣味”及“描写生动”才是其择稿的重要标准。作为寓言,《鹦鹉夜谭》之故事显然难以契合《风土什志》对“真实”的要求,但编者依然对《鹦鹉夜谭》给予极高的评价,甚至声称“其文学价值”可比肩“天方夜谭”。因此,《鹦鹉夜谭》又绝非仅仅凭借趣味性而得到编者的青睐,而是以其“诲人之言”和“文学价值”刊登于《风土什志》之上。
(二)《鹦鹉夜谭》的版本研究
在《风土什志》创刊号上的《鹦鹉夜谭》板块,有“波斯寓言”四字。波斯是伊朗在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旧称音译,虽在《风土什志》上《鹦鹉夜谭》被标为波斯寓言,然而《鹦鹉夜谭》和印度《鹦鹉故事七十则》却有着明显的联系。《鹦鹉故事七十则》是用梵语完成的古印度故事集,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模式,以鹦鹉的口吻讲述了七十则故事,形制与《天方夜谭》相似。在《谈印度故事》(《印度故事集》俄文译本序言)中提到:“‘鹦鹉故事’之基本的但非唯一的渊源,是用梵文写的和标题为‘轮加萨普塔谛’(照字面讲,意为‘鹦鹉七十’,即‘鹦鹉故事七十篇’)的古老的印度故事集。”又说:“第一部能够把日子确定,然而用的不是梵文而是波斯文加工写成的‘轮加萨普塔谛’,是一三三〇年西阿—乌德—丁·那贺夏比撰写的名著‘吐提·那美’(意为‘鹦鹉之书’)……那贺夏比(即“纳克沙比”,翻译的不同)的‘吐提·那美’和‘轮加萨普塔谛’却迥然不同。章数减为五十二,……”[3]7-8由此可知,这种鹦鹉故事集有许多版本,梵文撰写的“轮加萨普塔谛”有七十则,波斯文撰写的“吐提·那美”有五十二则。后者与前者存在诸多差异,在“吐提·那美”中,来自“轮加萨普塔谛”中的有些故事“被删削”,有些故事被“合并”或者被“分裂成彼此独立的故事小组”,有些故事被来源于其他印度故事集的故事所“代替”,有些故事则可能是“新创造”。“人物的名称”“活动的场所”“许多小节的名目”乃至“某些故事的情节结构”都被更动,可以说“文章全部基本上经过重编”。[3]8据编者按,刘书翰所购之书是“波斯文体”,全书有“寓言五十二”,并属有“最雅耶·赖舍备著”的字眼。潘珊在《鹦鹉夜谭——印度鹦鹉故事的文本与流传研究》中通过研究推论,《鹦鹉夜谭》所依据的底本是“纳克沙比”版本,即上述“吐提·那美”版本。[4]12具体来说,《鹦鹉夜谭》第七则——《奇士——耶乐艾》明显带有故事“合并”的痕迹,这个故事可以分为两个小故事。其一可以概括为:耶乐艾帮助乞丐德拉伟舍追求公主;另一则可以概括为:耶乐艾井底奇遇。前者和后者除了都出现耶乐艾之外,其故事内容并无直接联系,两者之间的过渡部分原文如是:
海折思听到这里,她插嘴问鹦鹉道:“喂,鹦鹉!你会如耶乐艾博士帮助那乞丐一样的成全我吗?”
“耶乐艾博士,可说是这盖世的奇人,他不仅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婚姻,而他那奇妙的事,还多着哪!”鹦鹉佯装没听见,又以另一故事逗引她。[5]
由上,过渡段之前所述是耶乐艾博士“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故事;而过渡段之后的内容则是耶乐艾其他的“奇妙的事”,后者是“另一故事”。因此,这第七则故事应该属于“合并”的一类。
据编者按,译为白话文的《鹦鹉夜谭》篇幅“约三十余万字”,但由于战乱、印刷等问题,《风土什志》只断断续续出版了14期,因此见于刊物的《鹦鹉夜谭》数量也只有十四篇,字数不达预告中的一半。另外,通过比较《鹦鹉夜谭》《印度鹦鹉故事》和《鹦鹉传奇》等译作,可发现这些译作往往有类似的情节结构和相同的题目,因此《鹦鹉夜谭》中没有刊载的内容大致也不出其外。事实上,早有学者对《印度鹦鹉故事》和《鹦鹉传奇》进行比较[6];也有学者注意到维吾尔文版《鹦鹉故事五十二则》[7]和蒙古民间口头流传的《鹦鹉的故事》[8];潘珊对“鹦鹉故事系列”的对比研究中,《鹦鹉夜谭》也只是淡淡一笔[9]13,这说明《风土什志》中的《鹦鹉夜谭》始终是容易被忽视的存在。
括而言之,《鹦鹉夜谭》的底本由刘书翰于亚拉伯游历时所购,此类“鹦鹉故事”流传历史悠久,版本众多,《鹦鹉夜谭》所依据的当是纳克沙比以波斯语翻译的“吐提·那美”版本。
二、《鹦鹉夜谭》的故事类型
《鹦鹉夜谭》所依据的“鹦鹉故事”版本篇目过百,但由于《风土什志》刊物出版期数本身的限制,见刊者不过十四。潘珊在对比刘书翰和格兰斯的故事编排时指出,这“两者至少有一位在翻译时变动了原本故事的次序”[4]13,笔者认为《鹦鹉夜谭》的目次应当经过了重新编排。可见,第9期至第14期的作者署名皆为某某“编译”,而此前作者署名要么为某某“译”,要么是某某“合译”。这种作者署名的变化和对“编”字的注重,明显体现出报刊编辑在报刊内容编撰上的严谨性。因此《鹦鹉夜谭》绝非完全依据底本一板一眼进行翻译印刷。通过对比波斯语译本的《鹦鹉的传说》与《鹦鹉夜谭》的目次与内容,笔者发现,在谢杨青加入《鹦鹉夜谭》的编译团队之前,《鹦鹉夜谭》和《鹦鹉的传说》编次基本一致。这些内容除了主人公名字不同,地点不同,其情节结构基本一致,相似度极高。
潘珊对手存波斯语译本《鹦鹉的传说》35篇(因对合并故事有所拆分,总篇目最终计为38篇)进行故事分类,得出结果为“动物类15篇,爱情类14篇,智慧类4篇,社会系统类3篇,贪婪之人类2篇”[4]135。据此分类标准,可对《鹦鹉夜谭》的故事类型进行划分。在划分之前,首先应明确《鹦鹉夜谭》的篇目,由于前文已提及部分篇目在内容上存在明显的“拆分”现象,第一则《海折丝小姐的故事》被拆分为《长生坠入爱河》和《商人之妻与鹦鹉》,第七则《奇士——耶乐艾》被拆分为《耶乐艾帮助乞丐追求公主》和《耶乐艾井底奇遇》。因此按故事文本来看,《鹦鹉夜谭》共计16篇。动物类2篇,分别为《商人之妻与鹦鹉》和《神鸟》;爱情类4篇,分别为《长生坠入爱河》《一个贞洁的女人》《美丽的女神》《耶乐艾井底奇遇》;智慧类4篇,分别为《金匠与木匠、偷藏金像》《王妃谗言害太子》《木雕鹦鹉惹风波》《公主巧智赎珠宝》;社会系统类5篇,分别为《杀子赎君罪》《耶乐艾帮助乞丐追求公主》《沙漠王怕食长生果》《海王登陆赴宴记》《音乐测验》;其他类1篇。第十四则《音乐的故事》主要讲了音乐的来历,虽然文末仍有“诲人之言”,但是两部分关联度不高,无法归入上述种类,故此则独立分入其他类。
两相对比,《鹦鹉的传说》38篇中有15篇动物类故事,其中前14篇有8篇动物类故事,而《鹦鹉夜谭》却只有2篇。这2篇故事都非单纯以动物为主角,人的出现对于故事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些完全以动物为主人公的故事消失不见。这种变化很有可能是编辑在目次编排时调整顺序而出现的结果。
三、寓理于言
(一)典型人物形象凸显的女性观
在经过本土化的调整之后,《鹦鹉夜谭》更多的是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在《鹦鹉夜谭》人物群像中,女性形象占据重大篇幅。《鹦鹉夜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方式趋同,即这些女性往往在男性视角之下被异化。但凡涉及性,女性便成为淫荡的代名词,而那些无关性描写的女性,又取得某种神化的特质,符合生活真实的女性形象却难以窥见。总体来看,《鹦鹉夜谭》虽有对女性的极端化书写之嫌,但其故事结构完整,情节精彩,语言灵动,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其女性观彰显于这些以人为主的寓言故事之中。
《鹦鹉夜谭》在大故事嵌套小故事的“连环穿插式结构”中展开叙述,从作为框架的大故事——海折丝意欲出轨来看,故事的开篇便把海折丝定位为爱情的背叛者。在第一则《海折丝小姐的故事》中,海折丝在丈夫离家之后,对星德城会长的儿子产生爱意,以“触迷”“勾搭”“燃炽着的欲火”“淫邪的愿望,谁也不能阻止她奔放的情感”等表述极力渲染海折丝那难以控制的情欲。每则故事都以海折丝小姐意欲出轨起始,以海折丝小姐在惋惜不能与情人相会之中落幕。在对“欲”的反复强调下,海折丝已然成为“欲”的化身,成为“淫魔”“荡妇”,而失去作为人的自制力。
在《鹦鹉夜谭》第八则《王妃谗言害太子》中,王妃也成为极力勾引新王的“欲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海折丝”抑或“王妃”,她们都已为人妻,却因无法压抑内心的欲望而背叛丈夫。寓言强调王妃勾引新王的种种行径,使其迅速成为一个寡廉鲜耻的负面形象。反观新王却始终不被王妃所诱惑,克己复礼,品节高尚。最后新王为了表示自己的立场,对其怒目而视,选择“离开这谄媚的人妖”。
“鹦鹉故事集”各个版本都塑造出大量的负面女性形象,寓言通过渲染女性鄙劣的一面,妖魔化和丑化女性形象,将女性置于男性对立面,引起男性对女性的警惕和强化对女性的偏见。《鹦鹉夜谭》与其他“鹦鹉故事集”实际上都完成了一种对女性刻板印象的重复和强化。有学者指出,在神话故事中,“男性在神话中是正义、勇敢、坚强的化身,而女性在神话故事里不仅被视为男性的变体、附属,而且被当作万恶之源,始终与灾祸、邪恶、胆小、柔弱等不良品质相联系”[9]。《鹦鹉夜谭》中此类被妖魔化的女性,实际上正是各民族留存且延续的对女性刻板印象的一种复现。这些故事将男女关系置入二元对立系统之中,通过突显其虚伪狡诈、放荡纵欲的一面,最终对女性形象妖魔化。
另一方面,《鹦鹉夜谭》中也出现了被神化的女性形象。她们往往外貌靓丽、智慧过人、无失德行为,以近乎完美的形象出现于文本之中。《鹦鹉夜谭》第十二则《公主巧智赎珠宝》便塑造了一个智慧超群的公主形象。故事呈现了一位泥匠挖掘出了一颗珠宝,计划献给国王,但珠宝在旅途中被四位旅伴之一所窃取。在臣僚和国王严刑逼供却无任何进展之时,公主选择了与严刑逼供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她对四位旅人加以特别的照顾,以“仁厚、宽恕、这种异乎寻常人的顾盼”来获取四人好感,再通过讲述故事,提出问题,从旅人的答案中判断他们各自的价值取向。这则故事突出描写了国王和臣僚找窃贼时的无能为力,在群臣无奈之际,公主独自解决了难题,凸显了公主的聪慧与睿智。在对国王臣僚和公主两种人物形象的对比中,寓言重点关注“智慧”和知识的重要性。
第四则《一个贞洁的女人》,赖舍克勒从军之后,妻子为保证自己不会出轨,递交丈夫一朵玫瑰,声称只要自己不失节,这朵鲜花便不会凋谢。寓言中赖舍克勒太太既温柔贤淑又美丽动人,而那朵试验贞洁的玫瑰又明显带有神奇色彩,以常开不败的鲜花预示其贞洁,伴随着这朵玫瑰的现身,赖舍克勒太太的能力和品行都被神化。在这种叙述中,她已俨然与生活真实脱节,被塑造成为披着神圣外衣的理想人物了。
第七则《奇士——耶乐艾》,乞丐德拉伟舍向柏翰斯国公主求婚成功。其中乞丐发出“爱情是没有富贵贫贱分别的”爱情宣言,所彰显的是突破阶级的爱恋,其中渗透着初步的自由恋爱观念。然而结局却是国王并没有询问公主意见,认为公主婚姻的最终决定权不应在公主手里,将女性自主的婚恋权移交到义父“耶乐艾博士”手中。这则寓言反映的是男性对美好女子的一种渴求,这里的恋爱自由仅限于男性对女性的追求,在女性角度,它依然是一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这也是男性中心思想在文本中的具体呈现。
第六则《美丽的女神》,竟然直接由男人创造出一位女神。这则故事里木匠给予了“女神”身体,裁缝缝制“女神”的衣裳,银匠打造了“女神”的首饰,道学家祈祷“施命的真宰”。虽然女神并未被男性占有,但它体现出一种男性创造女性,女性应附属于男性的想法。
如上所述,《鹦鹉夜谭》出现了两类典型的女性形象:一是被妖魔化的女性;二是被神化的女性。归根结底,《鹦鹉夜谭》中的女性都是在男性视角下被塑造出的人物形象,她们就像海折丝一样,被困在“屋子”里,从来没有走出去。
(二)复杂社会关系背后的“忠义观”
《鹦鹉夜谭》呈现了一个涉及各种复杂关系的社会结构。文本通过寓言的方式,对理想中的人际关系进行设想,又通过对这些关系的探讨,书写对理想社会的构建。
《印度鹦鹉故事》的前言页《谈印度鹦鹉故事》中,谈及这些故事的作者大多数是“宫廷诗人”“他们的处境使他们必须完全依赖统治者和他的近侍们”[3]3,因此这种理想社会的构建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从故事内容来看,第二则《杀子赎君罪》主要讨论君臣、父子之道,第三则《贪财的金匠》涉及朋友相处之道,第九则《沙漠王怕食长生果》虽是鹦鹉向沙漠王献长生果,但实际上是在表现人际交往中的忠信之道时,兼及对君臣关系的探讨。
《杀子赎君罪》中的陛下因饮酒作乐,“福气”将走,为了留下陛下的“福气”,需要巡查官弑子为陛下赎罪。这则故事其实强调了在君臣关系之中务必“忠诚”这一理念。皇帝让位时赞扬巡查官“你真是忠诚到极点的人”,指明此则故事的核心思想。但在巡查官之子遵循父亲之命准备献出生命时,又看到在父子关系之中,儿子对父亲的遵从。父亲说“子报父恩为圣孝,臣报君恩为大忠;皇上有恩于我们父子,你替赎皇身,是全忠孝呀!”所以,这则寓言还有第二点内核精神,即在父子关系之中,儿子要遵孝道。这其实和《论语·颜渊》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儒家思想“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是相通的。其本质上都是封建社会中,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所提出的道德教条。
在《贪财的金匠》中,金匠和木匠是一对挚友,两人从寺庙里偷走两尊金佛,金匠意欲独占金佛而抛弃良友,木匠为了报复,用两只锦鸡替换金匠的儿子,最后金匠醒悟道歉,“世间不可抛弃的是真实的情爱,金钱与富贵不过像锦鸡,只是有着美丽悦人的光彩,这些东西,结果有什么益处”,点明了人与人之间精神和情感的关爱超越了对物质追求的主旨。封建社会所呈现的是贫富差距异常悬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矛盾复杂激烈。寓言中金匠和木匠都属于被统治阶级,偷窃金佛就因生活“窘困”,而“窘困”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的压榨和盘剥。出自金匠之口的“金钱与富贵”和“有什么益处”似乎也就有了错位之嫌。从逻辑上看这应当属于统治阶级话语,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洗脑。统治阶级不断强调“真实的情爱”高于“金钱和富贵”,其实质是安抚被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手段。
《沙漠王怕食长生果》是告诫众人要分辨假意或真心,实际上却有许多地方值得推敲。首先,当猎人将鹦鹉献给沙漠王时,沙漠王并没有选择占有而是放生。在故事开篇,一个正面的统治者形象就突入眼帘。其次,沙漠王没有立刻吃食长生果的原因,来自于“所罗门神王”拒饮长生水的故事。所罗门不愿一个人长生,沙漠王仿效所罗门,这样沙漠王就戴上了“神”的光环。最后,他给鹦鹉自证清白的机会,并在真相大白之后大加赞扬鹦鹉“忠诚的美德”。在沙漠王眼里,鹦鹉就是忠诚于王的子民。寓言一方面大力宣扬沙漠王的优点,正面树立统治者形象;另一方面塑造理想的子民形象即忠诚的鹦鹉,为被统治者树立榜样,并通过沙漠王之口,呼唤更多的忠诚之士出现。综上寓言都彰显了臣对君以及人与人之间忠义与诚信的重要性。
(三)知识性内容的着重宣传
《鹦鹉夜谭》标题栏注有“波斯寓言”字样。“寓言”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首见于《庄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这里的“寓言”指借它之故事论我之道理。赵逵夫指出,“寓言是寄托一种哲理或说明一个道理的小故事,往往带有劝诫、教育的性质”。[10]陈蒲清认为故事性和寄托性这两大要素形成了寓言的双重结构。[11]这说明寓言不仅注重故事层,其意义层更是值得读者关注。这些意义又通过《鹦鹉夜谭》编者提到的“诲人之言”得以概括表现。
通过对《鹦鹉夜谭》的内容分析,可见《鹦鹉夜谭》的“诲人之言”在《风土什志》出版的年代不一定完全适用。《鹦鹉夜谭》之所以刊登于《风土什志》,多由于这种“寓言体”故事契合期刊的发刊宗旨,满足期刊的征稿要求。《风土什志》的受众群体非常广泛,它并不仅限于精英知识分子,更面向普罗大众。而“趣味性”和“知识性”的结合,是《鹦鹉夜谭》的优势所在。特别是《鹦鹉夜谭》发展到中后期,比起故事的“趣味性”来说更有一种“知识性偏向”。
第八则《王妃谗言害太子》是在曲折叙述中妖魔化女性形象的故事,而从第九则《沙漠王怕食长生果》开始直到终刊(除最末一则难以归类),其他全为智慧类故事或社会系统类故事。这些故事的“诲人之言”比起污名化女性的言论来说,显然更能予读者以启迪。尤其以第十三则《音乐的测验》和第十四则《音乐的故事》为代表,更是在寓言中传播了关于音乐的种种知识。《音乐的测验》中比较了“法兰”与“新德”在音调上的区别,颇具专业性。《音乐的故事》除了讲述音乐的起源,还介绍了摩西的乃沙奥赖斯博士依据天体的行动和星座轨道的道理,创造乐具的故事。文中详细说到“最乐之音”的十二音阶和十二时辰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些内容完全跳脱出了腐朽的道德说教,更多的是一种异国异民族的知识译介。
总览《鹦鹉夜谭》的内容目次,其中知识性的内容逐渐得到重视。从第九则开始的故事类型和内容转变尤为值得注意,这些变化又正好出现于“刘书翰、谢杨青编译”的文章里,这也许是人为选择的结果。
综上所述,《鹦鹉夜谭》作为《风土什志》的一个栏目,在目次的排列上受到编辑者的改动,在语言上经过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编译,无论在内容还是文本形式上都基本实现本土化的“改造”。在这种对传统故事篇目的重新编排中,可见编者的用心,以及迎合刊物宗旨的编辑策略。而从具体的文本内容来看,《鹦鹉夜谭》以寓言形式刻画典型人物,多用隐喻陈述观点,并注重对“知识”和“智慧”的强调。此栏目兼具趣味性和知识性,符合刊物的办刊旨趣,既以“诲人之言”凸显其文学价值,又因特殊的文化意义而体现其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