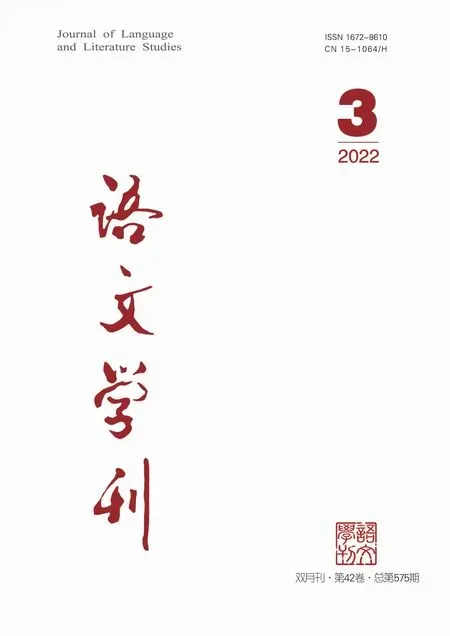语层结构视角下舒克申《怪人》中的作者形象探究
2022-03-18杨毅
○ 杨毅
(北京外国语大学 俄语学院,北京 100089)
一、作者形象理论——意与辞的统一
文学作品是语言学和文艺学共同的研究对象,然而两个学科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却各有侧重。语言学多从文学作品的语言角度入手,而文艺学则更多地偏向思想内容层面的研究,进而导致对文学作品的研究走向两条轨道。文学作品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由多种内容要素和形式要素构成。内容要素与形式要素之间不是“杯子与红酒”的关系,而是“生命与肌体”这样一种难以拆解的关系。尽管许多学者也曾试图寻求一种方法使两者相统一,但真正实现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则是苏联学者维诺格拉多夫(В.В.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格拉多夫是苏联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艺学家,经过多年苦心孤诣的研究,维氏终于发现了统摄一部文学作品的灵魂所在,这个灵魂便是 “作者形象”(образ автора)。根据维氏的观点,作者形象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作者其人画等号,也与他的人生经历、个人性格、阶级属性、社会地位没有直接关联,这是反映在具体作品背后的创作主体,是作家的一种独特的“演员”脸谱。作者形象是一种虚指,而非实指,是一种原则立场,体现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布局谋篇、情节架构、文体风格等各个方面[1]。作者形象是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的最高统帅,在对文学作品的人物、情节、语言等进行分析时,可以时刻感受到作者形象隐性或显性的存在。他决定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情节发展、语言风格和主题思想,像一双无形的手,操控着作品中的一切,同时也反映着作品主体——作者本人的情志、观点、性格、审美等。
具体而言,维诺格拉多夫认为作者形象是一部作品真谛的集中体现,它囊括了人物语言的整个体系,以及人物语言同作品中叙述者、讲述者(一人或更多)的相互关系;它通过叙述者、讲述者而成为整个作品思想和修辞的焦点及作品整体的核心[2]252,是作者进行文学创作时的总指挥,决定着作品中的一切形式和内容要素。“作者形象是一个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综合范畴,简单地说,体现在作者对所写世界的评价态度和作者对民族语的态度两个层面。”[3]由此可见,作者形象是使作品的意与辞得到有机统一的核心和关键。
正如我国学者白春仁在《文学修辞学》中所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更是思想的艺术,是饱含着人类生活智慧的社会观念形态。”[2]257在现实主义作品当中,作者将现实生活升华为笔下的艺术世界,在这一创作活动中,作者必然要表现出自身对所描绘的艺术世界的情感态度和道德评价,反映自身的价值取向,这是作者进行创作的目的和驱动力。作家创作,无不有感而发,他的苦心创作就是要“透过人物形象表现某种社会思想或触及某些社会问题”[2]258。作者对描写艺术世界的态度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层次,是创作意图的直接体现,它贯穿作品的始终,决定作品的情调和气韵,构筑着复杂的评价语层。维氏引用托尔斯泰的话印证了这一点:“任何文学著作中,对读者来说最重要、最珍贵、最有说服力的东西,便是作者自己对生活所取的态度,以及作品中所有写这一态度的地方。”[4]因此,作家对文学作品中所描绘世界的评价态度便是维氏作者形象的一个层面。
作者对民族语的态度则体现了作者形象的另一个层面。“作者对艺术现实的态度,他的立场和情绪,均非游离于文字之外的抽象概念,而是渗透在语言之中。若离开了作品的语言结构和修辞体系,简言之,离开了辞章文本,则个中态度连同整个故事内容,就完全荡然无存了。”[2]263语言是文学活动的核心和根基,是作家将生活现实编织为艺术世界的主要手段。为了建构文学作品的艺术世界,表达对这一艺术世界的评价态度,就需要在文学作品中创造性地运用多种语言手段。“作者在对各类修辞手段、语型、语体的使用中均反映出其本人对于民族语的认识、偏好、品评标准,显示出其语言修养、趣味、习惯以及好恶取舍。”[2]253例如,使用俗语、俚语,还是标准语,长难句或简单句,口语体或是书面语体。作品独特的辞章面貌便反映出创作主体对民族语的态度,而作品的创作主体也便由一般的语言主体升华为作者形象。
维氏指出:“在文学作品的结构里,使用哪种语言手段是同作品的内容有机联系着的,又是由作者对这个内容所抱的态度决定的。”[5]因此,作者形象的这两个方面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相互制约、相辅相成。作者的情态决定了如何选择和运用全民语以构成作品中独具一格的修辞体系。同时,“作者对艺术现实的态度,又只能通过作者对全民语的驾驭,依靠作者偏爱的艺术手法获得物质的表现和存在”[2]262。作者形象从这两个方面将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和形式要素贯通起来,成为解读文学作品的核心和机杼。
二、从语层结构看《怪人》中的作者形象
文学作品中的一切要素都通过语言来呈现。小说的语言结构是作者语言、叙述者语言和各种人物语言的统一体。其中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主体(即作者、叙述者、作品中的人物),都刻画着语言主体的人物形象,表现着主体的思想态度(即视角),体现着主体的语言风貌。作者与人物在思想感情和评价态度上的交织实际上就是作品中各语层的交织,在交织的语层中透视着作者形象。“在小说中,多视角产生多语层,多语层带来多语型。多视角—多语层—多语型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作品修辞体系的主线,实现了小说思想与修辞的浑然一体。而创作过程中作者形象的运用,正在于实现了小说思想与修辞的统一。”[6]
瓦西里·马卡罗维奇·舒克申(Василий Макарович Шукшин)的《怪人》是一部讲述体小说,小说以叙述人的话语为主体,以第三人称视角讲述“怪人”乌拉尔之行的七个片段,其中穿插着主人公怪人与各类人物的对话,用事实诠释着“怪人”这一绰号的深层意义。小说中作者悄然出现,旁白似的发声促进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作品主题的深化。《怪人》中的语言结构分为叙述人语层、人物语层及作者语层三个层次,下面试从各个语层分析小说中的作者形象。
(一)叙述人语层:爱憎分明的态度
在《怪人》这部小说中,作者假托一位无所不知却从不露面的叙述人讲述“怪人”生活中发生的“怪事”。在小说中,叙述人不具备特定的社会特征,不暗示自己的身份,只是以旁观实录的立场,毫无局限地利用外位超视的优势讲述怪人生活中的事件,甚至能够深入人物的心理,洞悉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中的叙述话语多为简单的词汇和句式,与作者语层言语风格相近,叙述人独白性的叙述话语平缓地铺陈叙事,构筑出小说中不同的场景,并通过不同的言语手段传达出作者对于不同人物的情感倾向。
叙述人语层首先在平铺直叙中奠定作品基调:
(1)妻子叫他怪人,有时还叫得很温柔①。
小说开门见山,指明了“怪人”这一绰号的由来,奠定了作品平和舒缓的基调,充满爱意与温情。开篇的叙述中作者语层和叙述人语层重合,侧面反映了作者对怪人的态度,不是反感厌恶,而是饱含怜爱之情。
(2)怪人有个特点:他经常要出点什么事。他并不愿意这样,为此十分苦恼,可还是常常惹事——虽然是些小事,但是挺恼人。
在这段叙述中,叙述人转入了主人公视角,透视主人公的心理,仿佛怪人的自白,替怪人澄清了常常惹事并非其本意,自己也深受其扰,满是无辜与无奈,流露出作者对怪人的深切同情,同时也预告着主人公即将登场,一系列可笑而又恼人的事件即将上演。
叙述人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观察并讲述着主人公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让人忍俊不禁的事件。在叙述中,既有对怪人行为动作的生动刻画,又有对怪人心理活动的准确传达,并且不掺杂叙述人的任何主观评价,仅通过客观叙述塑造出一个可笑而又可爱的怪人形象,下面将通过几个片段从叙述人语层分析文中的作者形象。
当怪人在商店地下看到一张50卢布钞票时的描写:
(3)好一个绿色的小宝贝呀,不声不响地躺在那里,谁也没看见。怪人竟高兴得浑身颤抖起来,眼睛也发亮了。他唯恐别人赶在他前面发现这张钞票,于是赶紧动起了脑筋,想该怎么把这张钞票的事告诉这些排队的人,怎么把话说得让人开心又俏皮。
当怪人在地上看到50卢布时,内心激动万分,此时作者想表达的是怪人内心的情绪变化,因而叙述人转向人物视角,从主人公心理角度进行叙述。叙述人以主人公的口吻将50卢布的钞票拟人化,称其为“绿色的小宝贝”,并暗自窃喜无人发现,体现了怪人激动、兴奋的心情。接下来则是以第三人称视角看待怪人的行为,“高兴得浑身颤抖,眼睛也发亮了”。略带夸张的描写将主人公的心情和行为状态表现得活灵活现。而更有趣的是,他不是因为捡了钱而激动不已,而是激动于终于有机会在人前表现自己,于是他动起了脑筋,想办法用开心又俏皮的方式把钞票的事告诉给排队的人。通过叙述人语层,我们可以看到怪人拾金不昧的美好道德品质,然而他在捡钱时的心理和行为状态却十分滑稽、可笑,甚至可以看到怪人的表演型人格和渴望受到关注的心理状态。
当听到兄嫂二人的争吵时,对怪人情态的叙述:
(4)怪人赶紧从台阶上走下来……他也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才好。他心里又难受起来。每当有人恨他时,他心里就万分难受,感到可怕,似乎现在一切都完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想到别的地方去,离这些恨他和嘲笑他的人远远的。
这段叙述将怪人心理的矛盾、窘迫、无奈乃至无望展露无遗。“怪人赶紧从台阶上走下来”一句中“赶紧”一词将怪人听到兄嫂二人吵架时的慌张、恐惧和茫然无措的神态刻画得淋漓尽致。面对陌生人的冷眼相对、嫂子的冷言恶语,他的心中不是怨恨,而是自责和委屈。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迎合所有人,却还是不被理解,反被嘲笑和侮辱,怪人觉得无地自容,倍感伤心,万分难受,并感到可怕,仿佛生活都失去了意义。这理所当然会唤起读者的同情:一个单纯善良的老实人却不被善待,让人倍感辛酸和难过。
当怪人从兄嫂家回来后,叙述的语调变得明快起来,标志着怪人的心情由阴转晴:
(5)怪人快到家时,正下着一场春意盎然的大雨。怪人走出公交车,脱下新靴子,在温暖、潮湿的泥土地上跑开了——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提着靴子。他不时地跳跃着,大声唱道:“白杨树啊……白杨树……”天空的另一边已经放晴,泛出蔚蓝色,近处一个地方还露出了太阳。
回到了家乡,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怪人终于可以不用再小心翼翼,处处察言观色、谨言慎行,终于可以尽情释放自我,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跳跃、奔跑、歌唱。种种委屈早已被抛在脑后,怪人恢复了往日的纯真,连周围的景色都呈现出光亮、明媚的色调,烘托出主人公欢快、轻松的心情,怪人的本真、质朴淳厚令人欣慰和动容。从叙述的语调中可以看出,叙述者和作者由衷地替怪人回归自我感到高兴,心情仿佛也和主人公一样终于放晴,走出了阴霾。在对天气和景物的描写中“太阳”“春意盎然的大雨”“温暖、潮湿的泥土”等意象象征着生机与希望,预示着主人公性格的闪光和未来的生活景象。
怪人在生活中不断地与他人冲撞,他与周围的人仿佛是指南针的两极,永远指向不同的方向。在对怪人日常生活的描写中,叙述者运用与描述怪人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刻画着冷漠、尖刻的他人形象。
当怪人向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讲一件自以为有趣的故事时,对知识分子这样描写道:
(6)“是您自己编的吧?”知识分子模样的同志从眼镜框上看着他,一本正经地问道。
“干嘛要编呢?”怪人没明白,“拉缅斯科耶村就在我们那条河对岸嘛。”
知识分子模样的同志把脸朝车窗外扭了过去,再也没说话。
这段描写颇为生动,“从眼镜框上看着他”这一动作细节和“一本正经地问”这一情态,将知识分子模样同志的高冷、孤傲刻画得十分生动。而后“知识分子模样的同志把脸朝车窗外扭了过去,再也没说话”。显然知识分子对怪人略显粗俗的故事并不感兴趣,甚至心生厌恶,“扭过头去”这一动作显示了其拒绝与怪人交谈的态度,行为决绝,态度冷漠,突显了两者身份地位的差距和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当飞机乘务员要求大家系好皮带时,对怪人和读报人行为反差作对比叙述:
(7)怪人乖乖地系好皮带。可他的邻座却毫不理睬。怪人小心翼翼地碰了他一下。
由于没系皮带,飞机快速降落时,邻座从座位上栽了下来,假牙也掉到了地上:
秃顶的读报人在寻找失落的假牙。
怪人解开皮带也开始帮他找。
“是这个吗?!”他高兴地大声说,把假牙交给了那位读报人。
他的秃顶竟然变成了血红色。
“为什么非要用手去拿呢?”他伊里唔噜地喊了起来。
怪人不知所措了。
“那用什么呢?……”
“我到哪儿去把它煮开呢?到哪儿?”
怪人也的确不知道。
“您和我一起走好吗?”他建议说,“我有个哥哥就在这儿住,到他那儿去煮……您是担心我把病菌带到您的假牙上吧?我身上可没有病菌……”
读报的人颇为惊讶地看了看怪人,不再喊叫了。
在这段情节描写中,叙述人独白和人物对话交替进行。通过叙述者语层,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固执己见又对他人吹毛求疵的人物形象。邻座先是对怪人的善意提醒置之不理,再是对别人的帮助不知感恩,反去责怪对方用手拿了假牙。叙述人对他的称呼经历了“邻座”(сосед)——“读报人”(читатель) ——“秃头的读报人”(лысый читатель)的三次转变,可见作者对其态度、评价的急转直下。而怪人则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先是“小心翼翼地”提醒对方系皮带,而后帮助对方找假牙。虽然因自己的善行遭受对方斥责而有些不知所措,但是依然报以善意,请邻座到自己哥哥家去把假牙煮开。“读报人颇为惊讶地看了看怪人,不再喊叫了。”怪人如此之善良、真诚,这是令邻座感到惊讶错愕的。从叙述话语“惊讶地”及“不再喊叫”可以看出怪人的友善的行为言语给读报人内心带来的极大震动。
(二)人物语层:特色鲜明的口语
《怪人》虽是讲述体小说,但其中贯穿着大量的人物对话,并由叙述者将一个个对话情境串联起来,犹如电影中的场景片段。小说通过怪人与形形色色人的交往对话,全方位地揭示怪人的性格特征,以及作者对这一人物的态度,也使读者具体可感地了解到怪人及其周围的世界,增加作品的真实性和形象性。
故事围绕着住在农村的“怪人”去乌拉尔哥哥家之行中发生的事件展开,作品中不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描摹的只是平常的普通人和他们最简单不过的日常,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情韵。人物的对话以简单的句法结构、口语化的词汇和句式为主要特点,但不同人物因身份、职业、教育水平、性格特点的不同而造成语言和修辞上的差异,而作者也正是通过这些形式各异的语言特点塑造出一个个更为立体的人物形象。下面通过举例加以说明。
怪人获准休假,决定去乌拉尔看望12年未见的哥哥,他在收拾行李过程中找不到钓鱼用的鱼形金属片时与妻子展开对话:
(8)“那块钓鱼用的鱼形金属片在哪……像鱼形钓钩一样的?”怪人在储藏室大声叫道。
“我怎么知道?”
“可别的鱼钩都在这儿呀!”怪人瞪大了那对圆圆的、又蓝又亮的眼睛,想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你瞧,别的鱼钩都在这,就是我要找到那块没有。”
“像鱼形钓钩一样的?”
“是啊,狗鱼形的。”
“噢,大概是我错把它当鱼给炸了。”
怪人沉默了一会。
“炸得怎么样啊?”
“什么?”
“味道好吗?哈——哈——哈!……”他根本不会说俏皮话,可偏偏还特别喜欢说,“你那口小牙没硌坏?鱼钩可是硬铝做的呀!……”
怪人与妻子的对话具有鲜明的口语化色彩,如口语化句式的使用,“Да вот же ж все тут лежали!”“ Ну и как?”“ Что?”不完全句“Щучья”“Зубки целые?”独词句“Ну. ”口语化词汇“нету.”“ж”,以及主人公边说边想造成的口语化句序“Все тут, а этой, видите ли, нету.”使对话场景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显示了作者对于日常生活场景描写的精准把握。怪人在找不到钓钩,问妻子是否知道钓钩在哪时,妻子的态度略显冷漠,而怪人依然不依不饶地追问,而当妻子说大概是错当成鱼炸了时,怪人又耍起了小聪明,想要说点俏皮话调节气氛,便问道:“炸得怎么样?”妻子显然并未理解丈夫的幽默,于是怪人继续逗趣地问道:“味道好吗”,“你那口小牙没硌坏?”并自以为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怪人想要通过这样的俏皮话增加夫妻之间的情趣。“зубки”(小牙)这一指小表爱形式突显了他对妻子的爱意,然而从妻子诧异的反映来看,他的俏皮话并没有奏效,他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通过这段夫妻间的对话,一个不懂幽默却强装幽默的滑稽形象跃然纸上。
当怪人顺利飞抵乌拉尔,在机场给妻子发电报时,与电报员的对话展现了冰与火的反差对比:
(9)怪人在机场给妻子发了封电报:
“安全着陆。丁香花枝落在了我的胸上,可爱的格鲁莎,别忘了我。瓦夏特卡。”
电报员,一个一本正经、冷冰冰的女人,看完电报说:
“请您重写。您是一个成年人,不是托儿所的小孩。”
“为什么?”怪人问,“我每次给她写信都是这样写的。这是我的妻子!……您大概以为……”
“在信里您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可是电报——这是一种通讯形式。电文是公开的。”
怪人重新拟了电文:“安全着陆,一路平安。瓦夏特卡。”
电报员改动了两处:把“安全着陆”和“瓦夏特卡”改成了“平安飞抵”“瓦西里”。
“‘安全着陆’,您难道是宇航员吗?”
“好吧,”怪人说,“就那么改吧!”
这一段描写也颇具戏剧性:怪人刚下飞机,就第一时间给妻子发电报报平安,电报的内容充满了爱意:“安全着陆。丁香花枝落在了我的胸上,可爱的格鲁莎,别忘了我。瓦夏特卡。”怪人诗一般的语句(Ветка сирени упала на грудь)、对妻子亲昵的称呼(милая Груша)和指小表爱形式的落款(Васятка)无不表明怪人是一个爱妻子、爱家庭,并充满着浪漫主义情怀的丈夫,哪怕是一封报平安的电报也写得如此诗情画意、情意绵绵。然而这封电报却引来了电报员的不满,并被要求重写:“请您重写。您是一个成年人,不是托儿所的小孩。”女电报员的语气十分生硬,透过女电报员的话语可以看到一个冷冰冰的、严肃的面孔,讽刺怪人像孩子般幼稚可笑。而怪人似乎还没反应过来,反而询问原因,并解释道:“我每次给她写信都是这样写的。”这一解释再一次深化了怪人天真、质朴的个性,对妻子永远充满关爱、倍加呵护。然而还没等怪人把话说完,电报员就揶揄道:“在信里您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可是电报——这是一种通讯形式。电文是公开的。”透过文字,读者已经窥见一个极不耐烦的女电报员形象。当怪人终于妥协,重写电报时,尽力去掉了浪漫的话语,只剩下 “安全着陆,一路平安”和自己的昵称“瓦夏特卡”,然而还是没能让电报员满意,而此时的电报员已经不愿再费口舌与怪人争论,而是直接将电报内容改到仅剩一句“平安飞抵”和署名“瓦西里”,并且还不忘对怪人嘲弄一番:“‘安全着陆’,您难道是宇航员吗?”充满着浓重的讽刺意味。寥寥数笔,几轮对话,作者对于电报员和怪人双方的态度已清晰可见,怪人对妻子细腻的情感、真挚的表达、澄澈的内心令人动容,而电报员板着的面孔、阴阳怪气的腔调、尖酸刻薄的话语、冷嘲热讽的态度不禁让人感叹世态炎凉、人情冷漠。除女电报员外,小说中的女售货员、火车上的知识分子、机长、飞机上邻座的话语也都十分冷漠,丝毫感受不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怪人的热情与善良。
怪人和哥哥多年未见,有无尽的话题闲话家常,但嫂子却对怪人颇为不满,对两人的闲谈也颇为厌恶,甚至恶语相向:
(10)傍晚,怪人和哥哥喝了酒,用颤抖的声音唱了起来:
白杨树啊……
白杨树啊……
他的嫂子索菲亚·伊凡诺夫娜从另一个房间探出身子看了看,恶狠狠地问道:
“别大声喊叫行不行?你们又不是在火车站,对不?”随即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
“你们到底要喊叫到什么时候?”索菲亚·伊凡诺夫娜有一次气势汹汹、神经质地问道,“谁想听你们那些各种各样的丑事,又是鼻涕又是亲嘴的。你们可好——还越说越来劲了。”
怪人为了哄嫂子高兴,在童车上作画,不料却引来了嫂子的不满,并和哥哥大吵了一架:
(11)“哎,这有什么呐!……算啦……索涅……算了吧!”
“明天我可不愿在这儿再看见这个傻瓜!”索菲亚·伊凡诺夫娜喊道,“明天就让他滚!”
“你算了吧!……索涅……”
“我就是不能算!不能算!别让他等着我把他的箱子扔出去,让他见他妈的鬼去,我说话算话。”
从以上两段对话中,可以看到嫂子尖酸刻薄、不近人情、势利又市侩的丑恶嘴脸。兄弟二人12年未见,自然有说不尽的话题。而嫂子却极为不耐烦,乃至厌恶二人的谈话,恶狠狠地问道:“别大声喊叫行不行?”嫂子的话语中使用“орать”(喊)而非“говорить”(讲),显示了她对兄弟二人的不满情绪。而哥哥也十分尴尬,替她解释道:“这……那儿有孩子在睡觉。总的来说,她是个好人哪。”可见哥哥对于妻子的无礼也万般无奈,并以孩子在睡觉缓解兄弟二人之间的尴尬,维护妻子在弟弟心中的形象,足以见得哥哥的善良。而后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回忆着青年时代,回忆父母亲,可以看出两人对于家乡和亲人的挚爱和个性的淳朴。可在妻子再一次的斥责后,哥哥终于忍不住哭诉起来:“瞧吧,这就是我过的日子!你看见了吧,这个人心有多狠呦!”显然哥哥在这样一个强势妻子的压迫下,日子过得并不幸福,整日忍气吞声。而嫂子看到了怪人在童车上作的画后,更是火冒三丈,跟丈夫大吵起来,并恶语相向:“明天就让他滚!”“让他见他妈的鬼去。”而哥哥只能唯唯诺诺地劝说:“哎,这有什么呐!……算啦……索涅……算了吧!”几句简短的对话就已经刻画出一位鄙俗、势利、粗鲁的村妇形象。哥哥在家中地位低下,没有话语权,而嫂子则咄咄逼人、作威作福、不通人情,非要将弟弟赶走才罢休。叙述话语中透露着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否定态度。而后从哥哥的口中得知,原来这位嫂子本也是乡下人,搬到城里后拼命融入,“爱慕虚荣,趋炎附势,极力洗刷自己身上的乡下印记”[7]。并看不起乡下来的弟弟乃至自己的丈夫。从这部分对话中,我们便可以深切感受到作者对嫂子为人处世态度的不耻和对兄弟二人处境的同情。
(三)作者语层:超越文本之上的评价
在《怪人》中,叙述者语层和人物语层是作品的主要语层结构,但隐居幕后、间或出现的作者语层从另一个侧面揭露着《怪人》中的作者形象,传达着作者的情感态度。在小说中,作者语层出现的频次并不高,主要是通过叙述人语层和人物语层叙述情节事件,描摹人物形象,揭示作品主题思想。但在作品的最后一段,在交代怪人的身份时可以发现叙述语调完全不同于前文中的轻松、诙谐,而是以严肃而庄重的语调,郑重其事地对怪人的基本信息进行介绍。因此,可以认为与全文风格大相径庭的结尾便是通过作者语层表达着对怪人的评价。
小说的最后一段对怪人的身份的交代:
(12)……他的名字——瓦西里·伊戈雷奇·克尼亚泽夫,39岁,在农村当放映员,崇拜侦探和警犬,童年时的理想是当一名侦探。
小说的最后一段使用标准语叙述,与整个作品的口语化风格明显不同,显然是从作者语层对怪人身份的补白。在整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被隐去,只是以“怪人”这一绰号称呼他,突显其与众不同的个性特点。而在作品的最后终于让读者了解到,尽管怪人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但他也有姓名,“瓦西里·伊戈雷奇·克尼亚泽夫”这种名字、父称、姓氏的全名形式充分表明了作者对其高尚品格的赞扬。作者对其年龄、职业、喜好的介绍表明了怪人也是普通的正常人,他的生活和普通人并无二致,也有自己的喜好和梦想,只是他的美好品质不被这个冷漠的世界所理解,因而显得奇怪,体现了作者对怪人人格的敬佩和精神品质的赞赏。作者语层以客观、冷静的笔触将读者从轻快、幽默的故事中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使小说掷地有声,引发读者无限深思。
三、结 语
维诺格拉多夫认为:“统摄一部文学作品的灵魂是作者形象。一部作品如果缺乏鲜明的作者形象,那就不是一部成功之作。如果其作者形象游移不定,飘忽变幻,那也不是一部好的作品。”[8]通过对小说《怪人》中叙述人语层、人物语层和作者语层的分析,可以看到文本中所呈现出的鲜明的作者形象。
小说以轻松诙谐的语调,略带调侃和嘲讽的语气勾勒出一个常常惹是生非、绞尽脑汁在各种场合说俏皮话、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得其乐并滑稽而可笑的怪人。然而当读者随叙述人的视角观察怪人在不同场合的言谈举止,通过叙述人话语透视他的所思所想,从人物语层听到他真诚的言语,从作者语层感受到作者对其人格的尊重,就越来越被这个单纯、质朴、天真、善良、热情的小人物所打动,真切体会到他美好的性格品质,高尚的精神境界,好似俄罗斯文学中的“圣愚”,在其愚笨的行为举止下隐藏着一颗金子般的心。同时,作者对待城乡的态度也浮现于字里行间。俄罗斯的城乡好似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乡下人学不会城里人的冷漠、孤傲,城里人不懂乡下人的淳朴与真诚,这就是隐藏在作品各个语层中的作者形象,启发着读者对于人性问题的深入思考。维诺格拉多夫提出的“作者形象”理论实现了作品语言和思想的统一,达成了通过作品辞章面貌揭示作品的思想内涵的目标。从语层结构角度入手分析作品中的作者形象则具有逻辑性和层次性,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分析文学作品的语言和思想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方法和手段。
【 注 释 】
①本文中引文均出自《俄罗斯文学名著赏析》中《怪人》一文,张建华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