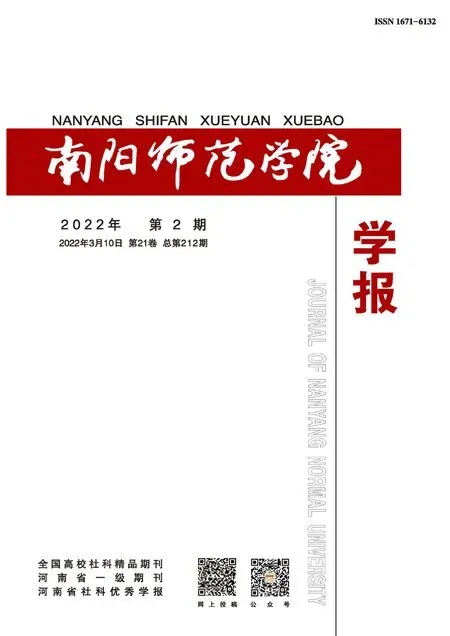近现代词集评点的发展历程
2022-03-18周翔
周 翔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2)
19世纪30年代以后,埋首故纸堆的治学方式已经走向死胡同,提前洞察到社会衰弊的文人士子发出文学应关注现实的呼唤。比如魏源、林则徐、龚自珍等人均在文学领域做出贡献。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导致文学发展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过渡,词学亦然。就词集评点而言,一是清初词人群体沉浸式的日常酬和以及群体的互相标榜已经成为过去。二是浙西词派统治下的清中词坛颓势渐显。为挽救浙派词学衰敝,张惠言率先推尊词体,提出“比兴寄托”的诗教观,强调作词应该重视内容,并且寄寓现实。随后周济等人继承张惠言的词论并加以完善,常州词派形成。同时,常州派以词集评点为载体的论词方式推动了近现代词集评点的兴盛。词集评点由营造词学声势向阐述词学观念转变。
综观近现代词集评点发展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1840—1895年。这一时期,常州词派占据词坛的重要位置,词集评点多出自常派词人之手。代表人物如庄棫、谭献、陈廷焯等。他们接受并继承常州派的主要观点,同时以词集评点为载体,深化和完善常派词论。此外,谭献和陈廷焯已较早关心国家前途和政治命运,在词集评点中多选评体现民族危亡和书写历史史实的作品。第二阶段为1895—1919年。这一阶段的中国,内忧外患更加严重,在词体益尊的情况下,词学批评逐渐向两极发展,词集评点亦然。一方面,以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为代表的清季词人更重视以“音律”为主的词体创作,逐渐形成以“严守声律”为宗旨的论词群体;另一方面,王闿运、梁启超等人更加注重“诗意”的表达,从主张词论向阐发词情的批评方法过渡。同时,在维新派文人的引导下,词被作为政治功利性的文体加以利用。这一时期也是词学观念逐渐向现代化过渡的阶段。第三阶段为1919—1949年。这一阶段的词集评点正式进入现代词学的范畴。在新旧文学的交替中,词学也出现传统与现代的并存。一方面,现代词集评点从体制到观念等都出现新变,比如新标点的使用、新语汇的运用、对女性词人的重视、强调“真性情”的抒发、对白话词的提倡以及对词乐关系的重新探讨;另一方面,以朱祖谋为代表的词学研究者及其后继者仍然在保持传统词学地位的道路上前行。词人之间品评作品的风气复兴,这类词集评点让我们看到传统学人对词学领域的坚守。19世纪30年代以后,时局的变幻主导了词集评点的风向。一大批以高校学者为群体的抗战词人希望通过对爱国词或豪放词的选评唤起国人的斗争精神和必胜信念。现将三个阶段词集评点发展历程作简要介绍。
一
第一阶段是1840—1895年,属于近代词集评点发展的前期。总体而言,在常州派张惠言、周济等人的影响下,词集评点成了词学批评的重要手段和词学观念的重要载体。
首先,词集评点重新引起词学家的重视。虽然清初词集评点之风盛行,但词体还未得到重视,仍然是词人群体之间的自娱行为。评点作为工具,是词人们相互娱乐、评比、交游的重要方式。评点体并未受到重视,甚至遭到传统学者的批判。这是因为当时学者认为词集评点多是溜须拍马的阿谀之作,影响读者对词本身的价值评判。评点之于词作,有喧宾夺主的嫌疑。比如曹溶《珂雪词》有350余则评点,孙默辑《国朝名家诗余》有3000余则评点。四库馆臣即认为当下大量词集评点充斥于书中,且多沾染商业背书之陋习,相互吹捧。如在《珂雪词提要》中提出:“旧本每调之末,必列王士禛、彭孙遹、张潮、李良年、曹勋、陈维崧等评语。实沿明季文社陋习,最可厌憎。今悉删除,以清耳目。”[1]由是可知,四库馆臣认为作品优劣,自在人心,无须受人吹捧。而评点者也无须借名人词集蹭热度,对于词集评点中那些“假借声誉”的内容非常排斥,因此将曹溶《珂雪词》中所附评点全部删除。然而,类似情况在后期遇到转机。词集评点的最终目的是推动词坛复兴,因此虽被正统文人批判,但也从未停止。比如许昂霄《词综偶评》即是对朱彝尊《词综》的发扬,其词学观念明显受浙西词派影响。随后,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逐渐统治词坛。常州一脉阐发微言,开宗明义,《词选》作为其早期传播词论的载体带动了评词风气。张惠言认为宋以后至时下词“雅郑互见”,绝少好词。其序言:“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2]再有,周济《宋四家词选》是专门点评宋代词人的选本,最早成书于道光十二年。周选两宋51家230首词。名为四家,实是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为四大家,其下各列风格相近者。这正与其“问涂碧山,历经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3]的学词门径相结合。
其次,常州词派对这一时期的词集评点产生较大影响。近代前期(即1895年以前),谭献和陈廷焯作为常州后劲,继续发扬常派词论。谭献《谭评〈词辨〉》《箧中词》、陈廷焯《云韶集》《词则》是这一阶段词集评点的代表。比如《谭评〈词辨〉》多是对周济词学观念的发扬,评点多处提到“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思想。如评冯延巳《蝶恋花》(六曲阑干偎碧树)曰:“金碧山水,一片空濛。此正周氏所谓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也。”[4]2以“寄托”说发展其“柔厚”之旨。然而,谭献亦从辩证的角度学习常派词论,比如对周济“正变”观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大约周济所言词之正,皆其所言词之变;所言词之变,皆其所言词之正。从谭献所处现实社会来看,他论词提倡能够关注现实、抒发胸臆的作品。因此其评《词辨》对体现书写内心情感的词,尤其是豪放词评价颇高。如评李煜《相见欢》:“濡染大笔。”[4]1又评苏轼《贺新凉》:“下阕别开异境,南宋惟稼轩有之,变而近正。”[4]4再如谭献《箧中词》,其选评从尊体、词艺、词史等多方面展现了清代词学的风貌。清代词学复兴,首要任务是尊体。谭献《箧中词》中认为:“无非小大,皆曰立言。惟词亦有然矣。”可见“立言”是谭编之旨。所选自吴伟业至庄棫凡200余家500余首清词,以张清词盛况。谭献评点还涵盖对清词流派的梳理,带有词史的色彩。这在谭献《箧中词》中多有体现。谭献选录朱彝尊、陈维崧词,并对其词加以总评,其言曰:
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到。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5]今集二,8
谭献认为清代词派自朱彝尊、陈维崧而始,且百余年间,十人之有七八不出朱、陈窠臼。谭献对朱、陈二词人的评价较为中肯。朱彝尊尚南宋姜、张一脉,固言其词碎;陈维崧尚苏、辛一脉,固言其词率。嘉庆之前,两派余绪尚存,追随者众。其中,谭献还对浙西词派的流变加以梳理,并对浙派词人多有指摘。如其言:“《乐府补题》别有怀抱。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辞其过。”[5]今集二,23又提:“南宋词敝,琐屑饾饤。朱、厉二家,学之者流为寒乞。”[5]今集三,5直言浙派学姜、张一脉,只得其形,未得其神,流于俗弊。又言后常州派起,词学为之一变。谭献作为常州后劲,于常州派词人用力甚多。谭献对张惠言词评价甚高,认为其“开倚声家未有之境”[5]今集三,12,亦言茗柯词后附录诸家,“以示派别”[5]今集三,13。同时认为,清代自常州词派后词学始尊。从其词评亦可知,谭献词学多从常州一脉,如“深美闳约”“言近旨远”等词旨多见于谭评。谭献对常州派词人评价亦颇高,如评周济《徵招·冰钲》:“掷笔空际,伟岸深警,如读杜诗。”[5]今集三,20谭评诸如“风喻”“深闳”“温厚”等语皆不出常州派“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之旨。
陈廷焯从《云韶集》到《词则》的评点可明显看到词学宗尚的变化,《云韶集》更多显示陈廷焯早期词学宗尚。其序言中讲要“以竹垞太史《词综》为准”[6]805,可见早期陈廷焯以浙西词派为宗。但此后受老师庄棫的影响,词学宗尚开始转向常州词派。他在序中提出:“卓哉皋文,词选一编,宗风赖以不灭,可谓独具只眼矣。”[7]由是可知,陈廷焯推崇张惠言及其词论。但他同时也认为张选过严,标准失当,因此《词则》是其承常派词旨而选。此外,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成文析评,与《词则》互见,是陈廷焯阐发“沉郁顿挫”说的重要作品。有关《云韶集》与《词则》的演进观照陈廷焯词学思想变化,学界已有深入研究,兹不赘述。但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两选本中所选唐宋词作品最多的是辛弃疾。浙西词派推崇姜、张的醇雅。这一点从选词量化来看,表现并不明显。《云韶集》中所选两位词人数量仅排第六名和第八名,执牛耳者乃辛弃疾。再看《词则》,辛弃疾亦高居榜首。主要原因是辛词体现陈廷焯“沉郁”说。《白雨斋词话》中指出:“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8]2结合辛弃疾一生,词中大有孤臣之感。陈廷焯词评给予辛词很高赞誉,如:“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8]8又:“稼轩词如龙蛇飞舞,信手拈来,都成绝唱。词至稼轩,纵横博大,痛快淋漓,风雨纷飞,鱼龙百变,真词坛飞将军也。”[6]92周济也曾言:“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9]可见,陈廷焯钟爱稼轩词一是受常州词论影响,二是辛词内心情感的喷发与现实生活的困顿,在强烈对比之下,更能阐发其“沉郁”说。
综上,词集评点仍在常派“诗教”传统下前行。常州一脉所谓“微言大义”即是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提升词学高度。在近代社会的疾风暴雨之下,谭献、陈廷焯等近代前期词评家将常派词论发挥得淋漓尽致。
二
第二阶段是1895—1919年,属于近代词学的后期。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词学界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分为两派:一部分继续在常州词论的影响下进行词学研究,此派以晚清四大词人为代表;一部分主动接受西方的文艺理论并运用到词体创作和词集评点中来,此派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综观这一时期,常州派词学思想仍旧浸染词坛,各家词评皆有依常州门径者。但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起了文学界革命,给词坛注入新鲜血液。晚清四大词人继承常州词派的传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自家观点。比如况周颐的“重、大、拙”说,尤其是对“重”的阐发,所谓“沉着”“厚”皆是比附常州“折中柔厚”说、“沉郁”说而来。然就常州词论以外,他更注重词之格律、词笔和气格。比如《况周颐批校陈蒙庵填词月课》,况周颐即从这三方面对门生陈运彰加以指导。从格律来看,况周颐《蕙风词话》提出“守律至乐”论。佳句好得,律工难求,他认为对音律的考究是填词一大乐趣。就评点内容看,况周颐将陈蒙庵词中四声、平仄、押韵等错误一一改定,至工乃罢。再如词笔,况周颐提出重要观点,即紧扣题目生发词意。如陈运彰填“金风”词,况周颐直言要紧扣“金”字;写“展重阳日”,就要紧扣此题,不可避重就轻,词浮于意。而朱祖谋和郑文焯也是求音律甚严者,朱祖谋更是有“律博士”之称。朱祖谋精于梦窗词研究,其与王鹏运共同批校梦窗词相当精细,且多有词评散见于各处。龙榆生曾辑录《彊村词评》发表于《词学季刊》。郑文焯最精音律,词评多涉及音韵律吕。如郑评《白石道人歌曲》《清真集》《梦窗词甲乙丙丁稿》,多从音韵、四声等声律论入手,为研究宋代词体声律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如批校《白石道人歌曲》中言及《暗香》一阕,郑文焯即注意到白石三字句夹协用法,评曰:“此二曲为千古词人咏梅绝调。以托喻遥深,自成馨逸。其《暗香》一解,凡三字句逗,皆为夹协。梦窗墨守綦严。但近世知者盖寡,用特著之。”[10]196又如考证白石填词与乐谱关系。郑举《凄凉犯》以示填词法。评曰:
近人作是解,起句似七言诗。盖未审“陌”上旁谱之么,为道宫起调之证。率以诗韵通转例,妄加入词。余曩尝举宋名家词中所用韵,证以古音谐例。乃知与今诗韵硕异,谁可胶柱求声,此词人以知律为贵也。[10]206
由是可知,徒诗并非乐词。填词识谱,非同于诗。亦可知郑文焯对词体声乐研究多加着意。况周颐精深词论,以“重、拙、大”评词。《蕙风词话》中多有词集评点。如况周颐将吴文英与辛弃疾二人词作比,言曰:“词太做,嫌琢;太不做,嫌率。欲求恰如分际,此中消息,正复难言。但看梦窗何尝琢,稼轩何尝率,可以悟矣。”[11]除词守音律以外,晚清词人王鹏运、朱祖谋、文廷式抬高苏轼的地位。常州派周济指出学词门径,标举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和王沂孙四家。王鹏运于四家之外又提出苏轼,朱祖谋晚年对东坡词亦着力甚多。文廷式更是标举“苏、辛”,但求豪放一路以抒襟抱。其实不难看出,诸家对苏轼、辛弃疾的推崇,大多是因为两家词的雄阔豪迈之气。这对现代词学家叶恭绰、龙榆生的词论影响深远。
于常州门径之外,王闿运、梁启超等独树一帜。王闿运别具匠心,其《湘绮楼词评》选评唐五代宋词,重张“词是艳科”“词乃小道”的观念,强调词的抒情性。既常州推尊词体之后,王闿运将“诗庄词媚”的思想再次带入人们的视野,可谓是与常州词人分庭抗礼。察其词集评点内容,一方面,王闿运没有门户之见。与常派词人论词主张不同,无论宗派,抑或是否名家,只要符合“词趣”说皆可入选。另一方面,王闿运词论反对蹈袭前人,提倡填词当有新意。分别以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和李清照“寻寻觅觅”句为例,其言初见则新,再见则可呕。然而王闿运选评,多妄改前人字句,可堪诟病。与此同时,梁启超作为近代词学的重要人物亦期跳出常派窠臼。梁启超虽赞同常州派“意内言外”说,但更推崇苏、辛。这主要与时局关系紧密。甲午中日战争的溃败,给仍然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人当头一击,国内众多阶层如梦初醒。此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士子“公车上书”,请求变法自强。梁启超率先举起“文学”的大旗,希望改造文学以唤起民智。于词一脉,他更为关注能够激荡胸怀、饱含斗志的作品。毫无疑问,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词更能涤荡人心。因此,梁启超在词评中更多的选取豪放词。比如评王安石《金陵怀古》即言其直逼清真、稼轩,评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绝似苏、辛,即是例证。同时梁令娴《艺蘅馆词选》序中提到梁启超“词乐”观。梁氏曾提到中国音乐与韵文的关系,提出词亦可歌。因此,他便提出“国乐独立”,成为教育的门类,以恢复词的可歌性,进而成为其政教美育的工具。总而言之,梁启超的“词体改良”是希望词体为政治服务。由此来看,较之近代传统词学观念,梁启超词论已初显现代性的特征。要之,这一时期在词学自身发展和社会历史的外部推动下,无论是晚清词人对于常州词论的突破,还是王闿运以“情”为主的“词趣”观,抑或是梁启超对苏、辛派的推崇以及“词乐”政教观的提出,都是近代后期词学转型的星星之火,为词学向现代发展过渡铺平了道路。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1908年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的问世。作为旧式文人的代表,王国维在政治观念上仍然属于旧派代表人物。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王国维是主动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并且介绍中国传统文学的第一人。学界将其视为现代词学的开端,确实是不刊之论。王国维的词学理论集中在《人间词话》中,但因其不属于词集评点的范畴,所以不在文章的论述范围内。然而,他的词学理念却对现代词集评点有较大影响。王国维《人间词话》可以说是建立在寻求情景关系的基础上探讨词学审美特质的理论著作。他以“境界”论词,其所谓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即是“写景”与“造景”的区别,他强调“自然”与“不隔”,同时注重词体情感的抒发,反对美刺教化的诗教。如果说王国维之前的词人词论具有功利性,比如宣传词学主张、标榜词学宗尚等,那么王国维词论是从词的本体出发,具有超功利性的审美。这是对常州词派词论的否定,也开启了词学本体审美的理论研究,即更加强调词的“内美”。由是以来,现代词人如叶恭绰《广箧中词》中的评点强调填词“不隔”;范烟桥《销魂词选》选评明清以来女性词人,突出词的真性情;邵祖平《词心笺评》更是在“境界”说的基础上宣扬“词心”说的理念等,皆受到王国维“境界”说的影响。
三
第三阶段是1919—1949年,这一时期是现代词学的开端。这一时期词学观念随着历史事件的演进而不断变化,反映在词集评点上,即是传统派与新变派并存。
首先,传统派词学家,以晚清四大词人为代表的词人群体进入现代以后发生了身份转换,他们大部分以遗民自居。在词学理念上,他们承续常州词派,传授衣钵。如朱祖谋、况周颐、陈衍、夏敬观、陈宝琛、沈曾植、夏孙桐等。朱祖谋寓居海上,成为现代词坛一代宗师。晚清遗老如郑文焯、陈衍、夏敬观、沈曾植、周庆云等一批词坛名宿多与其交游,在退出政治中心以后,词学成为他们日常消遣的重要内容。就词集评点而言,除前文朱祖谋、郑文焯以外,夏敬观是现代词坛中对唐宋词研究较为深入的词坛大家,《吷庵词评》(1)见《词学》第五辑。据前言知,《吷庵词评》由今人葛渭君辑所购夏敬观手批《彊村丛书》得。是其词集评点的重要成果。今人葛渭君曾将夏敬观手批宋人词集汇辑成编发表于《词学》杂志。据词评知,夏敬观以《彊村丛书》为底本评点唐宋人词集共8家11种。考察其具体评点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夏敬观于词之文学层面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涉及词艺、词韵、对仗、炼字、事典、情景关系等多方面。比如评张先词多以古乐府填词,其《菩萨蛮》“忆郎还上”“牡丹含露”皆是如此。又言张先、晏几道善以小令之法填长调,别具风味。再如对宋人词句中对仗的关注。二是夏敬观认为填词应学会另辟蹊径,比如熟调生作、生调熟作,应当求新。如其评晏几道词,就认为小山词往往能反出新意,或是新在词意,或是新在炼字。这一阶段,传统派词人除了评点前代词集以外,还致力于当代人词集的评点。其实,近现代人对同时代词集的评点多集中于词别集评点,词评人与被词评人往往有密切的关系。近代词集评点,如《箧中词》《词则》均有评点同时代人词的内容。然而多是选词评点,还不成气候。近现代之交,词学界开始出现大量的同时代词别集评点著作,比如朱祖谋、况周颐等评点徐珂《纯飞馆词》。察是集知,共有6人评点徐词集,并且6人与徐珂皆往来频繁。再如王闿运评点杨庄《湘潭杨叔姬诗文词钞》,杨庄乃王闿运入室女弟子,两人有师承关系。由序知,杨庄一旦有所创获,即请业师评点。此外还有杨圻《江山万里楼词钞》、许之衡《守白词甲乙稿》、关志雄《玉窗词甲稿》等皆有时人评点,或是友朋之间的评点,或是师生间的评点,都体现出词集评点在现代的兴盛。
除词集评点外,整理词集评点文献亦是现代词学的重要内容,集大成者是徐珂。徐珂师从谭献,多承袭常州派词论。他是整理词集评点文献的重要人物。与词集评点“著书立说”的观念不同,集评词集评点相当于对词集评点资料的二次整理,对研究词学理论而言,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如其《清词选集评》是汇辑清代存有名家评点词作的著作。与谭献“立言”说不同,此书目的在于传播学词途径。徐珂辑选清词620余阕,曾说:“以便初学者易于领悟云尔。”[12]从内容来看,徐珂选词多源于《箧中词》,集评多出于谭献,另有沈雄、况周颐两家评语。徐珂集评颇有词评选的意味。所谓词评选,既是对所存词作的筛选,又是对前人评点的甄别。从意义来看,集评清人评清词可以综观清人对同时代词人词作的标榜与推崇。有清一代,前期如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后期如清末四大家等人均备受推崇。整理清代词集评点文献,对清词经典化具有重要意义。再如《清代词学概论》中集评清人词集,可以考察清人评清词的理论价值和文化意义,体现出清代词学发展的时代风貌。再有其《历代词选集评》《历代闺秀词选集评》均是对词集评点文献的汇辑,除了徐珂所言“以便初学”之外,还为考察前人的词学理论提供了便利。
其次,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现代派词人为词学发展带来诸多新理念,词集评点中多有体现。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之风即对传统文学形成较大冲击。尤其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新文学者打着“反孔”的旗号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学进行猛烈抨击,对传统文学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然而,就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延续性来看,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比如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整理国故是对新文化运动将传统文学一网打尽的历史清算和自我反省,它使得一切中国传统文学得以重新回到学界的研究视野。就词学而言,新文学界中的部分学者对词持有积极的态度,只不过在传统词学理念上提出了新观念。例如胡适、章衣萍、郑振铎、柳亚子、林庚白、郁达夫等人,皆对词学发展表达过自己的看法。胡适是最早承认词学的新文学家代表。他认为词是平民文学,是古人创作的白话文。因此他提倡白话词创作,并躬身实践。其他如梁启超、章衣萍、郁达夫、朱自清等皆曾尝试填制白话词。白话词选、白话词创作以及白话文评词日渐兴盛。白话词选如凌善清《历代白话词选》,多选历代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之词。其选词多注意明白晓畅、浅显易懂之语,称之为白话词。胡适评价清词:“天才与学力终归不能挽回过去的潮流。三百年的清词,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所以这个时代可说是词的鬼影的时代。”[13]胡适认为清代既有词人,也有词作,然终不出宋人门户,活在400年前潮流的影子下。这固是其倡导白话词而言。如其所认为的宋代白话词,如辛弃疾《西江月》(七八个星天外)、《清平乐》(茅檐低小)、蒋捷《一剪梅》(一片春愁待酒浇)、向镐《如梦令》(谁伴明窗独坐)等,皆是通俗简明之作。反是辛词豪放一脉入选不多,再如蒋捷、向镐等前人评价不高的词人词作以及稼轩较为简单的词作由《词选》得以广泛传播。再如范烟桥《销魂词选》,所选评多是明清以来女性词,且评点均以白话行文。这两大特点均与时代变化有关。一是西学东渐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社会注入新鲜思想。女性逐渐摆脱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在男性话语权的主导下逐渐提高社会地位。还有新文化运动以来对白话文的提倡。二是王国维《人间词话》对词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王国维认为词学研究应该更注重词本体的审美特征,强调真情实感的抒发。范烟桥《销魂词选》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原因。范烟桥选评女性词,认为女性词更能体现真情、至情。
除了上述两派代表以外,还有一批词学家既接受了传统词学的熏陶,又受到现代词学的熏染。他们不仅是近代词学的传承人,还是现代词学的生力军。这批学者以叶恭绰、吴梅、陈匪石、乔大壮、唐圭璋、夏承焘、龙榆生、卢前等人为代表。这批学者承接前学衣钵,延续词学命脉,在词集评点方面亦颇有建树。从社会身份来看,他们或流于政坛,或执教高校,有相对稳定的词学研究环境。一方面,他们对传统的词学观念多有继承。比如叶恭绰、吴梅、龙榆生等人继承“彊村派”词学理念。叶恭绰《广箧中词》以广谭献《箧中词》为志,其中也体现了其对谭献词学观念的接受。从选词来看,叶恭绰所选现代词人多是彊村派词人,他们或多或少均被朱彊村称许或提及,比如陈衍、沈曾植。此外,奉朱祖谋为领袖的沤社社员词作入选达27人,几乎囊括所有社员。吴梅于彊村词学多继承“严守音律”一则,他评点《广箧中词》除论及少数词人本事以及表述词选观外,全是对叶氏所选词作音律的评价,足见其对词之律吕的重视程度。龙榆生奉彊村衣钵,校勘并出版《彊村丛书》,又创办《词学季刊》《同声月刊》引领词学风会,可谓名噪一时。至于词集评点方面,龙榆生主要是集评之功。如其《词学季刊》曾辑录《彊村老人词评三则》,此外还有《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夏吷庵手批〈东山乐府〉》等。此外,以高校课堂教案为底本的词集评点也在此时诞生。比如陈匪石《宋词举》、蔡嵩云《作法集评唐宋名家词选》、邵祖平《词心笺评》等。陈匪石《宋词举》被称为现代词学普及化读本的范本,是选体例独特,即以历史倒序排列选词。察词选内容,有集评文献收录在内。汇辑前代词家评点已经成为现代词选的重要特点,唐圭璋《唐宋词简释》、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等皆有集评。另一方面,现代词学家如叶恭绰、龙榆生对词体发展做出过新的尝试。他们从“词乐”的角度出发,提倡创制“新体乐歌”,以期突破传统词体对创作的束缚,而且得到当时音乐学家的鼎力支持。这一观点与南社诸子有关“词体革命”的讨论有相似之处。但无论是新文学家的尝试,还是现代词学家的探索,这种“应歌”的词体模式并没有成功。然而,对于现代词学的发展而言,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再次,20世纪30年代以后,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有识之士以词学研究为阵地,发起抗日救国的呼号。这一阶段的评点理念由重考证、重词艺向重政治倾斜,词的社会功用明显加强。辛稼轩等豪放词选评多受重视。最明显的是邵祖平《词心笺评》、李冰若《〈花间集〉评注》等。邵祖平笺评提出新的词学观,即“词心”说。邵祖平所谓“词心”从王国维“境界”说来。他认为王国维“境界”即“词心”。他说:
沧浪论诗之所谓“兴趣”,阮亭论诗之所谓“神韵”,皆不若“境界”二字为能探其本源,其言甚辩,词学家奉为圭臬。以予观之,王氏所谓词境者,皆“词心”也。世间一切境皆由心造,心在则境存,心迁则境异。[14]1
邵祖平借王国维“境界”说以提出“词心”说,认为“词心”就是词人要表达的深层意蕴。这类深层意蕴并非张惠言《词选》所评温庭筠《菩萨蛮》的“士不遇”“楚骚”等附会之语,而是“心思微茫,唱叹低回,蕴蓄深厚”[14]3之作。邵祖平在抗战大后方,率词操觚,以“词心”说标举政治立场。正如其言:“词心之哀感顽艳,足验世局之分崩离析矣……世之周旋斡奁之间,系心疆场之上者,岂可谓之无心之人哉?”[14]6足可见其词心所指。至此,我们不由得惊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每到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总有思想进步的文人以词为利器,谱写时代的序曲。有所区别的是,近现代以前的所谓家国危亡多是汉民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斗争,是民族内部之间的矛盾;而近现代以来,是整个中华民族与外部势力的殊死搏斗,此时选评前人具有爱国思想的豪放词作更能体现中华儿女与敌对势力决战到底的不懈信念。
总之,近现代词集评点经历了从“词学尊体”到“多元发展”的转变。一方面是常州派词人借诗教以尊词体,深化和完善常派词论;另一方面是以晚清四大词人为代表的传统词人深耕词体,侧重于词艺、词作法、词律的评析。除此以外,王闿运等词家独辟蹊径,以“诗意”取代“诗教”,以情论词,重视词本体的发展。梁启超等维新派文人从社会批评的角度出发,提出文学改良政治的理念,积极探索“词体改良”的模式,逐渐向现代词学过渡。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历史潮流涌动中,在各方势力坚守下,词集评点呈现出“尊体”“主情”等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为丰富词学理论、助推现代词学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