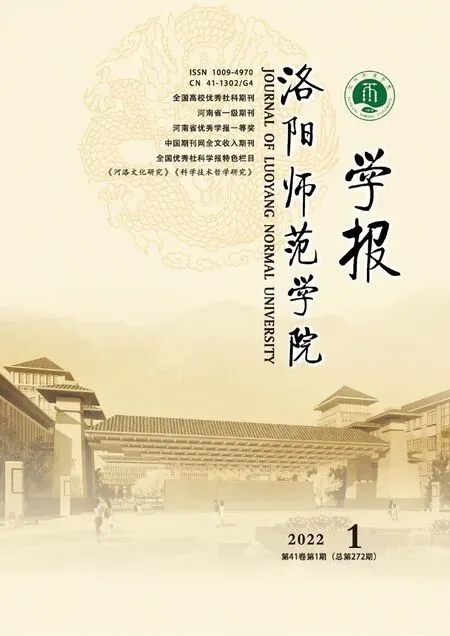唐代与北宋时期的洛阳私家园林考略
2022-03-18王雨晗
钱 伟,王雨晗
(贵州财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中国古代园林先后有囿、苑、台、榭、圃、林泉、林亭、园池、亭台等多种称呼; 类型丰富多样,有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庙园林、陵寝园林、衙署园林、学府园林、祠馆园林等类型。其中,皇家园林指古代帝王所拥有的园林,其特点是规模庞大,气势恢宏,体现了皇权至上的思想; 私家园林由官宦、富商、文人、地主等兴建,多为休憩、游赏、欢娱之所,其风格典雅隽逸,诗情画意,体现文人雅士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 寺庙园林是古代佛寺、道观的附属园林,其风格庄重而不失清秀,宗教色彩浓厚; 陵寝园林是古代帝王及其家人的长眠之所,其特点是以自然山体与人造山体为依托,其布局与古代的生态环境观有密切联系。事实上,这几种园林往往相互交织和影响,在风格上多有共通之处,通过凿池开山、栽花种树模仿自然,营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境界; 通过利用各种建筑物,如亭、台、楼、阁、廊、榭、轩、舫、馆、桥等,配合山、水、石、花、木等自然元素组成情趣盎然的景致,达到人工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另外,古代园林多通过“一池三山”“移天缩地”“壶中天地”“芥子纳须弥”等造园理念和手法在有限的空间创造丰富的景观。
中国古代私家园林肇始于西汉。东汉定都洛阳,御苑和私园的重心转移至中原。西晋时期,豪门贵族纷纷在都城洛阳建造私园。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石崇所建的金谷园。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方私家园林以洛阳地区最盛。唐朝时期洛阳为东都,北宋时期洛阳为西京,洛阳的私家园林发展到顶峰。北宋以后,洛阳因远离政治、经济中心而逐渐褪去了昔日光环,城市地位急剧下降,那些名噪一时的私家园林也走向衰落。
一、宏大壮丽的唐代洛阳私家园林
唐代政治昌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生活上求富、精神上求乐、居住上求适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的普遍追求。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富豪巨商和文人学士争相营造豪华的宅邸和园池,私家园林的建设进入高潮阶段。作为东都,洛阳城内外出现了大量的私家园林,在古代造园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洛阳名园记》云:“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1]仅洛南里坊区之内就有魏徵、宋璟、崔融、苏味道、狄仁杰、裴度、姚崇、张说、牛僧孺等人的园林。
这些园林大都筑山造池,山、池遂成为园林之标志。其中,城市园林俗称“宅园”,在初唐多称为“山池院”或“山亭院”,中晚唐多称“园池”或“池亭”。其特点是紧邻宅邸,呈前宅后园的格局,规模不大,常作休憩、宴乐、会友、读书之所。此外,还有少数单独建置,不依附宅邸的“游憩园”。建在郊外山林风景地带的私家园林大多是“别墅园”,时称“别业”或“山庄”。“宅园”以白居易的履道坊(1)据考古发掘,履道坊的位置大约在今洛河南狮子桥村东。宅园最著名,“别墅园”则以李德裕的平泉山庄最具代表性。
长庆四年(824),白居易 53 岁,被罢杭州刺史后移居洛阳,买下散骑常侍杨凭的履道坊宅园,在此植树、种花、挖池、建亭、开路、筑桥,至 75 岁时在此病故。白居易在其诗《池上篇》中曰:“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2]331俨然一幅隐士园居图,悠闲自在。白居易热爱生活,隐居深山与其性情不符。他愿意出门即是朝堂,回家就是山林,于是便探索到了一种“中隐”的生活方式:“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 深山太获落,要路多险艰; 不如家池上,乐逸无忧患。”[2]354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终身纠结的一个选择是做官还是终老山林,是达则兼济天下还是退而独善其身。白居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隐”思想,在为官和隐逸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即“心隐身不隐”,为中唐及后世的士人们探索出了在官场和集权政治包围中突围的道路。
在宣风坊中有初唐宰相、诗人苏味道的宅园,宅中有三十六亭子,时称巧绝。一座亭子有36根柱子,其造型之复杂是可以想见的。在道德坊中,后来还曾有唐末五代时后唐宰相郭崇韬的宅园,园中有十二逗角子,制作甚精。这里的“逗角子”应该是从古代建筑“钩心斗(逗)角”之结构譬喻中而来的概念,“十二逗角子”即有十二个转角的园林亭阁建筑。这种十二角的建筑在古代木构中也是不多的。从三十六柱亭和十二逗角子可知,唐宋园林中已经开始通过建筑物的奇特造型来作为园林的景观要素了。
除了城内的宅园外,洛阳郊野也有几处著名的私园。其一是中唐政治家、文学家裴度的别墅“绿野堂”,其故址在今洛阳市南。裴度平定藩镇叛乱有功,晚年因宦官专权辞官退居洛阳,于午桥建别墅,种花木万株,筑燠馆凉台,名曰“绿野堂”。裴度常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名流在此园以诗酒相会,昼夜相欢,不问世事。
另一处是晚唐名相李德裕的平泉庄。据《唐语林》记载:“平泉庄在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甚佳。有虚槛,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十二峰……平泉庄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四方奇花异草……怪石名品甚多……有礼星石、狮子石,好事者传玩之。”[3]《说郛》云:“李德裕东都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对引,泉水萦回,疏凿像巫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讫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以间。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磨之,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初德裕营平泉,远方之人多以异物奉之。”[4]平泉庄内栽植树木花卉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名贵,著称于当时。李德裕所撰的《平泉山居草木记》中记录的名贵花木品种计有金松、海棠、红豆等60余种。据考证,此园故址位于今洛阳南郊15 公里处的伊川县梁村沟,周回10余里。
李德裕平生酷爱珍木奇石,宦游所至,随时搜求,再加上他人投其所好,竞相奉献,平泉庄就成了一个收藏各种花木和奇石的大花园。此外,园内建置台榭百余所,有书楼、瀑泉亭、流杯亭、西园、双碧潭、钓台等,还驯养了各种珍禽异兽。当年李德裕常和文人名士在此园饮酒唱和,共赏风光,留下洛阳八景之一的“平泉朝游”。可见,这座园林的“若造仙府”的风格正符合了园主身为相国的显赫身份,这与前述白居易等一般文人官僚所营园墅是迥然有别的。遗憾的是随着宣宗时李德裕被贬崖州司户,平泉庄自此开始衰败,至宋代已成“遗基皆瓦砾”“池平无旧凤”的山野之地。
与平泉庄齐名的另一处名园是晚唐宰相牛僧孺的归仁里园,二者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对湖石的偏好。牛僧孺与李德裕在晚唐都曾官居宰相高位,但在政坛上相互敌对排斥长达40年之久,系晚唐政局中著名的“牛李党争”的代表人物,然两人同为唐代著名的藏石大家,有着共同的奇石癖好,对太湖石的开采和太湖石审美价值的宣扬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二人的带动下,收集太湖石作为园林点缀成为社会热潮。与此相伴,太湖石的鉴赏标准,如怪、奇、透、丑、润、瘦、漏、皱、清、古等也在此时被确立下来。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朝气蓬勃、繁荣昌盛的盛世,文学艺术成就灿烂辉煌,这促进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造园风格开始形成,为宋代文人私家园林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尽管安史之乱和唐末战乱一度使洛阳遭受了重创,但北宋时期,西京洛阳又很快恢复了生机。
二、精致写意的北宋洛阳私家园林
北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璀璨,私家园林兴盛一时。这一时期,西京洛阳虽不似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体的东京汴梁那般繁华,却因其浓厚的历史底蕴成为官宦文人们的理想居所,再加之洛阳山川秀丽,水源丰富,气候温和,那些前朝遗留下来的诸多无主荒地因此成为建园沃土。于是,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等大批地位显赫的官员纷纷在此置田建园,作为乐享清静的第二居所。苏辙曾说:“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而其贵臣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5]这些园林星罗棋布,彼此相望,春花秋实,修竹长扬。北宋私园的繁盛可从当时的文人著述中窥得一斑。
北宋晚期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以细致的笔触列述了洛阳最有名的19处园林,描写了各园的总体布局以及山池、花木、建筑所构成的景观。这些园林多是在唐代废园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风格迥异,主要表现在园林与住宅分开,建筑少,假山多,常以水池为中心且以植物景观见长。这些园林可分为花园、游憩园和宅园三类。
(一)花园
此类私园有三处,分别是:
归仁园:此园是当时洛阳私园中最大的一处,原为唐代名相牛僧孺所建,后归宋代门下侍郎李清臣所有。《洛阳名园记》说:归仁园“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1]43。该园植物种类繁多,以花木取胜,一年四季花期不断,是个名副其实的百花园。
天王院花园子:此园位于宣风坊(今洛阳安乐镇聂湾村一带),原是隋朝贵族杨文思之宅第,杨文思死后,隋炀帝将此园赐给东都留守樊子盖。此园既无池也无亭,系单一的牡丹园,共植牡丹十万株。
李氏仁丰园:此园是北宋开国功臣李继勋的园林,其名称来自《国语》中“畜义丰功谓之仁”[6]。这也是个著名的花园,除本地名花外,也移植外地花卉,总计达千种以上。
(二)游憩园
此类私园有九处,分别是:
丛春园:为门下侍郎安焘的私园。园内植有桐、梓、桧、柏等树。站在园中的丛春亭上,可望奔流的洛水,河水撞击天津桥,声闻数十里。这一借景园外、景声兼得的设计别出心裁、独具匠心。
松岛园:为五代十国大臣、归德军节度使袁象先的宅园,宋时归李迪(真宗、仁宗两朝宰相)所有,因园中参天古松而得名。园中竹篱茅舍古雅幽静、野趣盎然。
水北园、胡氏园:此二园位于邙山山麓,相距仅十多步,瀍水流经其旁。其特点是顺应地势,沿河岸掘窑室,开窗临水,远眺“林木荟蔚,烟云掩映,高楼曲谢,时隐时见”[1]47。由于“相地合宜”,达到“天授地设”之境界,成为洛阳城中胜景。
吕文穆园、东园:此二园分别是北宋名相吕蒙正和文彦博之宅园。二园因地制宜,利用自然水系,流水清澈,树茂竹盛,可谓“水清木华”。另外,其桥亭结合的设计手法也成为宋以后园林艺术的楷模。
紫金台张氏园:此园设四亭供游园者远眺近览,是个极佳的游憩类园林。
董氏西园:为工部侍郎董俨的宅园。此园模仿自然,取山林之胜,注重地形的起伏变化,运用障景手法,空间变化有致,面积虽小但意境幽深,进入后没有一览无余之感。
独乐园:这是司马光的宅园,以“洛中诸园最简素”而名重于时。司马光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政坛失意,于是离开政治中心,躲进此园专心编撰《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诗文《独乐园记》与《独乐园七咏》使此园以文传、园以文存,同时也彰显了园主的个性气质,所以李格非认为独乐园“所以为人钦慕者,不在于园尔”[1]48。此园以“独乐”为名系反用《孟子》中“与民同乐”的典故,表面上看好像很消极,但实际上蕴含着古人“穷则独善其身”的观念,反映了深刻的哲理和通达的人生态度。
(三)宅园
此类私园有六处,分别是:
大字寺园:此园原为上文所述白居易之履道坊宅园,五代时改为“普明禅院”,北宋时该园东半部被洛阳名士张师雄(号“蜜翁翁”)购得,更名为“会隐园”,后又更名为大字寺园。
苗帅园:此园系节度使苗授之的宅园,由唐朝天宝年间宰相王溥的宅园演变而来,“园既古,景物皆苍老”[1]51。园东有水,自伊水分行而来,可行大舟,在溪旁建亭,有大松七棵,引水绕之。有池,池中种植莲荷荇菜,建水轩,跨于水上。“对轩有桥亭,制度甚雄侈。”[1]52此园在总体布局中,水景至关重要,轩榭桥亭皆因水池、溪流就势而成。
环溪:此园是名臣、诗人王拱辰的宅园,其造园手法是以水景取胜,园中水流环绕,临水建亭、台、轩、榭等建筑,采取收而为溪,放而为池,既有溪水潺潺,又有湖水荡漾。全园以溪流和池水组成的水景为主题,临水构置园林建筑,绿化以松梅为主调,花木丛中辟出空地搭帐幕供游人赏花。借景的手法在环溪中也运用得当,南望层峦叠障,远景天然造就,北望有宫阙楼殿,千门万户,延亘十余里,山水、建筑尽收眼底。园内有宏大壮丽的凉榭、锦厅,可容数百人,正是“洛中无可逾者”[1]55。从园中的“多景楼”可以远眺嵩山、少室、龙门,一片层峦叠嶂; 而从北边的“风月台”北望,则是绵亘十余里的宫阙楼台。用李格非的话说:“凡左太冲十年极力而赋者,可一目而尽也。”[1]55左思耗十年之功所撰《三都赋》中的美景,在多景楼与风月台上都一览无遗了。这已不是一般的“聚景”,而是唐诗中“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境界了。在李格非的笔下,自然景物与人文建筑被赋予了时间的维度,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
赵韩王宅园:此园系北宋开国宰相赵普的宅园。赵普晚年还乡后隐居此园,但不幸百日后便辞世。由于其子孙居于东京城,故此园常年闭锁。虽园中有林木繁花、亭台池渊,但只是些小厮在看家护院。因此李格非感慨:“盖天之于宴闲,每自吝惜,宜甚于声名爵位。”[1]56上天的赐予是有限的,尤其是安闲享乐的生活,甚至比声名、爵位更难于获取。
湖园:此园原为唐中期政治家、文学家裴度的宅园。这是一个水景园,重视动静结合以及因时而变的景观效果,妙不可言,李格非对该园推祟备至。
富郑公园:此园系仁宗时期宰相富弼的宅园。该园以景分区,景区层次多,变化多,或幽深,或开朗,皆独具特色,形成岩壑幽胜、峰峦隐映、松桧蓊郁、秀若天成之意境。
北宋时期的小农经济稳步增长,商业文化空前繁荣,市民文化蓬勃兴起,大批文人参与造园林,洛阳私家园林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写意山水园林迈向了更高水平。
除上述园林外,北宋大儒邵雍的宅园安乐窝(2)遗址在今洛阳安乐镇东北的洛河滨河地带。亦是洛阳赫赫有名的私家园林。邵雍的好友司马光在《和邵尧夫安乐窝中职事吟》中这样描述:“灵台无事日休休,安乐由来不外求。细雨寒风宜独坐,暖天佳景即闲游。松簧亦足开青眼,桃李何妨插白头。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暇上高楼。”[7]由此可知,此园有松有竹,有桃有李,还有楼阁建筑,“安乐窝”并非虚妄之名。
邵雍是北宋理学家、道学家、诗人,终身未仕,却以名德动天下,是古代不出仕的文人代表。他的七言律诗《安乐窝中四长吟》“安乐窝中快活人,闲来四物幸相亲。一编诗逸收花月,一部书严惊鬼神。一炷香清冲宇泰,一樽酒美湛天真。太平自庆何多也,唯愿君王寿万香”[8],描述了闲适自得的生活状态,同时也有求道修仙的意味。他写诗来吟咏性情,以著书来阐述学说,以焚香来修身养性,以饮酒来安顿心灵,生活忙碌充实,精神快乐满足。
中国历史上,由文人和官僚组成的“士”阶层一直列封建社会民间等级序列的首位,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士人若想建功立业必须依附于皇帝,接受当朝的社会行为准则,但由于宦海沉浮,仕途坎坷多险,为了维护自己独特高雅的品格,不屈服于流俗,不献媚于朝廷,一些士人走上隐逸之途,隐士由此产生。宋代的隐士一般都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亲自参与园林的建造,从规划布局的理念到具体情境的塑造,都表现出对隐逸思想的追崇。上述邵雍即是一例。
总体而言,唐宋时期在文人儒士的推动下,诗文、绘画、园林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洛阳私家园林展现了浓郁的诗情画意,简远、疏朗、雅致、天然的写意山水园林成为主流。作为北方园林的代表,唐宋时期的洛阳私家园林不仅影响了后世扬州、平江(今苏州)、吴兴(今湖州)、临安(今杭州)等地的江南园林,同时还影响了邻国的园林发展。如在日本的江户时代,江户(今东京)建了“六义园”,金泽建了“兼六园”。“六义”和“兼六”源自《洛阳名园记》:“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 人力胜者少苍古; 多水泉者艰眺望。”[1]65也就是说园林空间的大与小、高与低、人工景物与自然景物的艺术谐美,这六者不可兼得。日本先贤对此观点推崇备至,遂将其概括为“六义”与“兼六”并直接用作园林之名,可见宋代洛阳的园林艺术对其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