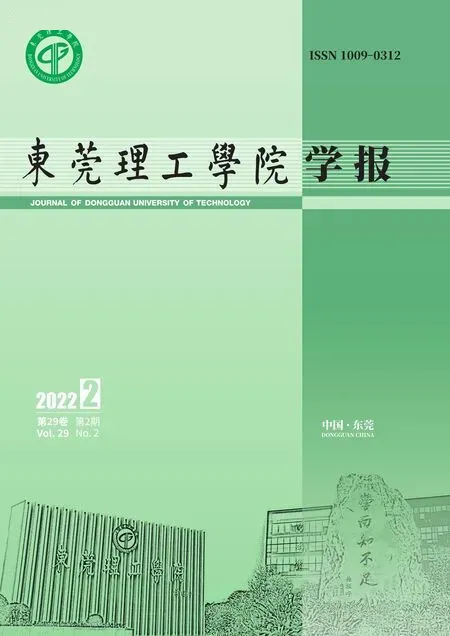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林语堂《琵琶行》译本美学探究
2022-03-18鲍艺雯李平
鲍艺雯 李平
(南京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95)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美学对中国文化、文学以及翻译事业的影响都不容小觑,因此翻译美学也是翻译研究中不可跨越的议题。中国最早的翻译美学命题来自于《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在中国翻译史上,也有千千万万的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实现了译学与美学的联姻,包括佛经翻译时期的鸠摩罗什与玄奘,清末民初的林纾与严复,现代的钱钟书与许渊冲等等[1]13。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学的翻译是离不开美学的,而翻译美学的重大作用就是保证在语际交流中进行有效的达意传情[1]22。
中国传统文化正通过大量文学作品的翻译走向世界,这些作品中就不乏一些古典诗词。中国古典诗词本身具有韵律美、节奏美、意境美等,而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活动。在翻译这些古诗词的过程中,译者能通过个人的审美将原诗的美再现出来。
林语堂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生都喜爱中国古典诗词,也关注古诗词的翻译,曾经论述过自己独特的诗歌翻译观。《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最著名的长篇乐府诗之一,林语堂在翻译时也将自己的美学观融入,使读者更好地体会到原诗的形式美、声音美、意义美、传神美以及文气美。
一、翻译美学理论概述
翻译美学理论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西方翻译美学相关的研究较少。翻译理论家Peter Newmark在ApproachestoTranslation中就以诗歌翻译为例,强调了语义翻译当中审美价值的重要性[2]。翻译学家Susan Bassnett与Andre Lefevere合著了ConstructingCultures:EssaysonLiteraryTranslation,其中第八章提到了文化对审美价值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更加多元化[3]129-133。Shirley Chew与Alistair Stead共同编著了TranslatingLife:StudiesinTranspositionalAesthetics,较早从美学角度出发探讨文化翻译,促进了翻译研究与美学研究的融合与发展[4]。
在我国,朱光潜于20世纪80年代就将“翻译美学”作为专门术语提出,指出翻译是离不开美学的。作为朱光潜的学生,刘宓庆深受朱光潜翻译美学思想的影响,于1995年在自己的著作《翻译美学导论》中专门论述了翻译美学,首次将翻译美学作为一种翻译理论进行系统研究[1]。
翻译,就像人们身边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离不开审美与美学,译学中的审美问题值得学者们深入思考与探究,而翻译理论更是从诞生之初就与美学理论紧密相连。翻译美学运用美学的观点认识翻译,分析并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在充分认识翻译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的基础上,翻译美学剖析原文的审美构成以及译者在翻译中的能动作用,明确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提供翻译审美再现的类型与手段,从而指导翻译实践[5]296。
刘宓庆这样强调学习翻译美学理论的重要性:“如果不学习翻译审美理论,就不会总结优化自己的翻译经验,不会作过程和产品分析,更不知道怎么进行审美价值论证。这样一干几年,事倍功半,自叹枉费光阴,实在是很值得惋惜的!”[1]17因此,他详细论述了翻译美学理论,指出翻译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科学性伴随着艺术性,而艺术性强化了科学性。中国译论与美学很早就有联系,“美与信”“文与质”“信达雅”“神与形”“化境”等命题也让这种联系越发紧密。西方译论与中国不同,它最开始从哲学的角度阐释美学,关注美的本质问题,但后来越发受到语言学的影响,以至最后西方的译论与美学分离。由此可见,现代翻译美学理论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1]1-73。
刘宓庆详细论述了翻译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认为二者是不可分离、互为依存的。刘宓庆专门讨论了翻译审美的价值论,从视听感性、结构形态、意涵容载、情感含蕴、意象寄寓、文化特色几个方面分析了语言美的价值[1]187-201。了解翻译审美意识系统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有利于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能更有效地实现客体美的主体化[1]204-205。由于翻译艺术具有普遍性、依附性、变通性这三大特征,翻译原语艺术作品与翻译原语非艺术作品之间只有层级的区别,所以刘宓庆叙述了基础层级的翻译艺术问题[1]242-243。
文学美具有综合性,既包括表现性的美,也包含再现性的美,并且常常表现中有再现,再现中有表现。“文学翻译”被称作综合层级的艺术性原语翻译,它有三个审美特征,一是“翻译审美必须整个心理结构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二是“翻译审美必须用想象校正对原文的理解”;三是“翻译审美必须与作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288-302。刘宓庆深入地探讨了文学翻译的审美图式和审美再现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在西方美学中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追求中西方文化的融合[1]348-349。
之后的学者也在刘宓庆的启发之下,对翻译美学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更新与完善。刘宓庆与章艳合著的《翻译美学理论》对《翻译美学导论》做了一定的补充,对翻译美学理论展开了全面论述,不仅讨论了汉语和英语语言的美,也梳理了中西方翻译美学的发展历程[6]。李智在总结翻译美学理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现代美学视角出发审视传统译论,对翻译美学中的言与意、文与质等命题展开讨论,并提到了自己对翻译美学发展的一些思考,以期促成传统译论的现代化转型[7]。龚光明的《翻译美学新论》整合了美学理论与翻译理论,从比较诗学、文化诗学以及比较美学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对翻译美学研究进行了新的尝试[8]。
作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一环,翻译美学理论已经开始展示出自己独特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相关研究层出不穷,研究方法也逐渐完善。虽然翻译美学理论植根于中国传统译论,但也应该积极吸纳西方先进的理论,以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这样一来,翻译美学才能够为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新的视野。
二、林语堂的美学观
林语堂的美学思想与美学态度不仅受克罗齐(Croce)和斯宾加恩(Spingarn)美学观点的影响,也受到道家文化精神的影响。在中西方美学观的双重影响下,林语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观,包括他的性灵观、幽默观、闲适观等。受袁氏三兄弟所创的“性灵派”影响,林语堂提出了自己的性灵观,指出艺术家在创作时应当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9]362-363。在此基础上,林语堂提倡近情精神,“近情”就是指亲近他人的感情,是一种人性化的思想。“近情精神”是人类文化中最高、最合理的理想,也是中国贡献给西方最好的一件事物[9]396-397。
林语堂的幽默观也是他美学观的一部分。幽默观与性灵观关系密切,因为解放性灵是幽默的前提。林语堂于1924年率先将“幽默”的概念引入中国,然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论语》发刊,他的幽默观才逐渐为学界所接受[10]148。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所有使人发笑的文字都是幽默;而狭义上,“幽默”可以是一种思维方式,也可以是一种人生观。“幽默”是客观与自然的,它基于明理,而不是讽刺[11]4-17。林语堂的闲适观,即悠闲思想,也是他的重要美学观之一。林语堂指出,中国人的悠闲哲学由来已久,根本上是平民化的,当一个人是恬静乐观的,他就有资格享受悠闲的生活。他认为道家学说使人相信祸福相连、静胜于动,这也促成了中国人好悠闲的性格[9]153-163。
林语堂的美学思想与美学态度更体现在他的翻译观之中。他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认为翻译的艺术依赖三个要点,“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问题有正当的见解。”[12]417基于第三点,林语堂在《论翻译》中用比较大的篇幅详细论述了翻译的标准问题。
翻译的三个标准分别是忠实标准、通顺标准和美的标准。林语堂认为,真正的忠实应该是相对的、比较的忠实。译者在尽量保持与原文主旨一致的同时,应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林语堂的忠实标准主要有三义:(1)忠实不是指字字对译,而是指译者需要忠实于原文的意义;(2)译者除了忠实于语意外,还要忠实于原文作者表达的情感与言外之意;(3)绝对忠实是不可能的,译者需要做到的是比较的忠实。在忠实的第三义中,林语堂极富创见地提出“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12]419-427林语堂认为,文字的“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不能同时译出,须有取舍,这在他的译文中也有所体现。
林语堂所提出的美的标准正体现着他独一无二的美学观。虽然这三大标准是在严复“信达雅”的基础上提出的,但林语堂指出,翻译与艺术文(诗文戏曲)的关系并不能简单用一个“雅”字概括。他一直保持着“为艺术负责”的态度,认为理想的翻译家应该将翻译当做一门艺术。林语堂赞同克罗齐的“翻译即创作”一说,认为翻译的美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译者的审美[12]430-432。林语堂关于翻译的美的标准所展开的讨论是中国翻译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后来的翻译学家也起到了深刻的启迪作用。
林语堂在《论译诗》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诗学翻译观,强调“意境第一”,他认为译文的流畅自然是最重要的,不需要刻意用韵,而译者要精通英汉两种语言,用字“精炼恰当”,并将原文的意境还原出来[13]317-319。由此可见,传情达意不仅是翻译美学理论的重要观点之一,也是林语堂在诗学翻译中总结出的一个美学观点。凭借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喜爱,林语堂也翻译了许多诗歌,更将自己的美学观融入了译作之中。因此,从翻译美学的角度出发探究林语堂的英译作品,也能更深入地理解林语堂本人的美学思想与美学态度。
三、林语堂《琵琶行》译本的美学体现
(一)林语堂《琵琶行》译本的形式美
在分析林语堂的《琵琶行》译本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原诗。诗人白居易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他的感伤诗《琵琶行》的体裁是歌行,属于乐府诗的一种,形式采用七言的古体,音节、格律比较自由。《琵琶行》写于元和十一年江州贬所,“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比兴相纬,寄托遥深。”[14]183在诗中,白居易描写了琵琶女的精湛琴艺以及她的曲调所传达的丰富情感,也刻画出他本人遭遇贬谪后郁郁寡欢的形象,表达出他对琵琶女的相知相惜之感。
在翻译中,林语堂在文体上做了一定的改动,原文白居易为《琵琶行》作序,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与地点,简述了琵琶女的身世,说明了自己创作的原因,为全诗定下了悲凉伤感的基调。但林语堂在译文中却没有将序言直接翻译出来,而是将其略去,作了一个导读与介绍。在导言中,林语堂向英语读者简要介绍了“行”这一特殊的古代诗歌文体,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琵琶”这一贯穿全诗的乐器。除此之外,林语堂提到,自己将这首诗由长篇叙事诗翻译为叙事性散文,灵活地叙述了诗人与琵琶女相遇的故事。与一般诗歌拥有固定的格式不同,散文体更为自由,也更能体现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在《论翻译》中,林语堂曾专门论述过艺术文的体裁问题,指出体裁指诗词的形式规范,需要译者在实践中选择最合适的[12]431-432。在翻译时,考虑到美的再现,林语堂认为将《琵琶行》翻译为散文最为恰当。之所以在翻译时舍弃“行”这一古代诗歌文体,而改用散文的形式,也是基于林语堂曾提出的译者对“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须有取舍这一点。虽然林语堂本人承认这样做会丧失一部分诗歌的韵味,但却可以更好地向外国读者传递原诗的内涵与意义,从而展现出形式之美。
(二)林语堂《琵琶行》译本的声音美
作为一种审美载体,语言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出现的,历史十分悠久。刘宓庆、章艳提出,语言审美是翻译美学的最佳切入点,探求语言美是翻译审美的基本任务,也是首要任务,而“视听感性”是语言美最基本的特色[6]78。“视听感性”中的“听”在诗歌英译中正是指译本所体现的声音美。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原诗的韵律美与节奏美,为读者带去听觉上的审美体验。
英汉诗歌中的音韵是有差异的,用韵方法也很不相同。明代陆时雍就写道,“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足见中国诗文中“韵”的重要性[6]46-47。在汉语诗歌中,押韵就是指用韵母发音相同的字放在句末。中国诗歌的节奏也有赖于韵, 借韵来点明与呼应,通过押韵使诗文更为流畅、动听。英文的押韵方式往往更为复杂,包括尾韵、头韵、谐元韵等。与中文诗歌相比,英文诗歌用韵较少,但在语音层面上有蕴含意义,转韵现象很常见,尾韵也灵活多变[15]75-77。
作为一首古体诗,《琵琶行》在平仄格律方面没有特定的要求,原文中押尾韵的情况出现较多,但一直在换韵,并没有一韵到底。“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一句,前后两句的音韵重心都落在了末尾一字上,押了“e”这个音。由于被译成了叙事散文的形式,无法保留原诗的韵脚,林语堂将“枫叶荻花秋瑟瑟”一句译为了“It was autumn and maple leaves and reed flowers swooped and flicked and snapped in the wind.”(那是秋天,枫叶和芦花在风中飞舞着。)[16]283,进行了巧妙转韵,“swooped”和“snapped”在句中押了头韵。头韵是指相连词语的起首发音相同而产生的音韵,能使译文更具音韵美,在平衡节奏的同时也能加深读者的印象。当词语中的元音音素相同,则构成谐音,使音调更为和谐与悦耳[17]95。“住近湓江地低湿”一句被译为了“The place is on low-lying ground and near the river.”(这个地方地势低,靠近湓江。)[16]285在译文中,“near”和“river”重复单元音/I/,这样处理不仅使译文更为简洁与生动,也体现了声音之美。
林语堂曾专门讨论过中国诗歌。他认为,如果没有诗歌,中国人就无法生存至今,正是诗歌让中国人以一种艺术的眼光看待人生,中国诗歌十分精巧,它不会很长,也没有很伟大的力量,但却因音韵节奏美而显得十分生动[18]236-237。在他眼中,诗歌的韵律美与节奏美一直十分重要。林语堂在《论翻译》中提到诗歌属于艺术文的一种,因此在翻译时能根据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译文中的音韵节奏等做相应处理,从而将原文的声音美更好地传递给读者。
(三)林语堂《琵琶行》译本的意义美
林语堂在论述忠实标准的第四义——通顺标准时指出,“通顺”要求译者对读者负责,译者需要在最大程度上令读者理解原文的意义。由于诗歌的特殊性,在翻译时译者只能做到相对的忠实。因此,林语堂在翻译《琵琶行》时,弱化了原诗的文体形式,而选择相对忠实地表达出原文的意义。
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一定差异,林语堂没有苛求译文与原文的句式保持一致,而是在翻译时采用了更为口语化的表达,如在琵琶女自述身世时,感慨道“Oh, she was very popular.”(哦,她真是太受欢迎了!)[16]285,又如将“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两句译为“Come on, stay a while and play some more for me while I write this poem in your honor.”(来吧,在我为你作这首诗的时候多为我弹几曲吧。)[16]285,这种口语化的语言使译文更为通俗易懂。
除此之外,林语堂通过添加注释的方法更好地表达了原诗的含义。他在译文中添加了三处脚注,前两处分别向没有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读者说明了“浔阳”(Kiukiang)的位置所在:“This is the same distinct where the poet built his mountain lodge in Lushan. See ‘The North Peak of Lushan.’”(这与诗人白居易在庐山修建草堂的地方是同一处。见《庐山草堂记》)[16]283;“教坊第一部”(the Court of Musicians No.1)的含义:“A government institution for training musicians and actors and actresses”(培训乐师与演员的政府机构)[16]285。林语堂将“老大嫁作商人妇”一句译为“What could she do but marry a businessman?”(除了嫁给一个商人,她还能怎么样呢?)[16]285,并在此加了第三处脚注。不似前两处做简单说明,林语堂较为详细地讲述了后世苏轼借用此句劝诫歌妓琴操,使其出家修行的故事,以表达琵琶女的无奈之感,将原文的意义相对忠实地传递给读者。林语堂对“蛤蟆陵”的翻译是“Hamoling[Frog Hill]”[16]284,这里不仅保留了拼音形式“Hamoling”,还添加了注释“[Frog Hill]”。在译文最后,林语堂添加了尾注,向读者说明白居易在创作《琵琶行》时已经成名,因此没有对诗文进行过多修饰与润色,而是进行简单的叙述,但这首抒情诗还是很快流传开来,被专业的乐者所吟唱[16]286。通过使用注释,林语堂既保证了译文的完整性,又向英语读者解释了原诗的含义,巧妙地再现意义之美。
修辞美是意义美的表现形式之一,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指出:“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种因素以美化语言。”[19]11为了再现原诗的风采,林语堂在《琵琶行》的翻译中使用了多种修辞语言。“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两句本身就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诗人以暴风骤雨来比喻琵琶大弦声的大气恢弘,以低声私语来比喻小弦声的幽细和缓。林语堂对于诗歌中比喻修辞的翻译多以直译为主,因此这两句的翻译是“The notes gathered up speed, those from the lower strings falling like fast raindrops and those from the higher trailing like whispers.”(节奏变快了,从较低的琴弦上落下的音符像雨滴,从较高的琴弦上落下的音符则像耳语。)[16]284。这里虽然增译了“The notes gathered up speed”一句进行铺垫,做了些许改动,但却没有改变原诗的喻体,并且选用了“fast raindrops”与“whispers”这样精炼的词汇,不仅相对忠实地传达了原诗的意义,也使译文语言更为生动形象。除此之外,“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两句译为“What can one hear except the song of cuckoos and the sad cries of monkeys?”(除了杜鹃的啼哭和猴子的哀鸣,还能听到什么呢?)[16]285,林语堂没有追求绝对忠实,而是将这两句诗翻译为反问句,更强烈地表达出原诗作者白居易对自身凄凉境遇的自嘲之感,以传递原诗的意义美。
模糊词的翻译体现了诗歌英译的朦胧美,这也是意义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转轴拨弦三两声”就被译为“She adjusted the strings and plucked a few notes.”(她调整琴弦,弹奏了几个音符。)[16]284。这里对于模糊词采取了对等译法,“三两声”与“a few notes”相对应,只不过前者是汉语中的模糊词,后者是英语中的模糊词。汉语中常用“三三两两”形容数量不多,而英语中与之对应的即是“a few”“a little”等。为求在翻译中达到与原诗相同的效果,林语堂以模糊词译模糊词,比较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意义,在语言表达上更贴近英文读者,使他们获得了一定的审美感受。
(四)林语堂《琵琶行》译本的传神美
林语堂在《论翻译》中指出,译者除了要在译文中展现出原文的意义,更要以“传神”作为翻译的目的。他解释了“字神”的含义,即一字逻辑意义之外的情感色彩[12]425-426。林语堂提出“意境第一”,“意境”是一种艺术境界,与“意象”“情境”关系密切,比较主观抽象,难以把握。通过“用字传神”,读者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原诗所要表达的情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原诗的意境[13]318-319。
《琵琶行》中的意境与一般的诗歌不同,是通过对相同景物的描绘层层递进的。林语堂的语言功底与审美水平可见一斑,这也保证了他能够在翻译中通过用词的精炼与传神还原原诗的意境。全诗第一个意境是前七句,被概括为“别时茫茫江浸月”。作为整首诗的序诗部分交代了背景,描绘了一幅冷清的秋夜画卷,渲染了白居易与友人分别之际的悲凉心境。这里的“江”与“月”两个意象奠定了全诗悲凉的基调。林语堂的翻译是“At this time, the river was flooded with a hazy moonlight.”(此时,河水笼罩在朦胧的月光之下。)[16]283,原文中“茫茫”二字被林语堂翻译为“hazy”。“hazy”正是林语堂重点强调的“字神”,在此处使用不仅再现了当时朦胧的月色之美,更表达了别离之际诗人内心升起的一阵凄凉与怅然若失。哪怕是不熟悉原文的英语读者也能通过译者选取的这一词汇,体会到原诗的情境,感受到诗人丰富的内心情感。
第八句到“唯见江心秋月白”是《琵琶行》的第二境。这句诗中的景物与前一境的“别时茫茫江浸月”一句一样,主要由“江”“月”组成,但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前一句的“茫茫”是句眼,突出景物的纷乱与渺远,而“唯见江心秋月白”一句的“白”字是句眼,突出听者的失神与陶醉,这里“白”的意象既单纯又复杂[20]68,不仅指水中倒映的明月泛起的白光,也指听完琵琶曲之后主人与宾客心中的愁绪与感慨万千。林语堂将这句翻译为“Only a white haze hung over the middle of the river.”(只有一层朦胧的白色薄雾笼罩在河中央。)[16]284,“月”这个意象没有被直接翻译出来,而是用“white haze”代替,与翻译“别时茫茫江浸月”一句时使用的“hazy moonlight”相呼应,描绘了朦胧月光之下,画舫和游船上的宾客欣赏完琵琶女的演奏之后产生共鸣但沉默无语、各有所思的场景,“hazy”一词烘托出诗人心中的悲戚之感。在这一境的翻译中,林语堂将“白”字直译,未译出“月”字,但却通过精当与形象地使用“hazy”一词,更好地表达了自己的审美情感,也将这种情感通过译文传递给了读者。
第三段到“梦啼妆泪红阑干”是另外一境,这一境发生在琵琶女自述完身世之后,被概括为“绕船月明江水寒”一句。这句主要的景物也与前面两句一样是“江”与“月”,但这一句的句眼却是“寒”字[20]69。这句的译文是“facing the cold water and the silent moon all by herself.”(她独自面对着冰冷的河水和寂静的月亮。)[16]285。与前两句不同,林语堂将此句中的“江”这一意象直接译为“cold water”,这是因为从“别时茫茫江浸月”到“唯见江心秋月白”再到“绕船明月江水寒”,这三大意境是逐步深入的,“绕船月明江水寒”更突出了“寒”这一艺术境界[20]69。林语堂强调诗歌翻译的达意传神,这里的“寒”一方面是指琵琶女回忆起自己的悲惨身世而升起的一种孤独悲凉之感,另一方面是指诗人借由琵琶女的经历联想到自己遭遇贬斥而感到的凄凉,这里将“寒”直接译为“cold”其实也是在向读者传递这双重情感。同时,译者在翻译中将“月”这一意象译为“silent moon”。听完琵琶女的悲惨遭遇,月亮并不能给予回应与慰藉,这轮“寂静之月”使整首诗中“寒”的意味更为明显。林语堂对原文意象所做的处理以及对译文词汇的选用,其实也是在自身审美的基础上追寻与原诗意境统一的结果。
(五)林语堂《琵琶行》译本的文气美
林语堂的译者主体意识与诗歌艺术性之间的碰撞促成了其译文的文气美。译者主体意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与创造意识;翻译主体性与译者主体意识息息相关,指翻译的主体及其体现在译作中的艺术人格自觉,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与审美创造力[21]9。文气之美说来复杂,其实就是指当读者阅读译文时,能感受到原文的力量与美以及译者的个人风格与气质。作为译者,林语堂的个人风格十分突出,这也与他本人的审美能力关系密切。
译者的审美能力是人所特有的在后天的实践和学习中形成的能力,主要包括语感、审美想象力、审美理解力、情感操控能力以及审美创造能力[22]192-204。除了拥有译者这一身份之外,林语堂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及作家。他编写了《开明英文读本》《开明英文文法》,为香港中文大学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其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更是先后获得四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对语言的感知能力自是不必多说。
译者的审美想象力一部分源自天赋,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审美经验,林语堂对不同译本所做的处理就体现了他丰富的审美联想力。译者的审美理解力具有感知性与直接性的特征,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克罗齐提出的“直觉即艺术”的观点,而林语堂也深受克罗齐美学思想的影响,认为艺术是作者个人的心境表现。林语堂在《论翻译》中完整论述了自己对翻译之美的理解,当这种审美理解力投射于他的英译作品中时,就显得更为复杂化了。
情感操控能力即译者的审美情感,审美创造力则是译者的艺术原创力。将这两种能力运用于诗歌翻译之中时,都离不开翻译主体与翻译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刘宓庆、章艳指出审美客体能够激起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激发审美主体的审美态度与情感[22]203-204。诗歌在林语堂眼中渗透于中国人的生活结构之中,甚至代替了宗教,教会中国人以艺术的眼光看待人生,诗歌创作更是体现了中国人的感性思维[18]236-237。正因如此,林语堂能感作者所感。《琵琶行》中白居易对自己遭遇贬斥的愤懑之情以及对琵琶女身世产生的共鸣之感能够引起林语堂的审美想象,进一步激发他的审美创造力,从而在译文中再现原诗之美。
林语堂曾经写道,像杜甫和白居易一样的中国诗人通过美来表达哀伤,使人类更加有同理心[18]251。以《琵琶行》译本为例,林语堂也具备这样的同理心,因此能理解原诗作者白居易想要传递给读者的悲戚之感,进而在翻译中运用自己的审美能力,结合个人的审美风格,表达出原诗丰富的情感,将原诗的美完整地呈现在译本读者眼前。林语堂不仅使读者体会到了《琵琶行》原文的创作风格以及他本人的个性气质,也促成了翻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良性对话与互动,使读者更深刻地感受到《琵琶行》译本的文气之美。
四、结语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而文化的对外传播离不开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语言审美理应受到重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古典诗歌凭借其精巧的形式、和谐的韵律、丰富的情感,越来越受到外国读者的青睐。林语堂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也一直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践行这一点。虽然中西方审美存在一定差异,但从翻译美学的视角出发,能更深刻地体会林语堂《琵琶行》英译本的形式美、声音美、意义美、传神美以及文气美,也能够更好地再现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内涵与审美特点。相信未来的学者也能够在这一基础上更深入地探寻翻译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