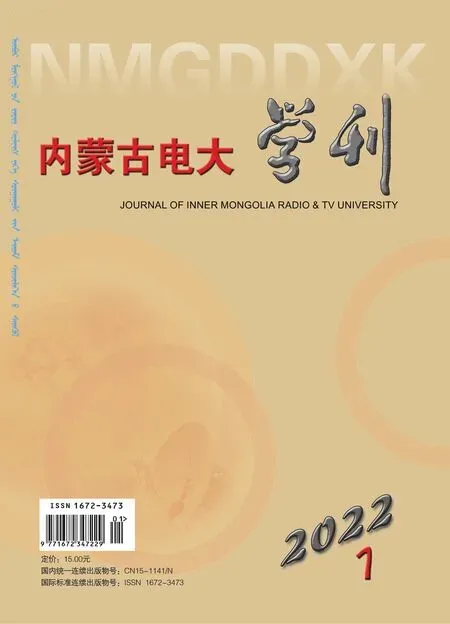元散曲家对《史记》刘邦形象的接受
2022-03-18张岩
张 岩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汉高祖刘邦是汉王朝的开创者,对汉民族和汉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巨大影响力。最早对刘邦一生有比较完整记录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为后世刘邦形象的文学接受提供了历史基础。自《史记》诞生起,历代都有评价并重塑刘邦形象的文学作品,且不同朝代对刘邦形象的接受各有侧重,刘邦形象随着朝代的更迭不断向前推进。不同于史学忠于“实录”,也不同于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对史实的演绎与虚构,散曲对刘邦形象的接受与重构有独特性。散曲是金元时期北方的一种新兴诗体,与诗词一样,散曲也是作者“情动而辞发”的成果,描写相对真实客观。就取材而言,自班固《咏史》以来,怀古咏史就成为诗歌的一个重要题材。元代散曲创作大盛,历史、古迹也成为散曲的吟咏对象。根据隋树森先生的《全元散曲》可知,怀古咏史类散曲约有300首。此外,散曲还受到唱赚、大曲等俗文学的影响,与诗词相比,散曲更加通俗自然,有“蛤蜊”“蒜酪”风味,质朴显豁。作为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裁之一,元散曲对刘邦形象的接受具有明显的时代特性。
一、元散曲对刘邦形象的接受概况
自古以来,分裂的时代和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就备受文人的青睐,不论是传统的诗词作品,还是戏剧小说一类的叙事性文学,都将表现战争,尤其是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作为描写的重点。刘邦作为楚汉相争中“汉”一方的代表人物,反复被写入文学作品。元散曲从多种角度接受了《史记》中的刘邦形象,涉及与刘邦相关的很多史实和传说。
首先,因为散曲篇幅有限,尤其是小令作品,调短字少,不便长篇铺叙刘邦的事迹。大部分散曲仅仅提到了以刘邦和项羽为首的“楚汉相争”,而没有涉及楚汉相争过程中的事件。如李爱山的小令【双调·寿阳曲·怀古】:“项羽争雄霸,刘邦起战伐,白夺成四百年汉朝天下。世衰也汉家属了晋家,则落的渔樵人一场闲话。”[1]P1346还有一些不专门写刘邦的套数作品,也是仅从楚汉相争整体出发,表达个人对历史和建功立业的看法,没有针对历史事件评论,如鲜于枢的套数【仙吕·八声甘州】中【大安乐】一曲:“从人笑我愚和戆,潇湘影里且妆呆,不谈刘项与孙庞。近小窗,谁羡碧油幢?”[1]P98
其次,刘邦其人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不同于后世史籍“为尊者讳”的修史态度和原则,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秉持“实录”精神,一方面凸显了刘邦志向高远、知人善任、机敏世故的优秀品质,塑造了苦心孤诣、开创汉朝辉煌基业的一代帝王形象,另一方面暴露了刘邦德行上的不足:好色好酒、懒惰、轻视儒生,尤其是为保全自己而推儿女下车、父亲被项羽挟持时说“幸分我一杯羹”以及诛杀功臣等一系列事件,使刘邦常为后人诟病。元散曲作家自然也关注到了刘邦形象的两面性,他们对刘邦建立的汉朝功业是基本肯定的:“虎视鲸吞相并,灭强秦已换炎刘姓”“汉祖胜乘威势,上苍助显号令”[1]P369;“咸阳百二山河,两字功名,几阵干戈。项废东吴,刘兴西蜀,梦说南柯”[1]P272。刘邦“斩蛇起义”的传奇经历也反复出现在元散曲作家笔下:“那老子见高皇斩了蛇”[1]P1167“斩白蛇高祖胜”[1]P1938“一个举鼎拔山一个斩白蛇”[1]P1937。“斩蛇起义”是《史记·高祖本纪》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常被文学作品引用。这是一则富有浓厚政治意味的神话,显然是刘邦为了迎合秦末社会动荡时人们寻求真龙天子的心理需求而进行的一场成功的政治宣传。同样,在《史记》的记载中,刘邦的神异之处还体现在他的外貌上:“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2]P433又有一老父相面说刘邦“君相贵不可言”[2]P437。神异的出身,加之外貌、经历的不同寻常,为刘邦获得政权的合理性奠定了基础。因此刘邦外貌的神异被写入元散曲:“楚霸王,汉高皇,龙争虎斗几战场。争弱争强,天丧天亡,成败岂寻常。一个福相催先到咸阳,一个命将衰自刎乌江。”[1]P841在作者看来,刘邦神异的面相是他成就功业的催化剂,他能先入咸阳是有“天助”的。元散曲家在基本肯定刘邦功业的同时,在散曲中表达了对刘邦的否定性评价,最典型的就是元散曲作家有感于汉朝建立后刘邦杀戮功臣的事实,在散曲中集中表现刘邦对韩信的猜忌,描写“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残酷现实。如薛昂夫的【中吕·朝天曲】“沛公,大风,也得文章用。却教猛士叹良弓,多了游云梦。驾驭英雄,能擒能纵,无人出彀中。后宫,外宗,险把炎刘并”。[1]P789刘邦渴求贤能之人,且任人唯贤,善听臣下建议,既能收服英雄,又能让英雄为自己效力,这是刘邦能成就功业的重要原因。但这些英雄不能逃出他的掌控,如他假借游云梦诈捕韩信,让猛士慨叹“鸟尽弓藏”。刘邦倾尽心力得到的汉室江山,却险些被吕后和外戚断送。再如赵显宏的【黄钟·刮地风·叹世】中有“韩元帅阵开,楚重瞳命衰,汉高皇拆了坛台”[1]1336一语。当初刘邦为了打败项羽重用韩信,设立拜将坛,以隆重的仪式拜韩信为将。韩信也因此感谢汉王的知遇之恩,帮助刘邦平定天下。可以说刘邦战胜项羽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韩信的力量,而且韩信在自己手握军权、军事实力最强的时候没听武涉、蒯通的建议背叛刘邦。可是汉朝建立后,汉高祖却“拆了坛台”,鸟尽弓藏,致使一代英雄惨死妇人之手,落得个夷灭宗族的悲惨下场。薛昂夫在另一首【双调·庆东原·韩信】中说出了封建社会里开国功臣的悲惨结局:“岂不闻自古太平时,不许将军见!”[1]P800通过《史记》可知,刘邦生性多疑,且又奸诈善弄权术,常借他人之手除掉对自己有威胁的人,以致很多功臣没有好下场,这也是后世学者诟病刘邦的一个原因。如林伯桐曾评价刘邦:“汉高一生最喜狎侮,又多猜忌,老成如酂侯,英雄如淮阴侯,皆不免于疑忌;他如黥布之勇,郦食其之辩,其始皆不免于狎侮。”[3]P1227
雎景臣的套数【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所叙事件在《史记》中是有记载的。高祖十二年,刘邦亲征淮南王英布,在击败英布得胜而还的途中,顺路回故乡沛县,畅饮数日,创作了流传千载的《大风歌》。历史记载中刘邦衣锦还乡,受到乡亲的欢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2]P389这是一幅其乐融融的美好景象。但散曲的作者雎景臣并没有如史书记载一样直接描写高祖还乡的场景,而是别出心裁地从一个无知乡民的角度出发,选取了第一人称的内在视角观察高高在上的刘邦。本应庄重、威严的帝王还乡场面,在老农的眼里成了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这一视角的独特和巧妙不仅在于这个老农没见过世面,也在于这个乡民是刘邦的乡亲。自始至终这个乡下老农都没有对刘邦采取仰视的视角,而是从一种平视甚至俯视的视角看刘邦,让这样一个人物揭刘邦的老底更显真实:
【二】你须身姓刘,您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
【一】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称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1]P612
面对威严的仪仗,老农是陌生的;但这个下了车的“大人物”,老农是熟识的:他就是当年的劣迹斑斑的刘三:贪酒、欠债、强买、偷盗、胡作非为。《史记》中也记载了刘邦贪酒、懒惰、不事生产的劣行,可知散曲所写并非虚构。一个德行有亏的人却摇身一变,成了国家最高统治者,雎景臣就这样用一个乡下老农将高高在上的大汉天子拉下了神坛,为原本严肃的历史注入了诙谐幽默的调子。
二、元散曲家接受刘邦形象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
“文学作品并非对客观社会生活的机械描摹,而是深深地渗透着作家本人对社会生活的情感态度。”[4]P338元散曲家对历史人物的接受,绝非是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简单再现,而是结合作者主观意识和情感的重塑过程,元散曲家笔下的刘邦形象是元散曲家表现自我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的重要载体。
(一)对统治者的质疑
通过上文可知,元散曲家对刘邦的质疑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是指控刘邦在汉朝建立后诛杀功臣;其二是雎景臣在套数【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中对刘邦早期道德品行的揭露。
首先,后世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对韩信是否谋反莫衷一是。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单就武涉、蒯通劝说韩信背叛汉王而韩信不听,就用了一千八百多个字描写,占全篇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加之漂母赠食等事件,可知司马迁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表现韩信隐忍、忠诚、知恩图报等品质,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英雄却因为谋反被夺爵失地,惨遭斩杀。且司马迁记载刘邦得知韩信已死的反应是“且喜且怜之”[2]P3168,证明刘邦早已有了想要除掉韩信的想法。后世学者有感于“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残酷现实,纷纷为韩信感到不平,如北宋名臣韩琦《过井陉淮阴侯庙》一诗中说:“破赵降燕汉业成,兔亡良犬日图烹。家僮上变安知实,史笔加诬贵有名。”[5]P4020-4021尤其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作家更是倾向于表现韩信之忠,批判刘邦诛杀功臣。元散曲家写刘邦“却教猛士叹良弓,多了游云梦。驾驭英雄,能擒能纵,无人出彀中”[1]P789,还因为他们有感于元代统治者尚武轻文的社会现实,科举制度被迫中断,“四等人”制及“九儒十丐”的社会地位带来的强烈心理落差,让他们四处冲撞,将批判和讽刺的矛头指向了皇帝。对统治者的不满是历代文学中常有的话题,但慑于当朝的文化政策,文人在文学作品中不能表现得过于直白。这一点之所以在元代是可能的,是因为元代的文化政策较为宽松,文人在创作时少有禁忌。元代没有文字狱已经是学者的共识,文人写什么、怎样写,几乎没有限制,才会有这样肆无忌惮的散曲作品出现。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文学创作才更加丰富、多元。
此外,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在北方游牧文化影响下,蒙古人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从总体上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等特点。”[6]P38元朝建立后,外向的、张扬的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的礼义文化在冲突中逐渐融合,传统观念、“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被逐渐打破。作为元代的代表性文体,散曲的题材风格和审美趣味不再追求温柔含蓄,而是以通俗自然、率真活泼为主,还有一股独特的诙谐之趣。这集中体现在雎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套数中。在这首套数中,雎景臣通过一个乡下老农的视角,将眼前高高在上的汉高祖还原成当年德行有亏的无赖刘三,撕下了皇权虚伪的遮羞布,还原了统治者的本来面目。汉高祖是刘邦的庙号,应是皇帝死后在太庙中供奉时称呼的名号,“作者却故意违背常识,拿皇帝尊贵的庙号做文章,说明其机锋所向,不止于历史上个别的皇帝,整个宗法社会的‘礼制’都在他笔下遭到嘲弄和亵渎”。[7]这首散曲嬉笑怒骂,痛快淋漓,非常能代表元散曲的“蛤蜊”“蒜酪”风味。
(二)对功名利禄的重新评价
秦王朝的残酷统治,秦朝帝王的昏庸腐朽,迅速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激烈反抗,“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8]P2332,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刘邦也自沛县加入了反秦的队伍。与其他的起义军相比,刘邦的实力并不强大,声望并不高,但他能凭借自己顺应时势、知人善任、善于纳谏等优秀品质在群雄逐鹿中战胜各方势力,建立了西汉王朝。可以说刘邦在历史上建立的功业是值得肯定和称颂的。但是在元散曲家笔下,表现的并不是对刘邦建立功业的颂扬。
在唐代,诗人借用刘邦斩蛇起义、与项羽逐鹿中原并建立汉朝的丰功伟业,表现的是“楚灭无英图,汉兴有成功。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9]P1258的豪迈气势。但在元散曲家笔下则是另一番景象,如马致远的小令【双调·蟾宫曲·叹世】:
咸阳百二山河,两字功名,几阵干戈。项废东吴,刘兴西蜀,梦说南柯。韩信功兀的般证果,蒯通言那里是疯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醉了由他。[1]P272
马致远借用人们熟知的史实,表达了个人对功名的看法:刘项兴亡不过是南柯一梦,韩信战功赫赫却落得个被砍头的下场,蒯通说的哪里是疯话呢?世道险恶,成败不由己,功名事业没什么值得留恋的。马谦斋的小令【越调·柳营曲·楚汉遗事】中写刘项二人“龙争虎斗几战场”,最终不过是“江山空寂寞,宫殿久荒凉。君试详,都一枕梦黄粱”[1]P841。成败不过是一枕黄粱梦。两首无名氏小令【中吕·红绣鞋】也如此:
楚霸王休夸勇烈,汉高皇莫说豪杰。一个举鼎拔山一个斩白蛇。汉陵残月照,楚庙暮云遮,二英雄何处也![1]P1937
搬兴废东生玉兔,识荣枯西坠金乌。富贵荣华待何如?斩白蛇高祖胜,举鼎霸王输,都做了北邙山下土。[1]P1938
当年争雄的楚霸王和汉高皇,举鼎斩蛇,胆力过人,意气风发,现如今都做了“北邙山下土”。这些元散曲作家无一例外地借刘项争雄表现自己对功业无所用心,作品弥漫着浓厚的历史虚幻色彩。本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终生奋斗的目标,但是元代社会的特殊性,剥夺了文人进入仕途的机会,也阻断了他们实现个人价值的道路。原本身处社会最高层的“士”阶层,如今被抛到了社会最底层,与娼妓、乞丐处于同样的地位。长期沉沦下僚,加重了他们内心的不平和愤懑。为了宽慰自己,他们只好故意降低功名在自己心目中的比重,装作毫不在意,借历史上那些建立功名的大人物说明英雄豪杰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过客,他们建立的功业到头来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罢了。
(三)尚隐思潮
元散曲家还借刘邦史实表达“尚隐”情绪,如赵显宏的【黄钟·刮地风·叹世】:
安乐窝中且避乖,倒大优哉。寒梅不顾栋梁材,别样清怀。小庵茅盖,主人常在。缄口藏舌,坐观成败。韩元帅阵开,楚重瞳命衰,汉高皇拆了坛台。[1]P1336
由于缺乏文献资料的记载,赵显宏的身世尚无可考。不过通过他的其他散曲作品可知,他大概在青年时期也曾读书求仕,但是“功名不恋我,因此上落落魄魄”[1]P1336,转而厌弃功名富贵,向往田园归隐,写下了许多表现耕种渔樵恬静生活的散曲。在这首散曲中,作者有感于韩信建功立业,却被刘邦“拆了台”,不得善终;项羽被称为“西楚霸王”,勇猛善战,显赫一时,最终被刘邦打败。可见“伴君如伴虎”,做臣子的稍不留意就可能丢了性命,而建立个人功业的成败又尚未可知。既然如此,还不如躲在“安乐窝”里“缄口藏舌”,不去做什么栋梁之材。再如徐再思,天一阁本《录鬼簿》记载他做过“嘉兴路吏”,也是一个地位不高的官职。他的【黄钟·红锦袍】即借用刘邦典故诉说归隐之情:
那老子见高皇斩了蛇,助萧何立大节,荐韩侯劳汗血。渔樵做话说,千古汉三杰。想著云外青山,纳了腰间金印,伴赤松子归去也。[1]P1167
显然徐再思借用了汉三杰之一张良的口吻,诉说张良曾有助于刘邦、萧何和韩信,却不贪恋功名,最终随赤松子“归去”。徐再思在同题的其他小令中分别以严子陵、范蠡和陶渊明的口吻诉说经历,同样表达了对归隐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士人形成了一种“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处世方式。天下太平时,他们积极入世,希望能有所作为;社会动荡、君主不思进取时,他们则靠隐居独善其身。陶渊明等淡泊名利的隐士又为士人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是“仕”与“隐”二极中“隐”一极的代表。元代的知识分子失去了跻身统治阶级的机会,自身的价值得不到实现。传统信仰的失落使他们对功名持否定态度,“隐”便成了他们倾向且无可奈何的选择。借历史人物的兴衰成败表达归隐之思,成了元代咏史怀古散曲的一个典型模式。这类散曲往往不针对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发议论,而只是借用一点史实,表现历史的空幻感、虚无感,进而表现归隐思想。
三、结语
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的历史上以及汉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秦朝末年风起云涌的起义中,刘邦所部趁势成为义军队伍中的一支。他在风云激荡的秦末战局中应时而动,赢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建立汉王朝。中国文学自古对升平治世的题材就不感兴趣,反倒是乱世英雄为人艳羡。自《史记》之后,历代的文献及文学作品继承了《史记》对刘邦形象的记载,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写,丰富了刘邦形象,同时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特色。元散曲是元代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是继诗、词之后盛行的一种新诗体,元散曲家与诗人、词人一样,借助这种文学样式抒发真情实感。在与刘邦有关的散曲中,元散曲家借助与刘邦相关的史实,表达了对统治者的不满、对功名的重新评估以及对归隐生活的向往,表现出元代文人特有的情绪。此外,元散曲又明显受到俗文学的影响,通俗自然,充满“蒜酪”和“蛤蜊”风味,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雎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套数。正因为司马迁没有受“为尊者讳”的限制,在表现刘邦审时度势、知人善任、善于纳谏等优秀品质的同时,表现了刘邦早期贪酒好色、不事生产等劣迹,雎景臣借此敷衍成篇,以一个乡下老农的陌生化视角曝光了这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不堪的一面,惹人大笑,也发人深省。因此,元散曲中的刘邦形象,既是历史上真实的刘邦,又是元散曲家表现自我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