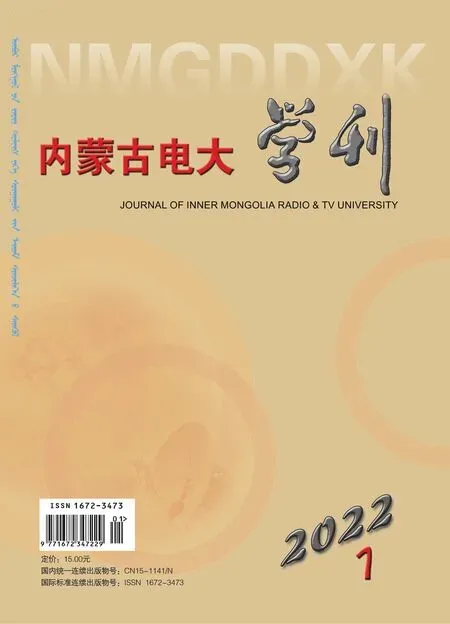怀疑与救赎
——《宗教大法官》中对于三个问题的探讨
2022-03-18丁宇平
丁宇平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9)
一、陷入泥潭的信仰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年代,东正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来自西欧的新潮思想不断冲击宗教传统,与此同时,日渐僵化的宗教很难再轻易解决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这一切形成了俄罗斯社会信仰缺失、异端横行的泥潭,同时让宗教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别尔嘉耶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中曾提及:“陀氏是一位深刻的基督教作家,他信任基督胜过信任真理。”宗教是陀氏创作中关注的焦点。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深刻剖析了宗教面临的问题。
《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一节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一个可怕、自我毁灭和否定存在的精灵向耶稣提出了三个问题:将石头变成面包、从殿顶上跳下以挑战上帝的奇迹以及由谁来接受权力和荣华。这三个问题从三个维度探讨了人类精神自由这一命题。“将石头变成面包”探讨了人类的自由与生存;“从殿顶跳下以挑战上帝的奇迹”探讨了人类精神信仰的地基是奇迹还是自由;“由谁来接受权力和荣华”探讨了不同形式的反基督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及经历,如同俄罗斯现实社会的折射,精灵的三个问题是横亘在宗教前的诱惑与危机。基督以人类精神自由的名义拒绝了这些诱惑,基督不希望人类的精神成为“面包、奇迹和地上王国”的奴隶。大法官则以幸福和安宁的名义接受了这三种诱惑,并拒绝了自由。前者希望人类走向“神人”之路,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信仰,而后者认为人类生来顽劣,只能臣服于统治。上帝与老法官关于人类精神自由的不同理解,体现出了神人与人神根本分歧和对立。两种思想的相互拉锯使信仰陷入泥潭,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宗教信仰缺失,神人思想消退,并出现卡拉马佐夫兄弟一家这样的惨剧。
首先,神人思想的消退表现为非理性自由的兴起。精灵将耶稣带到荒野,引诱他将石头变为面包,这一具有奇幻色彩的行为,体现了老法官与耶稣对于“自由和面包”的不同理解。老法官认为,人类需要先得到“地上的面包”,然后在面包的支配下走向老法官们给予的自由,达到“秩序的和谐”。《宗教大法官》一节中,老法官表示:“在孱弱、永远不知道感恩的人种眼里,天国的面包怎么能和地上的相比。”老法官的这一思想包含着认为人类卑劣不堪这一既定观点,这是对人类精神意义的消解。上帝则认为,他给予人类的“天国的面包”是源于对人类精神价值的肯定。人不应当囿于物欲的满足,而应当在内心深处自由地选择走向“秩序的和谐”。别尔嘉耶夫曾表示:“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自由,一种是原始的、非理性的自由,另一种是最后的、终结的、理性的自由……苏格拉底在《福音书》中提及的‘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自由’中的自由,便是第二种最后的、终结的、理性的自由。”这也是基督宣扬的精神自由的最高境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老卡拉马佐夫和德米特里是物欲的化身,前者贪图享乐,奸污疯女,并和儿子争风吃醋。后者酗酒玩乐,与父亲争夺同一个女人并扬言要杀了父亲。在他们死亡之前,他们的生活保持着一种“放纵式”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原始与非理性的。当非理性的自由占据人类的全部身心,神人思想将逐渐消退,这正是当时俄罗斯社会的现状。
其次,神人思想消散的另一个表现是奇迹信仰日益凸显。在《宗教大法官》中老法官指出,耶稣在别人讥诮他“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是你”时,不愿意从十字架上脱身并彰显自己的奇迹,因为他不希望通过奇迹奴役人,而是始终追求自由信仰。这是上帝在自由与奇迹之间的选择,但是在老法官看来,卑劣的人类不可能放弃眼前的自由。前者走向神人之路,而后者将走向人神之道。在十几个世纪前,精灵向耶稣表示,只有三种力量可以征服人类的心:奇迹、秘密和权威。精灵将耶稣带上殿顶,并诱惑他纵身一跃,以验证上帝的奇迹。耶稣断然拒绝了精灵的这一要求,因为他深知,即便只是在脑海中出现这个念头,那也是对上帝权威的质疑。跳下殿顶,意味着向“上帝奇迹”发起挑战,意味着想要去验证上帝的“奇迹”是否存在。用“奇迹”去试探上帝,相当于认为“如果不存在奇迹,那便也不存在上帝”,而这正是上帝抵触的“奇迹信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遍布这样的奇迹信仰,无论是在基督重返人间时祈求他赐予奇迹的民众,还是聚集在修道院前渴望佐西马长老降下福祉的霍赫拉科娃太太之流,他们希望能从宗教中得到力量,最重要的,是得到奇迹的力量。
最后,神人思想消散的又一大表现在于反基督思想的盛行。《宗教大法官》中,老法官向耶稣坦白,他们早已背叛了对上帝的信仰,如今在人间盛行的宗教裁判所,实则建立在假借上帝名义的欺骗之上。早在八个世纪之前,老法官们就从“他”手中接过了耶稣拒绝了的东西:世间的权力和荣华。在文本中“他”这一指代频繁出现。而“他”指向的一切与基督思想对立。“他”就是各个时期不同形式的“反基督思想”。别尔嘉耶夫曾表示:“大法官的精神是以反基督替代基督的精神,这种思想在历史上曾经以各种面貌出现,他们套用基督教诲民众的形式,但是实质内容不一致。”据《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记载,魔鬼将耶稣带上最高的一座山,并将世界万国以及荣华指给他看,并表示:若臣服,则赐予。此处的财富与权力是一种国家意识的体现,即以精神为统治武器,并进一步形成拥有完善制度的国家体系。利用精神信仰统治人类的现实生活,无疑违背了上帝最初希望人类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及道路这一愿景。而老法官们则趁机接过了这一权力,他们收回人类生而有之的自由,并对其进行异化统治。别尔嘉耶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中表示:“天主教在罗马教皇的神权体系中,将教会变为国家,而拜占庭的正教以及诸多君主专制或帝国主义中都体现出这一思想。”老法官们实行的“统治”是对宗教原旨最大的欺骗和背离。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便是老法官思想在现实中的化身,他大肆宣扬无神论思想,并间接教唆斯麦尔佳科夫弑杀父亲。正是这些反基督思想代替基督思想在社会中大肆横行,在神人消退、人神崛起的困境下,信仰陷入泥潭。
二、宗教与现实的“割裂”
信仰陷入泥潭,不仅是现实的不幸,也是宗教之殇。上帝对精灵的三个问题做出的选择——自由地寻找生存和谐、自由信仰以及拒绝权势与荣华,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宗教与现实的“割裂”。《宗教大法官》一节中提及,上帝自先知替他写下“我将很快回来”后,已经有十五个世纪未降临人间,期间异端邪说盛行,宗教信仰产生巨大裂缝。而当上帝终于以基督的身份重返人间后,在老法官一步步责难前,基督始终不发一言。此外,《宗教大法官》一节中还描述圣母流着泪跪在上帝的神座前请求他不加区别地赦免一切罪人,最后上帝同意在受难日至圣三节之间暂停刑罚。陀氏在这一章节中写下的情节是对宗教现实困境的暗示。上帝离开人间太久,他十五个世纪前的旨意已经不太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甚至会将民众引向盲目和虚无。同时,圣母请求的无差别救赎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泛滥,与现实的不公达成的无差别和解产生了一种“极致”的荒诞,这一思想也将导致人神的产生。宗教思想陈旧,人道主义泛滥,外加人神思想蠢蠢欲动,凡此种种,便是宗教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割裂”。
首先,《宗教大法官》中老法官揭露了上帝的一桩“秘密”,即上帝名义上宣扬救赎一切,但实际上只有少部分被选中的人才能进入天堂,剩下大多数“卑劣不堪”的人类只能怀着“等待救赎”的愿望在人间苦苦挣扎,这些本可以中选的强者中的许多人高举“自由”的旗帜开始反抗上帝。老法官的这一表述揭示了众多宗教反叛者的起源,同时暗示出宗教信仰的先天性危机:上帝的力量无法解决现实中的全部问题,难以发挥本应当发挥的作用,并由此导致反基督思想愈演愈烈。出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形象具有各自的社会身份。老卡拉马佐夫是地主,德米特里是军官,伊万是大学生,斯麦尔佳科夫是家厨,阿辽沙是修道院的见习修士。这样一个身份各异、阶级鲜明的家庭相当于一个微型的俄罗斯社会。在这一家庭中,信奉宗教的阿辽沙相当于一个前来解决问题的天使,佐西马长老也曾多次表示,希望阿辽沙去协助处理他们一家子的纠纷。然而,即便是集虔诚与纯洁于一身的阿辽沙,也没能处理父兄矛盾,最后只能接受家庭分崩离析的局面。此外,老法官也坦言,他曾经也是一位匍匐在上帝脚下的虔诚信徒,但是在苦苦追寻不得后,才开始高举旗帜,加入反叛上帝的大军。在众多信徒中,上帝只能够挑选有资格进入天堂的人,但是这样的人相比广大信徒来说,为数甚少。诚如老法官表示:“你只看中那几万个强者,但是其余几百万多如海沙,但是爱你的弱者就活该倒霉,活该为强者做陪衬吗?”这是对上帝及其宗教信仰的终极发问。
其次,上帝对人类的爱在于,他知晓人类卑微不堪,但仍愿意奉献自己全部的爱,感化人类这一族群。但反之,也正因为人类的卑弱,大部分人无法承担上帝的重任,无法将自己提升到与上帝同等的地位,从而造成了原旨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割裂”。《宗教大法官》中,老法官曾坦言:“你许诺给他们天国的面包……但是在永远不学好的孱弱人种眼里,这样的面包怎么能和地上的相比。”“地上的面包”对于人间的民众有着原始的、非理性的吸引力,无论是奇迹、秘密还是权威,都能满足人类的需求,而最重要的是,能让人找到赖以信仰的共同崇拜。保罗·科利在《从文本到行动》中提出:“所有的共同体都需要某种公民神圣,标志着公民神圣的是纪念、节日、旗帜的展开以及伴随着这些现象的整个崇敬热情。”人类将精神信仰交由权威的拥有者,并以让渡自身的自由为代价。《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霍赫拉科娃太太们看似尊奉佐西马长老,但实际上渴望获得宗教的赐福。霍赫拉科娃太太认为女儿利兹的腿疾将被长老治好,这实际上是一种将解除自身困境的权利交由其他人的行为,背后暗示出的是时刻期待奇迹的发生,这也是一种将精神信仰让渡于他人的体现。而佐西马长老死去,同时尸体发出腐臭,困惑的声音开始在信徒之间传播。霍赫拉科娃太太在听闻这一消息后表示太可怕了,同时其他信徒三缄其口,他们来修道院附近观望,似乎是想要寻找魔鬼存在的蛛丝马迹。佐西马长老如同信仰的化身,他的存在与否决定着民众究竟尊奉何种信念,他既会为人们指引光明,也会轻易带来黑暗。
最后,圣母式的仁慈本是想彰显博爱的救赎,但在现实之中导致了宗教人道主义的泛滥,这也形成了滋养人神思想的温床。伊万作为一名无神论者,最为著名的一句论断是“既然上帝不存在,那就无所不可”。这一言论表面上看是在宣扬无神论立场,但实际上暗含着对宗教过度泛滥的人道主义的消解与嘲弄。上帝代表着一种规范与约束,上帝的宗教给予了民众一份行为准则。如果上帝不存在,或不承认上帝,那么这种准则将荡然无存。《宗教大法官》中曾提及,圣母请求上帝对犯人进行无差别的赦免,在上帝同意在受难日至圣三节之间暂停刑罚之后,罪人们高呼:“主啊,你做出这样的裁决是正确的。” 无神论者希望逃避上帝的约束,圣母式的无差别救赎思想又体现出人道主义的“泛滥”。故而夹杂在二者思想下的伊万所说的“既然上帝不存在,那就无所不可”,潜台词或许是:既然上帝会赦免一切,那就无所不可。这种思想产生的,就是超越了宗教约束的极致自由。别尔嘉耶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中所述:“自由,作为自由意志,消解了自身,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瓦解并断送了人。这样的自由必然从内部导致奴役。不是外在的惩罚等待着人,而是内在显露的神性击溃了人的良心。” 人应当走向自由之路,但是当人在自由的恣意妄为中不想知道任何高于人的东西的时候,这种自由就转变为奴役,并毁灭人。而这也是俄罗斯社会的现实,人道主义泛滥,人的权力极速扩张,使人神思想大行其道。
三、救赎之道
无论是神人缺失还是人神当道,横亘于神人与人神之间的,是上帝对人类自始至终的“爱”。上帝给予人类以基督之爱,希望后者能踏上神圣与自由的神人之路。而同样,正是因为上帝某些不加差别的爱,导致人道主义泛滥,进而使人神思想横行。宗教信仰存在自己的缺陷,有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相比之下,老法官代表的反基督思想更加不可相信,因为后者从本源上认为人类卑劣不堪,同时他们的“统治”实际建立在以上帝之名的欺骗上。鉴于信仰混乱,反基督思想大行其道的社会现实,如何保持人道主义博爱的同时,避免人神崇拜的出现,是陀氏不断思考的问题,于是他塑造了佐西马长老这一新型基督徒形象,并希望通过这一人物展现出“即便信仰存在诸多问题,也仍希望通过宗教给予人类最后的救赎”这一观点。
在老法官的认知中,人类卑劣不堪,是永远不学好、永远不知感恩的孱弱人种。老法官的这一思想是对人类自由意志的消解与亵渎。在其认知中,只有极少数人能被上帝选中并跻身天堂,而大部分是只能在人间挣扎的“孱弱的绵羊”。老法官在民众面前隐瞒了上帝的这一秘密,转而以上帝之名,以人类的自由为代价,对人类进行异化的统治,这是对人类和上帝的双向欺骗。虽然老法官认为这将给大多数卑微的人类带来幸福,但是这一切行为的基础是建立在消解人存在的意义,将人的价值等同于“天生的弱者”之上。
伊万就是老法官思想在现实中的投射,在卡拉马佐夫一家中,伊万如同一个“傲慢的旁观者”,他以无神论者自居,无论是去往修道院寻求调解的途中与他人的争辩,在面对德米特里与老卡拉马佐夫之间的闹剧时表现出来的态度,还是对叶卡捷琳娜的情感,都体现出这一人物的自视清高。伊万是文本中人神思想的极致体现,无神论并未将其引向客观与中立,而是走向了非理性的偏执。在“无所不可”的指引下,伊万的亲情、感情等观念淡漠,他的思想让他驾临于一切人性之上。在伊万眼里,斯麦尔佳科夫、德米特里、叶卡捷琳娜等人都是“天生的弱者”,他在向阿辽沙讲述自己撰写的《宗教大法官》的故事时,也流露出一种对阿辽沙代表的基督教价值观的挑衅。此外,斯麦尔佳科夫是伊万人神思想的重要继承者,他接受了伊万“既然没有上帝,那就无所不可”的思想,并动手弑杀了自己的父亲。老仆人格利高里曾经表示斯麦尔佳科夫“他谁都不爱”。人神思想的兴盛常常伴随人性的退散,而当人性之爱消失,生而为人的价值也就被逐渐消解。
传统宗教陷入泥潭,人神思想不可相信。在这样的情形下,陀氏依然选择将宗教作为救赎的武器。他塑造出佐西马这一新型长老形象,并经由佐西马到阿辽沙形象的更迭,预示着在直面社会的不公以及避免泛滥的人道主义之后,新的救赎——人的精神自由之路即将重新开始。
佐西马长老临死前曾将教诲阿辽沙的任务交给帕伊西长老,后者对阿辽沙表示:“虽然近一个世纪以来,科学已经对所有圣贤书中的天经地义做了残酷的剖析,但是没有一个体系能够摧毁这种力量,它已经存在了十九个世纪,即便是那些反对基督的人,他们遵循的思想依然是以基督为基础。”这番借由书中人物表达的言论勘破了全书的主旨:即便宗教的触手难以企及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但宗教背后的思想——爱与精神自由已经成为社会最本源的基石,任何反叛思想都无法改变这一点。想要重新拥有这块基石,就需要踏上神人之路,也就是精神自由之路。
佐西马长老是陀氏塑造的新型基督教人物形象,他拥有传统宗教长老的美德,同时还睿智地感受到了救赎绝非仅局限于修道院。他指引阿辽沙摆脱形式的桎梏,勇敢地走向自然与民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表示:“对于人来说,人走过自我意志和造反之路,不是向大地的自然回归,而是经由基督,回到神秘的大地,回到自己的家园。”佐西马长老希望阿辽沙前往民间,就是陀氏这一救赎思想的根本体现。与此同时,别尔嘉耶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中曾说:“佐西马已经走过了陀氏正引领人走过的悲剧之路。他十分清楚人身上的卡拉马佐夫天性。他已经能够回答人的新的痛苦,这是传统的长老形象不能回答的。”佐西马长老如同陀氏本人的化身,他勘破了现实社会的不公与荒诞,同时他坦然承认卡拉马佐夫之流的软弱卑贱。陀氏不站在任何一方,他不对任何人物做任何偏向性的评价,他就是复调的集合。这种竭力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评判一切的行为,也暗示了上帝的宽恕:承认一切,同时原谅一切。
佐西马长老在参与卡拉马佐夫一家的调解时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授意,而是选择在德米特里面前跪下,并向周围的客人念叨:“请原谅,请大家原谅!”这似乎是在提前为德米特里之后的行径赎罪。《宗教大法官》一节中,基督在听完老法官的言论之后,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走到老人面前,在他没有血色的九旬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这就是全部回答”。同一章节的结尾,阿辽沙听完伊万的讲述,同样不发一言,默默地给了伊万一个吻。在伊万离去之后,阿辽沙看着伊万的背影,发现他的右肩比左肩低。在俄罗斯文化中,右肩站着天使,左肩站着魔鬼。陀氏刻意为之的这一情节,也是对人神思想终将得到宗教救赎的暗示。
小说最后,阿辽沙带领孩子们为死去的伊柳沙祈祷,而在仪式结束后,他将遵循佐西马长老的指引,从经院走向民间。从佐西马思想的指引到阿辽沙行动的贯彻,这两位人物的传承预示着一种新型救赎思想的到来——神人思想不再局限于修道院,它将通过基督徒,通过对现实的体悟与了解,走向俄罗斯社会更加广阔的人间。
四、结语
精灵的三个问题展现了宗教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三种维度的诱惑和困境,而十几个世纪后,老法官与基督对这三个问题的态度,表明了他们对于人类精神自由的不同理解。根据《圣经》原旨,相比上帝,人类是如此卑微与渺小。但是即便人类如此“不堪”,上帝也不曾放弃对人类的爱与救赎。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氏展现出了社会的荒诞与不公,但是他保留了一份救赎的种子。陀氏希望人类能走上通往“神性”的神人之路,同时这是上帝最后的怜爱以及对人类最后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