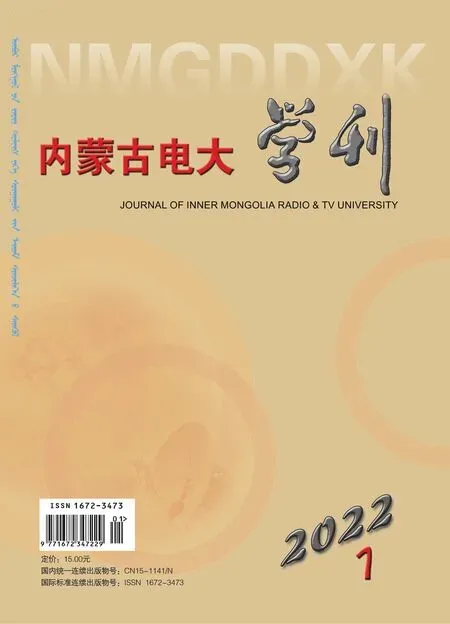宋词中“瘴疠”意象的情感表达及其意义
2022-03-18许柳泓
许柳泓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有宋一代,灾害频发,除常见的气象地质灾害外,更具杀伤力的当属疫病,“瘴疠”就是其中一种。这种地方性疫病因湿热环境引起,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极易使人产生不适甚至致死。宋代时以西南、岭南一带最为严重,在瘴疠严重的地区,因死亡人数甚多而有“大小法场”之称[1]P309。在尽人事、听天命的古代社会,面对“瘴疠”这令人谈及色变的“杀手”,文人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笔管,将其记录于诗文辞赋之间。而在以富艳为美的词体文学中,与“瘴疠”相关的“瘴云”“瘴烟”“瘴雨”“瘴雾”等意象逐渐登场。《全宋词》中,出现“瘴疠”意象的词作有42首,这些意象多用于景物描写,它们“具有典型的思想情感内涵和突出的文学表现作用”[2]P71,同时构成了宋词中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
一、或悲或喜的人生之感
早在唐代,人们对南方多瘴就已经有了较大的认识,与“瘴疠”相关的诗文不胜枚举,岭南因此有了蛮瘴之地、蛮烟瘴雨之乡的“头衔”。最早将“瘴疠”意象引入词中的是五代时期的花间词人李珣,其词《南乡子》中云:“愁听猩猩啼瘴雨。”[3]P197这种悲愁之感在宋人的词作中得以延续,但也不是只有“悲”,自然也有“喜”的感受。
瘴乡是宋人游宦、谪宦的主要场所,亲身经历过瘴区生活的士子,领略了瘴疠的强大威力。南宋廉介的爱国者高登,在编管容州(今广西容县)时就曾受到瘴疠的侵害,其词《行香子》中道:“瘴气如云。暑气如焚。病轻时,也是十分。沈疴恼客,罪罟萦人。”[4]P1293被病魔围困的他,无时无刻不在煎熬中度过。流于南荒,本已凄苦,何况又惨遭疠疾的摧残,一种困顿的流离之悲油然而生,词人才会“叹槛中猿,笼中鸟,辙中鳞”[4]P1293,此刻,词人与它们的处境并无二致。同样,刘克庄回忆在广东为官的日子时,也提到了“瘴毒如炊甑”[4]P2603,他只希求“山鬼海神俱长者,饶得书生穷命”[4]P2603。只是关乎生存,这本是一个最朴素的愿望,但在动荡的时代,恐怕是平凡人最大的奢求。
相比光辉灿烂的李唐王朝,赵宋时代经受着更多的波折与摧残。在腥风血雨中,坚强的宋人从未放弃过对人生、对生命的思索,即使吟咏着悲哀,但也留着某些希望,不会走向绝望。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人生可谓是一波三折,长年的贬谪生活并没有将他的心志击垮,反倒是历练出遗世独立般的旷达心怀。其词《西江月·梅花》中言:“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4]P284不畏瘴雾的侵袭,依旧保持自己与生俱来的冰姿仙风,这是梅花的品格,更是苏东坡伟大人格的写照。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李光《减字木兰花》一词,词中赞咏梅花“瘴雾难侵尘不染”[4]P786,孤高傲世的梅花是词人所爱,只因词人找到了花与人的共通性——一种睥睨人生忧患的自信。因受秦桧的排挤,李光的仕途严重受挫,久谪南荒的他在词中却常常诉说泰然自若、悠然自得的情怀。虽已经年华老去,但他仍要“行尽荒烟蛮瘴”[4]P785,凭着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坚毅,他愿“潇洒任吾年”[4]P785。也正因为有坦荡的胸襟,在面对恶劣环境时,他眼中所见的是“清江瘴海,乘流处分身”[4]P786的奇景。
宋人努力将目光引向外界,多角度观察社会,深入社会,生活的艰辛、生存的艰苦让他们惆怅过、悲痛过,却从未绝望过。正因为有多角度的观察与思考,让他们认识到人生不只是有悲哀的部分,人也绝不是受命运支配渺小的存在,相反,人应该是要超越命运以支配命运的。
二、深哀沉痛的故国之思
李唐的盛世大戏在“安史之乱”后渐渐拉下帷幕,所幸的是大部分失地被唐军收复,山河依旧在。而宋代则是不同,公元1127年,强悍骁勇的女真人举兵南下,曾经繁华一世的北宋王朝不堪一击,在刀光剑影里退出历史舞台,失去半壁江山的赵宋王朝只能选择偏安一隅于南方这片陌生的土地。异族那强劲的铁蹄踩碎了北宋人原有的平静生活,百姓流离失所,为了生存,成千上万的北宋民众如潮水般仓皇涌向南方,开始了逃亡的颠沛生活。
洛阳“词俊”朱敦儒在南渡前是何等意气风发,带着傲世的目光,高唱“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4]P843,他还无视权贵,“几曾着眼看侯王”[4]P843。但在流落南方后,自傲的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在异乡的中秋夜,他与旧友相坐而叹,写下了这首《浪淘沙·中秋阴雨》:
圆月又中秋。南海西头。蛮云瘴雨晚难收。北客相逢弹泪坐,合恨分愁。
无酒可消忧。但说皇州。天家宫阙酒家楼。今夜只应清汴水,呜咽东流。[4]P850
全词表达了词人对金人统治下的故乡深切思念,也流露着难以排遣的亡国之哀。“蛮云瘴雨”笼罩着南越之地,历久不散,就如同丧国之悲在词人心中刺痛着,久而不愈。飘零于南越,“蛮树绕,瘴云浮”[4]P855,这个历来被人们当成野蛮之地的“角落”,虽能求得一时的安稳,但终究比不过文明的中原之地。于是,词人才会感慨“断肠红蕉花晚、水西流”[4]P855,或许,蕉花的红艳是蛮树瘴云里的一抹亮色,但仿佛是用成百上千的北宋遗民的断肠血泪染成的,亡国之痛也必定如水流般绵延不绝地流淌在遗民心中。
又如曾在潭州与金兵激战的向子諲,在番禺齐安郡王的宴席上,怅恨故国已亡,向故人发出了“谁知瘴雨蛮烟地,重上襄王玳瑁筵”[4]P956的感慨。再如抗金名将张元干,南下之后,南国苍翠的榕叶并没有给身居枕溪而建驿站的他带来一丝愉悦与舒坦,倒是“海风吹断瘴云低”[4]P1086的暗沉牵动了词人绵长的忧郁。“岁晚可堪归梦远”[4]P1086,家国已灭,还乡如梦般遥远,恐怕只能在这瘴云底下了却余生了。
南越之地,气候炎热,多雨潮湿,层峦叠嶂,丛林茂密,空气难以流通,瘴气郁结。无形的瘴气融于云雨之中,暗沉阴郁,让本就情感郁积的词人越发不适。在蛮烟瘴雨严相逼的状况下,又无力改变眼前的处境,那么,向往美好应当是人的本能反应。于是,对往昔舒适富足生活的回忆,恰似秋风扫落叶一般纷纷而下,为身处令人窒息环境下的他们带来一丝丝新鲜的空气,但这“空气”也只是杯水车薪。如瘴气郁结于南越大地,经久不散的唯有词人们的异乡之思与黍离之悲,这也是词人们无法治愈的心病。
三、刚劲豪迈的报国之情
纵观这42首词作,不难发现,南宋词作中的“瘴疠”意象的书写相比北宋词作要多得多。在南宋前期的词作中,如上文所言,“瘴疠”意象的书写多衬托出词人郁结于心沉痛的故国之思,这种情感仍是内敛的。但到了南宋中后期,词人的情感逐渐向外迸发,将郁积已久的故国之思化为慷慨激昂的报国之情。情感的宣泄外放也使得“瘴疠”意象的书写逐渐发生了变化,“瘴疠”意象渐渐脱离了“瘴疠”景象,成为艰苦环境或是敌对势力的象征。
辛派领袖辛弃疾在其卷帙浩繁的词集里仅有三首词作运用了“瘴疠”意象,却可以看出此意象书写的变化。《满江红·送汤朝美自便归金坛》一词开篇就言:“瘴雨蛮烟,十年梦、尊前休说。”[4]P1869此词作于淳熙十年(1183)春,为辛稼轩送别好友汤朝美时所作。汤朝美曾被流放于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瘴雨蛮烟”既是对汤朝美流放时所处的艰苦环境的概括表达,也蕴含对其过往不幸的诉说。整首词起韵便呈现出洒脱非凡之态,将十年来的“瘴雨蛮烟”一笔勾销,之后又期望友人“待十分做了,诗书勋业”[4]P1869,勉励友人再建功勋之时,词人亦在自勉。同样,在此前一年,辛稼轩写给汤朝美的《水调歌头》中也写道:“千古忠肝义胆,万里蛮烟瘴雨,往事莫惊猜。”[4]P1872“蛮烟瘴雨”一方面确指岭南多瘴的恶劣环境,另一方面,既是深层的一面,又指汤朝美、甚至是辛稼轩本身经历的艰难岁月。但这终将会成为过去,二人拥有的报国的忠肝义胆才是千古不变的。除此之外,辛稼轩还在《蓦山溪》中直抒胸臆:“两手挽天河,要一洗、蛮烟瘴雨。”[4]P1910在此,辛稼轩所要洗净的“蛮烟瘴雨”,“不但包括威胁和平安宁的侵略者,而且包括阻挠他恢复大业的投降派”[2]P72。
又如辛派先驱张孝祥《念奴娇·张仲钦提刑行边》一词中所写的“弓刀陌上,净蛮烟瘴雨,朔云边雪”[4]P1691。这里的“蛮烟瘴雨”和“朔云边雪”显然是对侵略者凶横跋扈的比喻。不惧战争的残酷,愿与侵略者弓刀相向,道出了南宋男儿安定边疆的坚定信念。再如《鹧鸪天·提刑仲钦行部万里阅四月而后归辄为太夫人寿》中言“长驱万里山收瘴,径度层波海不风”[4]P1691,依旧展现出了铁骨铮铮的英雄气概。
爱国精神的表现可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优良传统,是历代有志之士讴歌的永恒主题。由前文的分析可见,宋词中的“瘴疠”意象书写里表现出的词人情怀,无论是沉重的,还是激昂的,均离不开深厚的家国之情。在动乱之时,偏安一隅的词人们仍深切表达希望国家安定统一的愿望;在国难当头之时,词人们正气凛然,携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魄力,慷慨请缨。“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它在人们深层次精神世界中起着一种潜在的作用,具有一种无形的强大的精神凝聚力。这一点,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5]P42的确,“蛮烟瘴雨”泯灭不了报国之情,这份情怀恰恰是在“蛮烟瘴雨”里显得格外令人动容。
四、意义与总结
词,兴起于唐五代,鼎盛于两宋。从唐五代至宋初,对“瘴疠”的书写少之又少,但从北宋中期开始,词人开始关注“瘴疠”意象,并于南宋词人的作品中广泛运用。这当然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原因,也关乎词体文学发展,突出表现为“词的诗化”倾向。
从题材表现上看,这无疑是宋词更贴近生活的反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谈论宋诗时曾言:“宋人的目光不仅仔细地注意着家庭或家庭的周围这些身边的事物,企图遍及它们的各个角落,对社会、国家——人类的大集团,其感觉之敏锐也是前所未有的。”[6]P16宋人向外的目光,敏锐地捕捉到反映现实生活的素材,也正因如此,“瘴疠”这一令人谈及色变的疾病才会化成各种文学意象进入宋人的词作,并呈现出不同的情感表达与思想内蕴。相比词的艳情、闺情等传统题材,“瘴疠”意象多出现于咏物、咏怀、祝颂等词作中,显然已经挣脱了传统题材的束缚,而更趋向于诗的创作题材。
从情感表达上看,这应当是词体文学情感表达的多样化呈现。历来,人们对词的情感表达认识,无非就是伤春悲秋、离愁别恨、男女怨别等个人微妙情感的展现。吉川幸次郎先生也曾在书中言:“最重要的情感,是寄托在诗中而不是寄托在词中的。”[6]P9确实,填词对宋代士大夫而言,毕竟只是娱乐性的活动,诗在宋代文学中依旧占据主流地位,词仍无法与诗并肩而论。但是,从上文的分析中也可看到,借用“瘴疠”意象传达出的词人的情感,已不再是个人瞬间流露的细微的悲怨之情,而是长久思索后的宏大的人生之感。宋人将“人生看成是漫长的持续,看成是默然的抵抗”[6]P20,因此他们将悲哀扬弃,以乐观豁达的态度笑对坎坷人生,减轻了恶劣环境对身心摧残的痛苦,用豪气呼唤美好,用信念拥抱未来。而将报国的豪情于词中抒发,这是士大夫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渴望。这都是对词体文学的“悲情”传统的突破,而向诗的情感表达迈进。
从审美境界上看,这显然是对词境的开拓,也是化诗境为词境。词境与诗境在审美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正如王国维所言:“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7]P19诗境是阔大的,而词境是细长的。诗的创作如登高远眺,将广阔视野下的万象勾勒而出,以情感的外物化,作为审美特质。词的创作如小楼听雨,将内心的微妙变化点滴记录,将幽微精妙的内心世界的描写作为审美旨归。 因此,诗要在波澜壮阔的场景中反映社会人生,词则要在精微细密的内心里显现个人情思。一般而言,词人总会将外在的景物以及由景触发的幽微的情感,通过细腻的笔触巧妙地结合起来,构成细美微妙、迷离惝恍又异常和谐的艺术境界。然而,从有着“瘴疠”书写的这42首词作来看,并非全是如此。因为“瘴疠”意象多以云、雨、雾、烟等自然物象出现,这类物象本身就难以确定界限,总以浑茫的状态呈现,因此,加上其他意象的配合便极易形成迷蒙之态,因迷蒙而觉无边,阔大之境由此而生。尤其是南宋中后期的作品,一改词体文学原有的精微含蓄特质,呈现出宏大壮阔之境。如南宋末年词人陈纪《满江红》一词中道:“只手为天行日月,寸怀与物同苏息。到于今,天定瘴云开,伊谁力。”[4]P3392这是人定胜天的自信,人与万物共存,与日月同辉,凭一己之力扫除一切障碍。这吞吐大荒、包孕日月的词境已不再是灵魂世界的瞬间触动所能呈现的,而是经过社会人生涤荡的感发,这恰恰是诗境所要追求的。
总而言之,“瘴疠”意象的书写是宋词长卷中独特的一抹色彩,既丰富了词的题材表现,以全新的视角展现当时的社会生活,又充实了词的情感表达,借以“瘴疠”意象流露出的人生之感、故国之思、报国之情已超越了词体文学的悲情路数,使词也能同诗一般寄托词人深厚的情志。同时,将“瘴疠”意象引进词的创作,又为词境的拓宽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词境从幽深细长向高远宏大转变。这些都是词的诗化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词的传统观念有着突破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