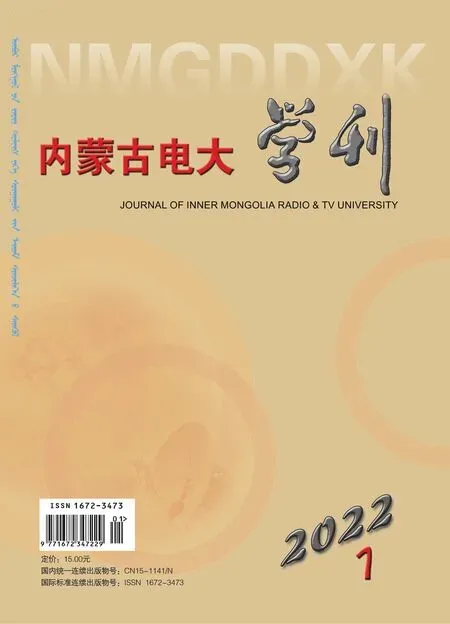当代农村题材小说家庭结构嬗变的伦理意蕴探析(1949-1966)
2022-03-18曹金合
曹金合
(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家庭的组织结构嬗变,对个体成员的生长环境、性格特征、情感意蕴和伦理道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小生活的家庭氛围会先入为主影响和制约一个人后天的伦理观念重塑。传统的“四世”或“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形成的壁垒森严的宗法伦理结构,对“一言堂”的秩序维持起到了保护作用,这种以长辈为本位的家庭结构体现出来的不平等的等级观念,有着相沿成习的宗法伦理和私有财产形成的物质基础支撑,但这种超稳定的家庭结构的宗法性、保守性和私密性面临着具有现代性色彩的合作化运动的冲击。尤其是“家庭私有财产范围缩小(特别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家庭生产功能被剥离出去,大大削弱了家长地位和其对成年子女的约束能力,进而对家庭形态、家庭规模、家庭代际关系等产生作用,农村家庭结构、代际全面趋向简单化”。[1]土地逐渐归集体所有,带来的家庭生产功能的弱化,自然让每一个处于问题旋涡中的成员面临不同的选择,物质基础比较坚实的家庭,都不希望通过分家造成力量的削弱,赵树理的《三里湾》中,干部王金生的笔记“高、大、好、剥、拆”就是对合作化运动冲击大家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简洁说明。面对入社之后人多地少、贫瘠土地居多的现状,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家庭成员都知道,如果按照全村人口计算土地和产量的平均数,那么拥有肥沃的土地、精壮的劳力、有利的生产条件的翻身户是不可能对损害小家庭利益的农业社感兴趣的,而家中的积极分子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提出的分家要求,显示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彻底性和坚决性。此时此刻大家庭中的主事人,因受到政治伦理对宗法权威的压制,已不能控制叛逆者急于向农业社靠拢的意向,所以在入社闹分家问题上出现的“拆”与“不拆”的叙述声音,体现出来的就是家庭内部结构的纠缠。因为大家庭的封闭落后带来的宗法价值观念已严重阻碍合作化运动的顺利进行,所以农村题材小说的叙事者一般采取道德归罪的模式,形象地说明大家庭成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大家庭以浓缩的形式包含的阻碍和对立的负面因子,只能以子辈们的分家告终。这样,大家庭的解体和小家庭的建立,就成为农村题材小说表现家庭结构变化的突出表征,蕴含的伦理价值观念的转变值得深思。
一、 大家庭解体的必然性:道德归罪模式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叙事者熟稔乡村的生活观念,他们清晰地意识到传统大家庭在一家之主的带领下,有时会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殷实的家底、合理的分工和高瞻远瞩的筹划会让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产生心理上的依赖感和精神上的归属感,特别是生产与消费功能集于一身的大家庭组织的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会在比较散漫的成员之间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由衷的自豪感,但这样的家庭结构形成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显然不利于异质的现代文化价值观念和伦理思想的传播。从普遍意义上来讲,“家庭的固若金汤会使外在的力量难以入侵,使家庭成员在面对国家权力时,保持着特殊的独立性。一家之长对家庭内部成员的直接领导,使权力的来源变得唯一。越是具有向心力的家庭,抵御外界的能力越强大,阻碍政治运动入侵的力量也就越强大”。[2]具有勤俭节约品质与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的当家人,领导管理的大家庭,一般对合作化运动保持冷淡的态度。一些落后的大家长会凭借手中的宗法权力阻碍家庭成员成为农业社的合格社员,但秉承传统的伦理精神的大家长,其发家致富的手段与管理成员的成熟经验,又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无法忽视的,农村题材小说的叙事者只能采取不同的叙事策略,应对文本中出现的思想主题与审美意蕴的裂隙。
一方面,小说的叙事者对当家人站在大家庭的权力结构顶端,费心操劳的坚韧精神以及获得的心灵满足是抱着一定的同情与赞美态度的。传统的大家庭金字塔式的内部结构不能简单地用黑格尔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观点进行敷衍阐释,它的源远流长与自身在不同语境中保持的独立性,充分说明它有值得借鉴的优势。在主流意识形态确定的批判基调与叙事者不自觉流露的主观赞美倾向的夹缝中,也记录了大家庭如何井然有序地运作。《创业史》中二十多口的大庄稼院的当家人郭世富,在关注柴、米、油、盐各货行情的基础上,及时对成员的花销做出必要的指示甚至警告,对兄弟、妯娌、子侄等与自己具有亲密血缘关系的成员,按照传统的民间伦理道德,治理得井井有条,并不因其中的成员与自己的亲疏远近就采取偏袒的态度,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的处理,这样减少了成员之间的利害冲突和情感摩擦,尽一切力量为将来“五世”同堂的理想目标而奋斗的精神,确实值得尊敬。尤其是在温情脉脉的亲情伦理的浸润下形成的和谐、繁荣、欢快、明朗的氛围,更是成为当家人凝固大家庭结构的精神动力,梁三老汉在养子梁生宝的大公无私精神感召下,尽管在理性上可以接受小家庭存在的合理性,还是在心中留下了难以去除的大家庭其乐融融带来的情感满足的印记。在他头脑中闪现的聪明能干的儿媳妇代替头发霜白的老伴操持家务的新景象,他仿佛看到贤惠孝顺的儿媳妇盛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饭,恭敬地放在他这当公公面前的饭桌上,那种家庭氛围的温馨与幸福是单门独户的小家庭感受不到的;他畅想一年以后出现的又胖又精的小孙子,为草棚院的生活增添无穷乐趣,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绝对超越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伦理规则的诉求。在李准的《一串钥匙》、王汶石的《井下》、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农村题材小说中,都记录了大家庭生活的真实面貌,在某些方面体现的有能力的家长统一管理大家庭过程中的高效率和凝聚力,也说明大家庭作为不受时代欢迎的“遗形物”的结构,有合理之处。
作为深受乡土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影响的作家,无意中表露的大家庭结构的优势,显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相距甚远,所以另一方面,叙事者采取了行为丑化和道德归罪的补救措施,对文本表达的主题意蕴的含混之处进行弥合。这主要针对处于大家庭结构的核心人物——当家人的投机倒把、肮脏龌龊、坑蒙拐骗、花心好色等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思想行为表现,所以在《创业史》中也对勤劳精明的富裕中农郭世富的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行为进行丑化改写,集中体现在作为当家人在买卖关系上,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贪小便宜的行为。在违背买卖公平的原则上,小说首先通过他在黄堡集上买东西拣点便宜的事,突出他乘人之危不道德的因素:主人因为用钱紧急不得不出手的骨架匀称、毛色一致的小骡小马等牲畜,往往成为他选择购买的对象;有些粜粮食的庄稼人,不愿意把辛辛苦苦带来的没有卖掉的粮食费尽心力带回去,只好减价出售,正是他占便宜、心情最为舒畅的时候。其次,通过他卖粮食以次充好的欺骗行径,揭露其内心阴暗扭曲的嘴脸。小说突出强调他准备装袋卖粮食的时候,在袋子的两端装好麦、中间掺杂劣质麦,以次充好的不道德行为的惯常性和心理的坦然性,充分说明传承孔夫子和朱夫子两位老人家的治家观念的落后性。对于道德品质不坏的当家人按照传统的“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约束和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则采取讽刺的艺术方式,凸显其秉承的价值观念的不合时宜性。王汶石的《井下》中的一家之主老八,以为凭借家长的权威,就可以不讲道理地对孩子们打打骂骂,但其实他的叫骂、抱怨、诉苦、牢骚在晚辈们的心目中已成为熟视无睹的一道风景,“他就是那号人”的共同认知和不屑辩驳的理由,就是对传统家庭结构推举的当家人的莫大讽刺!《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内外有别的话语表达方式,显然也是耍弄家长威风的不平等思想观念和伦理意识的典型表现。可是他继承老辈的家规对儿子学文、崽女满姐和菊满不容商榷的命令口气以及动辄打骂的坏脾气,致使孩子习以为常,结果事与愿违,无不是对他自以为是的家长权威的颠覆和消解。有时为了突出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家长的落后性,以达到教化民众的效果,就采取自曝其短的行为和语言丑化的方式,揭露其思想观念的顽固。最典型的是王杏元的《绿竹村风云》中积极分子葫芦的糊涂爹,对儿媳红梅劝他入社产生了矛盾冲突,面对儿媳苦口婆心地劝说和分析不入社对整个家庭的生产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他回答若日后采水果、砍竹木雇不着人,就让本来到手的果实烂掉发木耳,这样蛮不讲理的话,将一个胡搅蛮缠、不切实际的家长不负责任的一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当然,对那些在政治成分上属于反动阶级的特务、富农、地主等身份的家长,小说的叙事者就会按照敌我矛盾的处理方式,采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种民间最大的恶行对家长的思想行为进行道德归罪。《创业史》中如此精明的富农姚士杰,却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中最为人诟病的乱伦问题上一再犯错,甚至在利用侄女素芳的肉体满足自己的生理欲望的时候,竟然想在精神上控制自己的侄女成为破坏梁生宝互助组的一枚棋子,这些都体现出其阴险奸诈与荒淫兽性,显然是理性大于感性的作者巧妙安排的有意味的情节。这样,作为大家庭的灵魂和统帅的当家人的道德品质上的瑕疵,为大家庭结构的解体敲响了丧钟,小说叙事者借助民间道德与政治伦理的合谋,为聚族而居的大家庭结构的解体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合理依据。
二、 小家庭建立的合理性:政治与时代的共同趋势
从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蕴含的价值观念来说,传统的大家庭模式与宗法伦理观念的大行其道以及家庭成员对不成文法的惯例规则的自觉认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随着新中国成立带来的家庭成员不分男女老幼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支撑大家庭结构的等级观念和宗法伦理关系面临着不合法的尴尬局面。当然,家庭结构由大到小的发展嬗变也是由合作化运动的政治诉求决定的,因为“从本质上说,政治决定家庭的选择走向,任何家庭都是政治逻辑的体现”[3]。政治与家庭结构间接的决定关系,在农村题材小说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家庭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渗透形成的新的伦理观念,使得巩固大家庭结构的最后一根稻草失去了用武之地,原来的充满传统等级意识的生活空间,变成子辈们争夺政治话语权和个体独立权的崭新舞台,以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支持为旨归的政治伦理观念,会理直气壮地对落伍的民间伦理提出反驳和批评。由于小家庭成员的思想先进性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大局意识合拍,特别是合作化运动之后,子辈们组成的小家庭脱离了封建家长的监督和束缚,按照劳力分工获得的劳动果实具有支配权,体现的尊严和价值是在分配不均的大家庭中没有的。李准的《一串钥匙》中的白封举将象征一家之主的权力的钥匙交出来,引发的家庭结构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典型的证明,儿女们终于尝到付出与收获名副其实的甜头,由此带来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正在无声地说明小家庭建构的合理性。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叙事者,首先按照现代伦理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浸入比较牢固的家庭堡垒引起的不同成员之间的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作为分家的重要依据,在同一个家庭成员内部的思想观念的分歧,并没有达到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程度的时候,家庭结构修复机制会采取妥协的方式,在彼此的思想观念的相通之处找到融入的契合点。但农村题材小说恰恰在涉及个体成员的未来幸福生活的根本问题上,出现了父母与子女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当家庭中的成员对于幸福的定义,对于将来生活的定义的看法出现分歧的时候,矛盾不可避免。当冲突激化到一定程度,分家也成了必然的结果。”[4]《三里湾》中生活在封闭落后家庭的共青团员马有翼,在未婚妻王玉梅的逼迫下,不得不为未来的幸福掀起家庭革命,由此导致的不可调和的分家的矛盾冲突,用异质的伦理观念衡量,就是走合作化道路政治伦理观念与维护大家庭的宗法伦理观念的较量。对叙事者秉承的教化观念来说,无论怎样的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晚辈坚决与封建落后的大家庭决裂,如果性格气质懦弱的晚辈在气势强大的长辈面前没有充足的把握与父亲划清关系,从而出现相互妥协的局面,那么一定要找一个现实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帮手增强家庭革命的力量。所以小说安排本来不是统一战线的王玉梅加入政治婚姻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那些在父权的威势面前不敢反驳的年轻人树立斗争的楷模。作为一个深谙乡村文化习俗和伦理观念的创作者,赵树理认识到由此出现的小家庭的身份合法性问题,他在《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中提到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农村现在急需要一种伦理性的法律,对一个家的生产、生活诸种方面都做出规定。如男女成丁,原则上就分家;分家不一定完全另过,只是另外分一户,对外出面,当然可以在一起起灶。”[5]这种带有伦理色彩的法律条文将情与理的异质因子融合在一起的方式,有效解决了“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棘手问题,也为小家庭生活功能的简单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依据。小说遵循“好女爱先进”的政治伦理观念,促成的技术骨干王玉生与中学生范灵芝建立的小家庭,通过当事人的商量,打算结婚后能独立出来的话,那么就借助农业社的食堂和靠临河镇的裁缝铺提供的便利,解决家庭中最基本的衣食问题。此时,所谓的小家庭就是夫妻双方只有夜晚才在一起的安乐窝,这是赵树理对家庭的生产和消费功能降到最低标准后,形成的对未来小家庭承担的血亲组织功能的畅想。
随着政治化的革命对乡村私密性的大家庭的文化空间结构的渗入,政治伦理观念和时代精神的合谋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对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性产生了明显的冲击。这样,“被置于集体化进程之中的人们开始根据国家树立的新道德标准选择自己的婚姻对象,婚姻的稳定性有所松动,离婚、退婚、再婚等现象已不再罕见,一些家庭因此破碎或重聚,分家观念趋于流行,传统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开始向多个小家庭转化”。[6]由此在新的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观念影响下的小家庭的个人幸福和婚姻保障,都带上了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家庭的民间价值观念和传统习俗被政治意识和阶级蕴涵的革命诉求代替的现象,成为农村题材小说惯常表现的一道风景。《创业史》中的合作化事业的带头人梁生宝在失恋之后,与竹园乡的离婚女人刘淑良组建的小家庭的幸福,来源于两个人的志同道合,对他们终成眷属之前彼此的婚恋关系的破碎重组过程浓墨重彩的描摹,显然是为了说明二人打破传统伦理观念的合法性。他们为了合作化事业的顺利健康发展,尽量降低小家庭的功能羁绊,正是时代语境迫切需要的楷模,以党的儿子自居的梁生宝很自然地要将个人的私事纳入集体事业的天平衡量孰轻孰重,对他们结婚前爱情的坎坷曲折详细刻画,与修成婚姻正果后比较琐碎的日常生活一笔带过,形成了鲜明对比,突出了小家庭建立的政治基础。纵观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叙事者在刻画描摹情节和选材布局的过程中,都是在有意识地突出夫妻二人的阶级成分和政治身份,为阶级伦理替代血缘伦理,成为小家庭的合法性建立基础和实施依据保驾护航。周立波的《山那面的人家》中的社员邹麦秋和新娘子关心集体、热爱劳动的特征被一再突出,甚至让他们在结婚的神圣时刻做出了一些不合常理的举动,凸显他们符合意识形态的感人壮举:新媳妇面对贺喜的众人亮出的劳动手册中记录的两千工分产生的自豪感,确实与传统家庭中晚辈们的劳动果实被长辈据为己有的委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新家庭建立的道义性增加筹码;新郎表现政治伦理功能的符码性决定了他的行为要更出乎常人的想象,在拜堂成亲的关键时刻玩失踪的游戏引起众人的好奇心以及在储藏红薯的地窖里发现新郎在查看农业社的红薯种,这一谜底揭晓带来的效果,都是为了体现小家庭更符合时代要求的伦理主题。其实,表现此类主题意旨的小说比比皆是,比较典型的如谷峪的《新事新办》中的王贵德与凤兰、李南力的《唐兰的婚姻》中的杨志平与唐兰,都是借助婚恋的视角,淋漓尽致地表达劳动模范或退伍军人的身份对小家庭建构的助力,也从侧面凸显了政治伦理对家庭结构的干预功能远远超过封闭保守的传统伦理所能承受的程度,所以小说中表现的小家庭对顽固的大家庭的冲击,出现一边倒的摧枯拉朽的态势才顺理成章。
三、结语
不过,在个体农民的大家庭的功能结构由土改时革命衷心依靠的主力嬗变为被动改造对象的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左倾”话语罔顾社会现实和传统的血缘伦理关系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革问题,不容小觑。在这方面,“左”甚至极“左”的政治话语可以凭借权威优势,对处于劣势的民间伦理观念进行规约性的言说和指示,但作为上情下达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凭借人道主义情怀,对家庭的过激操作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显示了熟悉乡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作家,设身处地的悲悯情怀和艺术良知,也潜在地透露出他们坚守的伦理底线。方之在《浪头与石头》中描述的大流乡团支书小两口在入社问题上与长辈产生的分歧以及由此导致的矛盾冲突酿成的分家现象,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个鲜活缩影。长辈按照传统伦理观念积淀的权威,只是代代相传的行为规范的顺其自然衍生,对晚辈因为有新的价值观念的撑腰,就无所顾忌地挑战一家之主的权威行为当然不能容忍,二者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反映的是大家庭和小家庭对合作化的方针政策态度问题。依据政治伦理的要求,产生的分家后果是小说在谋篇布局的时候就筹划好的,不可避免的分家造成的人伦关系的破坏和个体情感的伤害却是有良知的叙事者关注的。所以,即使是秉承现实主义精神如实地刻画和描摹造成的不良后果,也会对表现的拆散大家庭结构的合理性主题意蕴造成一定的反讽效果。小说对他们年轻一辈闹分家出现的没有劳动力的严峻现实、由此“全家吵得鸡飞狗跳,老太婆差点上了吊”触目惊心的现象尽管轻轻掠过,但不经意之间出现的引人回味的细节和情节,却颠覆了分家的合理性主题,也许不能搞一刀切,也是叙事者偶尔露出的人道情怀的端倪。同样的现象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作品中叙事者重点突出大办公共食堂的政治任务,对家庭的结构和功能的解体起到的釜底抽薪的重要作用。康濯的《吃饭不要钱的日子》[7]描述公共食堂的出现,对家庭血缘纽带和亲密关系的破坏确实触目惊心,小说通过共青团员陈银海的视角,对名存实亡的家庭现状的打量,实际上透露出个体成员对家庭的心理依赖和血浓于水的情感交流的渴望,反映的是传统家庭的生育、生产、消费、生活等基本功能被取消后,个人与家庭的情感维系也就到了可有可无的边缘化处境。“哺”与“反哺”的长辈与子辈之间纵向扶养关系的断裂,兄友弟恭、其乐融融的平辈之间横向关爱关系的缺失,实际上就将整个家庭结构的核心根基拔地而起,家庭就真的名存实亡了。伴随公社化带来的集体大家庭彻底打破了传统的血缘伦理,屹立千年的大家庭和作为新生事物的小家庭,都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下失去了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