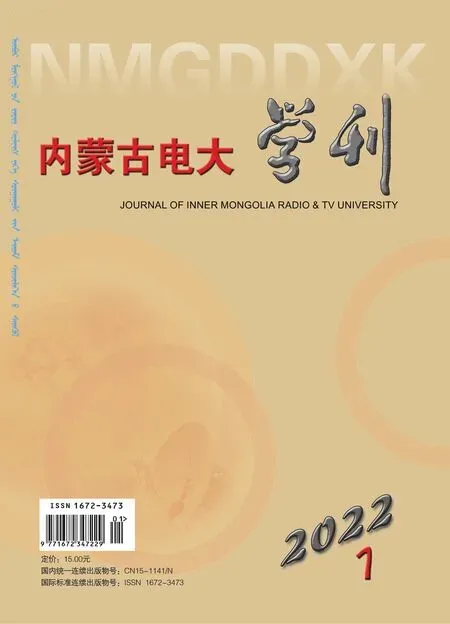元代汉儿言语和蒙汉混合语的关系与辨析
2022-03-18阮剑豪
阮剑豪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一、引言
《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元代文献中有许多佶屈聱牙、晦涩难懂,既不同于文言,又与宋元白话大相径庭的文字。试举例如下:
例(1)《元典章·户部》卷十三《斡脱每休约当》:斡脱每里多有勾当里行的,营运与钱的人每行运圣旨,交各处买卖里去呵,各路官人每“圣旨里他每的名字不是”么道,约当,很生受有,么道奏来。如今那般赍擎圣旨行的斡脱每的官人每处显验的文书将着行呵,将他每的人等根底休约当者。
我们再来看一段元代通俗类书《吏学指南》序言里的一段话:
例(2)《吏学指南》:尝闻善为政者必先于治,欲治必明乎法,明法然后审刑,刑明而清,民自服矣。所以居官必任吏,否则政乖。吏之于官,实非小补。
以上面所引的《元典章》和《吏学指南》两段文字对比,前者貌似白话,后者是典型文言,但后者远比前者浅显易懂。
长期以来,由于“重言轻文”的缘故,元代文献中的这类既像白话又不是白话的语料并未得到足够重视。进入二十世纪后,学界对于这些语料逐渐产生较大的兴趣,各种研究成果出现。近几十年来对于此类语料的研究更是逐渐深入,尤以田中谦二、太田辰夫、亦邻真、李崇兴、祖生利等学者的研究为人所重。
太田辰夫是较早注意到《元典章》《通制条格》中此类特殊语言现象的人,他在发表于1954年,题为《关于汉儿言语——试论白话发展史》的论文中提出一种明确的观点,他认为自五胡十六国以降,中国北方存在着一种“汉儿言语”。在元代, “真正以汉儿言语为基础写作的,并不是元曲宾白这样的文学作品, 而应看作是白话圣旨、《元典章》《通制条格》《永乐大典》中引用的包含着元代口语的文献、以贯云石《孝经直解》为中心的各种直译类著述等”。应该说,太田辰夫敏锐地注意到了“汉儿言语”和元曲宾白之类白话文的区别,见地可谓非同一般。但他只是粗略地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并没有详细展开,更没有阐述“汉儿言语”与直译类著述的关系。田中谦二将这种乖戾倒错的文字称为“蒙文直译体”,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发表了《蒙文直译体中的白话——[元典章]备忘录》,对《元典章》中“蒙文直译体”语料做了详尽的分析,指出了其语法、词汇方面的特殊性。 亦邻真是国内较早对上述语言成分深入研究的学者,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亦邻真把《元典章》、《通制条格》中这类佶屈聱牙的文字称为“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亦邻真说:“硬译文体的语汇采自元代汉语口语,而语法是蒙古式的,一篇典型的硬译公牍,等于一份死死遵循蒙古语词法和句法,用汉语作的记录文字。”①
二、直译体公文的口语基础与蒙式汉语
亦邻真认为他称呼的“硬译公牍文体”完全是一种书面的文字,是脱离口语的,这种观点在较长时间内被元代语言研究者认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语料的发现,特别是1998年《古本老乞大》在韩国被发现,一些学者开始转变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001年,李崇兴发表《元代直译体公文的口语基础》,指出:“由于《古本老乞大》是旧时朝鲜人学习汉语会话的教材,必定是以实际口语为依据,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元代确实有这么一种汉语与蒙古语混杂的口语存在。”在同一篇文章中,李崇兴认为:“我们承认直译体公文有口语基础,并不是说书面上写的与口头上说的完全一致,书面上的表现完全是口语的翻版。对汉族人来说,《古本老乞大》比起那些直接从蒙古语翻译过来的直译体作品来,可接受度显然要高。”在这里,李崇兴已经注意到《元典章》中的那些硬译体(直译体)公文与《古本老乞大》中的文字是有区别的,但是很明显,他依旧认为硬译体(直译体)公文是直接翻译蒙语的产物,虽然有一些口语基础,但并不是口语的书面化。2007年,祖生利发表《元代的蒙式汉语及其时体范畴的表达——以直译体文献的研究为中心》一文,明确提出“元代大量的直译体文献是以蒙古人所说的蒙式汉语为口语基础的”这一观点,同时他给“蒙式汉语”下了一个定义,“蒙式汉语,简而言之,指元代蒙古人所说的一种汉语民族变体,是元代语言强烈接触的产物之一。它以北方汉语为上层语言,但从语音到词汇和语法,都受到蒙古语底层的影响。作为一种中介语,它主要用于蒙古人和汉人的语言交际”。祖生利还认为,“蒙式汉语本质上是一种以北方汉语为上层语言、以蒙古语为底层的皮钦语”。他进而提出“蒙式汉语”形成的三个阶段:1.早期(1211~1260),即军事征服期和蒙元统治时期。这个时候蒙汉交流的皮钦蒙语或皮钦汉语开始逐渐形成。2.中期(1260~1294),即世祖在位的三十余年。这一时期蒙汉语言接触全面展开,早期“蒙式汉语”在结构和功能上逐步得到拓展,成为蒙汉语言交际的主要手段之一。3.后期(1295~1368),从成宗继位至元朝灭亡。这一时期蒙汉语言接触更加深化,“蒙式汉语”和标准汉语经过互动的“协商”,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北方汉语变体—— 汉儿言语。我们认为,祖生利提出的“蒙式汉语本质上是一种皮钦语”的观点是一个颇有建树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他提出“蒙式汉语”是在北方汉语和蒙古语两者接触基础上产生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祖生利认为先有皮钦语性质的“蒙式汉语”,后有元代北方口语——“汉儿言语”,对于这个说法,我们并不同意。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赞同太田辰夫的观点:“汉儿言语”产生于蒙古人到来之前,而不是之后。②至于“直译体文献”“蒙式汉语”“汉儿言语”三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元代北方口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祖生利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
三、所谓直译体文献是汉儿言语和蒙汉混合语的书面化体现
以《元典章》《通制条格》为代表的这种古怪的元代书面文字,不同学者有不同称呼,太田辰夫称之为“汉儿言语”(严格地讲,太田辰夫并未直接用“汉儿言语”称呼这类文字,只是说它们以“汉儿言语”为基础撰写),田中谦二称为“蒙文直译体”,亦邻真称之为“元代硬译公牍文体”,李崇兴称之为“直译体公文”,祖生利称之为“直译体文献”,指的是同一事物。我们认为,除太田辰夫以外的上述四位学者的称呼中都带了一个“译”字,并不是很恰当。因为此类称呼容易让人以为这些古怪文字是先有蒙古语形式,再翻译成汉语形式,实际情况恐怕并非如此。或许元朝的圣旨、诰令确实先有蒙语形式,再翻译成汉语布告天下,但其他种类的文书则很难想象都是先有蒙语底本,再转译成汉语的。以《元典章》为例,在各类公务往来文书中,既有许多“直译体公文”,也有大量的如《吏学指南》里的传统文言文,甚至还有不少非常浅显的白话文。 我们认为,这些不同风格的文字都是由吏员书写的,其中的“直译体公文”包含了一种蒙汉官员都能理解的交际语,这种交际语就是蒙元时期被广泛使用的皮钦语——蒙汉混合语,也即祖生利所说的“蒙式汉语”。学界之所以一直将这种皮钦语书写的文字称为“硬译体”或“直译体”,恐怕是受了《元朝秘史》和贯云石的《孝经直解》的影响。这两部书不同于多种语料形式并存的《元典章》和《通制条格》,通篇都是颠三倒四的蒙汉混合语。《元朝秘史》逐字逐句对蒙古文进行音译和旁译,附有总译;《孝经直解》则是将文言文的《孝经》直接翻译成蒙汉混合语,学者们才会产生错觉,以为这类文字纯粹都是生硬翻译蒙古语的产物。我们同意祖生利的说法,蒙汉混合语(祖称之为“蒙式汉语”)是一种皮钦语,但我们认为,他的“元代大量的直译体文献是以蒙古人所说的‘蒙式汉语’为口语基础的”这一观点表述并不清晰和全面。我们认为,所谓的直译体文献其实是两种口语的书面化记录,其一是带有若干阿尔泰语法特征的元代北方汉语(以下使用太田辰夫的说法“汉儿言语”),其二是作为汉人(包括被汉化的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下不赘述)和蒙古人交流用的皮钦语——蒙汉混合语。这两种口语有一定的相似性,书面化以后并存于元代文献,确实容易被混淆,但两者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要精准称呼元代文献中那些既不是文言文,又不是典型白话的语料,就必须把蒙汉混合语和汉儿言语的名字一起列出来。
四、蒙汉混合语是汉儿言语的皮钦语变体
汉儿言语是元代通行于北方,被汉族和契丹、女真等许多少数民族广泛使用的汉语通用语。中国以大都(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就长期处于南北分裂、胡汉杂居的状态,中间虽经历过隋、唐的大一统岁月,但从五代十国至金朝末期,又有三百多年的南北分裂史和胡汉杂居交融史。由于汉人在人口数量、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大量的少数民族成员慢慢学会了汉语,北方地区汉语变成了通用语言。同时,由于长期的语言接触,辽、金时期的汉语北方口语很可能已经带上了若干阿尔泰语的特征,与南方的汉语口语有了一定区别。《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第三十三程有下列记载:“自黃龙府六十里至托撤孛堇寨,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虏获异国人则迁徙杂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室韦,东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以汉语为证,方能辨之,是知中国被服先王之礼仪,而夷狄亦以华言为证也。”上述史料中的“汉语”,显然是指北方口语,即汉儿言语。从上文我们可以推测,最迟到辽代中期,汉儿言语很可能已经成了北方各民族的通用语。这种带有通用语功能的汉语,从现有的金院本以及《古本老乞大》的内容来看,虽然留有一些语言接触的痕迹,但其性质并不是皮钦语。
等到蒙古人灭金,占领中国北方以后,由于多数蒙古人驾驭使用汉语的能力很难达到母语的水准,而汉人也只有少数人能学会蒙古语,蒙古人和北方汉族民众交流就只能通过某种皮钦语进行。我们推测,当时官府公文书写、阅读很可能是这么一种情况:蒙古官员大多数不认汉字,但能听懂一些汉儿言语的变体——蒙汉混合语;广大中下层非蒙古族官吏则基本能读写汉语。由于蒙汉混合语(皮钦语)掺入了不少蒙语词,语法上也多向蒙语倾斜,将其书写成文字,给略识汉字的蒙古人看,或者由随员读给懂得蒙汉混合语的蒙古人听,基本上就不会有理解方面的困难。同时,因为蒙汉混合语是汉儿言语的一种变体,能识字的汉人当然看得懂。这种情况下,上下级的沟通交流、公文往返通过书面化的蒙汉混合语就完全可以进行了。《元典章》、《通制条格》里的公文请示和批复,皇帝诏书的传达大概都是这种情况。与此同时,与《元典章》、《通制条格》里的文言文和南方白话一样,作为北方汉人交际口语的“汉儿言语”,也不可避免地会大量进入这类官修公文合编,与蒙汉混合语混杂在一起。
五、汉儿言语与蒙汉混合语在词汇、语法方面的区别
随着蒙古贵族统治的加强和统治时间的持续,蒙汉民族间语言接触越来越多,汉儿言语和蒙汉混合语差异逐步减少,两者逐渐靠拢,变得越来越相像。尽管如此,蒙汉混合语作为一种皮钦语,性质并未改变,它与汉儿言语的区别还是明显的。这种区别存在于词汇、语法方面:
(一)词汇方面
蒙汉混合语是一种皮钦语,除了具备皮钦语的基本特征——“词汇的总量比较少”③,还有一些特有的词汇特征,比较典型的是出现了许多特殊三音词和同形别义词,而汉儿言语中较少见到这类词语。此外,蒙汉混合语中还掺杂大量的蒙古语译词,但这些蒙古语译词并不仅现于蒙汉混合语,即便是完全以文言撰写的元代类书《吏学指南》,书里也出现有“怯怜口”“斡脱”“大札撒”“斡鲁朵”“长生天”这样的蒙古语译词,所以我们不把蒙古语译词看作蒙汉混合语的特有词汇特征。以下着重介绍特殊三音词和同形别义词。
1.所谓特殊三音词,是指蒙汉混合语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词语:它们由三个字组成,外表像一个普通汉语短语,实际却是表达某个特定意义的词语,词语的真实意思与以短语形式体现的字面意思往往有不小的距离。下面举例说明:
大言语:煽动谋反、叛乱的话。
例(3)《元典章·刑部》卷三《乱言平民作歹》:木八剌小名的人,告讫马三、拦十等人每写立着文字,说大言语,么道说有。奏呵,差的买买去,将他每已招了的典刑了,转递号令者。
上面例句中的“大言语”是一个词,“煽动谋反、叛乱的言论”,并非表示“大的话语”意思的偏正短语。
要罪过:治罪,处罚。
例(4)《元典章·户部》卷十一《避差发》:前者,省官人每世祖皇帝根底奏了,说道:“职事低了或嫌地里远穷,受了宣敕不去的人每根底,依在先体例要罪过呵,怎生?”奏呵,“是也那般,要罪过者,交那畜生每种田者。”么道,圣旨有来。
“罪过”在元代的通常意思是“罪行、过失”,但这里的 “要罪过”已凝固成一个意义明确的词语,表示“治罪、处罚”,不能简单理解成“要(他)的罪行、过失”了。
其他常见的特殊三音词还包括:无体例——违法,违反规定。使见识——耍阴谋,使用诡计。根脚里——从前。添名分——升官。道不是——斥责,责怪。无疑惑(休疑惑)——果断地,毫不迟疑地。添气力——协助,配合。使气力——欺负,欺凌。觑面皮——徇私情。
2.所谓同形别义词,指的是蒙汉混合语中的某些词语,它们的内在含义和蒙古的典章、制度、文化、军事、政治紧密相连,表达某个特定的概念,与其在汉语中的通常意思有很大不同。我们认为,这种特殊用词现象的产生,和对译特定蒙古语术语有关。在用汉语转译某些蒙古语词语时,由于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概念,有时候就只能用意思相近的汉语词翻译。因此,当这些对译得并不精确的词语在文中出现时,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当作普通汉语词对待,而要仔细挖掘其在蒙汉混合语中的真正含义。
官人:管民官;亦指部落首领。
例(5)《元典章·刑部》卷十八《孛兰奚外驱不得隐藏》:“城子里的官人每,告发到官,觑面皮,依着圣旨不行呵,断三十七下,罢了他每的勾当。”
蒙汉混合语中的“官人”许多时候并不简单地指代官员,而是有“管民官”之义。“管民官”是对路、州、县等地方行政首长的统称(亦称“管民长官”、“长官 ”等),他们在达鲁花赤的监督下负责管理具体事务。管民官在蒙语中被称为“那颜”,经常被译为“官人”。但此官人非彼官人,具有特定的含义,和汉语中的“官员”相比,其内涵和外延有很大不同。有时候,“官人”还用来称代部落首领,如《元朝秘史》卷八:来时,路间被乱兵所阻挡,遇着巴阿邻种的官人纳牙答亦儿兀孙,说“这女子要献于成吉思”。文中的“官人”指的就是巴阿邻部落的首领。
城子:路、州、县。
例(6)《元典章·兵部》卷三《使臣驿内安下》:“中统二年,钦奉圣旨,节该:据往来使臣,城子里没勾当的休入去,如有勾当,入城去的使臣仰於盖下的使臣馆驿内安下者,官员、民户每的房子里休得安下。”
蒙汉混合语中,“城子”往往并不是指城市,而是指当时路、州、县等各级行政设置,甚至是某级官员管理、控制的一片地域。这和“城市”完全是两码事。
其他常见的同形别义词还有:告天——向神祈祷。营盘——游牧地,牧草地。委付——任命。小名——名字。推辞——抵赖,不承认。
特殊三音词和同形别义词多见于蒙汉混合语,但并不是说汉儿言语中就看不到它们的身影。道理很简单,蒙汉混合语本来就是汉儿言语的一种变体,两种语言的词汇并非完全隔绝的两个系统,而是互相渗透的,只不过这些过于俚俗、意思模糊的特殊三音词和同形别义词在以汉儿言语为交际语的人群中使用频率偏低而已。
(二)语法方面
蒙古语的语法特征在蒙汉混合语和汉儿言语中也呈现不同的面貌。作为皮钦语的蒙汉混合语,往往要照顾居优势地位的蒙古人的语言习惯,蒙语语法特征很明显,显得特别古怪乖戾,拗口难懂;汉儿言语本身就保留了某些阿尔泰语的痕迹(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加之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蒙汉混合语的影响,汉儿言语也具备一些蒙古语的语法特征。但相对于蒙语特征,汉儿言语中被保留的汉语语法特征还是要多得多,多数情况下,蒙语语法特征只是点缀和补充,一般不会影响对意思的理解。
关于蒙汉混合语的蒙语语法特征,田中谦二、亦邻真、李崇兴、祖生利等人都做过或略或详的阐述,简述如下:
1.长定语和长宾语的广泛使用,致使句子结构复杂。
2.用“么道”表明前面是引述部分,在句法上多起宾语作用。
3.大量使用“呵”表示假设。
4.只用方位词“上”和“上头”后置表原因。
5.大量使用后置介词“根底”,每一个“根底”的确切意思都要根据上下文来定。
6.用动词后加“者”表示命令祈使式。
7.属格人称代词放在名词后面,表示名词所属。
8.后置介词“行”,有“向”、“把”等意思。
9.“也者”表示一种不确定的语气,有“恐怕、大概”的意思。
10.宾语倒置,在谓语前面。
下面有三段例句,我们看看是否能从蒙语语法特征和蒙汉混合语词汇特征入手,将汉儿言语和蒙汉混合语区别开来。
例(7)《元典章·兵部》卷三《扎撒逃走军官军人》圣旨:亦黑迷失为头福建行省官人每奏:“跤趾国里、占城里出征时分,军官每、军每、水手每风水里推掉了逃了回来了的根底,罪过他每底不要了上头,去了的勾当每他怠慢了。如今俺大勾当里去了的时分,似那底一般逃走了不扎撒呵,勾当俺的怠慢一般有。更圣旨可怜见呵,怎生?”么道奏来。如今那般推辞躲闪的省官人每根底、没别里哥逃走回来的人每根底休疑惑,敲了扎撒者,道来,圣旨俺的,龙儿年二月二十九日柳林里有时分写来。
例(8)《元典章·户部》卷一《俸钞改支至元拘职田支米》:至大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天下诸衙门官吏俸钱不敷的上头,交俺商量了添与者。”么道,行了诏书来。俺众人商量来:“随朝衙门官员并军官每,如今见请俸钱内减了加伍,改换与至元钞,住支俸米。外任有职田的官员,三品的每年与禄米一百石,四品的六十石,五品的五十石,六品的四十五石,七品以下的四十石,俸钱改支至元钞、将职田拘收入官。又外任宣慰司、军官、杂职等官俸钱,十分中减去三分,余上七分改支至元钞两。随朝衙门、行省、宣慰司的吏员俸钞,减去加五,其余钞数与至元钞。至元钞一十两以下,每月与俸米五斗。外任行的小吏每的俸钞,依数改作至元钞,俸米依旧与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
例(9)《古本老乞大·6b6》:有甚么难处?刷了锅者,烧的锅热时,著上半盏清油,将油熟过,下上肉,著些盐,著箸子搅动。炒的半熟时,调上些酱水,生葱料物打拌了,锅子上盖覆了,休著出气。烧动火,暂霎儿熟也。
以语法特征来对照,例句(7)能体现蒙语的语法特征1、2、3、5、6、7、10。例句(8)能体现蒙语的语法特征2、4、6、8。例句(9)能体现蒙语的语法特征6、10。
以词汇特征来对照,例句(7)中的特殊三音词有要罪过、休疑惑;同形别义词有官人、推辞。例句(8)、(9)均无特殊三音词和同形别义词。
结论:例句(7)是典型的蒙汉混合语;例句(8)和(9)是汉儿言语。
六、结语
综上,我们认为,元代北方地区的通行口语有两种:汉儿言语和蒙汉混合语。前者是汉人之间通用的北方口语,后者是汉人和蒙古人交往沟通时使用的一种皮钦语。现存的元代文献中的所谓直译体公文语料正是这两种口语的书面化产物,具体而言,《元典章》、《通制条格》等文献中许多佶屈聱牙的语料既包括蒙汉混合语,也包括汉儿言语;而贯云石的《孝经直解》和元代碑文上记载的汉字文献,则基本是书面化的蒙汉混合语。蒙汉混合语是汉儿言语的一种变体,具有词汇和语法上的鲜明特征,汉儿言语与蒙汉混合语有一定的相似性,容易混淆,但细加辨析,还是可以将两者区分的。
[注 释]
①见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载于1982年《元史论丛》第一辑。
②见太田辰夫《关于汉儿言语——试论白话发展史》,载于1954年 《神户外大论丛》5-3。
③见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