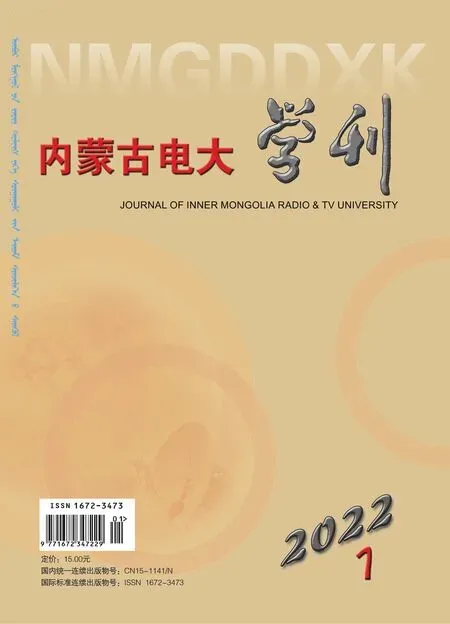从历史哲学境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的探析
2022-03-18田红梅
田红梅
(安徽开放大学,安徽 合肥 230001)
“人类之文明,无文象不生,无文脉不传。”中国历史悠久,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的位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顾名思义首先是“非物质性”,意为不能脱离人而独立存在,其次是“遗产”,即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同于近期的某种创造。[1]发端于历史和社会学领域的口述史,能有效地挖掘非遗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内在联系,展现非遗文化发生的原始情境以及当下发展的现实情况。
一、非遗口述史的价值定位
口述史是访谈者对受访者个人记忆的挖掘和记录。个人记忆包含着广义的人文资源,不但可以提供人类生活的信息,而且可以提供公共历史信息,本身即是可被认知、勘探、确认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的践行者冯骥才曾经指出:“对于保存于一代一代传承人记忆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只有将记忆转化为文字,才可以永久保存。”非遗口述史的价值,不仅在于传承人独特的人生经历,还在于每一个个体都是时间与空间、社会与历史的结点。
(一)口述史对非遗保护的意义
非遗的存在依靠传承主体(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实际参与,非遗的传承必须保持内在的活态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非遗传承人相继逝去,人亡歌息,人去史佚,许多第一手资料和技艺不复存在。抢救日渐凋敝的文化遗存,是当前紧迫的任务,广泛用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口述史方法,便顺理成章地被拿过来,成为非遗保护最得力且必不可少的工具型手段。[2]加大非遗口述史研究的力度,对非遗进行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口述史是非遗保护的重要途径
口述史作为一个史学学科,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是以笔录或影音的方式,搜集、整理特定个人、群体或组织的口头回忆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3]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汤普森曾说:“口述史是历史的第一种形式。”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往往依靠口述传承历史,传递社会记忆和生活经验。没有口述史,历史则不完整。非遗口述的现场感、真实感,决定了它与其他历史资料的不同,因为非遗是依托“人”作为文化信息链接、传承的基本载体,以身、口、耳相传作为文化链延续“活态文化”,主要是以记忆、声音、形象作为表现手段。[4]
(三)非遗口述资料类型的多样化
早期口述史研究广泛采用录音方式,少部分采用录像,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口述史访谈中逐渐使用数字录音笔、数字摄像机等器材,通过录音、录像记录,更好地传达非遗文化的语境与在场性,特别对于舞蹈、手工技艺等非遗文化,复刻核心技艺的产生、发展和流变,便于后来人习得技巧、领会要义、传承精神。[5]随着现代信息数据的数字化、数字维护技术、元数据标准与政策等传播技能的普及,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可以通过网络摄像机、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和网络移动应用程序,跨越地理障碍进行“跨时空访谈”,拓展了非遗传承范围。
二、非遗口述史蕴含的哲学要义
历史哲学是关于历史存在与历史认识的哲学探讨。历史哲学的研究,是把历史的具体性复现,从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研究中,复现各民族与各时代的历史。[6]任何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看似个人生命历程的讲述,表达的却是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时代的共同经历和命运。非遗承载着国家、民族的文化生命密码,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在历史、自然、现实的互动中,运动、变化是时间成立的必要条件,也显现出非遗发展的轨迹。
(一)记忆与直觉的融合
传承人既是非遗的贮存、掌握和承载者,又是发展、创新者。口述史是传承人记忆的叙述,表述出来看似是直观的感受,殊不知这种直觉是长期践悟的积累,不是瞬间的偶拾;是长期实践中的体认,不是单纯的冥思遐想,传承人不断学习专业理论,将无意识提升到意识的层面。意识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客观存在的根源上发展起来的初步认识。[7]同时,辅以解说阐释的经验,才得以将记忆中的理解表述出来。对非遗访谈人来说,记忆是个体经验,也是自我认同的形成,包含了以往的传承人所在历史时期的文化,又不断叠加着当代自身的文化。
(二)继承与超越的相关
后一代人从前一代人那里接受的不是本人的遗传,而是物质与文化的遗产,正是基于前一代人已经获得的成果,后一代人从事他们这一代人的创造活动。后一代人总要去超越他们的前辈,历史的发展就存在于这样一个继承与超越的无限关联之中。非遗是一种独特生活的文化形态,由先人为了生计营生而萌生,后人又为了现实生活的需求而传承,皆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创造延续着。辗转至今,作为精神文化财富,更赋予我们将其传承后代的使命,不单纯是为了怀古,而是让我们在分享前人的智慧经验中,更好地谋求发展。[8]
(三)主体经验与主导作用的结合
倘若时光倒流,我们回到童年,这段时光会立即失去刻骨铭心的魅力,还原成与现实中的每一天一样平常的日子。只有在缺席的情况下,过去才到场,才会成为经验。正如胡塞尔所说,思维不是对直接经验的回归。当直接经验成为思维时,那个刺激感官形成感觉的现象已经成为过去。对非遗传承人的访谈中,口述内容难免存在遗忘、不合逻辑、不合常识等情况,访谈者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在采访中尽量做到多访多问:多访是扩大采访的范围,访问更多的人;多问是尽量多提问题,激发受访者更多的回忆。
(四)个体孤独感的疏离
人一诞生,即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生活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历史对于每一个个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个体面对的社会,身处其间的生活境遇,都不是突发奇想的结果,而是基于人类物质和精神的实践活动,经年累月不断积累而来的成果。这个成果,可以体现为一个瓷杯,那是人类多年在陶器实践中得到的器具,可以体现为一首桐城歌谣,那是人们于日常生活与劳作过程中生发,是安徽地域桐城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人类具有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中,每一个个体都不是作为孤独的个体。每一个个体都是生活在前人实践活动的历史之中,前人把自己的时间凝结在生产力上,凝结在物质和精神产品上,[9]并通过作为后代的我们,将他们的实践活动发展下去。因此,个体单一,但不孤独。
三、历史哲学中的非遗口述史
非遗保护的关键就是保护传承人,非遗传承人是指在非遗传承过程中,参与非遗产品制作、表演等传承活动,并愿意将自己的高超技艺或技能,传授给政府指定人群的自然人或群体。一个民族的知识类、技能类文化遗产,主要是通过他们世代相承,非遗传承人是国家的文化瑰宝。[10]出于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需要、保护传承人的需要,冯骥才在《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序言中指出,“口述史便应运而生,派上用场;再没有一种方法更适合挖掘个人的记忆,记录个人的经验,并把这些无形的、不确定的内容,转化为确切有形和可靠的记录”。 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引入,将丰富非遗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角,促进非遗的保护传承和传播。口述史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历史、艺术、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还有助于我们了解传统审美、传统文化、传统科技,同时可以为我们创造新艺术、新文学、新工艺、新科技提供重要参考。
(一)历史的关联性
口述史是一种人格化的历史,不仅有历史的细节,而且有讲述者的体验、观点与情感。中国古人强调“知人论世”,意为个人的生平经历暗藏了社会历史背景的诸多重要信息。非遗受访人一般是非遗传承人,在涉足的领域能力突出,发挥着独有的创造性。例如安徽黄山的工艺美术大师甘而可,是徽州漆器糅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长期致力于精品漆器的创作,成功恢复了濒临失传的犀皮漆制作工艺,并赋予其崭新的面貌呈现于世。采访中他回忆年轻时是工艺厂的木工,木工的专业是刻漆,就此开始接触漆器。他做工十年,接着进入屯溪原木社,开始做木模,木模做工要求精密,要考虑很多细节。刻漆与木模的工作经历,为他日后做漆器打下了基础。甘而可指出,徽州是人杰地灵的人文故土,从唐宋以来,局较为稳定,环境相对封闭,当地的社会风俗、生活方式、文化礼仪、工艺技术保留得较好。浓郁的文化氛围,有利于手工艺从业者的成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奠定了手工艺底蕴。[11]在漆器创作上,甘而可始终扎根于徽派漆艺传统,工艺与原料恪守天然大漆的古法制作方法,守护并传承着以精、雅为风貌的徽派漆艺,同时探寻继续深化发展的可能性,将徽州特色的犀皮漆、推光漆、漆砂砚及精细漆面纹饰推向新高度。[12]非遗传承人甘而可在口述史中讲述个人生平,这一过程包含着非遗行业的跨界端口、手工技术的精准切面、与社会各方面的互动,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段的镜像;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内心丰富程度不一;每个人追索往事的能力不同,回忆内容多少不等,兼之表达意愿有别,年龄、性别、学养、行业状况、采访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使得受访人的陈述资料,就是一份独一无二的个人档案。结合非遗传承人口述史中的非遗特质、行业技能、社会历史,链接出地域、行业、社会的网络,便可获得丰富立体的非遗发展态势。当口述内容被记录下来,成为文字、音频、视频,抽象的符号便有了跳动的灵魂,个人的生命历程对接到宏大的历史中,会让更多的人产生共鸣。
(二)艺术的表达与解释的叙述
口述史就像是一座桥,搭建在非遗传承主体(社区、群体和个人)和社会之间,增进互相理解与认同。史学是一门文学性很强的艺术,如何传达知识和影响,取决于研究者的写作能力及其创造叙述、吸引读者的能力。[13]口述史研究者在将感觉经验转化为想象的过程中,需要贴近受访者的心灵,生动描绘出传承人的生活侧面,写实刻画出手工技艺的流程,围绕传承人师承、授徒、技艺介绍、工艺变迁、技巧心得、所获成就,传达出非遗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唤起传承人的技艺,根本上是为了向观众、听众“倾诉”,令其印象深刻。研究者了解报道一个非遗项目,不仅是学术上的深入,也是将自己交付出去,让自己的思想设身处地、将心比心重续传承人的思想,于理解与共鸣基础上,洞察入微地进行分析和解释。对山东高密扑灰年画省级传承人王树花,访谈者持续进行了一周访谈。了解到王树花挚爱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扑灰年画,全身心延续着历史记忆,她继承、恢复了170多种传统扑灰年画题材,她坚持“抹画子”风格,用色上大笔狂涂,恣意汪洋,坦言自己“不可能用别的技法,别的技法也不会”。经过对王树花的田野调查,访谈者认为由于生产、家务、生育的繁重负担,占据了女性的绝大部分精力,许多女性不得不将手艺搁置一旁,才情抛于脑后。在成千上万民间文化女性传承人中,王树花是幸运的,她在婆家的支持下,画业得以维持。伴随国家推动非遗保护,当地政府开始重视传承人,扑灰年画迎来了发展机遇。王树花相继参加了一些展览和大赛,获得赞誉和认可,传承扑灰年画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王树花由一个闭门抹画扑灰年画的艺人,成为名声在外的非遗传承人,国内外学者、行业专家慕名而来,在她的画室交流切磋。访谈者发现,在近4万字毛坯稿中,王树花45次提到“艺术”,并确定地指出使用的染边、点眼、盖花等特殊技法,造就了扑灰年画独有的风格,这本身就是艺术。由此访谈者总结出王树花对于传承的扑灰年画,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 已经从一位农家妇女转变为富有文化自觉性的传承人。[14]扑灰画法已经成了她的艺术生命,她也将传承扑灰年画内化为一种使命,这与农耕社会作为副业贴补家用的年画生产观念迥然有别。从传承范畴看,非遗主要分布在表演艺术、传统工艺技术和传统节日仪式三大领域,非遗口述内容的叙述解释中,包含科学、历史的成分。科学解释的本质是逻辑论证,而历史解释在本质上是修辞。逻辑关心的是必然性的推理、真伪的判断,而修辞作为以说服人为目的的论辩技术,则要基于常理的可能性,基于论辩的原则。[15]
非遗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是华夏儿女确认自我身份的重要方式。从“过去”数千年文化演进到“现在”,只有通过代代延续的非遗,在民间“口传”、技艺“身授”的活态文化中,去认识中国及中国的历史,通过中国的语言、习俗、神话传说、表演、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释叙述,才能回答子孙后代“有关中国人”的问题。做好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不仅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让中华文化多姿多彩地传承下去,而且满足了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让老百姓生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一个发达的国家,应当既有高度的现代文明,又让民众多选择地享受传统文化,达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响。在非遗的文化艺术天地里,细观慢品,仿佛能看见令人心驰神往的远古家园,听到中华先民的浅吟低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