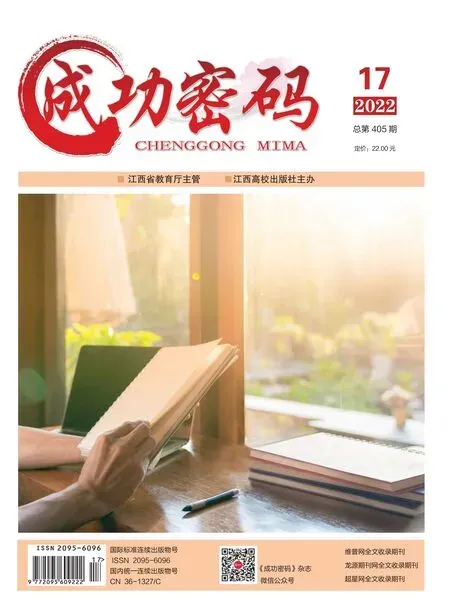《诗经》中的中华文化基因
2022-03-18康乐阗江西省景德镇市二十六中
◎康乐阗(江西省景德镇市二十六中)
余翡翠(江西省景德镇市十三中学)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的起点,蕴含了中华文化的DNA。其中既有族群之和、上下之和、家国之和、人与自然和谐的和谐观,也有不语“怪力乱神”、关爱下层、珍爱和平的文明观,还有敢爱敢恨、反抗剥削的自由观,更有体现矢志不渝救国之志、慷慨乐观爱国之情的爱国观。这些人文思想对广大中学生弘扬中国文化、提升道德素养、构建和谐社会、坚定文化自信等具有重要意义。
不知《诗经》,不足以言吾国文化之流变;不知《诗经》,不足以言中华文化之根源。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外来文化、网络文化等所谓“流行文化”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少中学生在文化素养方面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还不同程度地出现浮躁、自私、好逸恶劳等不良心态。让他们在本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成长,健全人格、培育民族精神非常有必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中的和谐、文明、自由、爱国等观念,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影子。
一、《诗经》中的和谐观
讲究和谐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处在集体中,我们讲究团结协作;面对自然时,我们得顺应自然规律。这种和谐观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诗经》当中既有族群之和,也有上下之和。有家国之和,也有人与自然的和谐。
族群之间的和谐。西周时期,周人力量相对弱小,要统一天下需要运用智慧。那个时代的人,普遍认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一个族群的人,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不亲。针对这种情况,周贵族用缔结婚姻的方式凝聚众多异性族群,周家的女儿、诸侯的女儿要嫁到不同姓氏的人群去。《关雎》就是在诸侯婚礼的现场,奏响的迎亲之曲。“寤寐求之”“辗转反侧”写出了君子求得淑女的不易,“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描绘出了婚礼场面的盛大。诗歌中透露出对这一对新人的美好祝福,对他们未来美满生活的期盼。为何《关雎》要放在国风的第一篇?因为婚姻在周代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十分重要。《周易》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仍影响着中国人对婚姻家庭的态度。了解这一点,对培养中学生正确的爱情观和婚姻观有着重要意义。
上下的和谐。西周封邦建国,诸侯国的周人人数少,国郊之外“野”的压力威胁又大,所以内部必须团结。周人用什么办法来维系、促进和表现内部的和谐呢?方式之一,就是宴饮。周时崇尚礼乐文化,礼乐文化倡导社会个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通过“有序”的外在表现,达到“崇和”的最终要旨。《礼记·乐记》中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要讲究尊卑之别,但是这样久了,必然就会生分,会离心离德。宴饮中的典礼,就是要消除这种阶级的因素。在“雅”中有大量的宴饮诗。比如《小雅》中的《伐木》,歌唱宴饮,就是为了表现王的慷慨,同时号召贵族慷慨地对待自己的下属和民众,这样民众才能跟着你走。所有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分子,即使是居上位者也要体恤下属,和大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听取大家的意见。
家国之和。某些特殊时刻,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就是无法两全。在《诗经》中,会用隆重的典礼以及歌唱来肯定社会成员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以情感的方式抚平小家受伤的心理。《周南·卷耳》第一章,讲的是一位女子拎着一个浅筐来采采卷耳,她思念自己在外为国事忙碌不归的丈夫。从第二章到全诗结束,诗篇的抒情主体变成了男人。男子怀念妻子,怀念故乡。即使山路曲折高险,即使马累得疲惫至极,也想登高上山巅去远眺故乡。在希望落空之后,只能借酒消愁。这首诗用演出的方式,表现那些为国家奔波的人的家庭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中的感情,并借此向做出牺牲的那些人表达高度的敬意,对他们进行精神的补偿。家是国,国是家。就正如当下,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的不眠不休、坚守岗位,社会对医务人员的高度赞誉,也正是家国之和的体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诗经》中众多的诗篇,都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桃夭》中“灼灼其华”“有蕡其实”“其叶蓁蓁”,就是借桃树的开花、结果、长叶,象征新娘嫁入夫家后,给整个家庭带来的幸福。农事诗《七月》描绘了百姓应和着自然的节律,在流转时光的旋律中辛勤而老练地劳作着,其中有劳作的艰辛,也有收获的喜悦。诗篇表现了农耕文化人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把握和自信。人们从大自然中获得生活的资料,而不是追求“财富”的观念去榨取自然的资源。“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有意识地爱护环境、顺应自然规律,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诗经》中的文明观
中外文化差异巨大,其实从文化的源头就能追溯。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创生、发祥期的文学相比,《诗经》是现实的人间,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另外,“国风”是世界范围内最早将文学的触角深入到社会下层小民生活的。而面对战争,《诗经》表现的是对和平的珍爱,对战争杀伐的厌弃。
不语“怪力乱神”的文明观。从内容上来说,《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颂”是祭神诗,是献给神灵的歌。但这里的崇拜神灵并不是崇拜鬼神,而是崇拜那些有德行的人,或者弘扬那些有德行、有功绩的人的价值。看《周颂》的颂歌会发现,周人献歌给后稷,是因为他为天下人提供了粮食;周人献歌给公刘,是因为他率领周人重新回到农业文明的轨道上来。传说,周这个部族曾经随着夏朝的衰弱“自窜戎狄”,就是窜到戎狄之间变成野蛮人,是公刘把他们带回来,重新回到农耕文明的生活中来。而周人祭奠周文王,是感谢他带领国家走向强盛,而且获得天命。与外国不同,中国一直有宗祠的概念,里面供奉的就是逝去的先灵,祭祀时以此告诫子孙后代,不可辱没祖上的荣光。这种文明观,是《诗经》一直传承下来的。
关注下层的文明观。《诗经》在表现贵族生活的同时,也以大量的“国风”篇章歌唱了胼手胝足的小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国风”是世界范围内,最早将文学的触角深入到社会下层小民生活的。为什么如此呢?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为,王朝兴衰的主导权在上天。上天是否对王朝和君主的作为满意,主要是听百姓的声音。他们认为百姓的歌声会像风一样传达给上天,老天根据歌的内容,判断把统治王朝的大权交到谁的手上。《卫风·氓》中的桑蚕之女,并不是周人,而是与“国人”相对的野外之民。诗篇对这位桑蚕之女婚姻生活的不幸,给予了高度的同情。《邶风·式微》则写出了受奴役者的非人处境,天黑了也不能回家,只能挣扎在露水和黄泥之中。他们的愤懑并没有被掩盖,而是通过“采诗观风”的形式,留在了《诗经》之中。
珍爱和平,厌弃杀伐的文明观。《诗经》中有许多的战争诗,或歌之于遣将出征的场合,或唱之于班师还朝的庆典。《召南·殷其雷》就是一首送别的篇章,充满了眷恋之情。而《小雅·采薇》则表达了将士归来之际的伤感情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今昔的强烈对比,令人不觉慨然。在《诗经》中,无论是出师,还是还朝,战争题材的诗篇都很少出现大段的血光杀伐的描述,这和中华民族对于战争的观念有关。人们走上战场,与其说是去创造杀伐的英雄业绩,不如说是不得已捍卫自己热爱的和平生活。这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中国依然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诗经》中的自由观
林语堂先生曾说:“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对自由的追求,可谓是人们的一种天性,我们的先民也不例外。《诗经》当中,就表达了敢爱敢恨和反抗剥削的自由观。
敢爱敢恨的自由观。“国风”本来叫“邦风”,因为要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邦风”就改成“国风”了。实际上,准确来说,“十五国风”是十五个地区,分别是: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郑是指今天郑州及其东南到南阳盆地一片。中国人奉行周礼,男女结合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郑这个地方传统的周文化不是很发达,所以保留了很多古老的风俗,并没有那么多禁忌。比如为了繁殖后代,国家允许适龄的男子和女子们在春天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去自由相会。在《郑风》中,大部分恋爱诗都是女子追求男子。《褰裳》开篇“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说的是女孩看上了男孩,就对他说,你如果心里有我,我就撩起裙子涉过溱水去找你,一个泼辣大胆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但这并不是卑微的求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女孩下了最后通牒,你看不上我,难道还没有其他人了?狂啊,你这傻小子。诗篇情绪表达直白畅快,如竹筒倒豆,透露出一种敢爱敢恨的自由气息。这就是我们民族年轻的时候所具有的开朗、热情、大胆和奔放,古老的风俗中洋溢着活泼的生命热情。
反抗剥削的自由观。除了描写婚恋生活,《诗经》中还有许多描写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极其反抗情绪的诗篇。《魏风·伐檀》写的是河边上的一群伐木劳动者,对于不劳而食的“君子”你一言我一语的冷嘲怒骂。“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不栽秧不割稻,凭什么千捆万捆往家里搬?不上山不打猎,凭什么家里满院挂猪獾?从诗篇中可见,人们对于现实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并且对这种剥削不是逆来顺受,而是极为不满。“不稼不穑”的剥削越加重,农民的反抗越强烈。《魏风·硕鼠》中用“硕鼠”比喻剥削阶级,非常恰当地揭示出阶级的本质。“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农民发出这样的诅咒,并决心逃亡,可见剥削已经残酷到使农民活不下去的程度了。他们渴望能去到一片没有剥削、自由自在的乐土。这种反抗剥削的自由观,经过历史的发酵,在浸透了农民的血泪之后,最终凝结成那一句呐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四、《诗经》中的爱国观
在中华民族5 000 多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近代中国之所以能从列强的桎梏中摆脱,离不开先贤的舍生忘死。“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是他们在本没有路的世界,带领人们踏出了一条血路。这种爱国之情,在《诗经》中也有体现。
矢志不渝的救国之志。《鄘风·载驰》写的是许穆夫人的故事。春秋时期,从太行山一带南下的狄,击溃了许穆夫人的母国卫国,卫几乎亡国。卫遭难后,是齐桓公、宋桓公出手援救,并帮助他们修了新的都城安顿下来。在祖国遭受了祸难、风雨飘摇的危亡时刻,许穆夫人毅然返卫,吊唁卫君。从“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可以看出,许穆夫人是提出了向大邦求救的主张的,但却被无血性、无远见的卫国大夫们否定。许穆夫人在忧愤之际写下了这首诗。“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閟?”在这连续的反问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有识有胆的爱国诗人,有人评价“许穆夫人的行止,固已贻愧须眉,其诗亦迥出流辈之上”。
慷慨乐观的爱国之情。《诗经》中有许多战争诗,充满战斗豪情和乐观精神。《秦风·无衣》就是一首秦国的军中战歌。“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在战争来临之时,我们是同袍、同泽、同裳的兄弟,我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这是一种在战争中舍生忘死的精神。我们仿佛能看见严阵以待的将士们,一身英武之气,面对即将来临的战争,毫无畏惧,为国而战。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诗经》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读一读《诗经》,才能明白中华文化的源头是怎样的,才能清楚古今的一脉相承,才能更了解我们自己的民族。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对《诗经》进行专题梳理。在引导学生学习相同主题下的不同诗歌后,选择合适的角度对学生进行提问,让他们通过思考和讨论的方式,明白这些诗歌的异同。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发散思维,积极联系身边的生活现象,思考诗经中的文化与现今文化的关系,以此培育学生的文化DNA。我们相信,《诗经》中的智慧和先哲风范,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全面发展能力,激发学生感于天地万物而胸怀万千气象的生命情怀,使他们在家庭、社会与国家的命运体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