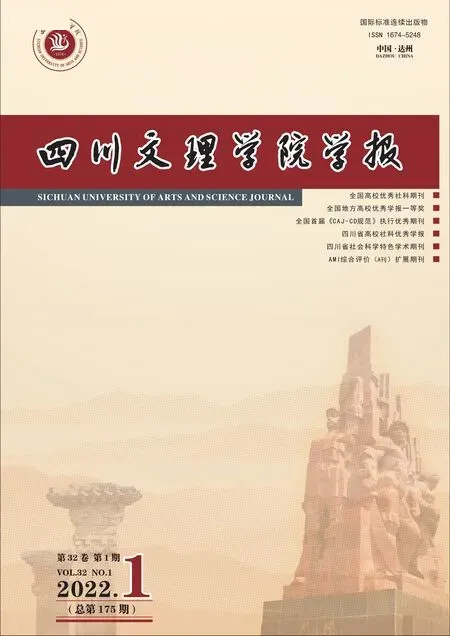论元代陈绎曾《文荃》的赋学思想
2022-03-17温沁
温 沁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沙坪坝 401331)
关于陈绎曾的《文荃》的赋学研究并不多,但其影响却是颇为深远的,许结先生的《汉赋“象体”论》[1]便是对陈氏《文荃》中的赋学思想的深度解析。
在陈绎曾《文荃》中对赋体有专门的论述,赋这一体裁经历了汉赋的鼎盛、唐律赋的变体、宋文赋的新格,至元代体式上已较少有新的创制,正如清代王芑孙云“诗盛于唐,赋亦盛于唐”,[2]376也就是说赋自唐已众体皆备。另外由于唐代以来以诗赋取士的影响,赋体(律赋)创作愈发趋于规范化,愈加需要有专门的文本对前代的赋体进行总结而用于指导元代赋体的创作,陈绎曾的《文荃》就在此情况下产生。从两个角度来看,元代对古赋尤为重视。一是出于辨体意识,元代文人以古赋为尊尚,元代祝尧《古赋辨体》即明确以“祖骚宗汉”为宗旨;二是出于考赋的历史经验,唐代虽以律赋取士,但至晚唐流弊渐显,至宋或以律赋取士,或以经义策士,代有轮替,其中原因虽多,但其中一主要原因便是律赋过于拘限士子才情,不便于考察士人才学。因此元代统治者有鉴于此,整个元代的科举乃回复到以考楚汉古赋为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文荃》中主要讨论的也多限于古赋创作。《文荃》中的“赋谱”一节陈绎曾按时代将前代的赋划分为三个部分:楚赋谱、汉赋谱、唐赋附说,每个部分又按照法、体、制、式、格五种特点进行分析,其中所论及的古赋创作技巧尤多,且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一、文章写作的两个枢纽
(一)养气
陈绎曾在序中首先思考了文的价值意义,《文荃序》言:“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三代以上明于礼乐刑政之中,三代以下明于《诗》《书》《易》《春秋》之策”。[3]407文章的意义在于,它是理的精华的呈现,是用以明道的载体;赋也好,文也好,不应仅注重文辞的华美而导致“以辞害志”,著文的目的在于表现个人的情志,故而,作文之道首先不在于对具体技巧的探讨,而应以作者的修养为关键。因此,陈氏在《文荃》第一章所论述的即是“养气法”,包含了“澄神”“养气”“立本”“清识”“定志”[3]413-412五个方面的修炼,既涉及具体的作文之法,也包含个人修养的培养。如“立本”与“清识”论,“立本”强调对文献的学习,其中既有传统的经书、子书、史书,也纳入了医书、器物书、草木虫鱼书等实用性的书籍,当然,针对不同类型的书,陈氏有相应的读书方法,其中需要专精的仍是经典著述。中国古代学者谈论文学创作,极为强调回溯经典的重要,诚如刘勰言“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4]16经典的价值一方面体现为雅正的文辞,另一方面则是其中蕴含的圣人品格、治国智慧,只有以经典陶冶性情,才能创作出具有典范意义的文章。
同时,在学习经典之外,还需“清识”,包括精究经典的“天理”;穷究眼前事物的“物理”;以己心度量他人他事他物的“事理”;“识自家神以照彼神”[3]420的“神理”四个方面,究其内涵不外乎是朱熹格物穷理理论的再阐释,朱熹便认为,格物的途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阅读书籍、接触事物、道德实践。而陈氏之论最可贵的在于,其将书本知识与自身体物结合起来,并突出实践的作用,所谓“眼前物理须一一就眼前穷究,不可专倚书籍”。[3]419马克思主义哲学讲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来看,汉大赋多宫殿苑囿、祭祀游猎题材,其原因之一即为汉大赋作者多为宫廷赋家,“赋家跟皇帝出去一趟,先要把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回来后再用辞藻描绘出来”,[5]《汉书》中即记载了扬雄扈从汉成帝游甘泉宫后作《甘泉赋》的史实。
“养气法”在《古文谱》章提出,似乎是针对古文而言,但从之后关于赋体创作的具体论述来看,此说在全书又起着纲领性的作用。试观陈氏之言,论楚赋法:“先清神沉思,将题目中合说事物,一一瞭然在心中、目中……取出喜怒哀乐爱恶欲之真情”。[3]463按陈氏之说,楚赋的创作以情为本,此情是从喜怒哀乐中提炼升华而达到的至情,再将其与理交融。从诗赋源流分析,赋本自诗出,班固言:“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即赋也具有与《诗经》相同的政教功能。换言之,楚赋在创作动机上也与诗歌相仿,需要根源于创作者情感的生发。所谓“至精而后阐其妙, 至变而后通其数”,[4]495对题目的详尽考究,在考场之上方可得心应手、胸有成竹,从而创作出合乎规范的文章,因而可以看出陈绎曾对审题的重视。
(二)识题
在陈绎曾看来,写文章,审题的重要性仅次于“养气”,故将“识题”放法在“养气法”之后进行阐述。
陈绎曾之识题分为三个层次:其一虚实,含虚题、实题两类;其二抱题,含开题、合题、超题、引题、张题、蹙题等十种;其三断题,分推鞠、磨勘、拟断、处置、详审五种。陈绎曾认为文章写作,第一要分清文体的虚实问题,古文与时文有不同的写法程式,“古文一主于实,实题实做,虚题亦实做,叙事则实叙事,议论则实议是也;时文一主于虚,虚题虚做,实题亦虚做”,[3]422古文创作往往有感而发,有其所指的具体对象,而时文乃揣摩古人口吻,设身处地,发为文章,以俳优之道,抉圣贤之心,钱钟书甚至认为时文“善于体会,妙于想象,故与杂剧传奇相通”,[6]恰恰印证时文以虚为主的特点。
第二则是“抱题”,即如何入题。他列举出开题、合题、超题、引题等近十种方法, 如引题指“先说别事, 忽入题中”;[3]423摘题 “摘取题中紧切要精者”,[3]423有选择性的撷取材料,选取最切合题目的景意事情之一,详加说明;张题、蹙题做法相反,张题“张而大之”、蹙题“蹙而小之”,[3]423即小题小做,大题大做,可见其对入题方式的精细推敲。
第三,对题目中的细节之处要仔细考究,也就是“断题”。在这里, 陈绎曾“以题目作考功问罪之人, 一一磨勘分明”,[3]426把写作酝酿的环节带入到审问罪犯的情景中。先要“推鞠”,爬梳题目当中景意事情的来踪去处,明确题目的本质含义, 需要注意与题相关的旁支末节并借助自己的见闻加以判断;要认真挖掘题中非显现的内容,明辨其真假之处,以求准确;接着“磨勘”,即推敲前面的论述是否有矛盾漏洞之处;再依据人情、天理、典故、格言等下断语,或“明正功罪”或“赦过宥罪”;[3]425最后,还要依据文献资料,详细审查人名、地名、岁月、宫室等是否有不符实际之处,一一确认之后,便可以运意下笔了。
对题目的详尽考究,正是为了在考场之上可以得心应手,创作出合乎规范的文章,这和他上文中所讲的立意法相似。立意时要仔细体察,慎加裁择,这也就是所谓的“至精而后阐其妙, 至变而后通其数”,[4]495可看出陈绎曾对审题的重视。
二、楚汉唐赋创作论
(一)楚赋论
陈氏对于赋体创作论并不是独立成篇的叙述,而是充融于各谱的叙述之间。对于赋体的创作,陈绎曾主要从法、体、制、式四点进行阐述。所谓“法”,即赋创作的方法,“体”是赋体的体制,“制”是赋体的具体规范,“式”则是赋体的句式和语式。
从楚赋来看,其“法”总言之“以情为本,以理辅之”,[3]463显然陈绎曾对楚赋的特征有明确的认识,在他看来,楚赋与汉赋是不同的,一是“以情为本”,一是“以事物为实”。[3]472即各自侧重于情理和事理的表现,但彼此又不是截然分开的。陈绎曾认为楚赋的创作要情理事三者有机融合,而要这三者同时发挥最好的作用,便需要创作主体的实践经验和才思,“以身体之,则情真;以意使之,则物活;以理释之,则事超情”。[3]463这带有明显的方法论的叙述,但这种方法又不是具体的技巧论,而是上升到一种带有感悟式理性的总论。如强调“情真”就要做到切己的亲身体验。写“物”也不是纯然的堆垛,而是凭主意驱遣,这样才能使之鲜活灵动起来。这实际不脱离于古赋的比、兴之义。
从“体”的角度,陈绎曾以屈原《离骚》为楚赋祖,认为宋玉及之后模仿屈原赋体的创作已经没有屈原的浑全,今后的创作者“只熟观屈原诸作,自然精古”,[3]464显然此处的论“体”或辨“体”仍带有范示的作用和意义。也即是说其并不在于要严格区分楚赋与汉赋,甚至唐律赋的差异,而其所树之“体”乃在于举崇本赋谱系列中的典范体制。因此陈绎曾在“楚赋谱”体类给出了楚赋创作的典范《离骚》《远游》以及《九章》,认为这十一篇已经包含了楚赋体制的各种变化,这依旧带有创作论的意义。
当然,历代诗赋文选多选楚辞《九歌》,但陈绎曾却并未将《九歌》列作“楚赋谱”的典范作品,这恐怕是与陈绎曾对楚辞体总体特征的把握相关的。前述“楚赋谱”类“以情为本”,而《九歌》之作,虽不乏情辞,然却滥于祭祀陈词,算不上因情兴起的即事即情之篇。王逸章句谓:“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讬之以讽谏”。[7]55也就是说,《九歌》之作在本义上是与南方祭祀文化密切相关的,其中虽有“讬之以讽谏”的成份,但却明显不同于直抒其情的《离骚》《远游》《九章》诸篇。陈氏在此“体”是推崇的情辞灿然之作。
从“制”的角度,陈绎曾将楚赋创作分为三个部分:起端、铺叙和结尾。这有点同于近代论文的体制篇章结构,其着眼点仍在于赋作的整体造制特征。在起端,包含了原本、叙事、抒情、设事、冒题、破题[3]464-465等情况;铺叙则可抒情、况物、序事、论事、论理、比物、用事、少歌;[3]465-466结尾也可述意、论事、设事、抒情、论理、乱辞。[3]466-467对每一结构部分如何来展开描写,陈氏列举虽简,然作用和意义颇深,此实可视为其后论八股制义技法之先驱,无论是开篇、中间及结尾部分,每一种书写方式都可见其对诸赋创作经验的细心总结。中间部分以“铺叙”概之,正是体现赋体“铺采摛文”[4]134的主要特征。其中所列“抒情、况物、序事、论事”等不是分类,而是对此部分书写方法的陈示。在铺叙部分,其认为亦可用“少歌”的写法,“少歌”似与“乱辞”功能相同,在后世的赋作中多置于辞章之末。然在《九章》之《抽思》篇中既有少歌亦有乱辞。“少歌”的作用正同庄子散文的重言或巵言的功能。洪兴祖《楚辞补注》于“少歌”后引王逸注云:“小唫讴谣,以乐志也。少,一作小。”补曰:少,矢照切。荀子曰:其小歌也。注云:“此下一章,即其反辞,总论前意,反复说之也。此章有少歌,有倡,有乱。少歌之不足,则又发其意而为倡。独倡而无与和也,则总理一赋之终,以为乱辞云尔”。[7]193
从式的角度,陈绎曾认为楚赋主要有六言长句兮字式、四言兮字式、六字短句式和杂言式,且以六言长句为正式,因其可增删句中字,而变为三四五七八九言。对于其中六字短句式,陈绎曾认为“此本题歌句法,后人有用为赋者,非屈原之式也”。[3]470所谓“题歌”,即是诗歌,六言句式的诗歌最早出自《诗经》,刘勰言:“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4]68按陈氏分析该句式的特点:“正上一单字,次两字双,中兮字,下二字双”。[3]471如果将楚辞中的语气助词“兮”去掉,很容易变为五言、七言诗歌,如《招魂》:“献岁发春兮汨南征,菉蘋齐叶兮白芷生。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7]213《湘君》:“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7]60去掉句中兮字,便成五、七言诗。[8]
从后世的拟骚作品来看,后人所模仿的楚辞六言句式赋作,虽有其形,但实际上又有所变化。如初唐时期,卢照邻创作的《悲才难》:虽有晏婴、子产,将顿伏于闾巷;虽有冉求、季路,且耕牧于田园。彼寻常之才子,又焉可以胜言?命鸾凤兮逐雀,驱龙骥兮捕鼠。
(二)汉赋谱论
前文已论及,汉赋更多的侧重于事物的表现,故陈绎曾讲“事事物物,必须造极,处事欲巧,造语贵拙”。[3]473赋的特征即表现为对物象的连缀铺写,刘勰言“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4]134而汉赋则将其发扬到极致,因而司马相如言作赋之法除“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外,赋作者应当“苞括宇宙,总览人物”,[9]实已点明汉赋取材的物象来源广泛。汉赋的创作基础建立在作者对现实的体察上,赋中的大量物象来源于创作者亲自观察、体验过的事物,只有做到对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宫殿楼台、天文地理等物象了然于心,才能在作赋时精心选取和安排以达到体物写志、蔚似雕画的特征。“《楚辞》尚神理,汉赋尚事实”,[10]436尽管汉赋中常采用虚构、夸饰的手法来对物象进行铺排,但这些物象并非作者凭空想象而来,而是基于创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再创造,许结先生便认为汉赋特别是大赋作品是“尊重客观现实的一种人工修饰美”,[11]也即刘熙载所言“赋取穷物之变”,[10]461作者想象的基础必是客观世界中的事物。
从体式角度,陈绎曾将汉赋分为大中小三体,与传统的按篇幅大小或题材主旨大小分法比较而言,其专设中体,似乎是对汉赋分类的进一步思考。陈氏认为,“汉赋短篇以格为主,中篇以式为主,大篇以制为主”,[3]483显然,陈氏的划分依旧着眼的是赋的创作技法,中赋和大赋强调文章结构、表现手法等,而小赋由于篇幅限制,故讲求语言风格。郭建勋便认为,就赋法而言,小赋较大赋更为纤巧细密,以清丽为胜。[12]但推敲陈氏之分法,中赋即为魏晋时期咏物抒情之骈赋。从陈氏列举的八篇中体典范作品看,《月赋》《雪赋》《赭白马赋》《鹦鹉赋》《登楼赋》《啸赋》六篇均为魏晋抒情赋,另两篇《风赋》《长门赋》虽作于汉代,但其创作实际已开骈赋先河,诚如清人林联桂言:“骈赋体,骈四骊六之谓也。此格目自屈宋、相如略开其端后,遂有全用比偶者,浸淫至于六朝,绚烂极矣”;[13]其次,陈氏所言“汉赋式”包括设问、设事、六言、四六言、四言、散韵语,[3]484六四言特为骈赋之显著特征,即便以《风赋》为例,结构上设君臣问答,语言上句式多样,既有三言,也有四言、五言、六言,但仍以四言为主。
从汉赋制的角度,陈绎曾总结汉赋为三部分:起端、铺叙、结尾。如前所说,汉赋以事物的铺陈为特征,故陈绎曾对此思考颇深,其总结的汉赋体物方法包括实体、虚体、象体、比体、量体、连体、影体七种。[3]482当然各方法不是截然分开,而要依具体情境综合使用,如实体与虚体之法,实体是可观可感之物,虚体则如声色长短动静之类,在创作中,实体易描,而虚体难状,如刘熙载言:“赋以象物,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10]462故在实际创作中往往以实写虚。
(三)唐赋附说
论及唐古赋,陈绎曾认为“汉赋至齐梁而大坏”,[3]483唐人有意扭转这一赋风,而“加之以气骨,尚之以风骚,间之以班马”,[3]484其创作实践与齐梁时期相比,已称得上有唐一代的赋体气象。但陈绎曾又认为,唐古赋“楚汉不分,古今相杂,谓之自成一家则可追配古人,未可也”,[3]484在陈绎曾看来,唐古赋的成就还难以达到与楚汉赋并驾齐驱的地位,而元代另一位批评者祝尧对唐古赋的批判则更为激烈,其《古赋辨体》云:“雕虫道丧,颓波横流;光芒气焰,埋鏟晦蚀。风俗不古,风骚不今”。[14]354-355当然,对唐赋的成就评价过低的观点发展到明代甚至出现“唐无赋”[15]之论。但从整个赋史观照,唐赋踵武前人又创制颇多,体式上有新文赋、律赋、俗赋的产生,内容上赋书写题材的扩大等,这些都对后来各类赋体的发展多有建树,正如王芑孙对唐赋的评价:“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之支流”。[2]376陈绎曾对唐代古赋的评价不高,“难以谱定”的缘由,一方面由于唐代科举以律赋为主,古赋创作自然式微,故“律盛古衰”;另一方面,则是此时期“祖骚宗汉”之说的影响,以楚汉赋的角度观照唐赋,自然评价较低。
从赋法上看,唐赋“以唐为本,以辞附之”,[3]484这明显有别于楚汉赋以情、以事为主的创作手法。陈绎曾此论依旧着眼于赋的创作技法,认为唐赋的特点在于讲求语言形式技巧。从初唐时期文坛来看,此时期的魏征、令狐棻、王勃等人虽然激烈批判齐梁靡丽文风,认为“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但并非完全否定齐梁时期的文学实践,其目的是重回文章序志言情的传统,即“道”的呈现,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提出的美文标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16]即是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实际上,以四杰为代表的文人在改造齐梁衰弊文风的同时又汲取其营养,其表现之一就在于对齐梁句式的继承,对音律、骈俪的坚持。叶幼明先生评价王勃《思春赋》:“全赋除序言外,本部204句,七言律句114句,五言律句占50句,诗句多,赋句少,也像一首律化的五、七言歌行体诗”,[17]除王勃外,骆宾王《荡子从军赋》、杨炯《庭菊赋》等皆有律化的特征。有学者认为,正因为四杰在实际创作中“包齐梁而薄汉魏,折中其诗学观,从而达到一种文质兼并的文学理论主张”。
从唐赋制上,陈绎曾总结唐古赋制包括五个部分,起端、承接、铺叙、承过、结尾。与楚汉赋制相比,唐古赋篇章结构更为细致,而写法技巧却更规范。起端,只包括破题和冒题两种情况;接着是承接,仅有入题一种情况;然后铺叙,可叙事、议论、用事;再者承过,则可歌咏、用事、议论、序事;最后结尾,或抒情,或议论,或评价优劣,或歌辞。从起端突出破题,到结构上增加入题部分,这种以律赋技法掺入古赋之创作,考其缘由,大约有三:其一,唐代试赋制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李调元言“唐人试赋,极重破题”。[14]22其二,律赋创作较古赋更易,唐宋两朝对律赋技法的总结较为成熟,学者更易模仿,而由易到难,自可精古,李元度即言:“循流以溯源,则由今赋之步武唐人者,神而明之,以渐跻于六朝两汉之韵味”。其三,“望今制奇,参古定法”。[4]522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是时代的折射和反映,因而文学需要随时代的变更而变化。
三、余论
《四库总目》提要称:“《吴兴续志》称绎曾尝著《文筌》《谱论》《科举天阶》,使学者知所向方,人争传录”。[18]1791陈绎曾著《文荃》等书的目的,在于指导学子写出符合场屋规范的应试文章,但从《文荃》的具体论述看,其效果或十分有限。如汉赋制列举“次序事以寓赋辞”的“叙事”一法,虽罗列了正叙、总叙、间叙、引叙、铺叙、略叙、列叙、直叙、婉叙、意叙、平叙[3]478-479计十一种方法,但每条技法下仅有抽象性的解释,缺乏大量鲜活的实例印证,如直叙“依事直叙不施曲折”[3]478与平叙“在直婉之间”,[3]478两种方法相近,如何使举子仅通过概念进行区分,并在写作时具体选用就成了问题,故该书的实际作用或十分有限。因而《四库总目》评价其“体例繁碎,大抵妄生分别,强立名目,殊无精理”[18]1799是恰中肯綮。
从撰述的赋谱角度来看,陈绎曾从科举的需要出发,以律赋为范论古赋创作,适应了元代中叶后考赋的现实需求。其对古赋技法的总结全面而多元,对汉赋长篇大作的教授不乏精心构思与鉴赏领悟,对学赋者有启发模拟之效用,故许结先生认为,“将高超的艺术落实于创作实践,提升了闱场古赋写作示范的理论价值”。[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