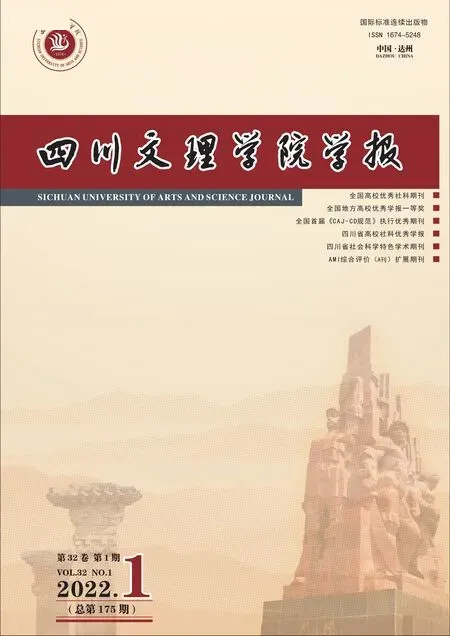寻找焦虑与不安的精神出口
——论蒋兴强小说中的父亲形象
2022-03-17彭辉
彭 辉
(开江县教师进修学校,四川 达州 635000)
一、家庭主角地位式微的理性观照
我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及其建构起的伦理道德体系完备了家族本位制,男权主义下的父亲在一个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和实际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真正代表着家族的实质权利。文学理论与批评将生命苦短、儿女情长视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底色,但作家、作品都绕不过父亲这个形象,这主要基于男性必然是在成为父亲那天开始,才真正意义上具备家庭主角的地位,成为权威、准则和担当的象征。也就是从这一刻起,男性便在生物传承或伦理称呼上有了新的定义,“父亲”成为典型的庄重符号,代表着深富道德、家庭权威,与此同时兼具着家庭重任和亲情关系,更是被纳入文学创作体系,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对父亲形象的描写既有对日常生活的纪实再现,也有对人生、对世界的认知情感。男子在成为父亲后,其形象渐渐从爱情的世界淡出,在家庭的天地里强化,丰富了家庭的权势、规矩和兴衰发展。就读者兴趣而言,是逐步弱化远离,更多地成为旧思想的维护者,新爱情的阻拦者,如《家》中觉新的父亲,《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现代作家张爱玲笔下的“父亲”形象也是软弱、低能、无耻。父亲的地位也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君臣父纲”伦理下的父亲绝对地位持续了数千年,特别是五四运动后,“父亲”随同男性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怀疑、挑战和抨击,其地位与角色被动摇了,更多的是代表着不合时宜的封建家庭伦理,这一趋向对现当代文学创作和评论影响较大,父亲形象也变得更为多元。在老龄化愈来愈明显的今天,身体状况和经济能力日渐弱化的父亲移交了家庭主角地位却背负起了不应承担的责任,家庭和社会伦理关系不断重构,成为新时代父亲的一个特殊现象。蒋兴强便是以冷静客观的视角来塑造父亲形象,给人真实可感而又耳目一新的呈现。
从农耕时代发展到后工业时代,从血气方刚蜕变到年老体衰,文学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更为丰满了。热播电影《你好,李焕英》的经典台词:“打我有记忆起,妈妈就是个中年妇女的样子,所以我总忘记,妈妈曾经也是个花季少女。”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的魅力与伟大也是在成为父亲的父亲后投射出来的,具有典型的生长性和延续性,彰显着在家庭地位中式微后的一种成熟和担当。蒋兴强小说大多指向父亲这一形象,在字里行间探寻着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发生剧烈变化的新时代,伦理文化的变与不变,以及现代人情感心理的衍变与走向,可谓是一个作家的理性担当与思考。如果说现代小说的父亲形象是纨绔、弱化、缺席,体现出儒家伦理的最后挽歌,那蒋兴强笔下的父亲却是地位式微后的担当与辛酸。父亲江长水早年丧妻,勤勤恳恳养儿育女,披星戴月任劳任怨,当子女长大,出息了,有钱了,却为了顾全女儿孝心进城,内心上却是百般别扭,万般难受。当女儿顺丽有苦难时,却在古稀之年,偷偷出去捡垃圾达半年之久,那一沓皱巴巴的、有着汗水和灰尘的辛苦钱,渗透着多少天下父亲对子女道不尽的爱和关怀,而江长水的形象却深刻反映着当前老年人较为普遍的生存现状,这正是蒋兴强的焦虑所在。即便有评论者提出网络文学创作不是焦虑性写作,而是去焦虑化的写作,即不在意是否获得体制和社会理性的认同。[1]但我们依旧不得不承认充分反映社会现状的作品才是真正经典的作品,为我们点亮了心中的灯塔。父亲不再是家庭的主角,父亲在社会交际中渐退,但父亲的形象却更为鲜活起来,成为众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的重要一极,这充分说明理性、睿智和富有良知的作家对这一群体的强烈关注,并影响着广大读者和观众,发挥着文艺作品应有的功能。
二、现代化生活加速下的亲情关系嬗变
在一个充满家国情怀的国度,“亲情”在中国的伦理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渊源,与之相应的亲情文化形成自然有着丰富的现实土壤,而父亲是这一文化的核心要素。父亲既是传统文化的脊梁,也是延续血脉亲情的精魂。谈及亲情,父亲形象不啻为文学创作的核心与抒写家庭亲情的支点,只不过父亲从圆形人物转变为扁形人物,更具真实性、亲近性和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超越了以母爱为主体的亲情价值。就以现当代文学为例,在小说《包氏父子》中,张天翼是一个中国老父亲形象,他为了儿子的成长省吃俭用、委曲求全,最终因儿子“不争气”而幻想破灭,典型地反映了时代特征。冰心笔下的父亲朱衡充满了慈祥、和蔼的性格,处事表现出开明通达的特点,父亲形象有着时代性的改变。“父亲”不再作为“父权”的代名词,不再着意展示父子关系的剑拔弩张,在父子关系的描写上引入民主、平等这样的进步思想。[2]这一变化深刻寓意着亲情关系的变化,其家庭关系、家风传承、感情纠葛也随之发生变化,但都以传统家庭观念为主流。特别是进入后工业文明的现代,人们在尽情分享现代科技带来的日新月异变化时,也意识到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淡化,因而有了对亲情更为强烈的呼唤。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主义的疯狂跟进,金钱至上思想有所抬头,追逐利益最大化成为普世价值,作为家庭主心骨的父亲以及成年的子女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淡化了亲情的培养和维系,为了金钱财富父子反目,三观不同而亲情疏离的现象屡见不鲜。在此背景下,蒋兴强系列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也呈现出多样化走向,如《瓜客》中的刘父嫌阮霞条件差、文化低,使得一桩美满爱情折戟沉沙。《等到天晴》中江月父亲缘于舐犊之情,为女儿的变形爱恋屡屡掩护。《二婚》中的邹父却在女儿离婚的情况下对女婿的关怀备至,指责女儿的不是,心胸不可谓不开阔(均选入蒋兴强中篇小说集《等到天晴》,九州出版社)。
成熟的作家即便是撷取枝叶也能筑成精美无比的艺术品,更能于细微之处彰显家庭亲情的强大张力。蒋兴强生活地域的那些父亲们有着刚毅果敢、吃苦耐劳、富有责任的精神品质,成为达州文艺工作者丰富而深厚的创作源泉,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便体现出大巴山老农的淳朴、慈善和希望。而经历丰富的蒋兴强更是敏锐地感受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父亲的这一形象在悄无声息中发生着巨大转变,用以维持亲情的“孝敬”“责任”“义务”等传统美德在金钱主义、实用主义、利己主义的侵蚀下渐行渐远。作为媒体人并已入花甲之年的他对当前现状是十分焦虑的,为了反映对现代文明进程的担忧和对人性世俗的终极关怀,试图努力通过小说的形式来追问生命意义,来呼唤不可或缺的亲情,为优良传统和文化风尚立法呐喊。小说《隔单》讲述了奶奶去异地带孙,留下爷爷薛亮看家和二儿媳为了私欲,阻止婆婆去陪护公公而阴差阳错导致薛亮死亡的故事。作家借主人公薛亮晚年生活的悲剧困境和贪婪的二儿薛胜夫妇故意将出具给父亲的借条少写一个“0”,变“80000”为“8000”以致父亲薛亮重病索款时当场气晕母亲石琴,洞穿人性被物欲、金钱困扰和绑缚而人心不古、精神溃败的现实。这无疑是源于作家对时代和生活的深切把握以及对薛亮这一父亲形象的专注塑造,才将一个日常的养老、啃老题材写出了新意和深意。另一亲情题材小说《丢失的人》(后简称《丢失》)描绘了老父亲江长水一大家子人平凡而波折的生活,在看似简单的情节中深刻剖析了俗世背后人性、亲情的蚀变,揭示了被金钱吞噬的尘嚣,人与人之间的善良与可信正在离我们渐渐远去,以此呼唤亲情、友情、人性的真实回归。可以说,当人们正感受着这种变化却又无法恰当表达时,蒋兴强便凭借这独特立意为传统亲情招魂,因而得到了读者的青睐和认同。
三、祖孙关系深厚中蕴藏的焦虑与不安
时代的变迁,岁月的增添,父亲最终成为父亲的父亲,扮演和蔼可亲的祖父角色,但其父亲的地位,慈爱的释放却不会因此而改变,反而会在浮躁的时代显得更加厚重,体现出更多的爱与关怀,这几乎成为一种生物演化的轨迹,而隔代的祖孙关系似乎是一个更好的情感和抒写出口。将其放在家庭伦理的传统体系里,我们更能感受到祖孙在生活环境和情感态势方面的独特意义,折射出的心理、道德、伦理、文化成为了文学作品关注的重点对象。纵观中西方文学,祖孙关系的亲密程度往往超越了父子情感,彼此寻找一种基于亲情责任的慰藉,化解那内心深处的焦虑与不安。契诃夫的经典小说《万卡》(又译作《凡卡》)中小主人公给乡下爷爷的写信就深刻集中地体现了这种独特情感,即便没有直接出现刻画爷爷的场景,但读者定然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个爷爷的慈祥,一个老父亲的可爱形象。或许根本无法送达的信是凡卡悲惨命运下对亲情的深情呼吁,更是作者对黑暗制度的猛烈控诉,反映出作家是个体的不安,更是那个社会的不安。同样,丹·布朗在小说《达·芬奇密码》中,将雅克·索尼埃描绘成一名接近完美的祖父,他有着坚强、负责任、正直无私的个性特征。这些良好的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自己的孙女索菲·奈芙,也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让人无形之中领悟到亲情的伟大和力量。从创作心理学来看,作家对父辈的追寻也是对自我亲情意识的追寻,审视自己与父亲在本质上是全然相同的,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而已,父亲角色正是自己观念的折射。就此而言,老作家蒋兴强感受是非常明显的,我、父亲、爷爷成为他小说和散文创作中占据首席的人物,其形神充满了连贯性和交融性,促成了作品的经典特质。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改善与变化丝毫不能改变一个作家对人生人性的追问,新世纪文学产生若干新质,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求索体现为对“我从哪里来”“ 我是谁”“ 我到哪里去”的“存在焦虑”的探讨,并体现于不同题材的作品中,产生了丰厚的创作实绩。[3]寻找生活中的故事是艺术来源的重要路径,就蒋兴强的个人经历来说,他的父亲是爷爷领养,在日常生活中更是把孙子当作命根子,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更是对他做人做事进行了引导。(详见散文《老家那盘青石碾》)从某种角度来看,那正是对蒋氏血脉的继承,家风家规的延续。因而在他的小说中,不遗余力地将祖孙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小说《隔单》里这样写道,“孙子一讲理,老薛便倚老卖老,弄得孙子不得不反像将就小孩一样,妥协道:‘好好好,重来重来。’而站在一旁的石琴,常常捧腹大笑:‘天呢,你像个啥爷爷哟,简直就是一个赖皮。一个老顽童!’”。[4]在小说《丢失》中,年事已高的江长水毅然决定去寻找离家出走的孙女春燕,不正是弥补亲情缺失的举动吗?作家巧妙地将这种情感融入到自然景物之中“一只羽翼未丰的小鸟,‘噗’地从船棚上惊起,在码头上盘旋了两圈,就顺着对峙的悬崖渐飞渐远,消失在茫茫天际……”[5]可以说,抒写祖父(世人眼中的老父亲)的过程就是抒写家庭亲情重要性的突破点,或许这种方式更能唤起广大读者对亲情的审视和珍惜。因为父子的亲情已然缺位,祖孙的亲密无间是对现代生活背景下的亲情关系响响的一记耳光,一槌警钟!可以说,作家巧妙的表达方式正是在努力寻找畸形亲情关系回归正常的出口。
四、父亲形象审视对当前文学创作的启示
评论家谢军评价蒋兴强的小说《隔单》能“深接地气、直击现实病灶、讲述巴山渠水的‘中国故事’,有温度,有情怀,有现实意义,有精神重量。无论是宏观把握,还是深度介入,都践行了作家呼唤社会风气向好、人心向善的责任担当。”[6]之所以能达到这一震撼效果,除去作家巧妙地结构布局,精湛的语言文字功底,与其父亲形象的塑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给文学创作者和鉴赏者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紧扣时代脉搏,把握人物形象。俗话说,弱水三千,只取瓢饮。优秀的创作者总能塑造出自己最合心意的人物形象,这一形象通常又因仿佛就在身边而被读者所喜爱,艺术和思想上的共鸣效果使得形象成为永恒的经典。蒋兴强的父亲形象几近炉火纯青,大抵上是他笔下的父亲已然不是简单固定层面上的形象了,这个“父亲”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时代和社会内涵,更侧重于多重价值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和哲学意义,理当是作家极力塑造展现的经典形象,是作家对当前时代的理性审读和深刻反思。如,劳累一生的薛亮在病危的情形中,未曾得到五个子女应尽的责任,反而却因各自私利而将亲情之路阻断,唯有长子薛诚送终聊且慰藉。就此而言,蒋兴强无疑给了文学创作者和鉴赏者一扇光明之窗,即塑造人物形象必然要紧扣时代特点,细致观察社会现象,从而达到明其质,表其意的效果。断然不会迎合世俗或为一时的奖项而放弃对现实的重视和自己的坚守,而丧失了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的唯一可靠途径,让艺术升华缺乏现实依据,成为空中楼阁,昙花一现。
肩负理性担当,展示作家焦虑。当代著名作家阎连科说:“焦虑,是一个作家写作的种子。甚至,焦虑的起点,本就决定着一个作家气象的大小,决定着一部作品的格局和风格,决定着一部作品的方向和成败。”[7]浮躁的时代往往需要冷静而睿智的文学创作者,一个真正的作家必然是充满焦虑和不安的人,即便是外表展示出一种闲适和平静。作家也只有在反观自我的生存状态的同时把这种内心深处的东西展示出来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换言之,烦恼和焦虑成就了写作,找到焦虑和不安的出口才是一个作家真正的救赎。著名作家贾平凹回到老家,发现家乡人都进城务工造成了街面的冷清,关系的淡漠,在孤寂之中写下了影响较大的小说《秦腔》。蒋兴强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退休者,完全可以安享晚年,但他却不辞劳苦一如既往地坚持创作,无非是寻找自己内心的一种平静与自得,希冀传达一种对现实观照下的声音,尽到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为社会传达一种健康向上的思想,这也是优秀小说作品不可或缺的使命担当。
富有哲学思维,成就经典力作。如前所述,现代生活给世人创造了闲适的生活状态,文学作品也层出不穷,但大多数是自我炫耀式的闲情纪录,其生命力和影响力都是极为有限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多重现实意味和价值,涉及到生存现状、文化教育、人格取向、精神状态等方方面面,尤其是哲学观点和审美意识的参与。对于作家而言,现实的焦虑和不安虽然不会成为独到的思想和哲学,但会成为独有的情感和作品。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文学创作的使命更为艰巨,有学者认为,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文化领域的重要事件之一,空间转向对当代哲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等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8]以父亲形象为例,他不再是那个淳朴善良的农耕者,不再是那个蛮横霸道的无知者,而是在新时代生存环境里的人文坐标,折射出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片段,其形象、情感、精神具有极为深厚的内蕴。作家有了这种理念,才能真正达成审美与文化的建构,促成读者的精神启迪和价值重构,诚如蒋兴强在《丢失》中的留白:“春燕走了,顺丽走了,老人走了,他们一一消失在暖融融的风雪中国年里……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