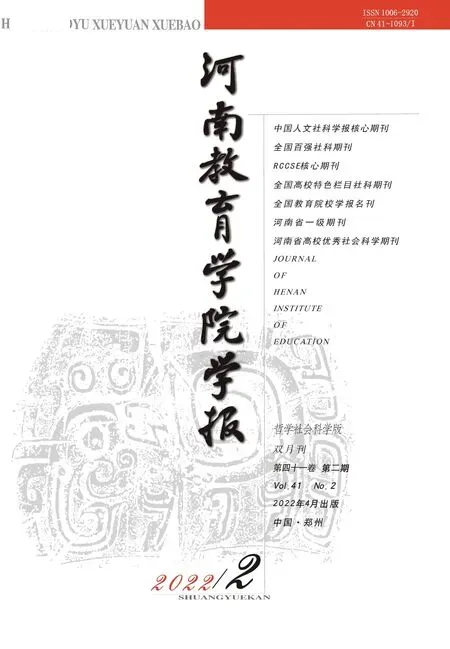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田园书写的常与变
——以废名、沈从文和师陀的小说为例
2022-03-17崔凯璇
崔凯璇
一、引语
20世纪20、30、40年代的田园书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曲优美乐章,一支清新而又宏阔的咏叹调。现代思想和文明打破了古老中国的旧梦,在那社会阶层、道德体系和家国命运正逐渐倾覆的大时代,最原初的乡土书写浓墨重彩于对黑暗和落后的控诉与谴责,如以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田园书写中对宁静田园风光的向往和淳朴人性的留恋,总是裹着批判的外衣——控诉和责难古老宗法对人性的压抑,现代文明对田园社会的摧残。自废名“以简朴的翠竹制作成一支牧笛,横吹出我国中部农村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1]450开始,田园生活成为现代作家的精神绿洲;沈从文精心构筑的“希腊小庙”成为引领人们探索通往田园神话的秘密幽径。在他们笔下,田园书写成为现代作家勾勒情绪、探索思想的“有意味的形式”,成为乱世之中安顿灵魂的一种方式。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田园书写也勾勒出“老中国儿女”以传统惯性在风云变化的时代大潮中苦苦挣扎的图景。
二、20世纪20年代静谧悠长的田园牧歌
1925年,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发表于《语丝》第14期,随后他陆续发表《桥》等篇目。1928年,《桃园》结集出版。在废名的笔下,黄梅故乡成为优美恬静、风俗淳朴,人们自重、自爱、自然适意、返璞归真的化外世界;人以及人的生活融入桃林修竹之中,宁静、谐和、波澜不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废名的田园书写不仅摹画乡村美景、淳厚风俗、人性之良善,更透露出体悟生命的独特方式——他“将乡村小人物不幸的同情,让位于对人间的‘真’与‘梦’的编织”[2]315,规避了乡村生活丑陋的一面,打造出一种“时光停驻”和“人间纯美”的梦想田园,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田园牧歌情调的文体风格。
以《桥》为例,小林少时天真的乡塾生活,在史家庄感受到的淳朴、善良的人性,谐和、愉悦的氛围,与琴子的两小无猜少年情意,小林长大后还乡微妙的感情世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田园小世界,构成悠长而特别的循环节奏。在废名笔下,史家庄成为一个自足的空间,这里封闭而悠长,好像同世界上其他地方断绝了联系;生活在这个空间中的人更像被赋予了魔法,永远宁静美好下去。空间的淡化模糊了时代、人和生活的变化,削弱了作品中人物的成长与生命延续,小林及其周围人的生活像是脱离了历史的车轮停驻在优美曼妙的时光里。《竹林的故事》《桃园》亦是如此。废名的田园书写淡化了时间、空间和历史的界限,营构出宁静和谐的意境,这里没有阶级、家族的区别,有的只是纯美、纯善的田园风景和乡土人性。这个被冠以爱和美的世界只会让人联想到慰藉、美丽、甜蜜、快乐、和平。在这个世界里哪怕是悲剧也充满淡淡的哀伤,甚至连死亡也蒙上了一层宽和圣洁的光亮。这种“冲淡为衣,悲哀其内”的田园牧歌包含着对乡间民情民性的观察,寄寓着现代知识分子对本真和谐的人性和田园风格的精神诉求,弥漫着现代知识分子对世相和生命所特有的忧郁情怀。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宁谧、优美的田园风光,淳朴、善良的山野人性,甜蜜、忧伤的故园情感,交织成融合了现实和幻想、浪漫化和理想化的安魂曲,撩拨着游子内心深处的优美、感伤和怀旧的情绪。这种亘古绵长的静默乡土,悠然伤怀的田园情绪,寄寓着作家理想的灵魂图景和生存模式,是田园牧歌小说的常态书写格调。
三、20世纪30年代田园牧歌中的感伤衰续
沈从文发表于1934年的《边城》,把田园牧歌情调推至巅峰。在这部作品中,沈从文围绕边城宁静自足的生活,醇厚的人情美、人性美,正直、朴素的地方民族性格和葱翠灵秀的山水之美,打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理想化世界。
沈从文延续了废名的田园书写格调,他的理想之地——“边城”也洋溢着爱和美的气息,散发着圣洁的光芒,折射出作家纯美至善的心灵世界。与废名不同,沈从文谨小慎微地保持着象牙塔的纯粹。在耽于内心所追逐的美、爱、善、真的同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理想庙宇”的脆弱和必将崩毁的命运。因此,沈从文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3]185在《边城》结尾,翠翠怀着酸软的心情守着渡口,那个人也许明天就回来,也许永远也不会回来;健康、美丽、纯真、生机盎然、自然朴素的翠翠最终要在平凡卑微的生活中被岁月和命运慢慢地剥蚀掉光华。在恬静的田园书写下,沈从文没有刻意回避现代文明下逐渐显现出的虚伪、世故、欺压、凌辱,甚至战争、屠杀。他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与隐忧,将沅水流域琐细平凡的人事、卑微的得失哀乐,放置于社会时代发展的巨大洪流之中。曾经的美好,理想之地的神性光芒都被卷裹在这极具摧毁性的势能之中,最终被小心翼翼地维持,抑或无可奈何地被吞噬、消亡。不管是少女、妓女或者水手,生命似异实同。
1943年,在《长河》题记中,沈从文写道:“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几乎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庸俗的人生观。”[4]78故乡年轻一代已然失去了世代积淀的品德和纯善的品性,而在趋时的享乐中变得日益浅薄;那湘西故土中被奉为神明的爱与性,亦不复圣洁和率真,而是衍变为物质交换与身体爱恋。《边城》中那个充满诗性、美感的湘西已经成为过去,悠然静默的田园风情终被堕落、畸形和扭曲的世态人情打破。从《边城》中爱与美的梦幻世界,到略带悲凉的《长河》,美的“幻灭”形成了反田园的情绪暗流。充满诗意美感的“人性边城”最终支离破碎,翠翠们的青葱岁月被剥蚀摧残,纯洁销蚀,美丽泯灭。反田园书写映照出现代工业文明给人性和田园牧歌带来的诸多冲击。沈从文以田园书写来描绘湘西,描绘他内心深处那难以言表的自由栖居、生命完整的梦想家园。当他有意无意地以感性的生命体悟和朴素的人性思索来质疑理性、文明、历史对人的压抑、戕害时,便在民族、传统和国家的高度以素朴的自然人性再塑民族血性,在书写层面形成了“田园书写”和“反田园书写”的巨大张力。
这种张力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沈从文的田园书写承载着“所向往的生活意义的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5]225。他用笔墨打造一个人人可以和谐生活,不管出身如何,阶层高下,和平相处的湘西世界;他用遗世独立的田园风光、恬静悠然的田园氛围来修复受伤的心灵;期冀这幻想的田园牧歌能抵挡外部世界的混乱,成为精神庇护所。因此,人与人之间淳朴善良的关系是他田园书写的精神内核,自然界与现实社会的爱与美是他的精神重心所在。第二,沈从文在进行田园书写时,敏锐地感知到自由、韧性却又无常的生命意识,敏感地捕捉到现代性的尖锐和焦灼。有关故乡、自然、生命本源、历史传统的认知与考量在互涉和衍生的思索中逐步衍变成反田园书写:田园梦想随着国家、民族意识的自觉、炽热而逐步清晰地演化成作家对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怀,对时代、历史、文化的尖锐批判和历时反思。第三,沈从文的田园书写在创作源头、主旨、期待、反思和沉潜等一系列环节中,对善良、爱等信念的渴求,与今昔对比的失落、断裂和缺失情感互为唇齿,相互关联,最终形成他田园书写的内在矛盾。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与封闭性和狭窄性,并注定灭亡的小世界相对立的,是一个庞大却抽象的世界”[6]317。沈从文努力把生命和灵魂与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湘西世界融为一体,然而又无法忽略外部世界的压迫和梦想坍塌的清醒与悲凉。田园书写中对自由和爱的向往和追求,伴随着反田园书写的忧愤和无奈。沈从文意欲构筑一个梦想的国度,可是又清醒地意识到美好之于消逝,个体之于命运,田园世界之于现实和文明进程都有着不可违拗的无力感。犹如二律背反的命题,挥之不去地萦绕在字里行间。
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田园书写中开始出现对现代文明的对抗,对田园生活的反思,对民族忧患的意识;优美静谧的常态田园书写,时光停驻的神往悠然,因对“美的消逝”的正视,在常与变的思索和发掘中,逐渐衍化成反田园的悲音。
四、40年代田园牧歌消逝的静寂
现代作家师陀于1936年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1937年出版《里门拾记》,1946年出版《果园城记》。师陀擅长以印象式的素描来刻画乡村的风景和人物。与废名和沈从文的田园书写不同,同样是怀着理想化的故乡想象,回到久别的故乡小城,师陀看到的却是衰败与破落。30年代田园书写中优美恬静的氛围至此消逝弥散,只留下一点泥土气息。《果园城记》更多的是描写北方农村的衰败之境。自然界的荒凉与人事的心酸紧密交织,乡镇的衰败和人生命运的无常相结合,对家乡的温暖回忆伴随着凄凉和哀伤情绪,在师陀笔下,现代文学中纯粹的悠扬牧歌变幻成中国箫笛的绵长悲音。现代作家理想中的诗意田园情调,在日益没落、走向衰亡的现实景象面前,衍化成反田园书写。
师陀说:“我不喜欢我的家乡,可是怀念着那广大的原野。”[7]127他把自然的美好和人事的丑陋并置。一方面,他沉醉于大野上的村落这种特定的家乡文学意象,于浓厚的怀旧情绪中爬梳凄凉、温暖又哀伤的回忆;另一方面,他又清醒于故土的沉滞、人情风物的鄙陋,以及故人没落的悲哀和无奈。这种矛盾而异质的情绪感受交叠并置在一起,成为贯穿师陀田园书写的情感主线;认同与厌弃相缠绕,缅怀与排斥相融合,使他的田园书写走出了乡思和眷恋的单一与纯粹,使那与田园意蕴相对抗、相矛盾的情绪暗流逐渐明朗,并汇聚成爱憎交织的复调情感。
师陀笔下,一方面是挥之不去的乡思,是难以压制的对故乡真挚浓郁的眷恋;另一方面是对故乡蒙昧、落后、封闭的嘲讽、批判,对时光流逝、社会发展的蔑视、嘲弄。师陀不去张扬故乡风情,而是着力于揭示乡里村落种种“生活样式”的病态和整个乡土中国“社会生态”的恶化:官绅对小城如铁桶般的钳制,对治下之人酷烈的刑罚;一个个美好善良的女性被戕害、蹂躏,乃至死亡;安分守己的平民逐渐地沦落、湮没;曾经的激进青年被扼杀、被逼迫、被放逐,终归于平庸、麻木和死寂;同一时空不同屋檐下,陷害、谋杀、包藏祸心、背离、丑恶与绝望,比比皆是。作者以历史理性审视那片冻土,书写出一种令人疼痛的真实:外面的世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镇虽有些许躁动,最终还是回复为绵长的静寂。就像那永远坐在街口闲聊的果园城里的妇女们,一个夏天接着一个夏天,一年接着一年,一代接着一代,永远没有聊完过。这个封闭、保守、停滞、落后的小城,如一块保存着昨天的活化石,黯淡无光。时间仿佛停止,历史仿佛在这里懒散地打了个盹。在这里生活的人们都有过一个幻境般的过去、悲惨的现在和哀愁莫名的将来。果园城不仅是故乡历史和现实的还原,而且是中原现状的缩影,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境况的投射。
从废名,到沈从文,到师陀,“故乡情感”逐渐“变质”。理想之国最终衍化成丑陋的,神圣美好和圣洁的光芒被世俗人心的乏力、丑陋和阴暗所销蚀,远大抱负和梦想最终陷于无所行动的失败。废名和沈从文田园书写的牧歌情调在师陀反田园书写的底色下,变为荒谬而充满悖论的人生哀曲。师陀将现代知识分子在荒谬的历史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幻化成反田园的笔触,将曾经的梦境似的纯朴快乐的田园生活植入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看似宁静优美的田园书写,骨子里却是对田园生活的对抗和拆解,“田园”和“反田园”的叙事缠绕、纠结在一起。因此,解志熙在《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中说,师陀笔下的乡里村落乃是一个有田园而无诗意、有自然而没有牧歌的所在。[8]231
现代作家关于故乡的美好的记忆,如画的风景和人物的淳朴品行,是自我生命经历的印记和生命体验的片断,不仅无法抹去反而会随着现实秩序和理性思考变得格外强烈,这是废名、沈从文、师陀等现代作家诉诸书写的最基本因子和生命躁动。在师陀笔下,鲜活的生命由萌生,到盛开,到凋敝、麻木、死寂,周而复始,“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线轴弯曲后复归到过去,形成了时光停滞、历史重演的默剧。他把故乡小城置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之中,历史的阴影浓重地笼罩在中原大地之上,人们的生活和命运就在这循环和阴影中挣扎、没落,直至衰亡。师陀将现代历史的理性审视和思考掺杂在自我的现实感和生命体悟中,将文明与愚昧的对抗上升为对时代与历史文化现状的不懈探索;将对小城历史的分析,发展为对社会历史、中国文化、民族发展等诸多问题的反思和尖锐批判。个体生命残片对历史和民族家国情感的融合,使感觉、情绪层面的田园书写逐步衍生为理性、审视的反田园书写,使20世纪40年代的乡土文学呈现出异样的抒情风格。
五、结语
田园是现代作家精神的栖息之地。现代作家从浸满血与泪的乡土走出,反顾那片生养他的土地,充满着无限的眷恋和哀思,因此有20、30年代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书写。当现代知识分子以悲悯哀怜、理性辨析的复杂情感重新审视故乡时,就不再是单纯的迷恋和沉溺,而是以反田园书写的笔触来描绘故乡的衰败和落后。在此过程中,现代文学实现了由田园书写到反田园书写的蜕变。